2023年8月,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新作《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在上海书展高调亮相,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贝马斯解读哈贝马斯”的著作,主要译者是大陆哈贝马斯专家,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光明日报》、《澎湃新闻》等一众官媒都报道了这次新作出版,相关的研讨会也在各大高校巡回进行。在大陆学界和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交流日渐减少的今天,哈贝马斯似乎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可以安全地“崇洋媚外”的欧美学者之一。
然而,四平八稳的官方背书和同期中国社会评论、舆论使用哈贝马斯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2022年下半年以来,在小区、社区、街道中反抗不合理防疫措施的行动、乃至于最后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中,参与者经常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口语中经常翻译为公共空间)、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乃至于延伸出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系列语言支持自己的主张。
分析和报道他们的评论者,尤其是关心中国政治的英语学术界,也纷纷庆祝中国终于有了公共领域和公民政治。可是,这其实已经是第成百上千次有人在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中寻找“新生的公共领域”了。在寄望于中国中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转型的人的下意识动作中,哈贝马斯已经成为了描述希望、潜力、美好愿景的语法,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用这种语法讲出完整的故事。
哈贝马斯,这位经常被认为早就去世了的史前哲学家(现年94岁),万神殿中的“欧洲之心”或“德国之心”,欧洲一体化思想最后的守墓人,在他的故土正经历尴尬的境遇。用2021年美国学者布莱克·史密斯(Blake Smith)在《为什么尤尔根·哈贝马斯消失了》一文中的话说:哈贝马斯在学界依然地位显赫,在学界外却日益边缘化。以“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分子通过塑造公共舆论来影响政治)概念而著称的学者,有变成自己理想的最令人信服的反例的危险。他的没落还代表着,他的职业所体现的那种政治可能要枯竭了。

在中国,他的境遇也很尴尬,却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从1970年代末起,中文世界接受哈贝马斯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后急切而犹豫、天真而狡猾、兜兜转转、亦步亦趋、进退两难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缩影。哈贝马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狐狸式学者”,著作极多、领域不定且言辞折衷,不同观点的人往往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找到支撑,但在中文世界,哈贝马斯最受瞩目的还是1962年就已经以德文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规范:公共领域。他认为,我们的世界由日常的生活世界和权与钱主宰的系统组成。公共领域在两者之外独立运行,避免系统入侵日常生活,造成压迫和不平等。所谓公共领域,是人们不带偏见、不存私心说话的地方;发言不预设立场,完全看协商的结果;理论上人人都可参加,但也有准入门槛:遵守共同的协商规则。协商是整个理论的灵魂,也是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和现实中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区别:不是一人一票谁声音大听谁的,而是不辜负每个人的理性尊严、尽可能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哈贝马斯认为,协商对于国家有利无害,现代国家应该保护公共领域、允许它的存在、接受它的监督。
公共领域理论有一个公认的模糊之处:公共领域到底是历史上存在的、现实中可以存在的,还是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哈贝马斯本人对此语焉不详,他一边提出,历史上的英国资产阶级咖啡馆曾经扮演过类似角色,另一边又说公共领域只是一种人们必须追求的理想境界。2000年代,这种诱人又让人迷惑的模糊可能性曾在中国让寻找/建立公共空间几乎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任务。而2023年过半的今天,曾被寄予厚望的白纸运动没有留下显著成果,人们渴望将疫情的阴霾抛在脑后;曾经在街头高喊按照法律最高可判处死刑的口号的少年,现在又回到了担心物价上涨、就业困难、喜欢的爱豆翻车、日本核污染、美国间谍的日常中。在这个似乎“无事发生”的当口,我们讨论总是给人希望又让人失望的哈贝马斯、仿佛就在明天又似乎远在天边的公共领域,不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而是希望反思:构建理论何其容易、分析实践则难上加难。除了在塞满宏大解放理论的哲学殿堂中晕头转向,我们是否还有其他共同思考解放与变革的方式?
从朝到野,从左到右,谁拥有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作为阿多诺的助手,身份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正统,但又深受康德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影响,非常适合作为安全的“他山之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讨论人性、尊严、民主,而不必冒险偏离马克思主义阵营。
哈贝马斯在中国一共被引进过两次,都是知识界有所动作的大时代。
第一次引进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第一批介绍哈贝马斯的短文大都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理论动态》一刊是1977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立的,创刊目标就是纠正极左思想和“两个凡是”,为之后的改革做铺垫——1978年5月10日,打响改革开放第一枪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首先发表在这里,之后再转载到《光明日报》上。在这个当口引进哈贝马斯,改革派的目标非常明确:哈贝马斯作为阿多诺的助手,身份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正统,但又深受康德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影响,非常适合作为安全的“他山之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讨论人性、尊严、民主,而不必冒险偏离马克思主义阵营。
同时引进的还有其他“西马”成员——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或背叛苏联的东欧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阿多诺、卢卡奇等。他们的观点和中国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思想相冲突,之前一直是禁区,而此时也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求改革出路的理论资源。这波引进非常“拿来主义”,西马学者到底怎么想,长期和欧美文化切断关系的引介者(往往还是因为有文化官僚的身份才能接触到只言片语)无法、也没必要系统理解。
任剑涛曾回忆,当时看西马的译作,通篇都在说“邮政自由主义”,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很多年后才发现原来是post-liberalism(后自由主义)的误译。引介者还创造性地使用了西马的“异化”说法,提出文革和四人帮异化了革命、异化了人;现在应该回归人性、回归革命正路——这当然和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所说的异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对于改革的目标并不重要。这波为改革张目的西马热在1983年达到高潮,借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由头,曾经的文艺沙皇周扬、《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王元化等名宿共同起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反响强烈,导致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八十年代剩余的时间里,文化讨论逐渐从被噤声的文化官僚,扩散到了对于能接触到大量印刷品和文化资源兴奋不已的城市市民中。在万人空巷看《河殇》的氛围中,“中国文化”还要不要保留都成了热议话题,马克思主义框架在民间已被抛在脑后,作为理论护身符的哈贝马斯就更没必要存在了。
六·四给这一切画上了休止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或因恐惧、或因心灰意冷,纷纷从政治讨论中撤离。哈贝马斯和其他著作较多、用语晦涩的德法学者被高校瓜分。学者们用尽可能专业的学术语言对他们进行尽可能去政治化的述评来彰显象牙塔存在的意义,哈贝马斯暂时淡出了大众视野。

徐友渔、许纪霖、邓正来、李慎之、秦晖、俞可平……当时热情介绍哈贝马斯的人,构成了初代“公知”的很大一部分,通过大众传媒让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等概念进入寻常百姓家,也奠定了公知这个词汇的自由主义/亲改革/亲欧美色彩。
对哈贝马斯第二次引进发生在世纪之交,从1997年左右开始,在2001年哈贝马斯本人访华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哈贝马斯已出版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译成中文,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其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世纪之交,中国一边经历加速的资本主义市场化、一边体会着市场动荡的阵痛。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准知识分子中间有两种矛盾的思想:一方面,被从市场涌入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吸引(也即今日所说的崇洋媚外),尤其是受到美国后冷战的主流社会学影响,认为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和中产阶级扩大可以自然地导致政治民主化。很多人被这种前景鼓舞,无论是相信市场调节、产权神圣的;主张人权至上、言论自由的;甚至一部分追求平等进步的左翼,都乐于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由派”。
比起九十年代初的噤若寒蝉,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无疑经历了又一次政治化,但却不是八十年代如飞蛾扑火般狂热的政治化——矛盾思想的另一方面是有恒产者的担忧:发展是真,欺骗、犯罪、贫富分化、破产的风险、失业的威胁也是真。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渴望规则和秩序能带来安全感。在这个背景下,社科院曹卫东等翻译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1999年出版,可以说是正中“时代需要”。
这本书不仅从英国咖啡馆说起,用欧洲历史在资本主义、有产阶级和民主社会之间建立了目的论的关系,还提出了一种更自由、更公平、更安全,又是基于温和的沟通交流的未来愿景,让曾主张将一切交给市场,从未想过全面市场化的残酷本质的后悔者看到慰藉和希望;更别说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性中立、互相接纳、遵守相同发言规则的合格沟通者,如果能够存在,也只能出自受了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于这点,批评家斯坦利·费什曾嘲笑说,哈贝马斯这是要把高端学术晚宴上的礼仪规范当作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流准则)。此外,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公共领域中法律的作用,既然沟通本身不设限、无前提,规范的保障就更为重要。他最常使用的例子之一是“十二怒汉”式的陪审团,商谈的素养和法律的规范互相保驾护航,正好切中了丛林般的新兴市场中中产阶级对法律保障的渴求。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迎合国内这种诉求,也向国外投资者传递信号:寻求“接轨”的中国,不再是朝令夕改、君威难测的地方。
上述问题:资本主义、市场、自由、民主、言论、法律……都是主要在自由主义框架内讨论的问题。这第二次引介中,哈贝马斯作为公认的左翼学者,却主要受到了自由派的热爱。徐友渔、许纪霖、邓正来、李慎之、秦晖、俞可平……当时热情介绍哈贝马斯的人,构成了初代“公知”的很大一部分,通过大众传媒让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等概念进入寻常百姓家,也奠定了公知这个词汇的自由主义/亲改革/亲欧美色彩。而哈贝马斯可以说是一种“元公知”:他对哲学的兴趣在于其解释现实的能力,比起准确抵达真理,他认为发言更重要。从青少年时经历的纳粹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贝马斯几乎评论过全部欧洲重大事件。
这些评论是及时的也是临时的,往往使用很大众化的语言,不预设立场、不回避争议性和开放性。这种风格也影响了中国“公知”的发言方式,后者常被其他学者指责为哗众取宠,不专业、不深入。部分因为和自由派的这层关系,哈贝马斯在2001年访华时,也被卷入了著名的新左自由派论争中,形成了一桩很有意味的公案。以汪晖、王绍光等人为代表,当时的新左派把社会普遍感受到的不公和风险首先归结为资本主义本质使然,或者要求继续革命,寻找“另类可能”;或者呼吁清理、保留社会主义遗产;或者干脆要求增强国家权力,铁腕控制资本。新左派也认同哈贝马斯的“金钱和权力的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侵蚀了公共空间”的观点,但对他“大家商量着来”的药方嗤之以鼻。而哈贝马斯本人受社科院邀请访华时,又当着一众自由主义者的面,提问:“我读了汪晖、黄平(均为新左派,原文较长,此处为大意)的作品译文,我感觉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服务、为文革辩护的倾向,是不是?如果这个感觉对,我感觉他们不应该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评改革开放,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为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这些话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引发了新左、自由两派长达一年多、诉诸于个人的扯皮。更火上浇油的是哈贝马斯本人对当时国际政治的立场。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哈贝马斯尽管意识到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自身政权利益,但出于对米洛舍维奇残暴统治的反对而支持出兵科索沃。而这场战争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点燃起空前高涨的爱国反美情绪。哈贝马斯的言论传到中国,很多自由派也觉得民族情感受到极大伤害。部分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哈贝马斯在社科院和清北等各大高校进行了七次演讲,其中半数是以人权问题为主题的。他提问中国观众:人权概念没有可能跨越文化障碍和国家博弈吗?中国用美国的实际利益质疑其人权申说,这是否足以否定人权本身作为价值和规范的意义?而观众则回以“人权不能高于主权”“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陷阱”云云。哈贝马斯的演讲,参与人数往往极多,从演讲厅一直挤到街面上,好几次警察不得不出动清场,这样一来争议传播得极其迅速。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不再尖锐,哈贝马斯的权利申说却留下了印记。人们继续使用哈贝马斯的整体框架,只不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法则中重新解释了“权利”。

从小区到互联网,公共领域何处寻?
理论上说,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中,参与者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利益中立,说对的话而不是有利于自己的话,但2000年代的中国观察者感到:似乎私人利益更能驱动公共行为,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检索中英文期刊,不难发现2000年代关于中国公共领域、公民政治的讨论大多和“权利/权益”(right)问题挂钩。这个权利包括健康、安全等基本的社会权利,还包括更“重要”的经济权利——产权。围绕产权又产生了消费者、业主、维权、自治等关键词,这些带有明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色彩的符号,描述了这一时期公民政治行动的主体身份、诉求和方式。理论上说,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中,参与者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利益中立,说对的话而不是有利于自己的话,但2000年代的观察者感到:似乎私人利益更能驱动公共行为,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秩序的商议和有组织的行动总是在最具体、私人的领域中展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封闭式商业小区。
小区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居住形式,也是孵化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温床。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封闭式商品房小区逐渐取代单位大院和家属楼成为了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组织起来的方式。小区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和销售,设置门禁、保安,由物业提供服务。小区受到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的管理,居委会表面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2000年前后逐渐被收为准官方组织,受上级基层政府组织:街道直接管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住在小区中,拥有房屋的产权、接受物业的服务,又被街道办遥控的居委会松散地管辖着。高昂的价格换来房屋所有权以及封闭空间中(理论上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让房主深刻体会到产权的含义。小区作为一个明确的物理空间,既是私人财产,又是业主共享,这种双重属性鼓励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已去政治化的中产阶级“为私入公”,参与小区事物。而这种介入也有现实必要:物业公司对业主负责,但往往由房地产公司挑选。在当时时髦的消费者话语中:物业是服务的提供方,如果服务意识不到位、服务质量不好,购买服务的人就应该投诉。
起初,业主依靠居委会和物业沟通,但居委会作为表面上的自治组织,没有实权、无法完成这个任务。1991年,第一个业主委员会成立于深圳毗邻罗湖口岸的一个高档小区——小区的地点和属性已经能够说明业主委员会的经营色彩。
成立业主委员会最早是因为业主和物业公司在电费收取方式上存在纠纷,以及小区的泳池要被改成草坪。协商未果后,房地产公司建立成立业主委员会提高协商效率。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选举、章程、决议、公约等要素一应俱全,万科老总王石还参加了成立仪式。此后,业主委员会不断向内地中高端小区扩散,到2000年代中期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业主为了生活舒适和便利,参与管理的意愿较高,学习复杂的选举、发言规则也有动力。很多人就是在业主委员会体验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协商和决策。
民主将从城市中产阶级中诞生。市民体会到掌握自身利益的安心感,学者为协商民主前景欢欣鼓舞,甚至政府也不反对业委会的存在——既然居委会无法穿透基层,业委会与之双向奔赴也不失为良策。
国内外很多评论者如唐贝贝、付强、本杰明·里德(Benjamin L. Read)邓利杰(Luigi Tomba)等都倾向于认为,业主委员会正是自发产生的公共空间或者至少是其雏形。其中的中产阶级利益不仅无损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甚至进一步验证了哈贝马斯的观点:民主将从城市中产阶级中诞生。市民体会到掌握自身利益的安心感,学者为协商民主前景欢欣鼓舞,甚至政府也不反对业委会的存在——既然居委会无法穿透基层,业委会与之双向奔赴也不失为良策。当局将业委会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基层自治。何为“自治”可以有很多理解,既可以是自己管自己而不让别人管,也可以是自己管好自己而不劳别人费心。保护产权需要约束的不只是物业还有共享同一空间的其他居民,自治中的互治内涵可以说和国家的管理目标是一致的。
小区之外,2000年代的维权也往往发生在一些类似的领域,如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和环保,其共同特点就是围绕中产阶级作为自然人和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环保问题往往牵涉到国企乃至政府,环保维权不免发展成政治抗议。以厦门2007年反PX(对二甲苯)化工厂抗议为例,该项目受发改委、厦门市政府鼎力支持,市民维权的出发点只是担心污染和爆炸,但很快发展成数百政协委员联署抗议、上万人手绑黄丝带上街“散步”。虽然据参与者说一旦有人喊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就会立刻被他人阻止,但事实上厦门政府的确受到了冲击,最后工厂也不得不迁址。类似的情况还有东莞(2010)、大连(2011)、天津(2012)、上海(2015)等等的环保运动。这些运动的前期组织、动员和后续谈判被很多论者视为公共协商的宝贵案例、和平民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这些评价不无道理,但这种行动始终局限在环保领域中,没有像乐观者期待的那样扩散。
最后不得不提,物理空间之外,哈贝马斯第二次引进的一个不言自明的重要背景就是互联网的兴起。2003年,学者杨国斌乐观宣称: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社会正在共同进化、相互促进,还有很多人把当时流行的BBS描述为理想的公共领域:人们互相匿名、遵守版规、在平等、友好的氛围中进行思想交流。BBS时代落幕后,虽然人们感觉到互联网的秩序日渐混乱、“戾气”逐渐增多,但对于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还是寄予厚望。毕竟这是用户基数更大、门槛更低、不那么精英主义的平台。
2010年,《南方周末》喊出口号“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一度(至少在2014年“公知”遭第一次清洗之前)成为共识。学术领域,论证微博、微信、以及后来的几乎一切社交平台的公共领域属性的文章曾出不穷,毕竟只要说话的人足够多,总会有令人振奋的讨论发生。哈佛大学雷雅雯2018年出版的《充满争议的公共领域》(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她乐观地认为:国家“依法治国”的纲领培养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国有媒体的市场化带来了新闻自由,公民的论辩素质在这两者的影响下提高,并最终在互联网上围绕法律和权力话语形成一个典型的哈贝马斯式公共空间。
按图索骥,不如让理论从实践中生长
这么多年过去,描述我们如何被压迫的理论日新月异,思考我们如何走出压迫的理论却未更新,哈贝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从哈贝马斯访华点燃大范围“公共领域”热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不难发现这个概念正经历实践和理论领域的双重困难:现实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并没有在讨论中层层推进这无需多言,理论层面,人们也是推磨般一次次在新事物中寻找希望然后失望,或者给公共领域增加无穷多的形容词,比如围绕利益的、特定话题上的、未受训练的、不成熟的……甚至还有人提出专制公共领域(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
这些事物看似有公、有域,但距哈贝马斯所说的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公共领域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盲目而不加甄别的乐观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惰性:既不愿意认真观察真实的实践,也不愿意长远地推动实践,更不愿意另辟蹊径进行理论探索。不止是普通人不愿意,学者和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这么多年过去,描述我们如何被压迫的理论日新月异,思考我们如何走出压迫的理论却未更新,哈贝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其实很容易发现,有问题的不仅是无法积累的实践,还有被套在实践上的公共领域框架自身。哈贝马斯一生致力于弥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否定一切、批判一切的理论洁癖问题,希望让自己的理论对现实更有建设性,可“公共领域”本身,也是空中楼阁。诚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中产阶级们被财产安全、食品健康、呼吸清洁空气的动机驱动去参加公共讨论,使用哈贝马斯式的语言而拒绝跳出私利谈政治。他们的“权利”观是对启蒙主义“公民权”的矮化、窄化和私有化。得出自私的中产阶级、以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为诱饵的专制国家不配使用从欧陆民主传统中生发的公共领域理论也再容易不过。然而在欧洲内部,公共领域所视为基础的私(生活世界)、公(公共领域)、国(系统)之分难道就成立吗?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其实是在历史上欧洲人的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区分的公和私——私是私人的家庭空间,公则是古希腊的广场·、贵族的沙龙和议事厅,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咖啡馆。然而,做为场合的公私和作为立场的公私并不能混为一谈。哈贝马斯既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承认资产阶级的兴起催生了公共空间,就也无法忽视:西方现代社会,包括其组织、文化和人都是以定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尽管他认为理论上/理想状况中/作为规范,人们应该在公共领域摒除私心,谈论"普遍利益问题",但现代社会最普遍的利益问题恰恰就是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哈贝马斯引为范本的16世纪英国咖啡馆中,资产阶级也是根据利益所在划分不同派别,和如今维权的业主、进行邻避抗议的市民没有本质区别。
哈贝马斯预设的公知仍旧是启蒙者身份,而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公知,沟通的条件才成熟。这个理想实在过于高远。
比公私关系更棘手的还有公国关系。常有人说,公共领域理论只适用于国家和社会分割较清的欧洲。他设想没有相关利益的知识分子、不仅不隶属于国家,还监督国家、反对国家的公共领域;而中国只有隶属于事业单位的高校教师,唐宋以来,公家就已经等同于国(皇)家。但其实比如在英语中,人们也会用“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公共财产”(public property)、“公共设施”(public infrastructure)等来描述被国家所有、所管的事物。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还发现,哈贝马斯其实也大量使用“公共权力”来指代政府,他对公的定义多少巧妙地混淆了不同词义,但现实却难以混淆:什么样的公共权力,能够亲手培养和保护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公共领域,然后接受它的监督?
最大的问题甚至还不是这些,和目前困境最相关的是:既然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被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限制,那么规则是何人设置的?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理论中,答案似乎是人的本性,只不过不是反求诸己、像康德所说一样从天性中迸发出的本性,而是从主体间性中达成的沟通本性——也就是说,沟通的前提是沟通出来的,问题就是答案。而现实中,正如史密斯和费什批评的一样,哈贝马斯预设的公知仍旧是启蒙者身份,而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公知,沟通的条件才成熟。这个理想实在过于高远,以至于我们用它触碰现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要么现实永远达不到这个理论高度;要么忽略一系列的先决条件,直接把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等同于谈话,并指望人们可以在微博上聊出个新世界。
史密斯在《为什么尤尔根·哈贝马斯消失了?》中说:“哈贝马斯日益失去与现实的相关性这件事情表明,欧洲自由主义也错误地,投身于一个类似的,为其预定目标寻找志愿者的计划了”。这句一笔带过的点评似乎揭露了问题的本质:先发明一种理想的状态,然后为了这种状态去发明优秀的能动主体,然后再为了这个主体去发明ta周围的世界。“公共领域”的理想虽然美好,但其中的协商者不像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人,其身处的国、公、私割裂的社会也并不存在。一种解放理论没有解释现实的能力,或许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希望指导现实却不从现实条件出发。社会、尤其是社会变革不是根据蓝图绘制的。与其长年累月地拉起理论大旗扯虎皮,或者用理论按图索骥,不如将精力投入到实践中,让新的理论从实践中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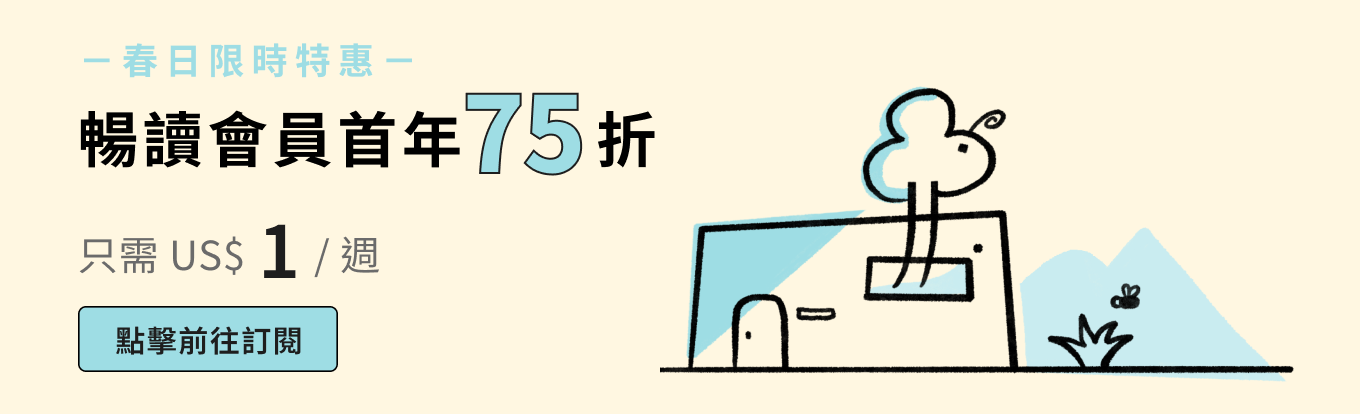



Haberemas 的很多理论在中国不能生搬硬套,比如Haberemas 就没有阐述过“广泛非互信环境下以血缘为纽带产生的小范围互惠”这种在东亚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和广义范围上的“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区别。小区避邻运动我更愿意解释成某种原子化社会成员因为共同利益损害而产生的短期协作,和公私领域相关的概念仍然存在差距
当然开卷有益,只有看过再做对比,才能体会欧洲社会演进和东亚这边的区别
也不是不好看,就是长难句好多,读起来会有点费劲,这条评论也不是很认真,说实话,有点迷失在一堆非常专业的词汇中,对我这种无知读者门槛不低。
其实也不太明白中心思想,记住了建构理论容易,推动实践困难的对于现实的描述,就是说比做易。另一点是关于很被推崇高歌的民主与逐私利的显得无趣甚至猥琐的出发点的对比。民主,听起来其实也很宏大叙事,不过说不定,就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琐碎日常中。
好文
我的一位好友,從清大人社院畢業後自稱哈伯瑪斯溝通理論的信徒,立志投身第一線的政治工作實務。十年後他退出政壇,現在連政治新聞都沒太大興趣討論了。
Haberemas 的 public sphere 理論從來都只是社會學上的 ideal type, 不完全反映歷史和現實,ideal type 是用來評估和批判現實,至於是否能通過批判來導正以至改變現實,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文中“借着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由头”应该写错了,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此处应为吉日。
這篇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