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忽然一夏,全球仍在疫期。医学惊悚小说《十月终结战》出版于去年4月疫情正盛时,如今也将有中译本。小说作者是普立兹奖得主作家劳伦斯‧莱特(Lawrence Wright),故事讲述了新型流感病毒如何肆虐全球,对病毒从哪里来、疫情现场、疫苗开发的难题、政治角力如何令人瞠目都有深入描述。恐慌与分裂如何给人类带来更多伤害?虚构与现实可相映照?我们在此节录部分内容先行刊出。
第一部 恐沟里
1. 日内瓦
日内瓦,一个大会议厅内,各国公卫官员齐聚一堂。下午,最后一场集会,主题是紧急感染疾病。出席者有些不耐烦,毕竟开了一天会,又得担心赶飞机的事。罗马发生的恐怖攻击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印尼一个难民营发生了不寻常的死亡事件,死者都是青少年。”倒数第二位讲者正在台上说。他的名字是汉斯什么的。来自荷兰。个儿很高,傲慢,一看即知每天膏粱厚味。他脖子上的灰金头发没有修剪过,挤出了领子,肩上的棉绒在简报投影机的光束下闪烁。
投影幕上是一张印尼地图。“西爪哇,恐沟里第二难民营,在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出了四十七张死亡证明书。”汉斯以镭射笔指出地点,接著几张投影片展示了一贫如洗的难民,他们生活在脏得吓人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根的人,几百万人塞入了匆匆搭建起来的难民营,四周以围篱封锁,当他们犯人似的;饮食不充分,医疗设施更稀缺。难怪大疫会从那种地方爆发,泛滥四方。霍乱、白喉、登革出血热——热带总是会酝酿出什么来。
“高烧,出血,传染快速,致死率极高。但是令这一批死者引起注意的是,”汉斯说,接著放出了一张图表,“死者年龄的中位数。通常感染病病人的世代分布是随机的,但是恐沟里这个例子,人口中最强健的年龄层却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大会堂中的公卫官员都在认真研究那张异乎寻常的图表。大多数致命疾病杀害的是孩童与老人,也就是U型分布,但是这个印尼的案例却大致像W型,死亡年龄平均二十九岁。“根据疫情刚爆发时获得的粗略报告,我们估计致死率是百分之七十。”汉斯说。
正当大伙儿因苦思而陷入沉默的当儿,“幼童或新生儿⋯⋯?”马莉亚.沙凤纳插嘴问道,她是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主任。
“大部分都确诊。”汉斯回答。
“会不会是因为性接触?”一位日本医师问道。
“不大可能。”汉斯说。他正在自得其乐。现在他的脸逐渐移进投影,在下一张投影片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接下来几周,死亡病例的特征维持不变,但是全体病例数大幅下降。”
“也就是说,那是一次性事件,”那位日本女医师结论道。
“留下四十七具尸体?”汉斯说。“太夸张了吧!”
日本医师脸红了,一面咯咯地笑,一面以手掩口。
“好吧,汉斯, 你逗弄够了吧。”马莉亚不耐烦地说。
汉斯环视全场,得意洋洋。“志贺菌。”他说,台下一片不敢置信的呻吟。“要不是颠倒的死亡年龄分布,你们也会想得到。我们也被它困住了。志贺菌是贫穷国家常见的病菌,牠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不计其数。我们询问雅加达的公卫机构,他们的结论是:在缺乏食物的环境中,只有年轻人身体强健得足以抢到有限的食物资源。在恐沟里,身体强健要了他们的命。我们的团队推测,病菌的来源是生牛乳。我们发表这个案例,是想请大家引以为鉴,人口刻板印象会让人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
本书献给为公共卫生奉献了生命的男男女女,表扬他们的勇气与创意——作者
十月终结战
作者:劳伦斯‧莱特(Lawrence Wright)
译者:王道还
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日期:2020年6月

汉斯在敷衍的掌声中走下讲台,同时马莉亚唱名最后一位报告人上台。他刚开口说:“威斯康星州曲状杆菌——,”突然有人打断了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一种严重的出血热,在一个礼拜内杀死了四十七个人,然后就消失无踪了?”
会堂里两百来人都把头转向那宏亮的男中音来源。光听声音,你会以为亨利.帕森斯身材高大。错了。他又矮又瘦,因为小时候患了佝偻症,身子不够挺,整个人有些畸形。因此他的长相以及教授口吻,让人产生不匹配的古怪感觉。但是亨利的丰神并没有受体态的影响,展现的是自信。在行内他是个传奇,知情的人谈到他,敬畏、不失顽皮,背后管他叫Herr Doktor(德语:医师大人;意思是主任医师),或“小鞭”。他会修理实习生,令他们泪流满面——要是他们没有正确地制作标本,或是没有发现一个事实上只有他才认为有意义的症状。但是,二〇一四年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率领一个国际团队到当地调查的,是亨利.帕森斯。他追出了第一位因感染伊波拉而就医的病人--所为的指示病例--是几内亚一个十八个月大的男孩。他是由果蝠传染的。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的更多。对抗新兴疾病的战争绝不会有终战之日;在这一战役中,亨利.帕森斯可不是个小人物。他是巨人。
叫汉斯的家伙瞇著眼搜寻,找到较高席位上的亨利,那里比较昏暗。“也不是那么不寻常,帕森斯医师,如果你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去的话。”
“你的报告提到‘传染’。”
汉斯笑了,很高兴能继续逗引大家。“印尼公卫机构一开始怀疑病原是病毒。”
“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亨利问道。
马莉亚已经感兴趣了。“你认为是伊波拉?”
“假如是伊波拉,我们就会观察到疫情向都市中心蔓延。”亨利说:“但是没有。想让感染病消失,只要根除污染源就可以了。”
“你亲自去过那个难民营吗?”亨利问道:“例如采集标本?”
“印尼政府一直十分合作,”汉斯不屑地说:“现在无国界医师有一个小组已抵达当地,我们很快就会接到报告,证实我们的结论。别指望意外。”
汉斯等了一会儿,但是亨利坐下了,用一根手指轻点嘴唇,若有所思。下一位报告人恢复报告。“密尔瓦基一家屠宰厂,”他说,几位很在意时间的听众迅速低下头朝出口走去。机场必然提高了安检层级。

“我讨厌你那么做,”马莉亚说。他们刚走入她的办公室——明亮、又有格调,可以看见白朗峰的美景。一群白鹳正在日内瓦湖旁盘旋,准备落地。牠们从尼罗河谷归来,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日内瓦湖是返乡繁衍下一代的第一个休息站。
“做什么?”
马莉亚身子后倾,以一根手指轻拍嘴唇,模仿亨利呢。
“那是我的习惯动作?”亨利问道,把手杖支在她的桌旁。
“只要看见你那么做,我就知道有事要我担心了。哪一点让你怀疑汉斯的研究的?”
“急性出血热。非常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怪异的死亡分布,完全不符合志贺菌感染。而且它为什么会突然——”
“消失了?我不知道,亨利,你告诉我。又是印尼?”马莉亚说。
“他们隐匿过疫情。”
“这次不像是上次脑膜炎疫情的重演。”
“当然不是。”亨利管不住自己,再度不由自主地轻拍嘴唇。
马莉亚等著。“我不应告诉妳做什么,”最后亨利说。“也许汉斯是对的。”
“但是⋯⋯?”
“致死率。太惊人了。万一他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马莉亚走向窗口。云气四合,遮蔽了壮观的山峰。她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亨利打断了她的思绪。“我得走了。”
“那正是我的想法。”
“我是说回家。”
马莉亚点点头,表示她听到了,也明白,但是她美丽的义大利眼睛透露了的忧虑表情,传达的却是不同的信息。“给我两天。我知道我在为难你。我应该派一个小组去的,但是我找不到信得过的人。汉斯说无国界医师在那里,因此他们可以协助你。只要采取检体就好。你回亚特兰大的途中,出入一趟印尼就成了。”
“马莉亚⋯⋯”
“求你了,亨利。”
他们是老朋友了,亨利好像看见了那位年轻的流行病学家,正在海地研究非洲猪瘟疫情,满面忧容。老朋友的记忆中才会不时冒出那种瞬间。那时马莉亚所属的团队主张的防疫策略是:杀光原住民的猪,根绝这种疾病。海地几乎每一家户都养猪;猪不但是主要的食物来源,还扮演通货的角色,猪圈就是农民的银行。在一年之内,由于美国政府与独裁总统“娃娃医生”杜华利的支持,海地特有猪种灭绝了,这是巨大的成功,几乎史无前例。根绝行动终止了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但是海地的农民本来就很穷,根绝之后更穷了——闹饥荒。美国提供的替换猪种,大部分都被腐败的菁英阶层据为己有,可是那些猪太娇嫩了,无法适应当地环境,饲养成本又太高。由于资源稀少,海地民众转而生产木炭,不久森林就砍伐殆尽。海地从未恢复。当初是不是该采用“杀猪政策”,其实有辩论的余地。亨利想,当年的我们是多么有信心的理想主义者呀。
“两天,绝不超过,”亨利说:“我答应吉儿会回家为泰迪庆生。”
“我会请秘书为你订到雅加达的机票,红眼航班。”马莉亚保证会打电话给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CDC)表达歉意——亨利是CDC副主任,主管感染疾病。这是马莉亚基于职责提出的紧急请求。
“对了,”亨利说离开的时候说,“罗马那边有新消息吗?妳家人还好吧?”
“我们不知道。”马莉亚不抱希望地说。

罗马恐攻行动发生在嘉年华期间——大斋节之前,全义大利都会举行一连几天的节庆。罗马人民广场挤满了人,来看化装游行以及著名的马术表演。那个早上的新闻充斥了美丽动物的撕裂尸体,散落在死去的神父、以及双子教堂的瓦砾之间。“罗马有几百人死亡,清点仍在进行,”美国福斯新闻网主播说,“义大利会采取什么反应?”
年轻的首相是民族主义者,两侧的头发修剪得服服贴贴,头上留了长发,席卷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者都喜欢的发型。用不著说,他提议大规模地驱逐穆斯林。
吉儿·帕森斯听到孩子轰隆轰隆的下楼脚步声,就关掉电视,听到了孩子在拌嘴。原来泰迪要与朋友到乐高乐园去玩,海伦可不可以一起去?其实海伦对乐高积木根本不感兴趣。
“谁要松饼?”吉儿开心地问。孩子都没有反应,仍然陷在没有意义的争执中,连家里的救生犬皮伯斯(Peepers)都惊动了,蹒跚地走过来调停。皮伯斯是一只混种狗,眼睛周围有黑色补丁,像猫熊一样。
“这是‘我的’生日,”泰迪气愤地说。
“我生日那天,我让你到六旗乐园。”海伦应声道。
“妈,她偷我的松饼!”泰迪嚎啕大哭。
“我只咬了一小口。”
“你‘碰了’它!”
“海伦,吃自己的麦片,”吉儿不带感情地说。
“太湿软的。”
海伦大剌剌地又咬了一口泰迪的松饼。他愤怒地大喊起来。皮伯斯也来帮腔。吉儿叹起气来。只要亨利出城去,家里就会变成一团乱。她正在心里责骂亨利的时候,她的iPad响了起来,那是亨利用FaceTime打过来的视讯。
“你有读心术吗?”吉儿问。“我刚刚才用念力召唤你。”
“我根本状况外,”亨利说,听到孩子吵嘴,以及背景中的狗吠。
“我刚才正要咒你,因为你不在家里。”
“让我跟他们来说。”
泰德与海伦的情绪立即平复下来,变得可爱万分。吉儿想,这是一种魔法术,亨利对他们下了咒。皮伯斯摇著尾巴表示崇拜。
“爹地,你什么时候回家?”泰德盘问爸爸。
“礼拜二晚上,会很晚,”亨利说。
“妈说你明天就回来了。”
“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我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别担心。我会赶回来陪你过生日的。”
泰德好开心,海伦拍起手来。真不是盖的。吉儿从不能像亨利一样将孩子摆平。也许我太爱挖苦人了,她想。一定是因为亨利对孩子说话的神态太诚恳,孩子给折服了。不知怎地,孩子知道可以信赖他。吉儿自己也有那种感觉。
“我做了一个机器人,”泰德向爸爸报告,拿起iPad展示由塑胶零件、电子线路、以及一具旧手机组合成的一个玩意儿。他要拿去参加科学展览。机器人的面颅上,装了一对相机镜头当眼睛。吉儿认为他看来像墨西哥的亡灵节娃娃。
“你自己做的?”亨利说。
泰德点点头,他的脸洋溢著骄傲。
“你叫他什么?”
泰德转向机器人。“机器人,你的名字是什么?”
机器人的头略歪了歪。“主人,我叫亚伯特,”它说。“我属于泰德。”
“天哪!太棒了!”亨利说。“他叫你‘主人’?”
泰德咯咯地笑,收起下巴,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他真正开心的时候就会那样。
“换我了!”海伦说,抢过iPad。
“哈啰,我漂亮的女儿,”亨利说。“妳今天一定有球赛吧。”
海伦是六年级女生足球队的队员。“他们要我当守门员,”她说。
“那很棒,对吧?”
“很无聊。你只是站在那儿。他们要我当守门员,只因为我个儿高。”
“但是每一次你救了一个球,你就是英雄。”
“要是没有成功,他们都会恨我。”
这是典型的海伦,吉儿想。令泰德满眼阳光的地方,海伦只见黑暗。她流露的悲观主义赋予她一种奇异的力量。吉儿注意到,她的同班同学有一点怕她的点评。那种素质,加上细致的五官,使她成为女孩的爱慕对象,对青春期的男生而言,则是教人心烦的警示灯。
“我听到你说不回家的部分,”吉儿说,终于等到再次说话的机会。亨利看来很疲倦。在iPad萤幕上他看来轮廓鲜明,像一幅十九世纪奥匈帝国贵族的画像,圆型眼镜之后的眼神非常锐利。她还可以听见背景中呼叫乘客登机的广播。
“也许根本没事,但是,要是有事的话,就是大事,”亨利说。
“这次是在哪里?”
“印尼。”
“啊,我的天,”吉儿说,不禁忧从中来。“孩子们,赶快吃完早餐,校车要来了。”然后对亨利:“你还没有睡过觉,对吧?我希望你吃一颗佐沛眠,晚上好好睡一觉。药带了吗?一上飞机就要吃。”亨利自己是医师,可是却不喜欢吃药,这让吉儿很反感。
“我感到妳在我身边的时候,就能再入睡,”他说,他说过一些教她爱得发狂的情话,这是其中之一,它会一直在她耳中回荡,直到他回家。
“不要冒险,”吉儿说,明知说了也白说。
“我从不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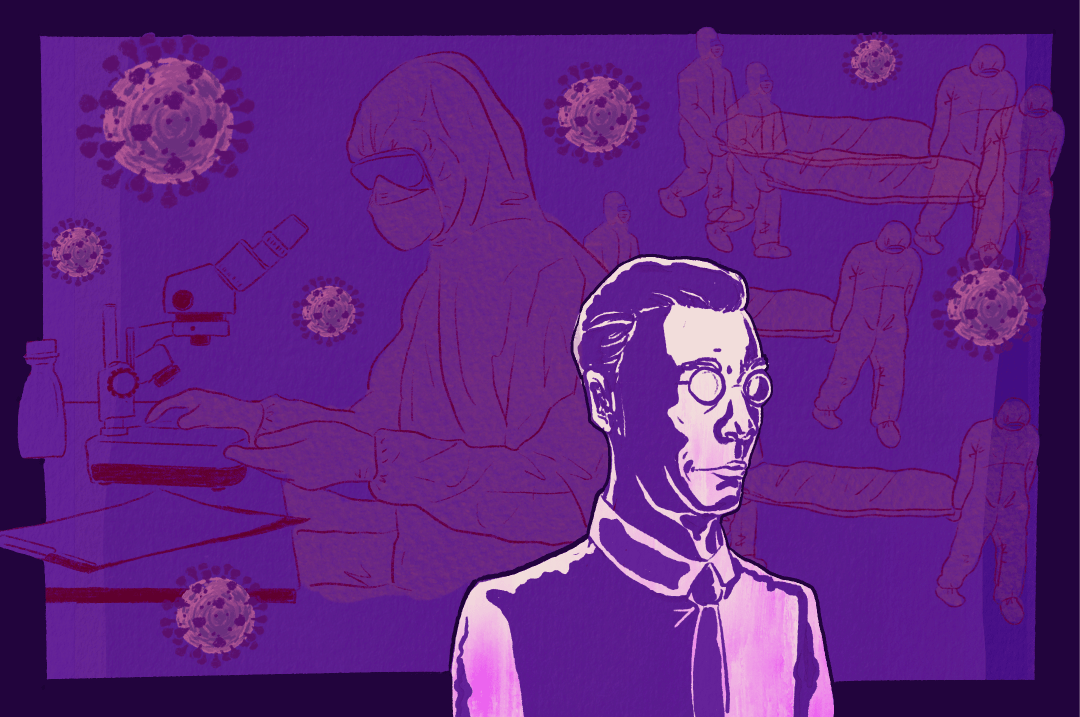




译者是《张大春泡新闻》的常驻嘉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