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座劳工建造的城市。当他们搭建的大楼竣工后,这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就不见了。当最后一块砖砌好,玻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电梯可供使用,管道也开始运转,每一个劳工都开始褪色,最终完全消失。有人相信,他们变成了鬼魂,萦绕在建筑外墙上。当你探访这座城市,可要记得,如果在室外、附近又有建筑物,那么,鬼魂可能已经坠落下来,甚至可能落到你身上。”
这是小说《临时人》(Temporary People)开篇第一段。在这本描述外来劳工众生相的小说里,刚出生就被父母带去阿联酋的印度裔作家乌尼克里希南(Deepak Unnikrishnan)没有立即点破“这座城市”在阿联酋的哪里——很可能是拥有全球最高大楼的迪拜,也可以是拥有世上唯一“八星级”酒店的阿布扎比。
当然,说到既依赖外来劳工又可以随时让他们“消失”的城市,我们可以想到复制“用石油换金钱”以及“在沙漠起高楼”模式的任何其他海湾国家,譬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又譬如我此刻所在的卡塔尔首都——多哈。
“你想知道多哈劳工营是什么样的?”
如约而至的私家出租车稳稳停下,司机瓦斯姆(Wassim)请我上车。车不新,但很干净,驾座旁搁着一大瓶白开水,就快见底。像我在多哈遇到的所有出租车司机一样,瓦斯姆肤色黝黑,来自南亚。他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几口,把看来从不离身的耳塞挂在耳后,精神满满地对我打包票,“找我就对了。”
卡塔尔很小,大约台湾的三分之一;居民很少,仅有250万人。理论上,生活在此的人极其富裕:2016年,该国人均生产总值近13万美金,全球最高。只是“人均”在此地是极不恰当的算法。卡塔尔借石油,尤其天然气贸易换得的巨额财富,全都掌握在“卡塔尔人”手上。而卡塔尔人只有32万人。剩下的200多万居民,都是来自别国的“外籍务工人员”,大多来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斯里兰卡。外劳占卡塔尔劳动人口总数的95%,其中近80%为男性——瓦斯姆便是一员。

“一旦来到这里,你就走不掉啦,”
到下午4点,早上5点半出门的瓦斯姆已不停歇跑了10小时车。过去一整年,他每天都跑15个小时,一天未歇。他有个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许过半年就能达成,到时就能减少工作量到每天10小时。
“我要盖一间大房子。”
45岁的瓦斯姆来自孟加拉小镇。197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孟加拉人奔赴海湾国家打工。为补贴家用,瓦斯姆19岁那年随亲戚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城市迪拜,一住便是15年。等到父母搞好包办婚姻,他才回去老家。
可老家日子不好过。在迪拜打工那些年,要顾家人,又要送弟弟们上学,剩下的存款并不算多。回去一段时间后,母亲埋怨他给的补贴越来越少,婆媳关系也越来越差,迟早得分家。分家意味着再盖套房子。一双儿女也在长大,盖房子的钱、孩子以后上学、结婚的钱,一笔一笔,瓦斯姆越算越忧心。
在老家找份工作不是好选择。瓦斯姆的父亲曾是警察,在镇上有头有脸,容不得长子一把年纪还开出租车、做散工。可高中毕业就在迪拜打工的瓦斯姆,干过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就是汽车销售。他试着在孟加拉做日用品销售,但工资低得可怜。
赚钱的希望在别处。回家八年后,也就是三年前,瓦斯姆狠心花了5000里亚尔(约1300美金)买到卡塔尔工作签证,重回中东。当时,迪拜陷入经济危机,工作紧缺,恰好瓦斯姆的表亲来到多哈,便也捎上他。
担保方是间出租车公司,瓦斯姆又借了4万里亚尔买二手车,每个月给公司缴500里亚尔租金。他多跑一些就多赚一些,最好时一个月能赚八九千里亚尔。这是他在老家打工所得的十倍,也比他能在多哈找到的其他工作都多。
“我算是技术工人,而且懂得跟客人打交道,”瓦斯姆对收入很满意。虽然为节省开支,他跟另外两个司机合租一个房间,但每个月,他都要买高级巧克力、进口玩具寄给家中孩子。
“95% 以上在卡塔尔打工的孟加拉人都是底层劳工。在孟加拉就是底层,到这里依然是底层。”很多人两年才能付清为买签证欠下的高利贷。工资最糟的每月只有700里亚尔,一般则在1200到1300里亚尔,稍好的服务业岗位可以达到三四千里亚尔。
这些劳工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公司集中安排在“劳工宿舍”里。
“一旦来到这里,你就走不掉啦,”瓦斯姆叹口气,他有很多老乡在多哈工作,偶尔见面,最常聊的就是:赚够钱了吗?半年后、一年后,就能回老家了吗?若听到有人说再过几个月就回去,瓦斯姆总是不相信。
“赚到一点钱不难,难的是决定何时收手离开;老家永远有更多的难题,永远需要更多的钱来解决,你就永远栽在这儿了。”
多哈的繁华只在几处,其余街区大多简陋,布满未完成的工地。偶尔,街边有一些树,被沙漠的阳光晒得无精打采,要是没有劳工定时浇水,就会干死。我们驾车离开市中心,逆着夕阳往城南工业园区走,劳工营集中在那区。我问瓦斯姆,你喜欢多哈吗?
他颇为不满地抬眼,提高音量说:“当然不喜欢”。

“这地方要的不是奴隶,它只是不停索取我们的青春。”
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
八个月,一年半,三年,五年,八年……
第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
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多久了?
第三个问题,你喜欢多哈吗?
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前,建筑公司安排的大巴陆续将工人送回宿舍。瓦斯姆和我在一间专为劳工开设的“大卖场”外,拿这三个问题问路过的工人。前两个问题有些机械,但第三个问题大约太过奇特,大多人听了都略惊讶地顿住,然后笑出声。
一些人笑得搪塞:“这有什么好问的”。
另一些人像被刺中,笑得讽刺,皱起眉,狠狠摇头:“当然不喜欢……但这有什么好问的。”
2010年,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在炎热的沙漠里踢球,卡塔尔承诺设有先进露天冷却技术的体育馆,并以此为契机大批引进南亚和东南亚的建筑工人。
为降低比赛风险,卡塔尔世界杯已被安排在温度适中的冬天,球员不必面对酷暑。但是,一砖一瓦搭建场馆的民工却不能避开夏天动辄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报告显示,由于残酷气候和不当管理,卡塔尔建筑工地上每年都有数百工人死亡。而气候亦非唯一挑战,尽管输出国的劳工中介在“贩卖”签证时,会说“耐热”是在卡塔尔工作的唯一要求。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6年发布报告称,修建世界杯场馆时,来自亚洲的劳工一直遭到剥削和虐待,“包括缴纳高昂的招聘费用、住宿条件恶劣、拖欠工资、不得离开工地、不得换工作、被威胁、被恐吓”。
宣传这些外籍劳工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悲情故事也有些效果。临近大卖场的宿舍看起来刚建成不久,被高高的围墙挡住。一位常年跟踪卡塔尔劳工权利的专家告诉我,卡塔尔政府颇花了些心力建立设施齐备的劳工宿舍。为了堵住批评者的轮番轰炸,“能见人”的劳工宿舍如今已是卡塔尔重要的“形象工程”。

11月,卡塔尔已入冬,过6点就夜意浓厚。路上行人只一种:刚离开工地的建筑工人。破旧衣服沾满一天苦工留下的尘与汗。全是壮年男子,三三两两,不吭声走在路上。沿街偶有店铺,都是给工人开设的饭堂、手机维修店、修鞋店,见不到一个女性或孩子。女性也不准走进大型宿舍。事实上,为了避免恋爱(或其他麻烦,譬如性交易),雇用女性劳工的公司通常设有宵禁,晚上8点后,这些女工便不准再出宿舍了。
在卖场买好蔬果食物的工人走回宿舍楼,门口的警卫拦住他们,仔细查看购物袋。瓦斯姆说,公司担心工人偷偷带酒回宿舍。生活在一个禁止饮酒的伊斯兰国家,非穆斯林员工要有公司开具的许可才能买酒。全国只有一处可以凭证、限量购买。当然,黑市卖很多酒,啤酒10里亚尔一罐、廉价的威士忌一小瓶50里亚尔。
下了工回宿舍便无事可做,有人会赌博。
“一开始赌博,那可就不能回头了,也剩不下钱寄回家。”瓦斯姆和我离开“示范宿舍”,往更南的方向走。在这里,“劳工宿舍”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
任何店铺后头的小楼里,挤挤都可以住几十人。有精明的商人,从卡塔尔人手里租下荒地,再建些简易棚,又可以挤下一大群人。在整齐宿舍里偷偷摸摸的赌博,到这区,便是几百号人大街上的集体活动。
瓦斯姆随便往黑夜里一指,说四五十公里开外的沙漠深处还会有那种特别大的劳工集中宿舍,住著成千上万人。“那才是完全没有指望,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2018年9月,国际特赦组织追加了一份报告,许多尼泊尔和菲律宾的工人为得到工作机会,给黑心中介付钱而欠下高利贷;来了卡塔尔,又被公司拖欠工资,等脱身回国时,竟比离开时更穷。
“哪怕让他们在卡塔尔过得再好一点点呢?哪怕能让我们的老婆一年有十多天来看看我们,哪怕有一点点娱乐场所?而不只是工地、宿舍两点一线呢?”
夜又深了些,瓦斯姆终于有了倦意。
“这个地方要的不是奴隶,它只是不停索取我们的青春。”
“一切都是卡塔尔人说了算。”
与瓦斯姆见面前几天,我第一次踏足多哈有名的海滨大道。
这条7公里长的大道,沿城市最东边的海湾画一个半圆,把南边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与北边的西湾连在一起。这是多哈风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博物馆延展出的一个人工半岛尖端。小小半岛上,有间露天咖啡馆,沿海而坐,西湾几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一览无遗。

满脸胡茬的乔治(George)休闲打扮,在这儿独自呆坐半天。他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某座摩天大厦。这个周六,他心里不畅快,盯着西湾,任咖啡凉去;有清洁工来扫地,他叹口气起身离开。
三十出头的乔治是个不喜欢阿拉伯世界、甚至不愿使用阿拉伯名字的黎巴嫩人。他已在多哈待了8年,一直都是银行的客户经理。比起南亚、东南亚的劳工,外来的阿拉伯人口只占卡塔尔劳力的12%,但基于语言和教育的优势,占据九成以上高收入、高技术含量的工种。
在黎巴嫩老家,乔治有个11岁的儿子。他常年独自在外,已与妻子疏远。两年前,乔治试着回国发展,跟家人做酒店生意,未果,只好又回多哈。为归国,乔治付出好大代价:他从多哈银行辞职。当他想再回多哈找工作时,多哈银行不愿意出具“无异议证明”——在卡塔尔,上家公司的肯定是外来劳工寻得新雇主的前提。若没有来自上个雇主的证明,乔治便无法再去找同行业的工作。
幸好,在金融业这些年,乔治积攒了一些人脉。一个相熟的卡塔尔人愿意给他“担保”,至少保他能留在多哈。不久,乔治在多哈一家来自黎巴嫩的银行办事处找到临时工,合同三月一签。他说,全球金融业都在整肃裁员,而这家银行新上任的执行总监,便以精简人员为首要任务。这个周六,便是乔治上份合同的最后一天,虽说人力资源部门口头答应下份合同已经在拟,他心中的石头仍放不下。
限制乔治求职的与限制建筑工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都是一个叫做“卡法拉”(Kafala,意为“担保”)的外籍劳工制度——要在海湾国家工作,外来劳工必须获得当地个人或公司的“担保”。在卡塔尔,担保人曾拥有极大权利,雇员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卡塔尔,不得更换工作,不得自行结束合同。
世界杯引发的争议使卡塔尔做出部分改革,2018年开始,大部分工人如果想要自行离开卡塔尔,无需公司出具“出境证明”;合同到期另寻工作,也不必上个雇主出具“无异议证明”。虽然法律明文已有修改,实际情况却没有好转。
“在这个国家,普通劳工是没有权利的,一切都是公司说了算,”听我提起建筑工人的境况,乔治同情之余,也想起自己,“不,一切都是卡塔尔人说了算。”

即便合同三月一签,乔治还是这座城市里专业高薪人群的一员。底层劳工的难处离乔治很远。景况最好时,乔治还住在西湾再往北、多哈最高级的住宅区:“卡塔尔之珠”(Pearl-Qatar)。
2004年开发的“卡塔尔之珠”是片400万平米的人工岛,在高空看像一串珍珠项链。开车入内,满眼欧洲地中海风格的建筑,若非仍会见到身着长袍的卡塔尔年轻人在咖啡馆约会,就像置身于空荡荡的南欧小镇。这是卡塔尔唯一允许外国人购买的地产。乔治买不起,但曾遇到业主吸引租客,放低房租,也搬去住过一段。
但过去一年,乔治只能住在酒店。卡塔尔的租金一年一交,每三个月就要担心一次自己是否仍有工作的乔治,只好长期住在酒店房间。虽说人前光鲜亮丽,客居他国的不安感也笼罩着乔治这样的高收入人群。
乔治想逃脱三个月“诅咒”,不久前找了阿拉伯半岛最东端国家阿曼(Oman)银行的面试机会。可他底气不足。“我所在的行业重人脉、重客户资源,在多哈待得越久,越是将资历集中在了这座城市。”若真去阿曼,不仅工资更低,核心业务也要从头打点。
“卡塔尔所谓的中产也是外籍雇员,大多与地产相关,承包商、人力、保险、贸易。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会把收入寄回家。”没有外籍雇员会把“生活”建在这里,这里不给你构建生活的机会。妻儿都不喜欢来多哈,乔治只能在新年回国探望她们。
而卡塔尔人拥有最好的福利,无需缴水电费,出国念书到博士都免费,政府给地、给特别优惠的贷款盖房子,乔治撇撇嘴:“只要愿意,他们就肯定有工作。”
“人生,怎么能够重选呢?”
第一次来卡塔尔时,尼日利亚人尤斯(Useful)还少不知事。十年前,14岁的他只记得自己穿着唯一的西装,从尼日利亚首都机场忽而就到了多哈机场。
尤斯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父亲是收入颇高的空调技师,来多哈后,还能把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接来同住。但他又不确信是不是用完了运气,因为他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多哈。
尤斯曾“成功”逃离过一次。刚来多哈时,他念的是菲律宾人开设的高中,17岁那年,菲律宾的大学来招生,他便顺势去菲律宾念大学,工程专业,专攻水利。毕业后,他被打回原形:要是回尼日利亚,便得志愿给国家服务一年;要是回到父母所在的沙漠国家卡塔尔,水利工程无用武之地,便要加入劳工大军。
见到尤斯的这个午后,多哈难得地忽降暴雨,像个休止符,打住了整座城市工地的运转。乘午休,尤斯从工作的医院出来与我吃午餐,头上还戴着白色的安全帽。工地上安全帽的颜色象征工种,也象征级别,戴白色帽子的通常是工程师、监理或者领导。他的职位是安全员,负责保护戴黄色帽子的普通工人不受伤。在多哈各种各样的工地上,安全员是紧俏岗位。两年前,尤斯考了安全员证,加入来自葡萄牙的建筑维护公司,“至少不用在酷暑,露天作业。”

卡塔尔像磁石,紧紧攥住尤斯一家。他的父亲想念故国,几年前试着回国,但尼日利亚的高消费、低工资让他打退堂鼓。离开卡塔尔等于离开稳定的收入。可长久地留在卡塔尔,又绝无可能。
“如果我明天能走掉,”24岁的尤斯笑容灿烂,“我完全不会回头看。”年轻的他,不喜欢卡塔尔人与外籍社群的隔离、更不喜欢这儿几乎没有同龄女孩可以约会。可到底哪天能离开?离开这儿,又能去哪里?尤斯没有答案。
饭后,踩著雨后的积水往工地走,尤斯想起一个人,收起笑容对我说:“要是时间允许,你可以去机场送送吉米。”
吉米姓翁,来自菲律宾,有一半中国血统。一个月前,他刚满60岁,大半辈子都在海湾国家打工。大约20年前,他在沙特工作时,不幸遇上瓦斯爆炸,失去右眼。浑身的伤痕至今可见。
就像尤斯的父亲,吉米也在卡塔尔有份不错的工作:维护建筑的工程师。60岁是卡塔尔法定退休年龄,翁吉米的工作签证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在生日戛然中止。
“来卡塔尔只是一时之策”——我遇到的所有劳工都这么告诉我。但是,仔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暂时”,在用工作换取价值的时候,他们也将人生交给这个陌生的国家。后者,只需要你的“劳力”,不会接纳你的“生活”。
飞回菲律宾的这趟航班,便是吉米在海湾国家工作近30年后,最后一次离开。
“回到三十年前,再选一次?”听到我的问题,站在登机口前的吉米笑出了声,“人生,怎么能够重选呢?”
“但如果能的话,肯定不会再选择来中东了。”回看多年打拼,吉米的总结很简单:因为在这里赚钱,所以可以培养子女长大;因为在这里赚钱,所以“完全错过了子女的成长。”
“至少我还能回去好好地做祖父,不再错过孙辈。”个子矮矮的吉米挥挥手,不似对最后一次离开有什么特别的伤感,快步走进了机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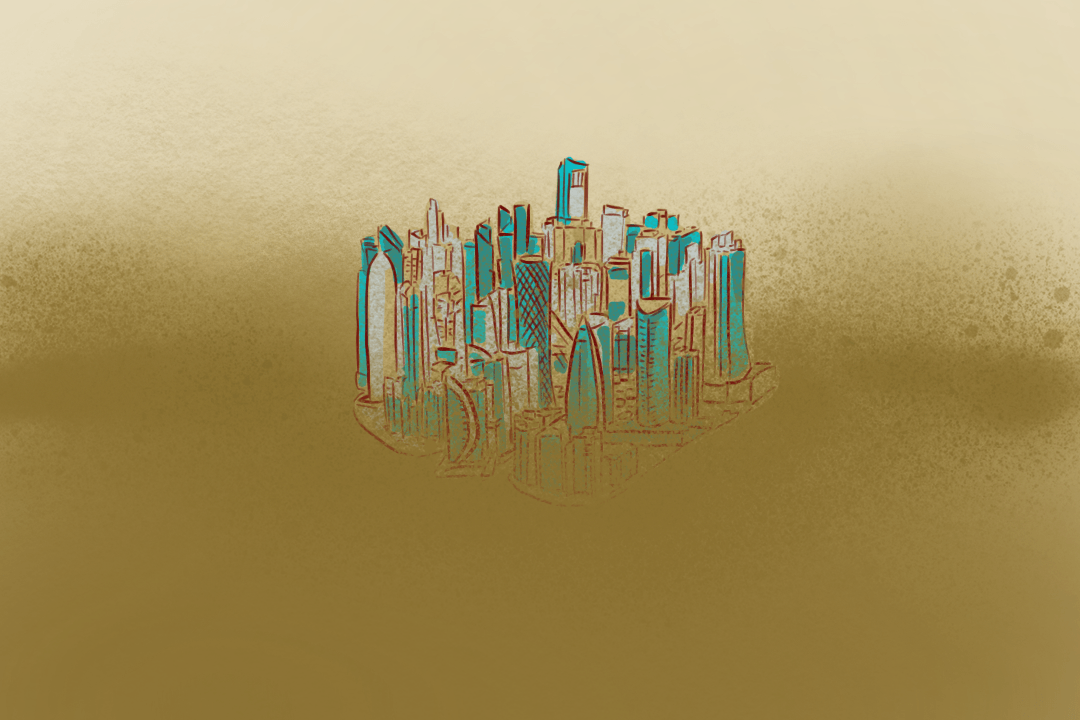




好看 還想讀到更多小人物故事背後的大背景 本土卡塔爾人又怎麼看外來勞工?
中东有意思
好文章
好看👍🏻
现代奴隶啊
財富由一小部分人掌控,這是全球的現象。到外地打工換取更好的薪水,純屬個人選擇。雖然卡塔爾外地勞工的遭遇令人同情,但畢竟我想不到有哪些地方存在絕對的公平。
胡茬 / 鬍渣?
“进城务工人员”
漂在异乡,阅完潸然……
小人物,大故事。好文章。
小人物中窥探卡塔尔的真实状况,写得很好!
似乎是錯字:「就會幹死」,應該是「乾」死嗎?
感謝指正,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