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左岸文化新书《禽流感的哨兵》,这本书集结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凯克 (Frédéric Keck) 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三个哨站进行的多点民族志调查,揭示人类在漫长的禽畜饲养历史中,与其他动物间出现了危险的失衡。以及新加坡、港、台各自发展出的应对策略。其核心是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预警工作里经常混杂不同的语言,如为了维护多数、优势者或者人类的安全而牺牲少数、弱势者以及动物的维安话语。
正如家禽养殖场排笼末端的哨兵鸡,香港也被赋予监视禽流感大流行的哨站重任。请回想导论提到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者的一段话:“1970年代香港曾进行流感生态学研究,并扮演著流感哨站的角色;这些研究指出,我们首度有可能在禽鸟层面上为流感预做准备。”在全球层面,香港全境变成禽流感的哨站,这是什么意思?它如何表达了香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为了调查在禽流感大流行的预测活动里人鸟之间的认同模式,我想在对两个层面进行类比:哨兵鸡、疫苗鸡与鸡场管理者,以及香港市民、中国邻居与当地政府。
长沙湾家禽批发市场位于九龙市中心,那里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8年12月,我听说爆发H5N1疫情,便去了长沙湾,拍下一些扑杀活鸡的照片。当时在记者的注目下,一万只鸡被气体毒死。这些鸡来自距黄宜全的养鸡场三公里内的另一间养鸡场,牠们基于预警措施而遭宰杀。由于附近另一间鸡场也必须杀死一万八千只鸡,加上黄宜全鸡场的七万只鸡,这意味著这场疫情造成十万只鸡被扑杀。因此,批发市场的扑杀作业只是整个养殖场大规模扑杀作业里公开的一面。在2001年与2002年的两次H5N1疫情期间,分别扑杀了120万与90万只鸡,这显示出香港的家禽饲养量有所下降。不过,1997年11月香港首度爆发感染H5N1的人类和鸟类病例时,被杀掉的家禽数目达到130万到150万之谱。渔农自然护理署有个公务员小组,负责监督“汰选”作业。该部门主管表示:“这些公务员多数过去都未曾看过活鸡。他们得要去学。但现在有些人已经变成汰选专家了。”相较于宰杀,汰选是借自园艺的一种实作,意味著去除生病的部分以提高整体的健康。
第一次以大规模扑杀鸡只作为禽流感预警手段,是发生在1983年美国宾州:由于高病原性H5N2病毒(这种病毒不会传染给人类,但能在家禽饲养密集地区迅速传播),1700万只鸡被杀。1995年,《新共和报》(New Republic)引述“流感教皇”罗伯特.韦伯斯特的话:“宾州〔在1983年〕鸡只的数目就像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数。假设病毒出现在人类之间,那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是无数的鸡,等著被感染。”该文作者麦尔坎.葛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强调这样的类比有些问题:“人类不是住在铁笼子里,一个挨著一个。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粪便里打滚。他们有脑袋,知道采取怎样的预警措施对抗疾病与传染。人不是鸡。但为何突然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鸡了?”然而在香港,我的访谈对象在谈到可能发生的禽流感时,便经常拿鸡和人做比较。香港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遭遇到禽流感危机时,可能也会用上这一比喻。

1997年时,陈冯富珍担任香港的卫生署署长。2003年她辞去此一职务,并于2005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在香港市民的记忆里,她曾在电视媒体的注目下在家禽市场里说:“我日日都食鸡㗎,大家唔好惊!”我在日内瓦遇到一位她的顾问,他想起1997年两人在一场紧急会议上的对话。她说:“杀晒啲鸡啦!〔把鸡都杀了吧!〕”他反问:“咁如果重有病毒点算啊?〔如果还有病毒怎么办?〕”“杀埋啲鸭啰!〔那就把鸭也杀了啊!〕”“咁如果都无用点算?〔如果还是没用怎么办?〕”“咁就杀埋我算吧!〔那就把我杀了吧!〕”
这段引言很惊人地表现出皇帝在危机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危机往往伴随著政权更迭,或者革命。这种类比思考(analogical conception)已被纳入儒家正统,根据这样的思考,君主或其代表必须通过祭祀的考验,集结天下万物,在政治空间里宰杀作为牺牲的动物(猪、鸡、牛)。对中国当权者而言,禽流感来自大规模的人流与物流。在此,“人”既有人类、也有德行之意,“物”则包括了动物和一切万物,“流”则同时包含了流动和流感。每年,当中国移工(“流民”)从工作的大城市回到家乡,政府当局都会担心传染病的传播(“感病”)。
1997年的禽鸟大扑杀给香港市民一种矛盾复杂的感觉,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恐惧。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宣示北京对此一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之际,杀掉这些可能受感染的鸡只既可视为是在保护人民,又可解读成动物发出征兆,提醒即将到来的政治危局。当香港市民担心被中国军队镇压时,鸡只却遭到自己的农业当局屠宰。诚如中国俗话“杀鸡儆猴”所言,这意味著大规模杀鸡也是中国恢复对香港主权的符号。超过一百万只鸡被杀,这也可能让人想起毛泽东在1958年动员中国人民消灭被视为危害的麻雀。
1949年后,许多人逃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这个条件艰苦的英国殖民地工作。后院自家散养的家禽对他们而言既是伙伴,也是蛋白质来源。2006年,为了预防禽流感,香港政府禁止家户散养家禽。尽管政府鼓励民众购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冰鲜家禽,但各世代的香港人仍然爱吃养在自家土地的现宰活禽。他们仍旧到活禽市场(又叫做“零售市场”或“湿市场”)买鸡;在活禽市场,鸡贩在顾客面前现宰活鸡,让顾客可以确认买的是健康的鸡。因此,尽管政府宣称扑杀鸡只是为了照顾市民,这个非常态的鸡只扑杀作业仍被视为破坏了民众与家户散养家禽之间长期的情感关系,同时也指出香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日增;同时间,活禽市场里日常的宰鸡活动,仍吊诡地维持住香港市民与家禽之间的亲近性。

然而,我们不能把牺牲的举动视为只是展现了由上而下施展的主权权力,毕竟许多人即便质疑扑杀作业造成很大的经济与伦理后果,他们大多数仍然分享了牺牲理性。香港佛教联合会为死在香港边界的鸡超度亡魂;这些比丘不在香港的市中心摧毁鸡的肉体,而是让鸡的魂魄得以离开,以便减少牠们转世的业障。有些佛教徒会从事“放生”的宗教行为。从字面上,“放生”一词可解读为“释放生命”(release the life)或“放任其生”(let live),实际上的做法则是从市场上购买禽鸟,把牠们放到自然保留区里。不过,由于许多被放生的鸟后来都死了(有时还染上禽流感),因此佛教联合会已经禁止放生。过去,新界的村子在举行一连三天的吃斋建醮祭典之前,会斩杀公鸡,把血洒在村子周围。传统用意是要驱邪,避免坏东西进入醮坛。不过,基于卫生之故,杀公鸡的仪式也已被禁止了。
我遇到的佛教和道教信徒向我解释,因为鸡肉消费增加,所以才会出现像H5N1之类的恶业或邪灵。他们还说,鸡为了报仇,便把病原体带给人。尽管宗教团体反对香港政府所支持的禽畜产业与肉品供销系统,但佛教徒与道教徒仍分享了跟政府一样的观点,视香港为一块封闭的领土,必须加以保护,以免受到外部危险的侵扰。他们批评他们眼中属于儒家式的牺牲,认为这是主权者在体制变换期间为恢复自身权力的作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使用德斯寇拉所谓的“类比主义”存有论,或者借用傅柯对主权权力的形容,他们同样采用了“令死而让生”(make die and let live)的技术。
相较之下,香港的微生物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看待禽流感。尽管他们大部分都不是生于香港,而是生于澳大利亚、斯里兰卡与中国大陆,他们都协助重塑香港的新身份,视其为中国统治下的哨站。1972年,甘迺迪.邵力殊在香港大学创立了微生物学系。他是罗伯特.韦伯斯特在墨尔本大学的同事,两人都是WHO在日内瓦的流感生态学专家委员会成员。1968年的大流感病毒造成全球约100万人死亡。因为该病毒首先在香港辨识出来(因此被称为“香港流感”病毒),邵力殊及同事预测下一场大流感应该也会出现在中国南部地区。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WHO成员国,因此并不与成员国分享中国境内的流感病毒株资讯,同时也不认为流感是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邵力殊和广东的兽医建立了私人关系网络,收集当地鸭与猪的流感病毒样本。随后他提出,在华南地区,人们在稻田养鸭以清除害虫,鸭、人、猪的生活范围非常接近,这样的生态因此让当地成为全世界的“禽流感震央”。他与英国著名的流感专家查尔斯.史都华-哈里斯(Charles Stuart-Harris)合写道:“中国南部毗邻香港的地区人口稠密,且采用集约养殖,因此有利于不同宿主物种身上的病毒发生交换。”为了支持这一假设,他指出汉字的“家”里有一只猪在屋顶下,仿佛从这个字的各种特征,人们可以看到来自动物的病毒突变。
1997年2月出现首批禽流感病例之时,邵力殊去了家禽市场,并发出警报。当时香港有一千多间活禽市场,对部分市场的检测显示,36%的鸡只带有H5N1病毒。他回忆道:“前一刻,鸟儿还开心地拣谷物吃,下一刻,牠们便用慢动作侧身倒下,喘著粗气,内脏慢慢渗出鲜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我当时在想:‘天啊,这病毒要是传到市场外,会发生什么事啊?’”稍后他又说香港湿市场的鸡尸让他想起了母亲的描述:1918年他的家乡昆士兰发生大流感,当时也有很多人死掉。邵力殊原本设想的策略是:趁病毒还没传给猪并减弱毒性,便在鸟身上找到病毒,以便在病毒从猪传到人之前,便能做出相应的疫苗。然而在1997年,要对可以直接从鸟传给人而且对人鸟都致命的病毒做出相应的疫苗,简直不可能,毕竟疫苗必须要在鸡胚胎里培养。因此,他建议政府扑杀香港境内所有的活禽,以便消灭H5N1的动物储体。

在一次访谈中,邵力殊对我说:“我们不是在汰选,我们是在屠杀。”我问他香港市民如何接受这种大规模扑杀,他告诉我,五年前曾爆发马流感,这种流感对马有致命危险,但不会传染给人。当时他曾建议关闭香港的赛马比赛。然而在香港,赛马是唯一的赌博机会,而香港赛马会又是最有钱的协会,关闭赛马的代价比杀死后院散养的家禽还要高。稍后,邵力殊为文辩护为何有必要一再扑杀感染禽流感的家禽;他认为这是一项先发制人的措施。
当迹象变得很明显时,便要开始一间一间市场宰杀家禽,甚至干脆先发制人,全面实施扑杀,以防止人类遭感染。2002年和2003年,又再度下达指令,进行早期侦测与早期反应。因此,现在我们对大流感预备工作的期待是,不只是在人类层面上做准备,最好是要在基础的禽鸟层面上做准备。因为如果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便被消灭,流感事故或大流感便不会发生了。在1997年时,世界距离发生禽流感大流行大概只差一到两次突变事件,但2002年时,由于较早的侦测,则大概还差三到四次突变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邵力殊在评估病毒大流行所需的突变事故次数时,用的是一种机率的语言,但描述的却是一种本质上有赖于想像的预备技术,毕竟他提起家人对1918年大流感的记忆,或者诉诸呼应流感震央之说的汉字。陈冯富珍根据牧养逻辑谈论预警,邵力殊则用军事逻辑谈论如何“先发制人”。两人都把古典的预防与当时新兴的预备技术混合在一起。
邵力殊在1982年提出一个最坏的可能情节:大流行病将随著动物在中国南方出现。稍后,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让这个情境成为现实。2002年11月,广州出现首批神秘的肺炎案例,同个时候,位于新界沙田马场附近的彭福公园有三十多只野鸟被侦测出带有H5N1病毒,随后农场和市场也发现受感染的家禽。2003年3月,透过急诊室的空气传播,香港医院出现了首批SARS病例,不过当时香港大学的微生物学者花了两个星期在检测禽流感病毒,从而未能及早辨识出造成此新疾病的病原体。SARS在香港医院与中产阶级之间快速传播,这场危机因此被认为是香港公共卫生的一次失败。这也是为何陈冯富珍会从卫生署卸任,而香港卫生署也迅速重组,成立负责危机管理的卫生防护中心,并与医院管理局分开。不过很快地,SARS又变成早期发现人畜共通传染病的一个成功案例。
《禽流感的哨兵:中国边界上的病毒猎人和赏鸟者如何预备传染病大流行 》
作者:费勒德里克·凯克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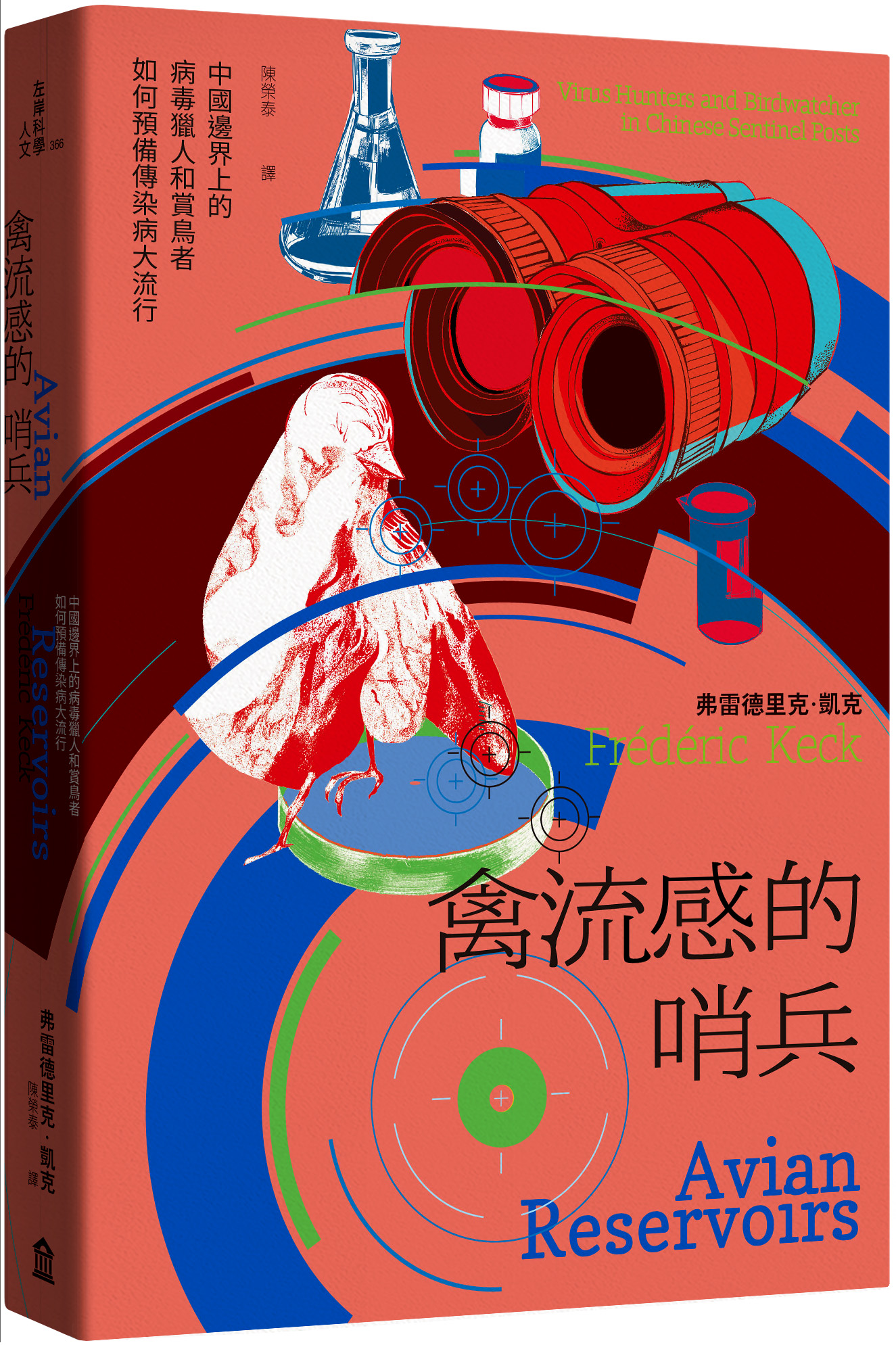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