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现在是深夜两点四十三分。
隔壁病床的阿伯刚被成功抢救回来,护士在清理身上沾满鲜血的防护衣,疲惫的眼神中略带一丝轻松。拉上布帘,调暗光线,一场生死间搏斗的战争又结束了,ICU再次恢复到死寂之中。这种死寂让人感到很不安,脑袋越发聒噪。监测机器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耳朵中震荡,我甚至还能听到其他病人的呼吸。ICU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慢到时间就要凝结在呼吸中一样。不知道宇航员在月球漫步时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我看看自己身上连接机器的各种管子,这里确实就是外太空无疑。作为这个房间唯一有清醒意识的病人,有时我宁愿自己和大家一起昏迷,时间慢行得比刀子还锋利,割在身上,越割越痛,越割越清醒。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两点五十分。脑袋还在转,还是睡不着,只能让思绪在漫无边际地游走。
把头转过枕头一边的瞬间,刚好和宝珠的眼神对上了。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就像是一对玻璃珠子,光线进去然后出来,没有残余。我总企图从她的眼神找出一点思绪的痕迹,仿似一块石头扔到井里,咕咚一声就沉下去了,只剩下我的倒影在水面轻轻浮动。不仅是我,所有医生都希望从宝珠那双大眼睛中捕捉到什么,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哦,忘了说,宝珠是一个植物人,一个会转头,会眨眼,像洋娃娃一样的植物人。
宝珠今年五十三岁,九年前躺在手术台上做甲状腺囊肿切除手术后就没有醒过。这当然是一场医疗事故,医院对她负全责,否则我想没有人能躺在ICU九年不破产。当时麻醉科、外科、神经科等大部分医生都围着她团团转,极力想办法让她醒过来。但人世就像报纸新闻一样,只要地球不灭亡,外星人还未登陆地球,火山爆发、飞机失联、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每一件特大新闻迟早都会变成旧闻,天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发生什么更大的新闻。在这样三甲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身患奇难杂症的病人。宝珠渐渐地被淡忘,开始在各个科的ICU流转,最终来到NICU(神经内科)偏安一角。每个在ICU的病人都只有两个结局,要不病情得到控制后转去普通病房,要不永远离开,只有宝珠,在这里经历过生命的人来人往之后,依然日复一日淡然地在靠窗户的病床上躺着。
每个新来的实习医生一开始都怀着雄心壮志,要解开医学难题,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每天拿着手电筒为宝珠仔细检查,宝珠也一如既往地心甘情愿为医学研究做贡献,眨着大眼睛,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对于整个ICU来讲,宝珠的存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她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
医生每天开一样的医嘱,护士每天照常地护理,吸痰、冲尿管、换鼻饲,抹身、换衣服、换床单,有时帮她洗头发,剪指甲。有时护士给宝珠吸痰的时候,时间太长,吸得太深,双腿都自然反射往上跳,看得我也心惊肉跳。宝珠却依旧静默,她不会像我一样投诉护士打针太痛,抱怨吸痰吸不干净,无论你对宝珠做什么,她都只会眨眼睛,没有其他回应。她的存在,等同于不存在。
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开始,存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这里可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相信这就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一个副产品,将西方文化中极其顽固且占主导地位的二元论植根到我们的思维中。从古希腊的先哲开始,身体就被贬低为禁锢灵魂的可怕牢笼。柏拉图的理型世界中,只有崇高的灵魂才能超越身体的欲望。如果身体体验和精神世界真的极端对立,那么,宝珠现在对世界的体验是什么。还是说她早已离开这副躯体,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只是存在的一个过去式。
可对于宝珠的亲人来说,她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她的丈夫吴先生在病床边放了一个音乐盒和一张他们的合照。我没有看过照片,但护士都说年轻时候的宝珠长得很漂亮,那也是,她有双水灵的眼睛。每天下午四点,吴先生都会准时来探病。一进门就和宝珠热烈地打招呼,打一盆热水帮宝珠擦身子、按摩手脚、梳头发,一边谈谈今天的天气和身边发生的事,有时会读读报纸,就像平常的夫妇一样,日日如此。其他病人的家属都一副悲戚的样子,时而大哭,时而大叫,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喊惊”一样,竭力把走得太远的亲人拉回来。只有宝珠和吴先生照样在一旁安安静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如果宝珠没有生病,他们现在一定过着平淡的夫妇生活,上班下班,买菜煮饭,打扫卫生,为孩子读书操心,偶尔去一趟短途旅行,有时会拌嘴,甚至互相怄气,但从来不和对方说爱你。我不禁地想,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还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走远过。
护士说吴先生每天都会准时来这里看宝珠。如果哪天没来,肯定是生病了。有次我妈妈来探病的时候和吴先生交谈起来,他说他们有个儿子在日本读书,但自从宝珠生病之后都没有再回来过。每次吴先生走的时候,都会扭开音乐盒,让音乐代替自己多陪宝珠一会,但再动听的音乐都会停下来,然后重新回归到寂寞之中。
宝珠又扭过头去了,我望着窗外婆娑的树影映衬着宝珠倒映在玻璃窗上的脸,墨绿的叶子上渐渐泛出一层淡黄色的光晕,一阵风吹过叶隙,摇曳的光影随之又映在窗帘上。宝珠的大眼睛仿似是万花筒一样,旋转出各种迷离的图案。远处的小鸟开始叽叽喳喳地叫了,很快就要天亮了,连沉睡的树木也要回到清醒的生活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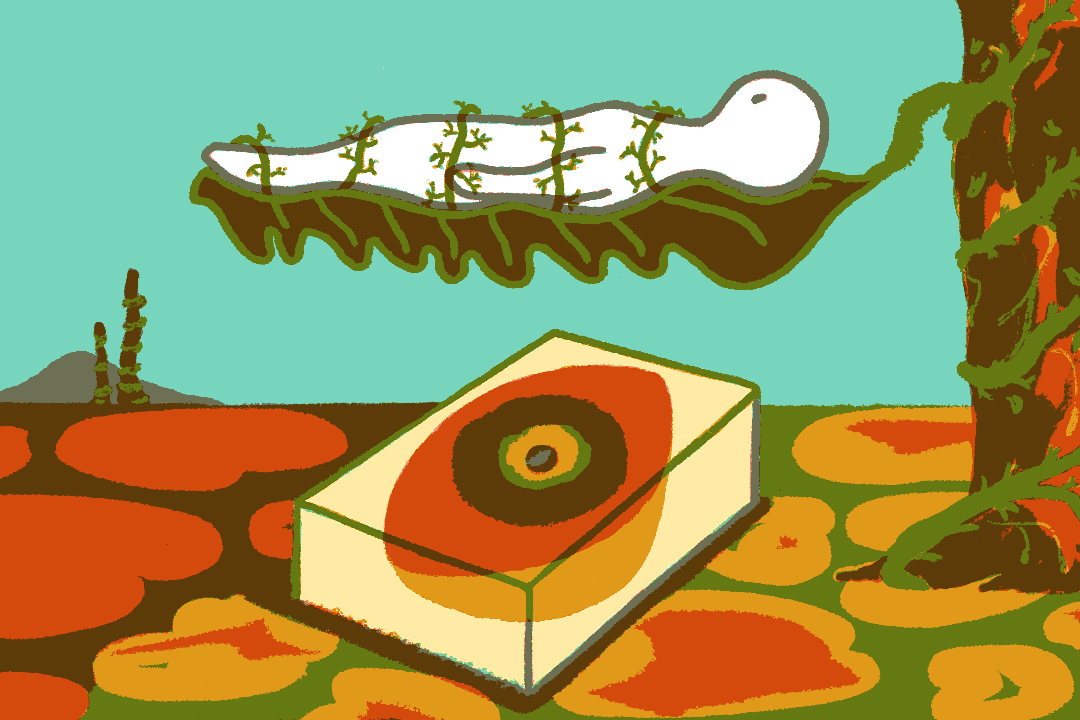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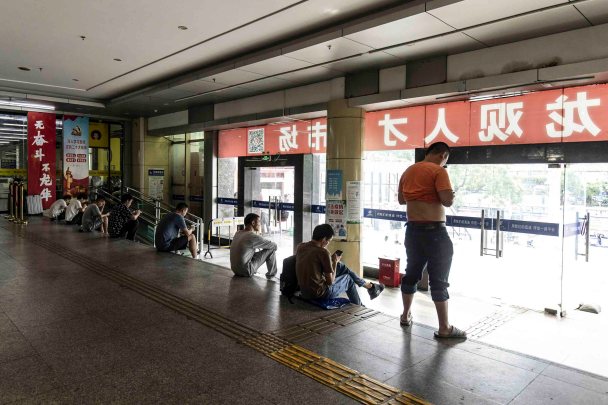
宝珠是植物人么?能转头,还能眨眼睛,能对外界做出反应的,但是不能移动四肢不能说话的不应该是高位截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