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陽春菊出生在廣東省陽春市,她是一個棄嬰。 這一年出生的孩子,福利院的人會為其取名為「陽春+花卉的名字」,她被叫做「菊」。一歲六個月的時候,她有了一個英文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白人家庭收養了她,養父是匈牙利移民後裔,為她取名Mary Ruth Tomko。平時,大家都叫她Mei。
她在賓夕法尼亞的小城約克長大。用她自己的話說是「美國鄉下」,「學校裏96%是白人,4%是非裔美國人,基本上沒有亞裔。」從小到大,她都覺得孤單。從外貌上,她看起來格格不入,身邊也沒有人對亞洲文化感興趣。養父母支持她去學習自己的種族文化,他們付錢讓陽春菊上中文課,為她報名專門為從中國被收養的孩子打造的文化夏令營,後來還牽線搭橋讓她去上海實習,增加了解中國的機會。但是,她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去,父母從沒一起參加過。「他們通常會說,『哦,你可以去做這個。』他們自己卻並沒有很大的興趣。」
在白人社區、並被冠以白人姓名長大的過程中,沒有人告訴她作為亞裔美國人究竟意味着什麼。
她認識為數不多的亞裔同齡人,是夏令營裏的朋友,還有被從中國廣東領養的哥哥。「但他們對亞裔文化一點興趣也沒有,」她的哥哥更習慣和白人交朋友,「所以我和他沒有什麼共同話題。」而夏令營,她覺得「又假又奇怪」,孩子們在那學習簡單的中文對話,試着煮一些中餐,學習武術招式。給她上課的老師們不是華人,而是收養了中國孩子的白人。
根據國際收養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是世界上收養中國孩子最多的國家。自1992年中國收養法通過以來,美國成為超過17萬中國孤兒的家。這些孩子大多由白人家庭撫養,在白人社區長大,潛移默化地將自己也視作白人,直到懂事後,常常因為自己和周圍人不一樣的面孔而遭遇身份認同危機。當他們接觸種族主義或經歷種族歧視之後,常常有兩種反應,「抗爭或者逃跑。」在馬塞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從事亞裔美國人研究的C.N. Le說。
「逃跑,就是放棄他們的亞裔身份,脱離關係。另一種是抗爭,與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人聯合起來面對種族主義。」C.N. Le補充。
她第一次按照「東亞人」的模樣給自己打扮
有很長一段時間,陽春菊會刻意逃避自己是被收養的事實。和父母一起出門的時候,她會故意走在他們的前面或後面,讓別人覺得她和他們沒有關係。她記得初中的時候,媽媽曾說學校的男生都喜歡陽春菊,是因為她的「異域風情」。這話讓她不舒服。後來告訴她媽媽,長時間以來,她都覺得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白人」,以試圖去融入自己的的家庭和社區。同學們都在玩Instagram的時候,她把照片裏自己的眼睛改成藍色,因為她曾覺得「棕色的眼睛不好看」。為了能和身邊的白人朋友有更多的話題,她常常要假裝自己也對「舞會、遊戲或者談戀愛感興趣」。

她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從來沒有一個「亞裔美國人榜樣」(Asian American role model)。哪怕是學習打扮。她記得青春期的自己第一次去商場的化妝品櫃枱,服務員不知道怎麼為她的單眼皮和亞洲人臉型化妝。「那些化妝品在我臉上顯得非常奇怪。」她回憶。直到她開始追隨YouTube上的亞裔博主,跟着她們學習妝容和服飾。那是她第一次按照「東亞人」的模樣給自己打扮:用輕薄的底妝代替濃重的修容,去掉粗黑的眼線,打上腮紅和淺色的帶閃片的眼影,用更適合亞洲膚色的橘色化妝品。再後來,她迷上韓國流行樂(K-pop),看着Girl's Day裏面的音樂和舞蹈,她覺得亞洲人「也可以很美」。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痴迷,但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東西回答了我的懷疑,給了我自信心。」陽春菊說。
上大學之後,陽春菊加入了亞裔學生社團,結識了一群在亞裔移民家庭出生長大、和她「外表相似」的孩子,終於實現了「長久以來都在渴望的、屬於自己的社區」。她最好的朋友在夏威夷長大,是菲律賓和老撾後裔,篤信佛教。陽春菊從她身上學到了不同的亞洲傳統和宗教文化,亦發現彼此之間對「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她覺得,亞裔家庭重視「家」的觀念,是完全建立在血緣關係上;而於她,一個被收養的孩子,她的「家」完全由情感來支撐。
原來自己的經歷是獨特和寶貴的,陽春菊慢慢為自己搭建起「跨種族收養者、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三重身份認知。
同樣是中國收養兒的周江雯(Charlotte Cotter)對端傳媒記者說,收養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它沒有一個終點。「說到收養,很多人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比方說收養者過上了很好的生活。但其實,有得有失,在得到的同時,我們失去了原生家庭、文化、語言和國家,這些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拿回的東西。我覺得我很幸運,也很感激我所擁有的,但我也想承認收養的複雜性。」
周江雯出生於1994年8月,被遺棄在江蘇省鎮江市的街上,後來被美國波士頓的一對同性夫婦收養。她的兩個媽媽都是律師,她還有一個從江西省九江市被收養的妹妹,和幾個在美國境內被收養的堂兄弟姐妹。
填滿我們生命中的一些空隙
2008年,周江雯讀到一篇《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三個從中國被收養的女孩,長大後回到中國福利院當志願者。她開始意識到很多人有着和她相似的成長經歷,也發覺被收養者這個身份代表着一個全球現象。要是能有個平台把我們這些人都聯繫起來,那該多好,她想。
2011年,周江雯17歲的時候,和另一位從中國被收養的女孩馬酉學(Laney Xue Allison)一起成立了NGO組織「中國的國際孩子」(China's Children International,CCI)。經過十年的運營,她們把這個起初只在臉書群組裏活躍的組織,發展成一個擁有超過4000名、來自世界各地成員的國際組織。他們舉辦過各種活動,譬如去中國做志願者、學習中文,以及尋找親生父母。
周江雯對端傳媒說,對她影響很大的一個項目是「無名收養者的口信」(Message from an Unknown Adoptee)。這個項目受到作家薛欣然的《無名中國母親的口信》的啟發,向全球各地的來自不同年齡層的中國收養者,徵集他們想對親生父母說的話。
「作為一個被收養的孩子,我是100%的華人和100%的美國人。你們給了我生命,我的美國媽媽讓我成為現在的我。」周江雯在給親生父母的信中寫道,「但有時,我會想,你們為什麼不要我了?現在的我足夠優秀了嗎?我是那個會讓你們驕傲的人嗎?」

2016年,當時在耶魯大學念東亞研究二年級的周江雯要到台北交換一學期,她決定提前出發,先去中國,和另一個從新疆被收養的女孩李美珍(Willa Mei Kurland)利用暑假開啟她們的尋根之旅。出發前,她們製作了尋親海報,發布在社交媒體上,很快就受到媒體關注。江蘇鎮江的一個報社記者走訪後發現,1994年夏天,一名女子在鎮江一家醫院留下的生產記錄,與周江雯的出生日期十分吻合。接着,記者通過醫院提供的聯繫方式找到了這名女子,並最終確認她就是周江雯的生母。 這一切發生在一週之內,快得讓周江雯有點措手不及。她之後在鎮江見到了她的親生父母和親戚們,他們相處了一週,一起慶祝了周江雯的生日。認親之旅在媒體的鎂光燈下引起社會轟動。直到半年後,她從台灣回到美國,才開始慢慢地消化這件事。
談及當時的情形,周江雯有些語無倫次。她說直到今天還在應對這個現實,有好的、也有壞的感受。她不願透露與親生父母在鎮江相處的細節,表示「在沒見到我的親生父母前,我一直都在想像我出生時被拋棄的情景是怎樣的,現在突然有了答案,一時間有點難以接受。」
「只是一切都超出了我所可以控制的範圍」,但她覺得自己是「超級幸運的」,就像她和李美珍在最初的尋親海報上寫到的一樣,「我們想多了解我們的家庭背景,我們生命最開始的那一段......這樣我們才能填滿我們生命中的一些空隙,安心地把我們生命的故事繼續寫下去。」
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2020年6月,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蘇達警察壓頸而死,這一事件在美國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反種族歧視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同命)。在美利堅大學學習國際關係的陽春菊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長度跨越整個夏秋的街頭運動令陽春菊開始回溯成長過程中「被白人化」或者「被標籤化」的細節,亦開始重新審視她與父母的關係。
父母在過去總是對她說:「我們不把你看成亞裔,我們只把你看成我們的女兒。」她不滿意這樣的答案。她記得母親在閲讀一本與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相關的書時,曾感到被冒犯——因為她是一個民主黨人,也是兩個亞裔孩子的母親,母親認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不應該被控訴享有特權。「我才發現,對很多白人家長來說,他們很難做到對自己的行為更加覺察。他們也很難面對自己本身固有的偏見和根植於心的種族歧視。」陽春菊說。
她開始有意識地在幾個收養兒的群組裏開展話題,也舉辦了線上研討會討論「如何與你的白人父母開啟種族主義話題?」她在研討會上提到,跨種族的被收養者通常在潛意識裏覺得應對養育自己的父母心懷感激,所以在遇到來自家庭內部的種族歧視時,會選擇沉默,做一個乖小孩;而父母處在一個權威的地位,通常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個時候,收養兒們需要把討論種族話題提上日程,設立一個目標,告訴自己打算從談話中實現什麼,做出改變。
她告訴父母,家人們也應該嘗試了解亞洲文化,而不是只有她壓抑着自己的情感以求同。她告訴媽媽,過去一些刺耳的話令她至今難忘,媽媽隨後向她道歉,說之前從沒意識到這些話說有問題的。她上大學之後,每一次放假回家,父母都會發覺她身上作為亞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更多了一些,因此必須要去給予支持。2021年的農曆新年,她給媽媽轉發了一篇傳統年夜飯的文章,媽媽響應了,主動上網去買家裏沒有的亞洲食材,譬如春捲皮和料酒。
這是她家第一次真正地慶祝農曆新年,陽春菊穿上了之前從上海買的旗袍,白底絲綢面料,上面畫着水墨潑染的仙鶴,領口處點綴着紅色的牡丹花。她和媽媽花了一整天時間做年夜飯,餃子、香菇菜心和烤雞,她開心地在Instagram上發圖片:「牛年大吉」。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也加入了關於種族的討論。近幾個月來,美國各地出現了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陽春菊的父母給所有的家人朋友都發送了反種族歧視的信息。感恩節團聚的時候,她向親朋介紹自己在學校的亞裔學生社團十分活躍,親戚開玩笑問她,「你現在只和亞洲人交朋友了嗎?你是亞洲精英嗎?」還有親戚在陽春菊的臉書上發表對亞裔不友善的評論。這時,她的父母會站出來,給對方打電話溝通。陽春菊開始覺得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用自己跨種族領養者的身份,去參與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1999年出生在江西余春的宜文東(Emma Coath)和陽春菊一樣,也是在賓夕法尼亞一個亞裔人口只佔1%的白人社區長大。但不同的是,她有三個同樣從中國被收養的姐妹,還有一個鄰居收養了三個中國女孩。因此,她與六個年紀相仿的中國領養兒相伴長大。雖然會有「不知道該像美國人一樣吃沙拉,還是像中國人一樣吃中餐」這樣的困擾,但「家裏有和我長得很像的人,她們都有黑頭髮和深色的皮膚,」令她感到「非常幸運」。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來源,還一起做了基因檢測。」宜文東說。她的父母亦用照片、文字和視頻詳細地記載了下來她被收養的過程。 走進宜文東的家,走廊掛着的四季山水圖,客廳玻璃櫃裏有熊貓擺件和印着吹簫仕女圖的五彩瓷盤,她的床頭擺着泥塑小格格。「到處都有中國的影子,」宜文東說。
她曾在賓州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isity)修讀平面與交互設計,意外發現兩個女同學也是中國收養兒,彼此也都渴望結識更多相似背景的收養兒。於是,在一次設計作業中,宜文東興奮地向教授展示了自己設計的、服務於中國收養兒和收養父母的社交軟件。她把這個軟件取名為Péngyou,即中文的「朋友」,不僅讓收養兒們互相聯繫,也要讓收養父母組建在線社群,分享養育的心得。
然而教授沒有明白這個設計對宜文東的意義。她因此很鬱悶,「很多人都不把收養看作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卻很有被提及的必要。」
從2020年末到2021年初夏,紐約、舊金山等地「停止亞裔仇視」(Stop Asian Hate)運動如火如荼,但宜文東所在的賓州小城卻猶如遠離人間煙火。但她最近在另一個城市找到了一份設計師的工作,很快就要離開家了。興奮的同時,她很擔心——不知道其他人將怎麼看待沒有和白人父母在一起的她,她的同事又會怎麼看待身為亞裔的她。
「2020年的事情向所有人表明,特別是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不能理所當然地認定他們會自動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非常脆弱和不穩定。」C.N. Le說。
「我希望亞裔收養兒不逃避他們的身份,應該直面敵意,與其他遭受種族主義的人聯合起來,無論是其他亞裔美國人,還是非裔美國人,或其他有色人種。」C.N. Le補充。

周江雯亦對端傳媒表示,很多中國收養兒從未真正對亞裔美國人和華人移民群體產生真正的歸屬感或認同感,對於最近頻現的暴力事件,大家還在尋找排解的方式。很多人傾向於在收養兒的小圈子裏討論他們的恐懼、悲傷和憤怒的感受。
在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之後,周江雯參與組建的組織「中國的國際孩子」(CCI)舉辦線上活動,讓遭遇過種族歧視的領養兒相互結識、溝通和鼓勵,她將這樣的活動稱為「一個安全的空間」(a safe space)。這場活動還有在英國和愛爾蘭的亞裔領養兒參加,活動時間也考慮了美國和歐洲兩個時區。
宜文東在社交媒體簡介中寫道,自己是一個領養兒(Adoptee),也是一個博愛的人(Philanthropist),她還在讀當代中國平面設計的書。陽春菊積極地分享亞裔與非裔結盟的信息,希望以更大的力量抵制種族主義,她同時在研究如何喚起白人對種族的敏感意識。她回到自己的中學和社區演講,呼籲人們捐款,關注不同身份的人群。她對端傳媒說,她學到了如何「用自己跨種族領養者的身份,去參與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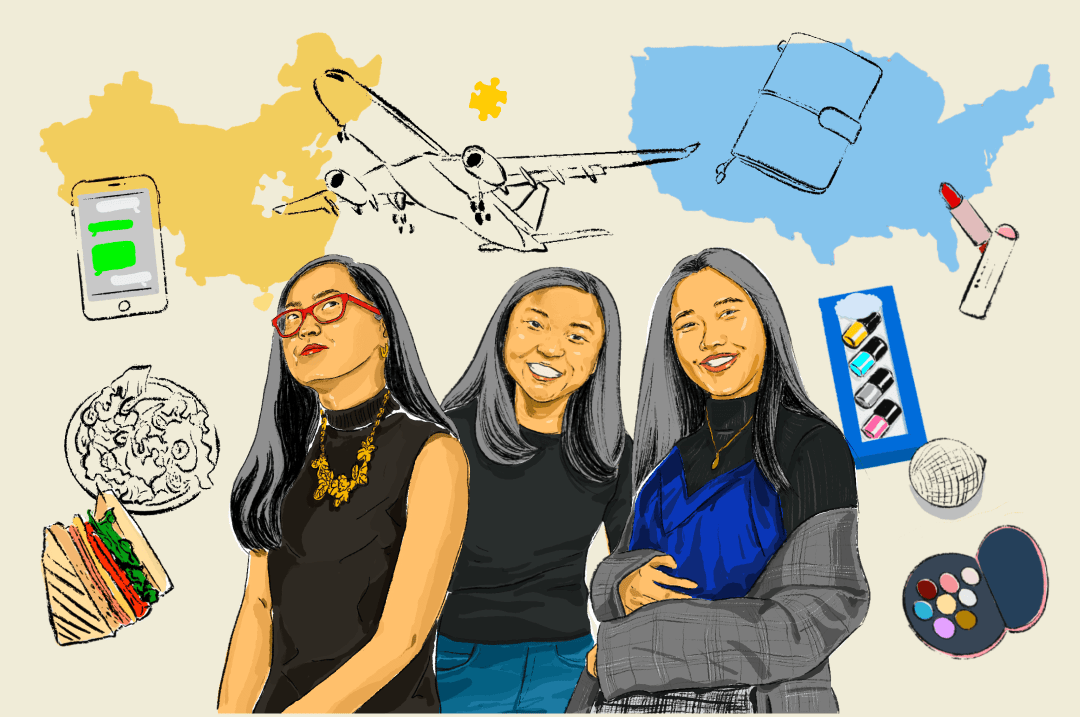




部分同意Deadone
沒有長期在美國生活的經驗,但有短期的;「亞裔」本身就是很大的概念,因為美國白人文化的強勢與排擠性所以種族本位式、工具性地挪用東亞文化以建立自尊,是情有可原,但這樣的作法真的沒問題嗎?又這個資訊流通、擁有美國護照者機乎可以全球自由移動的時代,真心想要理解血親所在地區的年夜飯文化真的有如此困難?
此外,文章也有提到被收養亞裔跟於東亞家庭成長亞裔的隔閡;能自由選擇要不要戴上裝扮、選擇如何裝扮,但東亞人與一些類型的亞裔是沒有選擇的。中心與邊緣的是相對的,當一些亞裔在努力破除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時,文中的被收養亞裔將「亞裔就是不愛戀愛、打電動」「亞裔作kpop式打扮才是美的」等極致刻板印象與符號當作fancy的異國情調為佐料,不免讓人覺得情何以堪。
感謝樓下兩位的補充,長知識了。
我看到許多的批評也停留在「這些女孩人心不足蛇吞象」,明明有了好生活還要挑三揀四。但是對我們而言他們過的這種日子是「純粹的好生活」嗎?要注意的是,要批評別人之前,請先理解別人的生命經驗。在一個膚色格格不入的社區、在一個被父母推薦學習種族文化但他們卻沒興趣的家庭、在一個找尋自我的混沌下,他們提出對自我存在的質疑不正是我們所推崇的「自我省思」嗎?
//
就陽春菊的故事來說,若她沒有起疑、沒有試著跟父母聊起種族主義,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和解。所有的反問、解答、再反問看起來像是庸人自擾的蠢事,但人活著不就是不斷拋問題解決問題讓自己好過一些嗎?
謝謝端的這篇文章!
比较赞同@V6iE1S09oC4a0
很有意思,这篇文章的评论大都是在批判被收养的华裔孩子的做法、想法,或是对文章叙事表示不能接受。我能理解大家的质疑,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大家没有真的在美国生活过,大家的质疑还是站在一个纯粹抽象层面的想象和推理,对现实中美国语境下亚裔面对的尴尬处境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我自己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和白人、亚裔都有很多接触,关注美国种族问题,也和不少亚裔聊过身份认同,我觉得还是很理解文中的几位被收养者的。以下是我抛砖引玉,希望其他有相关经验的读者也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大家可能对美国抱有某种善意的想象,觉得美国文化就是无所不包的“世界性文化”,华裔没必要在其中强调自己的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毫无疑问,美国文化在有些方面有比较强的包容性,甚至采纳很多外来元素(比如现在流行挪用东方神秘主义),但美国主流白人总是毫不犹豫地将美国社会文化核心识别成“欧裔白人的西方文化”。白人对自己的种族-文化身份的优越感是很强的(大多数政治上主张种族平等的liberal美国白人也免不了如此,不过表现上有所不同)。一个亚裔在其中必然是感觉困惑的,当周围人把自己作为伟大的西方文明的继承人而自鸣得意的时候,亚裔到底是该怎么自处呢?是应该加入他们?但是我并不是什么有基督教信仰的白人后代啊?如果只是单纯地附着于美国主流文化,是绝对无法摆脱一种次等感和不和谐感的。
第二,在这种环境下,当代美国主流只有两种种族政治,第一种是conservative,就单纯认为白人文化高于其他族裔;第二种是如今声势越来越大的liberal,就是鼓励多元族裔的文化。美国liberal主流应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方法就是鼓励少数族裔去认同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强调差异。所以文中这些华裔选择这一策略也是自然的。再说一遍,评论者诸君可能认为美国是已经高度实现去种族化的文化大熔炉,实际上这个熔炉最多只是欧裔白人间的熔炉(祖先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白人过了几代一般确实就没什么区别了),少数族裔则是要么选择被这熔炉熔进主流的白人文化,要么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很遗憾的,当代还并不存在一个去种族化的主流文化氛围。
第三点,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形成的自我文化认同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他们祖先的那个文化。诚然,如有位评论者所说,中国及东亚不同地方年夜饭差别就很大,被收养者搞的年夜饭多半不是其生父母地方传统的年夜饭。讲得不好听一点,在土生土长的东亚人眼里,这些美国亚裔的东亚认同会像是一种cosplay。但是需要知道的是,他们既然生长在美国,根本就没机会知道原汁原味的故乡文化是什么样的。他们只能通过他们有限的、选择性的接触拼凑出一种“东亚想象”或是“中国想象”。但是这种想象虽然可能和真实的祖籍文化大相径庭,却能在我上述的美国种族文化的大氛围中让他们获得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身份认同、一种自信和自尊,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
阳春菊成长在一个经常反思的文明中,所以我认为她在文化上的追求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她和领养她的家人不断反思后的结果。
不同的文化只是有不同的风俗和习惯而已。
代入时代背景,阳春菊的养父母既是移民、又是他们那一代族裔的主流,所以他们既能理解身为移民的杂感,又不可避免的在面对不熟悉的文化时,会有轻视、忽略的举动,同时还带有大国沙文的习惯。但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每个地方都会出现的。对中国来说几十年前,大家对一个异乡人或异乡群体的看法难道不是类似的吗?对其口音、风俗、习惯的嘲笑、轻视,我想这个比方会更易让人理解阳春菊她们这代人面临的处境。
尽管,阳春菊同内心矛盾自洽的方式,局外人来看实在是通过最进步的思考达成了最纯粹的退步结论:一个从来没接触过亚洲文化和语言的人,却因为外貌的差距认同为了亚洲人,并找到了进步的理论武器批判自己的父母,也就是说这个进步案例中的进步人回到了种族主义的出发点:种族完全是一种生理种族。
但她是如何堕入这个陷阱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她宁愿陷入困境也要找到答案,我想是需要进一步需要探究的事。
总而言之,我自己能够理解阳春菊对文化上的追求,也并不觉得她有想跳出所处的文明,或许她的思维上有缺陷,方式上有局限,但不得不承认她的努力对其他人是有启发性的。
有关女性弃婴的背景,可以参考电影One Child Nation
多亏了这些好心的人,让她们成长得如此自信且美丽!感恩
文章並沒有說的很清楚,不過看描述陽春菊的父母並沒有只是說說,從小到大都主動送亞裔女兒去接觸參與各種活動;我覺得這跟女兒成年後轉貼網路文章給父母、父母去幫忙採買文內食材差不多程度,只是成年女兒能精準地提出想要的。也不禁想:別說是一般喜好了,這種事情要求不同文化圈的人也得要有同等興趣與參與深度是否太強人所難。
整篇文章讓我覺得不太舒服,也是因為覺得處處都能嗅到一切種族本位的氣味;純粹以種族作為文化認同是個人選擇,但許多描述令人懷疑看待其他族群似乎也是這樣的定義
穿什麼服裝、什麼化妝風格是美的、甚至自己喜不喜歡遊戲與戀愛,都歸以種族劃分;也不如非領養家庭的美籍亞裔有成長於亞洲文化家庭的背景與隨之而來產生和美國社會/原生家庭的摩擦,這種飄在雲上的限定「亞裔榜樣」的需求意義難道也只是基於其種族外貌而已?
不免感覺文章談論對「東亞人」的取用與理解更像是一種純粹服務自身需求的愛好興趣…
@c_c
父母的配合,有點像子女渴求認同時,希望父母參與表達對子女的重視,而不是說說而已,這種脈絡就不會令人感到困惑了。
####
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是,當陽春菊認為白人母親閱讀白人特權相關書感到被冒犯,她指出白人家長很難面對自己本身固有的偏見和根植於心的種族歧視,所以不滿意父母「我們不把你看成亞裔,我們只把你看成我們的女兒。」回應。
這不也是對白人父母非同族產生的本身固有偏見及根植於心的種族歧視嗎?(因為父母不是亞裔所以跳躍認為無法同理的他者歧視)
說實在我會傾向是否父母本身與子女的溝通已有其他問題,否則過度投射不被同理到種族因素,可能太表面了。
“從小到大,她都覺得孤單”這句話應是全文的開端。有的小朋友個性會比較敏感,會放大自己與周圍人的差異性,强化自己“與他人存有隔閡”的印象,然後進一步將自己孤立出去。孤立時,試圖以再審視自己的差異性來進一步尋找原因,結果即是陷入一種惡性的循環之中。作爲家長,理應將其從這種自我懷疑中拖拽出來,而非送她去什麽强化差異性的“學習文化課程”。
多謝你們的努力。
被遺棄的都是女娃? 難怪留下來的男娃現在都娶不到老婆
文章有些部分好令人感到困惑,父母即使以行動支持兒女去尋找不同的文化認同,自己也必需一起配合才行嗎?(又,反過來的話呢)
即便是亞裔美國人與東亞(韓國kpop)的化妝風格差異也很大,更多的是恐怕是基於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審美觀而不是膚色五官特質的差異;又比方說年夜飯——不同地方年夜飯的異質性也很大,文章介紹的傳統年夜飯內容會是其生父生母的傳統嗎
文化認同何以等同於血緣主義,即便當事人根本從來未曾經歷這樣的文化生活、可能也極不了解?文中相同被領養的哥哥就沒有選擇基於血緣的文化認同,不知道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越看越感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认同”不过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动。若白人种族主义没有造成大问题就消失了,出于危机下的对抗意识的少数族裔认同也会自行消灭。
都是女生,哎中国的性别歧视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