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新聞上看見台北電影節的新聞,年度極受矚目的《范保德》拿下三獎,雷光夏憑藉着本片,上台領取「最佳電影配樂」。
作爲一個樂迷與朋友,實在很替光夏開心,畢竟,她從來是低調的創作人,或許,有那麼點太低調了。
儘管低調,一想到雷光夏的音樂與人,千言萬語,還真難簡單起頭介紹。她是90年代一批開疆闢土的重要女性創作者之一,是電子音樂的行家,有古典鋼琴與爵士樂的底蘊,也是在民謠裏吟唱的詩人。她的音樂總有着極佳的旋律,同時不斷破格而出。實驗與純粹,在她身上,總能有着最幽玄的光。
上過幾次她所主持的節目(台北愛樂電台「聲音紡織機」,每週日下午三點到五點,幾乎全勤直播),當然會覺得她的品味,做起什麼來都沒有問題吧。然而做為朋友,亦然深知光夏對於每一份工作,都有着苛刻的自我要求。
這些年來,作為一個配樂工作者,雷光夏與電影之間的關聯已經很明確,卻鮮少讀到有訪問,能夠邀得深談。那天,下了「聲音紡織機」廣播節目,我突然跟光夏提:我們來做個訪問吧,從《范保德》開始聊聊⋯⋯那時,還沒得台北電影節的獎項,可在我心中,能夠請她把心中的秘密與想法袒露出來,比起什麼獎項,都來得有意義。
光夏大概想了一週,答應我。我們於是有了這場回顧,一方面端詳重量級電影配樂工作者的心情,另一方面,也窺探了一部分珍貴的台灣電影配樂史。
端=端傳媒
雷=雷光夏
合作的對象大部分是朋友
端:像妳這樣的工作者,多數時候機會是怎麼來的?接案子的時候,妳會考量哪些事情?
雷:大部分,老實說,都是認識的朋友。比方說蕭雅全導演,侯導拍《海上花》時,他是副導,我寫主題曲,當時並未相識,而是幾年後做廣告片才認識的。有很多狀況裏,是對方聽到了我的作品,無論是專輯、電影配樂,也包括一些純音樂的作品,他們聽到了,很喜歡,就來找我。
有一次,很有趣,我太久沒出門,決定去一個朋友辦的聚會透透氣,結果初見面的一位監製直接拿着劇本問我意願,也有這種例子。
如果談到林強第一次找我,那更是完全不認識,我們都是透過作品去溝通。
端:林強找妳,那時是做《南國再見,南國》⋯⋯
雷:對,是我第一次認識他。那個時候我發專輯,他可能聽到了我的音樂,就透過唱片公司來找我。他問我有沒有還沒發佈的歌曲,我就給了兩首,最後都用上了。但是,我其實並不知道,他會怎麼樣在電影裏使用這種歌曲,我猜想應該是林強把歌曲搜集好,給廖桑(編按:廖慶松,知名剪接師)看怎麼樣適合。
端:兩首歌曲,都用得很好,現在還是覺得,那張歌曲原聲帶很棒。
雷:現在看很多電影裏,都是這樣使用音樂的:使用已經有的作品,放在對比感很強烈的場面。當時的實驗,算是很成功的。
林強有跟我說,他找我時還以為我是男生,他大概以為,在這張原聲帶裏,自己找了一票流氓般的男生吧!後來廖桑跟我說,當他們把〈小鎮的海〉放在高捷、林強和伊能靜在山路那段,簡直覺得不可思議,彷彿音樂就是為了那一幕而生。高捷跟女朋友談話那一段則是〈老夏天〉,原來流氓也可以那麼「文青」吧。
目前都是靠緣分⋯⋯但畢竟如你所說,我不是一個大量生產的作者,我更期待自己能被不同的電影開發,那樣可以學到更多,感受自己無窮的潛力。就像當時在「南國」裏,對於〈小鎮的海〉這首歌,竟能被用得這麼驚悚,充滿暴力的隱喻,實在讓我感到驚奇。
最近我跟朋友王登鈺合作動畫短片,是超級黑暗的一部片,很科幻,影像風格很強烈,我們倆合作起來,非常開心:能夠透過影片這樣的載體,被發掘自己的黑暗面。有一部分的我,其實非常喜歡《異形》、喜歡未來世界、科幻⋯⋯只是,多數時候,那並不是我給別人的印象。所以,這樣的合作,讓我自己能有機會被影片引導,激發與醞釀。
特別不好的電影音樂才會讓人察覺
端:有沒有曾經看哪一部片,特別覺得,對畫面非常有想法,也想要嘗試替這樣的影像來配樂?
雷:通常看電影時,就是沉浸其中,除非那配樂做得特別不好,否則不會有覺察,就是沉浸於電影中。
倒是有些導演或者作品,自己特別喜歡的,很吸引我的,會讓我去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
會吸引我的,是「不只是把配樂當音樂」,而是把聲音一起都考量進去的導演。當然,很多時候,配樂作品是從音效設計、音樂跟導演三個方面充分合作而得來的。
當然一定得提到最經典的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他的電影裏,幾乎沒有配樂,都是用所謂現實中的聲響,可以放大火的聲音,可以放大水滴的聲音,是用這種方式去呈現聲音、視覺、旋律跟語言⋯⋯
比方說,在《鄉愁》(Nostalghia)裏,其中的角色搬了一台唱機放貝多芬「合唱」的同時,自己身上澆了汽油自焚;又比方說《犧牲》中,在男主角燒房子之前,先放唱片,有日本樂器尺八交錯其中,大火反而變成是暫時無聲的。音樂不只是為效果與情境,配樂當然有其服務的功能,但更可以是在音樂上整體的思考。
《絕美之城》(La grande bellezza)與《年輕氣盛》(La giovinezza)的導演 Paolo Sorrentino,也蠻會用音樂的;未必是原創的音樂或歌曲,也會找一些素材,也擅長做對比感的配樂,這真是有想過後,才會有的事情。類似這種情境,就會想到自己是不是也來嘗試做些什麼呢?
每個人做音樂的啟蒙都不一樣,對我來說,電影配樂啟發了我做音樂的想法,從高中時就一直在聽,不斷的聽,那是已經成為底蘊,直接影響了我做所有音樂的過程。
愛上電子合成樂的過程
端:在過去的報導裏您曾提到,當初聽到《俘虜》(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決定要以合成器作為配樂的方向。這些年來,也嘗試了真實樂器與合成器的交融,到目前為止的配樂生涯裏,真實樂器的使用與合成器的使用,對妳而言,有產生什麼新的想法與感受嗎?
雷:在看到電影《俘虜》之前,就很喜歡電子合成器。《俘虜》是我十幾歲看的片子,可是在十歲以前,我的父親(編按:作家雷驤)跟張照堂、杜可風、阮義忠等人做過一系列的《映像之旅》,是很早期台灣的藝術性紀錄片;那個時代沒有版權問題,這幾個人都會互相丟一些音樂作為配樂的參考,比方說 Mike Oldfiled、Vangelis 等等,這些音樂讓我第一次認知到,這叫做電子合成樂。
回想起來,去看《俘虜》,是很新潮,很帥的經驗,有大衛鮑伊,有坂本龍一,導演是大島渚,有同志的議題⋯⋯後來才知道,原來配樂也是出自坂本龍一。
再後來,看他的訪談,原來他覺得自己當時並不是真的在根據電影「配」音樂,而是把自己的音樂作品有點強加上去,就像「貼」在電影上一樣,他認為當時的自己並不是個好的「配樂家」。但也許反而正因為如此,這配樂的獨立性強,敘事性強。電影只能去電影院看,但配樂可以在家一聽再聽。我就在自己那台合成鍵盤上抓類似的音色跟和弦,青少年時候,就想,要是有一台坂本龍一使用的電子樂器,該有多好。
考上大學,我獲得了一台新的鍵盤,是真的能夠進行取樣的樂器。當時也還不是用 DX-7那種有既定可選取的音效,而是卡西歐出的 Sampler FZ-1,必須把聲音素材錄好存進去⋯⋯
那時也拜訪了郭巍,他是很早期就在做電子音樂的編曲大師。我去了他的工作室,就一台鍵盤,一束光從天花板透進來,照在那台鍵盤上⋯⋯想起來真是非常令人激動。
這些都會是素材,在畫布上塗上什麼顏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完整度。
在年輕時,合成器音色前衛的吸引與可能性,與取得的方便性,這是最有效率,也最能刺激我的部分。
雖然我是學鋼琴的,家裏也聽古典音樂,但是我當時沒有真心愛上古典音樂,對過去的我而言,那是老的,是大人的聲音。直到到了台北愛樂電台工作,每天要聽超過三到四個小時的古典音樂,才聽見所有演奏的細節,樂器的比配與延展。每天聽,就開始有了些想像。
後來我也在唱片裏開始採用真實樂器。比方說,陳主惠是這麼優秀的一位樂手,那時候我聽了葉樹茵的〈傷心無話〉,就好想要找她合作,那是在〈原諒〉裏面發生的事情。她的弦樂層次好像撒過一道光,此後,對真實樂器,我開始產生了憧憬。
很多人做音樂到了後來,會獨尊真實樂器,這對我而言並不是必要的。我不介意這個樂器長什麼樣子,只要他的靈魂符合我所要的整體。在素材添加或刪減的過程中,這些其實是比較技術層面的考量。
關於《范保德》
端:無論是歌曲被收錄,或者自己擔綱製作,電影配樂當然已經成為妳的代表象徵之一,有沒有自己特別滿意的作品呢?
雷:我想,一部都要比一部更進步,最好的東西一定是剛完成的。
現在剛完成了《范保德》,是竭盡兩三年來時間跟力氣,非常艱困而糾結的過程,別人可能看不出來,但幾乎算是咬着牙生出來的。

從劇本發想,我們就開始生東西給導演,後來,導演算了一算,我們給了他六十首,六十首!你看一部電影的過程生出了六十首歌曲⋯⋯
導演越是暗示與鼓勵,自己會想要激發更多,可是期間,家裏也發生一些私事,一切都像匍匐前進,長達五年吧,心都懸在這個電影上面。
最後還是很感動,我還是把一個作品給完成了。不僅是配樂,作為完整的原聲帶,曲序和聲軌等等,甚至非常多細節的部分,都堅持到最後,盡了所有的心力。
導演給了我一個舞台,但要如何去達到平衡跟共識,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是不是我最喜歡的作品?這絕對是投入非常大心力的作品。
端:我揣想,妳做專輯的時候,一定是非常專注在自己的東西上面,跟他人合作會更輕鬆還是更難呢?
雷:創作上,讓別人一起參與,反而是更輕鬆的,當然如果我參與製作,那過程就不會是那麼輕鬆,但我是喜歡的。
在《第36個故事》找來的樂手們,在錄音室裏即興的部分就很出色。找樂手的過程一向都很有趣,除了之前的老搭檔侯志堅,這次也找了子豪跟小白老師⋯⋯
《范保德》使用的音色,弦樂是一個方向,畢竟是一個悲劇型態的作品。但本來沒有想到這麼「大」,後來因為有補助,整個資源來了,陣容就變得超級大。
在電影院裏觀賞,不可諱言,真的因為這樣的編制,加分很多。
大致上,跟別人合作,心情是輕鬆的。《范保德》的話,其實是我自己私底下的狀況不那麼的好⋯⋯
端:從點題的曲目〈深無情〉,弦樂的感覺慢慢地溢出來,蔓延出來,這首歌曲像是一個支點,可以談談這首歌曲在整個過程中裏的角色嗎?
雷:這部電影的劇情,有循環的概念,從一個微小的事情擴散開來。其中有一幕,在一個天井裏面,爸爸用水去沖天井的牆面,電影裏的音效是重製導演曾經聽到的聲音,因為太熱,水在牆上就有冒泡一般的聲音,這是現實中的聲音,我們則要用音樂去處理這樣的情境。
影片裏不斷引用羅大佑的〈未來主人翁〉,不斷重複,飄來飄去。所以,我一開始就決定做極限主義的風格。
我想,這部片音樂上不需要具備太多「主題」,樂念應該緊緊附着在一兩個主題上。
〈深無情〉裏,是走一個下行的音階,跟男主角的命運有關係,即將墜落,即將死亡,卻又能轉而再生。我於是想要把所有聲音扣緊這個旋律。例如在天井那一幕暗藏着音樂符號——原聲帶和電影中採用的版本不太一樣,在原聲帶裏才聽得到這樣清楚的下行「深無情」主題曲旋律,在電影裏,不會那麼清楚聽見,只會感覺熟悉的和弦一直走。確實在配樂裏,我想要扣緊一兩個專屬這個影片的主題。
這很有趣,我們時常在談風格,但風格不僅是靠直覺,要不斷想過,而不能是現在想要什麼就來一點,等等又來其他的風格⋯⋯這樣成不了整體。尤其就製作面向來說,思考所有元素與樂器,讓音樂的細節與靈魂呈現。所有支點或暗示,聲音維度等等,都要經過許多思考。
一切沒有白費
端:有時候,我聽了原聲帶,覺得太棒了,感覺反而沒那麼想看電影;心裏的畫面已經充滿了,這樣就夠了。電影配樂者的企圖心,會不會有可能壓過了導演的主題呢?或者應該說,有些配樂不那麼「適合」電影,卻很適合單獨來聽⋯⋯如果我們不討論好或不好,只是經驗分享的話,會不會真的有那麼一些配樂是如此奇特的存在?
雷:最近我一直在聽《霓裳魅影》(Phantom Tread)的原聲帶,實在是太喜歡了,到現在,我還不想看電影,雖然,有一天是一定要看的。
《星際效應》(Interstella)是有趣的例子,看片當天,因為時差,覺得很睏,真心覺得配樂好吵,當下真的認為,這配樂也太糟了吧。
這不只是我的想法,另外一個做音樂的朋友,也覺得配樂好不適合。可是,後來我單獨下載原聲帶來聽,實在是超喜歡的,是很優秀的音樂作品。
這個環節來看,我不知道是 Hans Zimmer 出了問題,還是電影院的音響出問題(笑)⋯⋯有些導演真的願意給配樂工作者很大的權力,去做很自我的嘗試,我想 Christopher Nolan 就是這樣的導演。
端:在電影配樂這件事情上,得獎對妳來說,心情是什麼?得獎還是⋯⋯不錯的吧?
雷:我那天好淡定啊。真的得獎時,沒有想到會有「啊,一切沒有白費」的心情。我朋友都說我上台領獎一副沒有準備好⋯⋯

我爸在我出門前祝我好運,說,「沒有準備感言嗎?就把北投快炒店的菜單拿去唸一唸吧!」
其實很珍惜。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份很大的榮耀。幸好在快要揭曉前,突然想,「如果得了要怎麼辦!」趕快想,趕快擠出一些東西來。
《第36個故事》在金馬獎獲得的最佳電影原創歌曲,那一屆,我知道林強會去,還跟林強說,「那如果得了,你幫我代領吧」,林強也答應了,是導演跟我說「不可以這樣子!」,我才去了典禮,還好有去。
端:這個問題來問妳特別有趣,因為妳對獎,真的沒企圖沒期待。
雷:對啊,真的是沒有準備⋯⋯
後來想想,得這個獎,就真是謝天謝地,我居然沒有死在配樂的過程中,然後還有獎金五萬塊⋯⋯
然而,同時又很清楚,自己在下一次的配樂裏,還是會賣命的,竭盡全力投入。這就是性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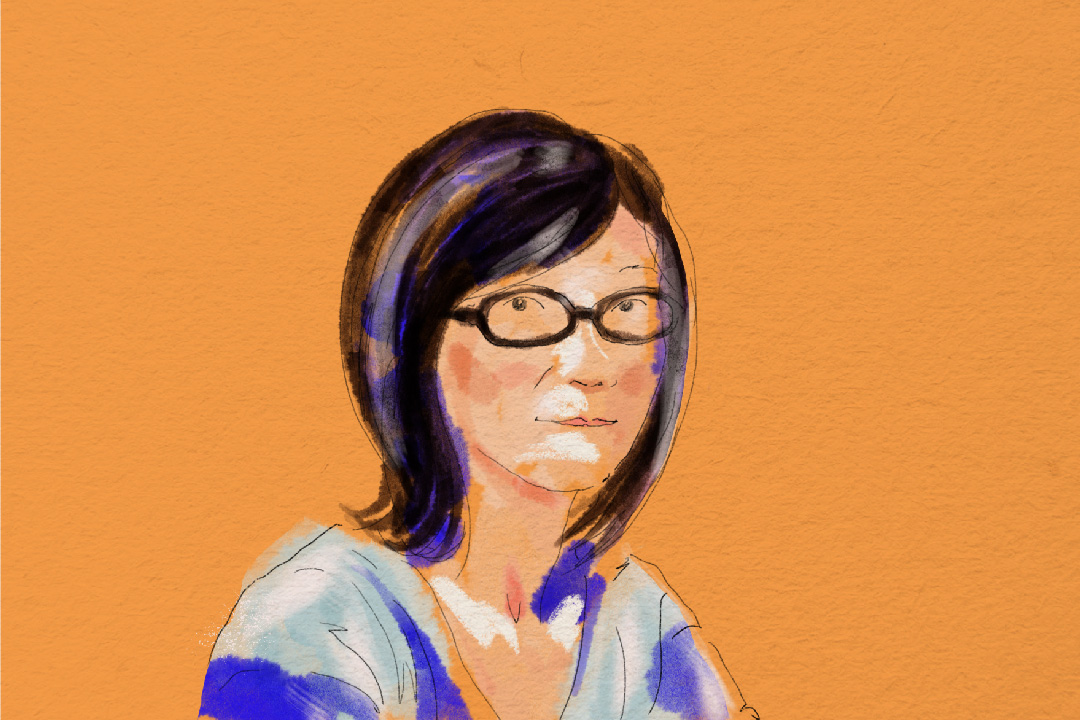




謝謝雷光夏的音樂陪我在看《范保德》時一起死了一輪,間又重生
電影配樂,近年最欣賞張經緯。
端好棒!採訪到雷光夏
范保德配樂真的很棒,霓裳魅影也是!!
雷爸好幽默啊,居然讓念快炒店菜單。(笑)
好喜歡范保德的音樂啊
雷光夏好可愛啊!靦腆中又帶有直率和堅持。作者開頭的介紹很貼切。
居然能採到雷光夏,有端真好
是「那時候」而非「那時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