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恐懼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憤怒,不是苦惱、失望或沮喪,而是真正的憤怒。
編者的話:這是托尼.朱特(Tony Judt)與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長談,在前者生命最後階段進行。二人同是西方學界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家,長談的內容則是20世紀歐洲歷史和政治。2012年,這場對話被結集成書《思慮20世紀》,其主題涵蓋了納粹大屠殺、猶太復國運動及歐美社會規劃⋯⋯這裡轉載的文章是朱特太太 Jennifer Homans 所寫,三輝圖書編輯潘夢琦翻譯。我們經譯者與三輝圖書授權編修轉載此文,譯者說:「在讀完朱特夫人的這篇文章後,我才知道《思慮20世紀》的成書過程遠比我想像得艱難。在生命逐漸流逝的日子裏,這本書對朱特的意義越發重要。這是留給家人的記憶,也是他留給世界的禮物。」而我們於此,則期冀這份禮物被更多人收下。

托尼.朱特:最後的勝利(節選)
文 / Jennifer Homans 譯 / Annie 潘夢琦
一
我嫁給了托尼.朱特。當他面臨 ALS(也稱盧.格裡克症,即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病痛困擾時,我們和兩個孩子在一起生活。從2008年他被診斷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這長達兩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難寫下三本書。在《沉痾遍地》(Ill Fares the Land)和《記憶小屋》(The Memory Chalet)之後,最後這本《思慮20世紀》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對話基礎上完成的。在確診後不久,托尼就開始着手這本書的工作;短短數月內他已四肢癱瘓,不得不使用呼吸機,但他依然勤奮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個月,他和蒂姆終於完成這本書。這本書伴隨他整個疾病過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思慮20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出版時間:2016年2月
出版社:三輝圖書 / 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 Tony Judt / [美] Timothy Snyde
譯者:蘇光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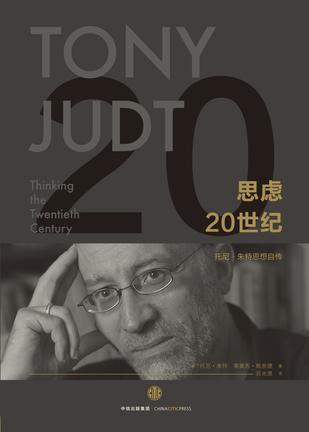
本書記錄了20世紀思想史,以托尼對猶太理想主義和猶太人在歐洲遭遇的反思為開端,以他對美國政治在後冷戰世界的失敗的驚人描述為結尾。我們也能勉強把本書看做一部精神自傳,說「勉強」是因為托尼幾乎不以第一人稱寫作,本書所有自傳性內容都是後來插入的——幾乎是不情願地——因為那些觀念、歷史、政治和倫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
這本書伴隨他整個疾病過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這並不意味着這本書沒有個人色彩。對托尼來說,觀念是某種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數人在乎悲傷或愛之類的情感。正如本書所展示的,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開端——甚至在生命開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親的表妹托妮(Toni),年輕的托妮在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慘遭殺害。長大後,他父親將自己對左翼政治和東歐歷史的熱愛傳給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歲生日禮物就是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傳(又譯「先知三部曲」,包括《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對他來說,觀念以及對歷史解釋的需要根深蒂固,貫穿着他的過去和這本《思慮20世紀》。
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覺得需要對這本書做些解釋——背景介紹或場景描述,因為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太灰暗了,正是這種灰暗造就了這本書的形式和內容。我對《思慮20世紀》有一些話要說,因此我寫了這篇文章,我相信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讀者知道的。
當托尼被診斷患有ALS時,他知道他很快就會死去。在所有醫生告訴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當我們嘗試了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案,他對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這一切,因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擴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盡,堅持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醫生每天都帶來壞消息,難以承受的結果接踵而至,這一切混雜着困惑、決心、怒氣、悲傷、絕望和愛。
二
《思慮20世紀》一直存在托尼的腦海中。在他剛剛生病的時候,他就開始着手20世紀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當他的同事和朋友,同為歷史學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對話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計畫中的書變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慮20世紀》。
連續幾月,蒂姆帶着他的錄音筆,每週來到我們家和托尼坐在客廳裏談話;他們會不知疲倦、沒有間斷地長談兩個小時。托尼不會提前準備,也不會做筆記。我們對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記得最清楚,托尼對事實和歷史的記憶尤其清晰。我經常在廚房聽他們的交談,每次都為托尼的廣博和宏大的視角而震驚,尤其當他談到世紀之交紛繁錯雜的政治、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起源和戰後右翼民主政治的命運時。我對托尼的淵博和自如的控制力習以為常;而現在,他毫無障礙,暢所欲言。
這是一次知識的洪流,所有他親身經歷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結合在一起。蒂姆堅持認為托尼不止是在「說」20世紀,更是把他自己放在這個時代背景裏。比如說,他們把猶太復國主義視為猶太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時刻,給予這場運動在整個歷史中應有的地位。同時,猶太復國主義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託,他再一次回顧了他曾對猶太復國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深深的熱忱,而他這段年輕時的經歷(在他加入基布茲[Kibbut,希伯來語,意指「聚集」,後引伸為集體社區。]並主動成為「六日戰爭」的志願翻譯之後)以及隨之而來的覺醒,使得他「得以辨認其他人身上同樣存在的狂熱、短視和狹隘的排外主義」。這段經歷也讓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紀意識形態的災難時多了一些歷史的同情。
連續幾月,蒂姆帶着他的錄音筆,每週來到我們家和托尼坐在客廳裏談話;他們會不知疲倦、沒有間斷地長談兩個小時。托尼不會提前準備,也不會做筆記。我們對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記得最清楚,托尼對事實和歷史的記憶尤其清晰。
對托尼來說,完成這本書的動機(必須是一個強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適和絕望的動機)主要是為了闡明思想史。蒂姆深知這一點,當他們的談話進入狀態的時候,托尼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飯、塗寫甚至呼吸,他的身體飽受癱瘓的苦痛;當他和蒂姆談話時,竭盡各種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尋回一些慰藉和欣喜。這其中有蒂姆的功勞,他的嚴謹,他的知識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個方面激發托尼做到最好。
在這個不合時宜的時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對思想的關注超過了任何事物,甚至超過了對朋友——以及某種意義上對他自己的關注。他真的相信,思想遠比他自己更重要。他無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當托尼病得越來越重,這本書的意義也就越來越大。他花了點時間回顧舊作,比如他在2003年寫的一篇關於以色列一國解決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堅持認為當代政治專家誤解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英國政治哲學及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和國家計畫的觀點,忽略了當時奧地利處於兩次戰爭之間的歷史背景,這導致了一個令人遺憾的後果,即「奧地利的經驗……被昇華成了一種經濟理論」並且「不僅影響了芝加哥經濟學派,也影響了當代美國有關公共決策的討論。」
三
正如他所說,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裏,人們承認自己無法預言遙遠的未來,但當下卻是實實在在的。我們也許不知道十年後的自己會變得如何,但多數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麼。對托尼來說,這一切突然顛倒了。未來——甚至是不久之後的未來——變得無比清晰:他將不久於人世。然而,現在卻變得不可預知。今天他的手臂還能動嗎?他還能呼吸嗎?
托尼腦內的計時器,這種令人不安的「紅移現象」(譯者注:紅移現象,最初是針對機械波而言的,即一個相對於觀察者運動着的物體離得越遠發出的聲音越渾厚,相反離得越近發出的聲音越尖細。)也改變了托尼的政治觀點。所有事情都變得緊急起來,當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寫作變得更加激進,我和他都認為《沉痾遍地》裏關於美國經濟增長不平等的論述,關於社會民主原則被普遍踐踏的觀點,以及其他論述,使這本書稱得上他個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思所著)。而在《思慮20世紀》中,托尼對正義的思考更加超前。本書涵蓋了一些其他東西,正義、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現在又多了一些別的思考,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恥辱、羞愧、恐懼、怒氣;但同時它們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們不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恥辱是其中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觸時,這種情感最為強烈。這其中許多人比托尼年輕,他們非常貧窮,沒有醫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需要實際的社會和醫療服務。恥辱是一種糟糕的情緒,但同時也是——或者說應該被視為——一種醜陋的社會現實。他的文章〈夜〉(譯者注:本文收錄於《記憶小屋》)中寫道的這種「無法被假釋的監禁」部分是為了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思慮20世紀》——托尼盡力攀登的高峰——的終點,為了我們能夠「思考社會」——使人們不再僅僅考量社會政策的財政效益。但這並非殘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這是共同的責任以及我們每個人對彼此的義務。
本書涵蓋了一些其他東西,正義、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現在又多了一些別的思考,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恥辱、羞愧、恐懼、怒氣;但同時它們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們不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當他快要完成這本書的時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於呼吸道問題和注射嗎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時間有限而無法預知。疾病對托尼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樣痛苦的還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發生了任何讓他對世界更加憂慮的事情,他幾乎難以承受,隨時可能離去。
就拿他在這本書最後對我們時代——「恐懼的時代」——的討論來說。對失業的恐懼,對失去養老金的恐懼,對經濟衰退的恐懼,對可能出現投下炸彈的陌生人的恐懼——政府無法再掌控我們居住的環境,我們對此深感恐懼。這種恐懼不能讓我們變成一個以一己之力對抗全世界的孤立團體,這樣一切都會失控。我想美國人深知這種無能力為的恐懼,當他們意識到曾經遠離恐怖主義的人身安全不再時,恐懼感被加強了。
對恐懼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憤怒,不是苦惱、失望或沮喪,而是真正的憤怒。恐懼是一種終極的情緒,托尼一直與之相隨:恐懼自己無助地倒在堅硬的水泥地上;恐懼呼吸機突然失靈(如果真的發生了,在那之後還是會恐懼再次發生);恐懼被陌生人把導管塞進鼻子和喉嚨(他一直希望是我來做這件事,即時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對死亡的長久的、無法忽視的恐懼。在托尼看來,對恐懼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樣,是最嚴重的道德濫用。
四
面對社會不公,托尼一直是一個坦率的批評者,如今他對此更是零容忍。但這並不意味着對折中解決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決方案也是一種解決方案——而是對政治欺騙和在智識上的不誠實的零容忍。某種意義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為什麼人們沒有更生氣呢?當然一些人確實發起反抗,托尼沒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原本是他最有興趣研究的問題。
這些並沒有使他成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至少他是這麼想的。他不喜歡這個詞語,在他看來,這恰好證明了試圖在學院和公共生活之間建立聯繫的學者的失敗。這種劃分意味着知識份子對原則的背棄(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後半生的職業生涯都試圖通過清晰的授課、思考和寫作來彌補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軍奮戰,而他關於如何成為一名知識份子的思考就根植於這種孤獨感中:遠離知識份子群體,堅守原則,不加入任何組織或派別,同時獨立地衡量某個事件或問題,實事求是,而不是根據任何宏大的藍圖(他支持對波士尼亞的干預,但反對出兵伊拉克)。
這種沒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識的寫作,在我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眾——托尼所面對公眾——出現在他的寫作中,說來有些矛盾,事實上公眾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獨立和思考的「場所」。
事實上,疾病給托尼帶來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當他口述《思慮20世紀》時,他失去了他的學生、他的教室、他的書桌、他的書本,他不能再到處旅行或散步。換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幫助他釐清思緒的地方。也許其中最嚴重的是,他失去了陣地:他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弱,對生命的實際存在感到疲憊不堪。寫作包含了身體的動作——通過筆、紙、鍵盤——將思想傳達到頁面;寫作是有韻律、感覺、姿勢和節奏的,這是一種身體的搏動。但是托尼已經失去了寫作能力,或者說被嚴重削弱了,這種迷失感原始而深切。
如果沒有疾病,一切又會如何?這種沒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識的寫作,在我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眾——托尼所面對公眾——出現在他的寫作中,說來有些矛盾,事實上公眾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獨立和思考的「場所」。他確實在公眾場合中「自言自語」,他聽見自己的聲音通過郵件、採訪、博客等電子形式不斷迴響,繼以評估它們的影響。他借此融入這些場所,指導這些人們。「他們」成為他的學生和同事,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過讚美,而是通過爭論。
這很重要,因為公眾構成了他的寫作場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鋒物件——這才是他最終的對手。讓疾病、命運、身軀、過去和未來都見鬼去吧。托尼可以讓對話一直進行下去,不斷增加論辯的難度;他面對的公眾會回擊——當你在戰鬥時,你才感覺自己是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讓對話進行下去,這就是為何他堅持完成《思慮20世紀》的理由,這本書是戰鬥的一部分,從他對支持伊拉克戰爭的知識份子的猛烈批評,到他充滿先見之明地捍衛國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紀律,即時他在戰鬥時處境險惡,他依然堅持下去,說出那些必須說的話,精煉和打磨每一個字。這才是他唯一認可的公共知識份子。
英文原文於2012年3月22日刊在《紐約書評》,題為 Tony Judt: A Final Victory。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