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春期間,除忙着走春拜年、與親朋好友共聚天倫之外,也是空閒下來與自己對話的好時機。面對紛繁世態,每天都要作出不同的選擇,決定自己所走的再一步。在一年之初,作家李靜睿與我們分享了他在2016年所閱讀的書目,以書來討論基於人性與社會語境下,人如何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選擇?也許是迫不得己,也許是受社會氛圍所影響。當下的每一個抉擇也如雪球積累成現在,以及未來。
傳統習俗中的年初二是新春的「開年」,是諸神歸位的日子,故有重新啟動的意思。就在這一天,我們讀着這張書單的書,重新審視過去,更有意識地作以後每一個會影響人生走向的選擇。

1 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Hannah Arendt
譯者: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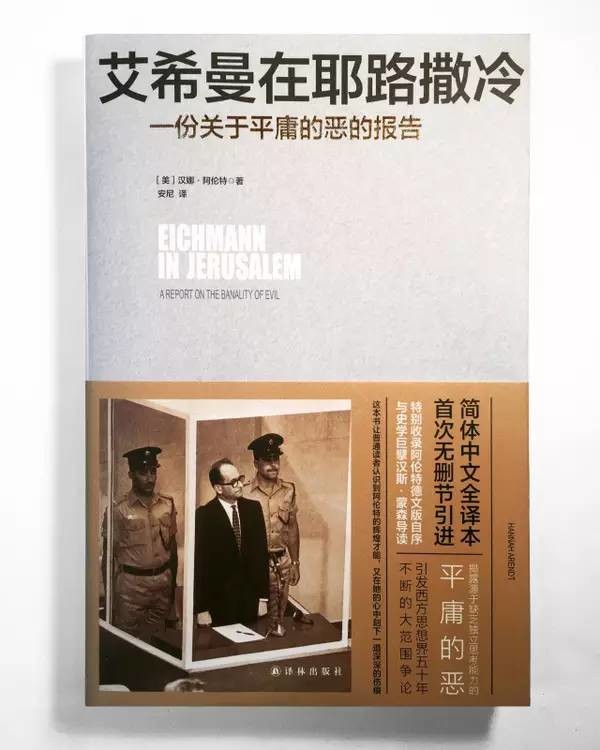
「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早已被人熟知,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又譯漢娜.鄂蘭)這本書其實今年才出簡體中文全版,它與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一起,展示了理性和職責能造就何等超越人性的災難。
法庭之上的艾希曼給阿倫特的第一印象讓人訝異,「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也不是難以理解的」。總而言之,在阿倫特看來,身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以冰冷縝密的計畫將幾百萬猶太人送入毒氣室,艾希曼卻不過是一個正常人類。正如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結尾處所說:「在一個理性與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邪惡巴望着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不會輕率、鹵莽地行事——反抗邪惡是輕率而鹵莽的——它就可以開展它骯髒的工作。」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發表之後,阿倫特一直飽受質疑,猶太人普遍認為她是在為艾希曼不折不扣的反人類罪行開脫,也不斷有新證據表明,艾希曼並非納粹體制中一顆混混沌沌的螺絲釘,而是主動影響和參與了希特拉的種族滅絕戰略。但不管如何,阿倫特創造了一個偉大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並非「艾希曼」式的官員,在半個世紀之後,「平庸的惡」依然具有其持久獨特的生命力,希望更多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借此審視自己的生活,以及這些生活疊加在一起,所造就的制度和命運。
2 所羅門.沃爾科夫《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出版時間:2015年11月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Dmitri·Shostakovich口述、Solomon Volkov整理
譯者:葉琼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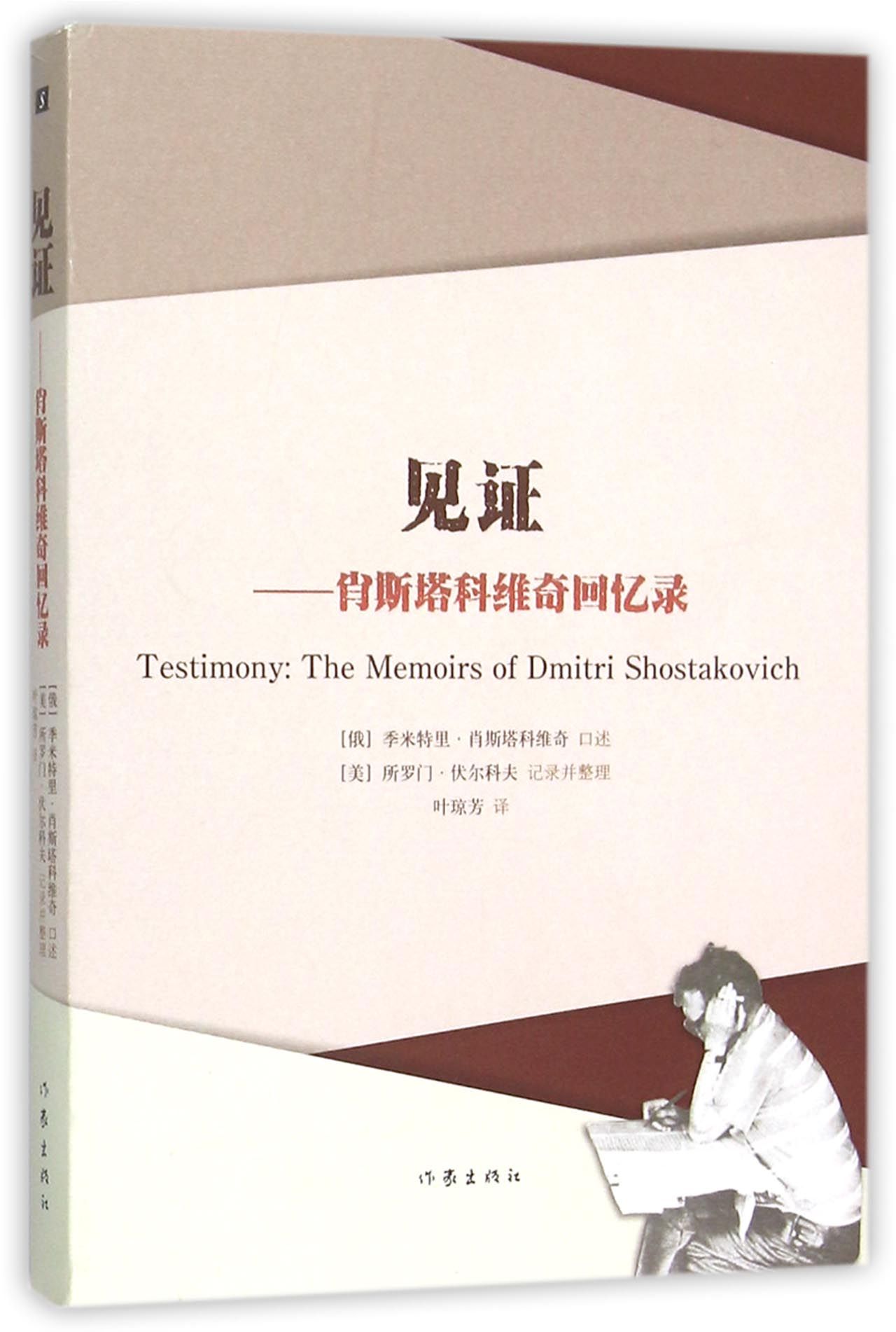
讀這本書是因為我很喜歡的英國作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今年出版了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蘇聯時期俄國作曲家)的傳記小說《時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而《見證》是巴恩斯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見證》出版於1979年,據說是肖斯塔科維奇1971年至1972年的口述,整理者所羅門.沃爾科夫(Solomon Volkov)也是《布羅茨基談話錄》的作者之一(編注︰另一位作者是俄裔美籍詩人Joseph Brodsky)。1976年他移民美國,肖斯塔科維奇則死於1975年。這本書一直有諸多爭議,但巴恩斯認為書中的肖斯塔科維奇有很大的真實性,無論如何,它寫出了極權政體之下天才藝術家的悲劇——曼德爾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蘇聯詩人與評論家)是慘劇,肖斯塔科維奇則是悲劇。沃爾科夫在引言中說,「二十年代後期,真正的藝術家們與蘇維埃政府間的蜜月過去了。權力終於使出了它一貫的、必然的行徑:它要求屈從。要想得到青睞和任用,要想平靜的生活,就必須套上國家的籠套聽任驅策。」
肖斯塔科維奇認為《李爾王》(King Lear,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中的重要問題是李爾的幻想破滅,「不,不是破滅。破滅總是突如其來的,然後就過去了,那不能形成悲劇,也引不起興趣。但是,眼看着幻想慢慢地、逐漸地破碎——這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是痛苦的、令人心驚的過程」。在諸多蘇聯知識份子還處於倫理昏迷時,肖斯塔科維奇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預言,創作於1935年至1936年的《第四交響曲》被認為是他情感最激烈的作品,在首演前他自己決定取消演出,從此擱置了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蘇聯通過新憲法,而史太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是「適宜」的年代,史太林說生活將會變得更美好,肖斯塔科維奇卻創作出了悲劇色彩濃厚的《第四交響曲》。
很多人說,肖斯塔科維奇後來對蘇維埃政權的屈服讓人費解,他無法為史太林寫頌歌,卻確實為不少社會主義電影譜曲。沃爾科夫在和布羅茨基對話時,就說過他想不通為什麼1973年肖斯塔科維奇要在《真理報》上簽下反對薩哈羅夫的信件,因為這已經不是隨隨便便會丟腦袋的年代了,當局已經不能給他帶來什麼特別的損失,布羅茨基則說,我們討論的這個悲劇就是如此,「房頂業也不復存在,爐子卻仍然兀立着」。
制度可以輕易翻雲覆雨,人心卻不可以,習慣了活在恐懼之中的國民,會下意識低下頭來,迎合權力,普通人如是,天才亦如是。
3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罪與罰》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Fyodor Dostoyevsky
譯者:耿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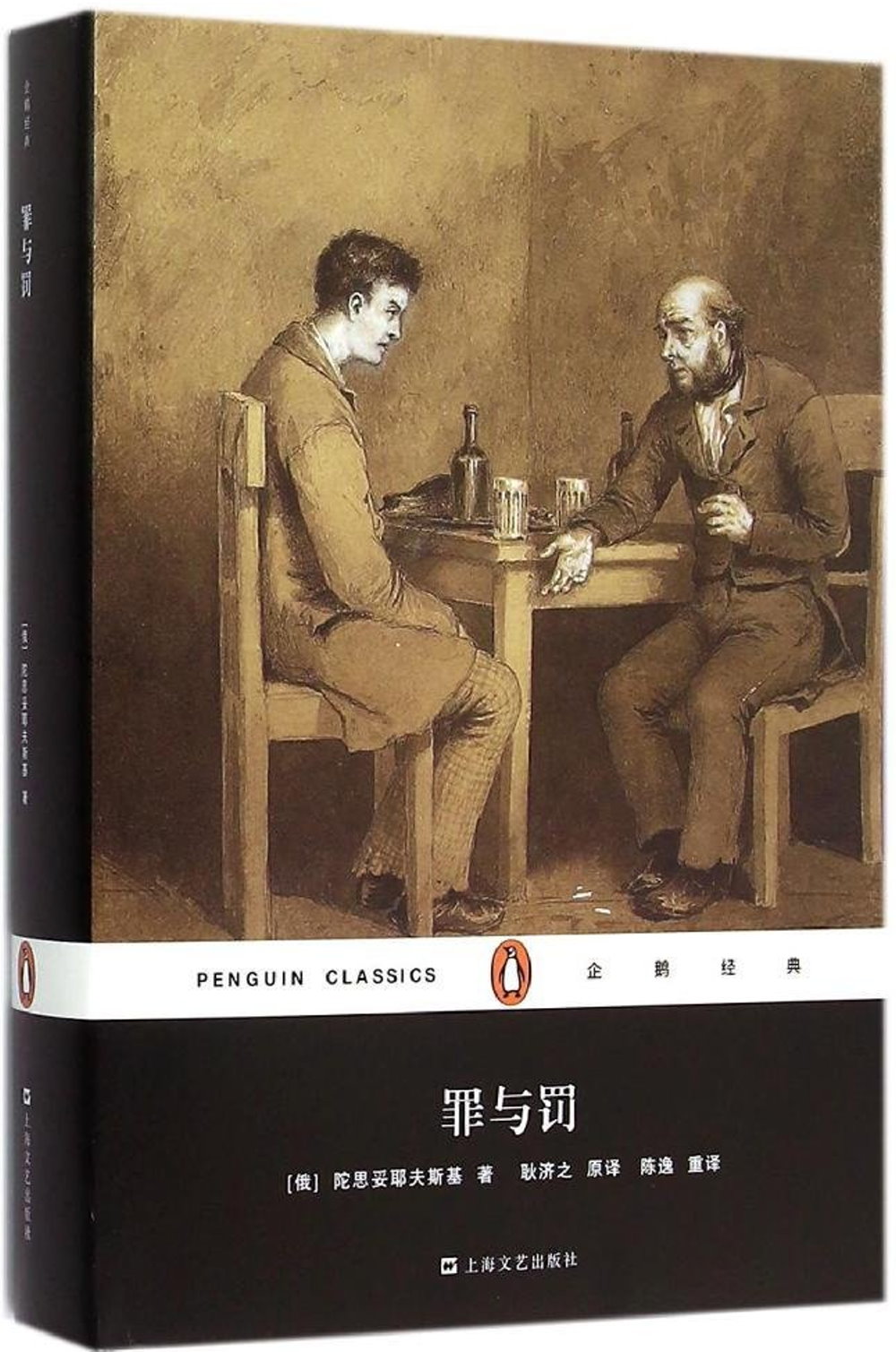
去年對雷洋案(編注︰發生在2016年5月7日的北京,疑因警方執法拘捕手段導致被捕人士雷洋死亡。)最憤怒時,我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又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順帶又重看了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賽末點》。
《賽末點》(Match Point,另譯《愛情決勝點》)開篇不久,網球教練克裡斯在自己租的倫敦小房子中,閱讀企鵝經典版的《罪與罰》,這一秒鐘預示了克裡斯的命運,他最終會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犯下謀殺,並且試圖掩蓋罪行。兩者的區別在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相信,罪惡會得到懲罰,如果不發生於外部,就會發生於內心。如果不是人間的律法,就將有上帝的審判,在謀殺真正發生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發現,「我殺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毀了,永遠地毀了……」
但在伍迪.艾倫這裏,罪惡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發生了,他們殺了人,後來卻都活得挺好,也看不出內心有何真正痛苦,時間稀釋一切,到最後,沒有他人知道的罪惡,終將等於從未發生,死去的人默默地死去,活着的人快樂地活着,罪惡變成虛幻,運氣替代道德,成為命運的最終答案。
半年過去,雷洋案已經塵埃落定,雙手沾血的人逃脫了命運和內心的雙重懲罰,大概正在慶幸於自己的好運氣,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並沒有《罪與罰》式的結局。
4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
《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
出版時間:2016年6月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作者:張灝
譯者:崔志海、葛夫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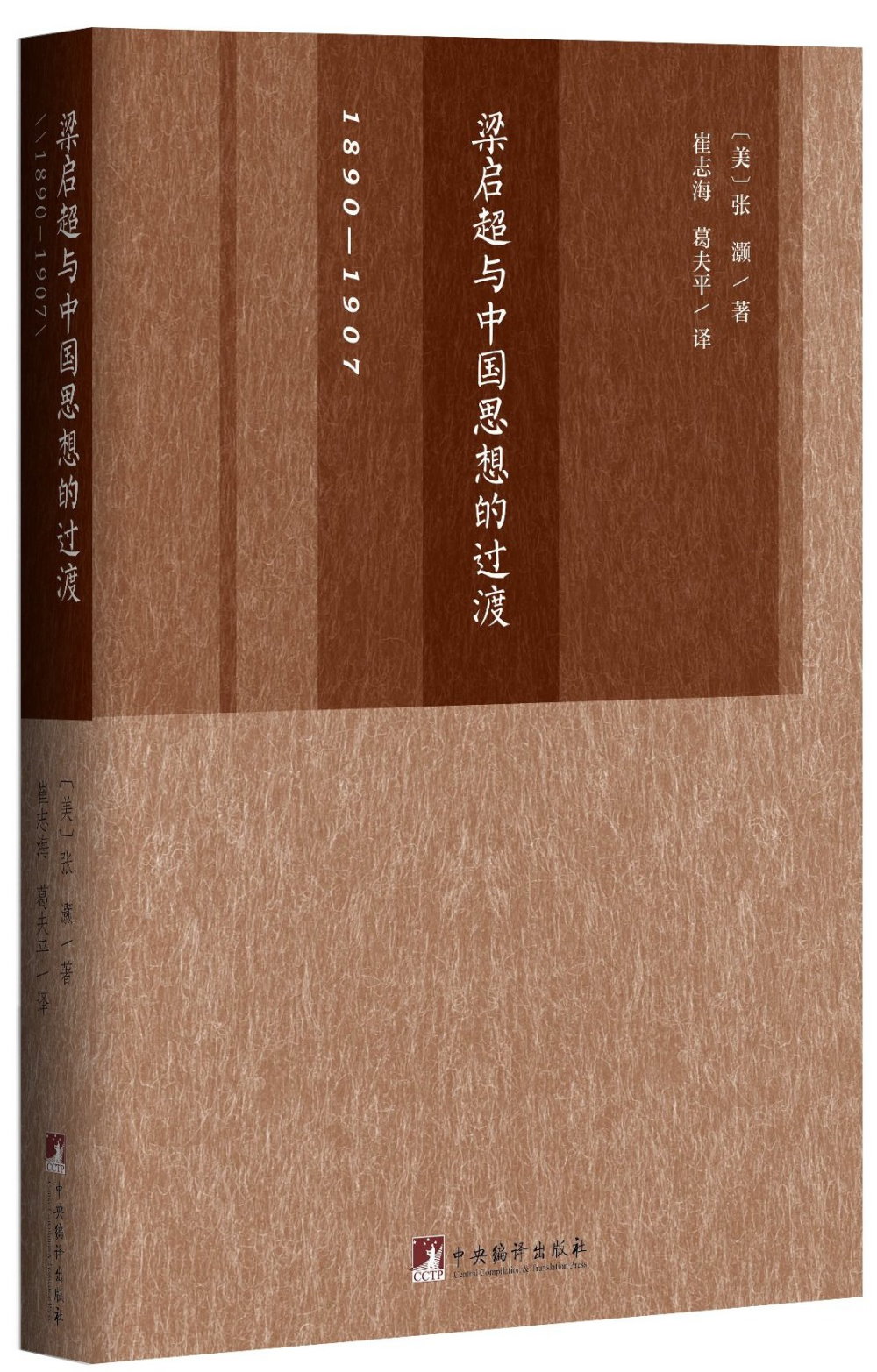
對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書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類似,都是能快速入門的梁啟超簡易讀本。
梁啟超早年支持君主立憲,但在革命已成定局後,又支持共和,反對冒然再改國體。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他同樣反復,變法失敗後他曾希望清廷能誅殺袁世凱,開放戊戌黨禁,但武昌舉事之後,袁世凱成為內閣總理大臣,他卻又稱應「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張灝的書中也寫到,雖然1900年漢口起義瓦解後,梁啟超就停止了與革命派合作的嘗試,但他在改良與革命這兩個問題上尚無定見,「就廣泛的社會目標和人格理想來說,他十分明確未來中國需要什麼,但在採取何種政治途徑實現這些目標的問題上,他依然猶豫不定。」
革命是那個時代的核心詞,但革命的涵義卻曖昧不明。書中寫到,梁啟超曾強調他所說的英文詞「革命」,真正的意思是「國民變革」,而不是「王朝革命」,然而在另外的文章中,在梁啟超又傾向於承認有暴力推翻政治現狀的必要,「所有這些自相矛盾的表述意味着這是一個複雜而難以決定的問題」。
這種態度,隱隱約約有點像幾十年後卡繆(Albert Camus),他身為左派,卻對共產主義蘇聯充滿懷疑,他是阿爾及利亞人,卻並未對法國的殖民行為進行直接批評,托尼.朱特(Tony Judt,英國歷史學家)說過,這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卡繆在個人知識、記憶和他對平等適用正義原則的追求之間真正陷入了進退維谷狀態,「知識份子的責任不在於採取一個立場,而在於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採取立場」。
5 卜正民《掙扎的帝國:元與明》
《掙扎的帝國︰元與明》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作者:Timothy Brook(主編)
譯者︰ 潘瑋琳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漢學家)主編的這套六卷本哈佛中國史,暫時唯讀了他寫的這本。卜正民是孔飛力(Phillp Kuhn)的學生,典型的西方漢學家,特別精細,習慣從小切口進入,他自己也說,元明卷與其他幾卷有一個顯著不同,因為他喜歡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本書認為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歷史中,對民眾生活經歷和政治時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因此在回答元明時期的許多歷史問題的時候,卜正民把整個世界的寒冷和乾燥程度都考慮進來。
作為外行,似乎很難接受這樣的闡釋框架,這本書和他另外一本《縱樂的困惑》一樣,細節充沛,但讀完和書名一樣困惑。明史似乎中國人最能接受的還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文字典雅,既吃透材料,又沒有被材料困住,既瞭解中國歷史的微妙之處,又能巧妙地用韋伯解釋中國官僚制度。
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通史,但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卜正民第一章寫「龍見」,即元明時民間對龍的記錄,因為就像威爾士(又譯威爾斯)的黑豹,無能為力的農民借由自然力量,「用以對抗難以捉摸的國家權力」。書中還說,朱元璋本想把中國變成一個道家的烏托邦,但後來淪為了法家的古拉格(GULAG的音譯,是前蘇聯政府的機構,管理全國的勞改營)。從來如此,幻想天堂的人手握權力,最終把所有人拽入地獄。
6 奧爾加‧格魯辛《排隊》
《排隊》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出版社:三輝圖書/漓江出版社
作者:Olga Grushin
譯者:翁海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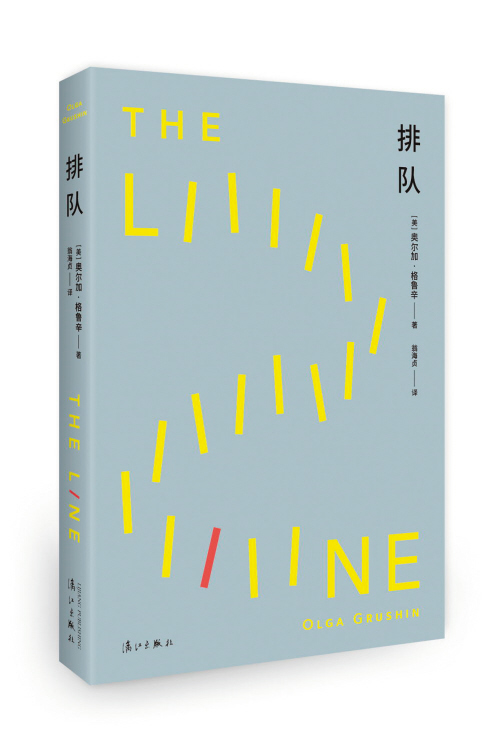
奧爾加.格魯辛(Olga Grushin,俄裔美籍作家)在《排隊》(The Line)最後的「史實記注」裏寫了這個故事的來源。1962年,著名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俄國作曲家)接受蘇聯的邀請,回到祖國訪問,他將在列寧格勒(Leningrad,十月革命的發生地)指揮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門票在演出前一年開售,購票過程演變為一種複雜而獨特的社會體系,人們相互協作,輪流排隊……《排隊》這部小說雖在整體上將蘇維埃俄羅斯虛構化,但最基本的思路來自這個歷史插曲。」
《排隊》糅合了史太林、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又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又譯布里茲涅夫)時代,最終把它變成了一個既卡夫卡又現實主義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售貨亭裏賣些什麼、什麼時候開始賣,但大家都默默排隊,渴望某種不確定的東西。到後來,演出的消息漸漸傳開,排隊成為所有人的執念,因為他們都以為這場音樂會能改變一點什麼,讓人在哪怕一瞬間掙脫這窒息的生活,「但是,不管我們怎麼對待時間,什麼也不會改變,你理解嗎?至少這裏的一切不會改變」。
在故事之外,改變最終還是發生了,1989年,奧爾加.格魯辛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去美國就讀本科課程的蘇聯學生,在她留學期間,蘇聯解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格魯辛說這讓她堅定要投身於寫作,因為「藝術超越政治」。在《排隊》的最後,音樂會被取消,但排隊再次開始,因為「據說」又有著名畫家的畫展要售票了,政治粉碎生活,藝術卻提供希望,虛幻的也沒有關係。
(李靜睿,資深法律記者與作家。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願你的道路漫長》和長篇小說《小鎮姑娘》。)




没想到在端也能看到她,我关注了她的公众号😄
對第一本書很感興趣,已收藏,謝謝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