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台北雙年展提供了近80組藝術家的作品,一時間難以清晰且全面地梳理脈絡。我們特地以兩篇文章分別描述和記敘。《2016年台北雙年展:台灣是一座共振體》是一篇索引;本篇則旨在從多位策展人的角度和經驗,談論台北雙年展20年來的定位,缺失,迷茫和未來,或可為觀眾展示雙年展某幾個層面的景觀。

走進這次台北雙年展,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顏色,燈光暗沉沉的,刻意壓低的色調,營造出一種理性且冷靜氛圍。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反覆思考着,為何策展人柯林.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在媒體導覽,講完第一個作品法國藝術家 Jean-Luc Mouléne《39 個罷工物件》就麥克風交給了美術館館長林平。或許就是她一再強調,展覽應該是留給作品和藝術家,讓他們自己說話,而不是策展人替他們發聲。
她(狄瑟涵)希望作品不是單一的命題式下產生呼應,而是在貫穿整個展覽之中,讓藝術品,或者是說藝術家如何用美學的姿態,將過去塵封的檔案,表現出來,不只是展示檔案,而是可以交織出「共鳴」。
以布魯塞爾為根據地的狄瑟涵是2016年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也是自1996年以來,台北雙年展轉型成為國際雙年展後,第一位獨挑大樑的女性策展人。這一次,狄瑟涵屏除了以往命題式的展覽方式,採用一個敘述性的文字做為展覽的標題「當下檔案・未來系譜 雙年展的新語」。這樣文謅謅、充滿學術性的標題,讓本質上不平易近人的雙年展,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相較於有明確命題的展覽,非命題的展覽,可以讓觀眾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藝術品中探索,去慢慢尋找作品的脈絡,從中整理出策展人想要表達的。同樣的,缺乏命題的展覽,觀眾需要具備相當的藝術鑑賞能力,或多或少去連結,主題和展覽之間的關係。這一次,策展人明確的表達,她希望作品不是單一的命題式下產生呼應,而是在貫穿整個展覽之中,讓藝術品,或者是說藝術家如何用美學的姿態,將過去塵封的檔案,表現出來,不只是展示檔案,而是可以交織出「共鳴」。
不過這種低聲迴盪的共鳴,有時容易成為獨自低喃,不容易輕易地發覺。舉例來說,像是入口處 Jean-Luc Moulène《39個罷工物件》的目錄成疊成堆放在走道上,供來訪的人拿取,即是可以和主題做起連結的作品之一。因為作品隨着展覽時間的遞遺,會慢慢地減少,型態因數量多寡而改變,檔案的圖片不只是停留在書本裏頭,而是跟着在不同的時空之中移動。展覽主視覺的西裝,便出自於其中,是當時抗爭期間員工製作的灰底西裝。
因此,我分別邀請了兩位策展人,一位是時任台北文化局長謝佩霓,以及有貼身採訪狄瑟涵經驗的關渡美術館策展人高森信男,來分享他們所感知的台北雙年展。
女性獨有的細膩,把策展人身份壓到最低
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也是前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的謝佩霓表示:「很久沒有這麼清新的展覽」,認為策展人很敏感的拾起了北美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現代主義建造的過往和氛圍,重新盤整,來回應有十屆歷史的台北雙年展,覺得該有的關鍵字都有,在視覺意象、氛圍、正反面並存。因此,在解讀策展人上頭,沒有問題,而且呼應着她過去在比利時求學和工作經驗,從感知到學術訓練的基礎,再到策展人訴說的方式,對她來說是非常類似的經驗,尤其從80年代末期到現在:「任何策展人一定會指涉某段自身的生命經驗,帶着先前集體的生活經驗,對生命經驗的投射,對未來盤整,對未來訴說什麼。」
尤其在布展的方式,策展人非常的貼心,有別於傳統的博物館藏寶盒的呈現方式,她採用框架式的方式,不是展示,而是讓作品本身作為事件來展示,擺盪虛實之間。
「很乾淨 – 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喧賓奪主,脈絡交織很清楚」,這是謝佩霓給這次雙年展的評語,尤其是低調和細膩的展覽方式,是給她最主要的印象。她覺得,尤其在布展的方式,策展人非常的貼心,有別於傳統的博物館藏寶盒的呈現方式,她採用框架式的方式,不是展示,而是讓作品本身作為事件來展示,擺盪虛實之間,讓塵封的樓梯再現,拿掉一些硬要封版,露出可以透光的窗戶。她回想起昔日的比國歲月,「對我而言,身為比利時生活經驗的共同擁有者,她的風景就是這樣子,灰色調,沒有強烈的陽光,沒有對比。」
她隨後舉了幾個關於比利時,或是法蘭德斯地區的美學特色,作為欣賞這次策展人的風格。她認為,相較於南方的文藝復興,北方的文藝復興是淡淡的,很細的,沒有仔細看,很容易就會錯過,因為是透過反射的,細膩的盤整、細節,訊息和所有的可能性,都偷偷暗暗地藏在這裏。她說:「她(狄瑟涵),不會讓你覺得是被排斥的,因為藝術家沒有處理好,是對立的。我想,她不是不願意談,而是很難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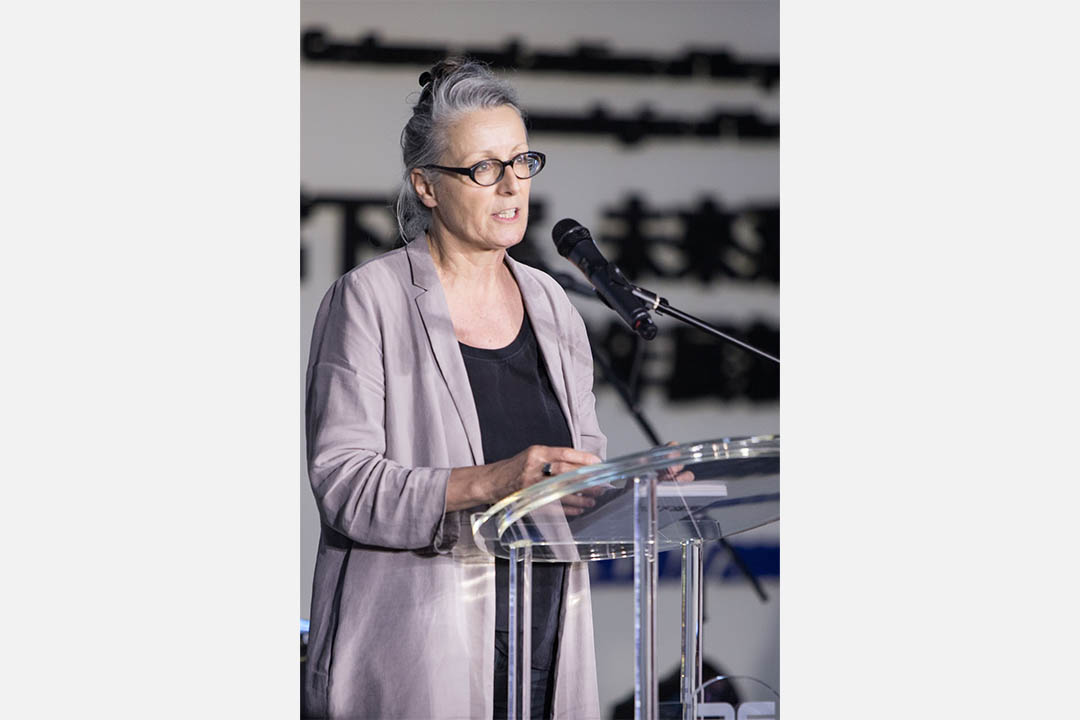
在展覽裏頭,狄瑟涵處理幾位過世藝術家的手法,即是讓人可以去馬上辨認、去感受那個藝術家好像是活着的,像是藝術家葉偉立經由拜訪已故的藝術家葉世強,創作出來攝影和裝置作品就能感受到,透過藝術家詮釋,從前藝術家的靈魂部分彷彿都被招喚回來,而且更為深刻。
關於「共鳴」這一件事,謝佩霓覺得,狄瑟涵並沒有把標語寫在上頭,然後註記一些概念性的主張,而是自然地邀請觀眾展場裏頭,招喚感知,而不是告誡般地說,要看到些時麼,或是要摸到些什麼。在展覽裏頭,狄瑟涵處理幾位過世藝術家的手法,即是讓人可以去馬上辨認、去感受那個藝術家好像是活着的,像是藝術家葉偉立經由拜訪已故的藝術家葉世強,創作出來攝影和裝置作品就能感受到,透過藝術家詮釋,從前藝術家的靈魂部分彷彿都被招喚回來,而且更為深刻。
缺乏視覺焦點的雙年展
身為少數有機會貼身採訪狄瑟涵的媒體之一,也是關渡美術館策展人的高森信男,他認為,雙年展的完成度可以再高一點。不過他也坦承,策展人強調的共振式的感覺,是透過談話之中,才更清晰一點,「我大概猜得到,應該說沒辦法去理解這個精確的詞。因為他展覽設計不是只有作品的展示、表演、電影、講座,感覺她是要組織一個社群的感覺。」
「我相信每次雙年展對一般人來說都很痛苦」高森信男笑着說。他認為雙年展在討論檔案這件事是可以看得見的,但是反檔案似乎就沒有那麼明確的討論。在他的理解之下「姿態」是藝術家個人,面對這個世界或是社會體制,所展現的藝術姿態,每個藝術家所採取的方法都不同,建議是要熟悉展覽中的藝術家,才能更明白姿態是什麼。他說:「這裏指的藝術性的姿態,比如說她長期合作的藝術家,南非種族隔離的歷史,或是黎巴嫩的恐怖攻擊,藝術家不適用直接去衝撞,血腥,而是用一種精巧、美學姿態的方式進到裏頭。」像是台灣藝術家陳界仁展出的《殘響世界》即是用這樣類似的手法來處理衝突。
在他的理解之下「姿態」是藝術家個人,面對這個世界或是社會體制,所展現的藝術姿態,每個藝術家所採取的方法都不同,建議是要熟悉展覽中的藝術家,才能更明白姿態是什麼。
在「反檔案」的手法上,高森在雙年展的脈絡之中,舉了2012年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策劃的《現代怪獸 / 想像的死而復生》為例,大量呈現檔案 ,再透過這些檔案,陳述歷史;狄瑟涵的做法,則是透過藝術性的作品,不做資料的呈現,「不是說不用檔案化,而是用檔案材料來做呈現」高森說,是一種看見過去,把歷史當作是參考資料,所展現的美學表現方式。
翻閱狄瑟涵過去的展覽紀錄,高森發現,她平常都以個展為主,這個應該是她策劃最多人的聯展,雙年展裏頭有幾個藝術家,都是她長期合作的,也許可以從這裏理出一些端倪,像是她長期在中東、巴爾幹、非洲這些錯綜複雜的領域,但很可惜在這次的雙年展沒有相當的呈現。其中,南非藝術家桑圖・莫佛肯(Santu Mofoken),則是讓他感到較為有印象且符合主題的作品,他說:「我喜歡她累積經驗的厚度和深度,相對是比較誠懇的表現,不是為了做展覽做了視覺上的奇觀,或是特別的展示方式。」
策展人反而讓過去雙年展視為最重要視覺印象的大廳,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空曠,讓台灣表演藝術家黃立慧,藉由撕下在大廳玻璃印上有歷史關係隔熱紙,產生殘膠和撕下來的貼紙的剩餘物,來回應她自身的經驗,以及北美館在地的歷史。
對整體雙年展而言,高森覺得,空間安排得較為零散了一點,大空間缺乏一個視覺焦點,尤其是在動線是否有軸心,不過他欣賞策展人對於小空間處理的能力,他表示:「看這次雙年展,說不出哪裏好,但又不致於印象深刻,視覺和設計沒有去創造一個給人一種較為鮮明的感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策展人反而讓過去雙年展視為最重要視覺印象的大廳,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空曠,讓台灣表演藝術家黃立慧,藉由撕下在大廳玻璃印上有歷史關係隔熱紙,產生殘膠和撕下來的貼紙的剩餘物,來回應她自身的經驗,以及北美館在地的歷史。
另外高森認為,台北雙年展還是有它的限制所在。尤其是找外國策展人,他們需要在短時間熟悉台灣的環境和北美館的體制。即便就要開幕了,他們也不一定熟悉東亞的藝術,「但是她選東西都蠻準確的,背後應該有人指點。」不過,從這一次雙年展的名單裏頭,會發現這是歷屆台灣藝術家參與最多的一次,狄瑟涵在這裏採取部分公開徵件的方式,來彌補她對台灣藝術家有限制的熟悉,尤其能在短時間看到這些東西,同時也讓機構有了開放性和實驗性。

20年過後,台北雙年展展望
說到對於台北雙年展未來的展望,謝佩霓和高森信男兩個人把持着不同的經驗,尤其是對於雙年展的策展人。回溯過去20年,從1998採用日本策展人南條史生後,便經歷了兩個階段,從雙策展人 – 外國策展人加上一個台灣的策展人,到2012年之後,採用單一策展人的制度,目前尚未有本土策展人獨挑大樑,策劃整個雙年展,這是爭議之所在。另外一個曖昧不明是雙年展的定位問題,是帶給台灣觀眾一個欣賞國際當代藝術的平台?還是讓台灣的藝術家能夠被國際看見?這都是多年以來尚未釐清的。
尤其面對雙年展的氾濫,謝佩霓表示很多雙年展有百分之99都沒有被提起,她反問我說,問題在哪裏?她說,「大部分是用本土策展人」她表示,國際策展人掌握着通路是其所在,她用飲料作為例子,表示「為什麼我們都熱愛的黑松沙士或是維他露P,這明明才真正是我們的最愛」,但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能夠這麼受歡迎,是因為它們有着廣大的國際通路。
她表示,台灣在當代藝術上頭,遠比其他亞洲國家成熟太多,除了日本以外,但是日本非常的保守。謝佩霓認為選擇策展人來自於那裏,是一種選擇,「要不要擁抱全世界?有沒有這樣的可能,你去擁抱我們台灣的策展人,看到反而是最不國際化的?換句話說,回過頭來,台灣在舞蹈、視覺藝術、音樂,真實地反映台灣的又有哪些國際人物呢?」她強調,這句話應該要放在讀者的心中。因為,台灣是國際化的,是自由的文化混種,所以是要扣住雙年展的模型,還是台灣的?對她而言,「我一輩子都在做展覽,身為一個策展人,我一直做的是國際風的呀!我不會為了台灣,做得很台灣。」所以她覺得策展人的國籍不是最重要,更進一步提出疑問:台灣雙年展有比較台灣嗎?還是根本不要策展人嗎?
另外一個曖昧不明是雙年展的定位問題,是帶給台灣觀眾一個欣賞國際當代藝術的平台?還是讓台灣的藝術家能夠被國際看見?這都是多年以來尚未釐清的。
高森信男則是覺得,外國策展人對於了解台灣的時間實在是有限,而且他指出先前的雙策展人制,就很像雙方父母許下婚配,根本沒有時間認識,原本設定來互相激盪,但是外國策展人往往被視為偉大的那一方,兩個人總有一個社會位階。如2004年范黛琳、鄭慧華的雙年展,即是這樣的情況,外國策展人的強勢作風,讓本土策展人變成只是協助的角色,和原本期待的互相扶持、互相學習落差非常大。另外一個他提出台北雙年展定位的問題,認為台北雙年展在近年來漸漸失去方向,早期還可以作為建構國際的平台,讓大家看到什麼叫做策展人,可以讓策展人來認識台灣,願意來台灣,同時也讓台灣的藝術家被國際看見。今天條件都不同了,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嘗試20年都無效」他說,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
「本土和國際不是對立的」高森信男說,像他舉例,古巴的哈瓦那雙年展,就非常的接地氣,但是很好看,很多國際人士也都前去。因此「如何定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本土也可以是一個國際區域性的本土,像是新加坡雙年展,就是聚焦於東南亞藝術,一次看完區域的創作趨勢;有一些小型的雙年展,如「蒙古360度大地藝術雙年展」,就把2、30個藝術家,和第一線的藝術家放在一起。「可能還是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整體區域作為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個工具,市民參與式的藝術節慶也無不可,或是呈現歐美最精銳,第一線的藝術家。」
在面對越來越多的雙年展,尤其是韓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光州和釜山雙年展,後來崛起的上海和新加坡雙年展,以及因 Art Basel Hong Kong(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成為亞洲藝術中心的香港等,台北雙年展要如何在這股洪流之中重新被看見,無外乎就是對於自己的定位,找出自己的策略,以及在僵化的行政體制內,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時間,來好好地進行。這一屆的雙年展,不若以往的外放,也恰好,讓喧鬧奔騰的過去20年有了新的沈澱,來思考雙年展的未來。
如同狄瑟涵在開幕酒會上和我的閒聊一樣,「國際就是在地;在地就是國際。」是由觀賞的人決定的,並不是一種衝突。




未必是一种而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