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上週落幕。雖然文化界在展前指出,書展推廣閱讀的能力有限,不少書商亦唱淡市場,今年香港書展的入場人次仍漲至102萬人次,參展商達七百多間。
很多文章在商言商,討論書展如何拓展消費群。但這類分析,只把書展參加者當成買賣方,忽略很多人真的讀書。這種把出版生產跟書籍消費割裂的解讀,也讓人誤把書展當成一個各取所需的合理交易平台,忽略當中潛藏的權力關係。要拆解書展的本質,除了談文化和營銷策略,更重要的是點出「暢銷書」的本質。
展場充斥的暢銷書,總是針對普遍市民心中的問題,例如身份認同、健康危機,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和指導意見。但這些意見看來時效短暫,不具收藏價值;當讀者渴望脫手,二手書店通常拒收,理由是退書的人如此之多,店內沒有空間囤積,也找不到人再買。
暢銷書的本質無疑是短期市場。隨著競爭越多,出版者提高市場佔有度,增加品牌價值(方便集資以至易手)和賺錢同樣重要。何況書商的利潤並不高,降低人員待遇和稿費等手段,也有其極限。要薄利多銷,不能依賴細水長流的高價作品,要抓住一些短期的社會熱點問題,讓書籍提供一套廉價又精美的答案,盡快回本。
從二手書店拒收暢銷書來看,書展之所以存在,除了會展新翼的廣闊空間,更因為動輒數十萬、不斷增加的基本客源,提供短週期暢銷書的流通平台。而許多香港讀者似乎也以為,自己心中的疑問在書展裡找到了答案
社會問題的包裝炒作
在1990年代,香港書展在時間規劃上經歷了兩大變化,其一是展期由四天增到六天,其二是星期五六的開放時間延至晚上十二時,但入場人次不過維持了穩定增長,徘徊在20萬至40萬之間。參加人數在下個十年才突然飛漲,由2003年的約43萬,遞增至2009年的90萬人。
遙想2003年沙士(SARS)病毒肆虐,坊間百業蕭條,觸發龐大民怨,香港政府為了人心回歸,大灑金錢去推廣維港巨星匯、幻彩詠香江等娛樂事業。這股氣氛下,香港書展迎來分水嶺,邀請各地作家,舉辦講座及展覽活動,吸引大批人流。這就是大型社會議題引領書展走向的開始。
社會的確有很多問題,但不一定奪人耳目。如何串連牽連甚廣的社會問題,進而結集成書,公然販賣答案,乃是一門學問。在2010年,陳雲反對雙非移民來港,表示自己如果不做出頭鳥,香港人就會在沉默中死去。經過一年的時間在 Facebook 等媒體醞釀,他寫出《香港城邦論》(2011)這本暢銷之作,催生無數討論本地文化及中港矛盾的文章。後來陸續推出《香港遺民論》(2013)、《城邦主權論》(2015),對前作理論的伸延和補充,不斷和香港本土思潮互為引證。
一連串的預言可能是先見之明,也可以是自我實現。高舉民族旗號、捍衞香港本土的,會是歷史必然下的勇士,還是受到影響和感召的一般人?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就表示,《香港城邦論》和黃毓民的議會表現,是他中學時的政治啟蒙老師。
更多的議題操作來自教育、健康這兩大區域。除了母語教學、DSE 考試、國民教育這些催生大量教材和練習的政策,屈穎妍《怪獸家長》(2010)所刮起的教育反思,更能示範一個來自日本的概念──如何透過媒體說動家長,促使他們在書裡尋找答案。近年,導演嚴浩在報紙專欄不斷描述病症,公開偏方,進而現身書展,推廣《嚴浩秘方治未病》(2015)這類著作,把未發之症,視為待治之病。
今時今日,電子媒體上的言論縱成氣候,仍需出版成書,才能把社會問題的答案,轉化為消費的實物,而在書展裡隆重其事首發開賣,更能觸動大眾神經,讓問題進一步滾存。事實上,我們明白《老懵董》(2000)的嬉笑怒罵,和《有一種幸福叫忘記》(2014)的小品抒情,都只是聊以自慰,難登大雅之堂。但它們在書展大賣,一石激起千層浪,又在讀者心中變得舉足輕重。
隨著政治形勢瞬息萬變,教育政策朝三暮四,健康問題更是無日無之──各種看似重要的問題,轉眼之間就要被新的問題蓋過,千言萬語,頓成廢紙。沒有人抽出半分鐘,反思問題本身的意義。這段尋問的旅程,就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止。
毒害人心的問答文化
若然各項社會議題,真的切合事實,有深究之必要,上述不過談及了書籍啟迪群眾的作用,並無惡意。相反,市面所充斥的各種假命題,刻意營造了社會上的焦慮和不安,公眾在閱讀裡尋找答案的同時,就患上一種厭棄思辨的精神疲勞。
近20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及建制團隊不但鞏固既得利益者的權力,亦創造了一些駭人聽聞的所謂社會問題。在我處理社區組織工作時,就聽到不少危言聳聽的消息:香港金融地位將被新加坡和上海超越、大學的教育水平大幅下跌、最低工資導致過半中小企結業、佔領中環讓國際投資者離港、觸怒中國會失去龐大市場。
這些消息,後來證實只是危言聳聽的流言,卻令很多街坊惶恐不安,縈繞逾年。他們從未懷疑問題本身,只確信解答是存在的。當你用心引導思考,他們卻一再推卻,繼而反問:別說那麼多了,你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這套問與答的文化,深深的毒害了人。日本福島核電事故之後,兩岸三地民眾搶水搶鹽,只談解決,不問原委。又像受鉛水問題困擾的啟晴邨,一萬三千人追究不了一個官員,反而被換水管這個解決方法所哄騙,被迫接受鉛水對下一代思維發展的傷害。
當政權有意識地利用政治能量,滾存虛假的需求,哄騙民眾去購買空殼似的解答,一場騙局就在眼前。民眾相信書籍可以提供答案,加入書展這場嘉年華,一起鼓吹消費。當虛假的社會問題被遺忘,答題就變得一文不值,但是在政權的操控中,新的社會問題、新的焦慮不安將再度襲來,吞噬人民的金錢和希望,週而復始,萬劫不復。出版界也日益依賴社會問題的推動,往往緣事而發,不能前瞻局勢。久而久之,政權一再製造災難,出版業被動地拆解,我們被動地讀,培養出問和答的默契,無了期地玩這個詭異的解謎遊戲。
書籍提供指導答案,協助人類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從來就不是罪孽。然而在急躁的問答文化下,再有價值的紙本,也因為錯誤的用法而成為凶器。從補習社到公開考試,填鴨式教育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除了迷信權威答案的可行性,社會也漸漸失去追索問題來源的能力,遑論去審視問題是否合理。在資訊爆炸的世代,如何篩選互聯網上的海量文字,成為新的困難;踏入書展反而是方便的,既有問答兼備的暢銷書,更有推銷員和人群去引導你找什麼答案,而又容易找得著。
這樣的香港書展,一年一度在夏天舉行。恰好,香港市民在歷經《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做過遊行、六四晚會等「例行公事」,經歷各種社會問題累積和爆發的過程後,得以湧入展場,跟無數放假的青年學子們,一同到場尋找答案。
問答之間的權力關係
回歸本源,每年一度的書展,應是在日常生活分割出一片暫時的寧靜,讓讀者可以專心去閱讀和交流。知識需要長期積累,智慧需要個人思考,《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豈能聽信既定的問題,尋找既定的答案?
現實卻是,社會的一些短期問題,催生了書的短期市場,以問答制度,建立一套由上而下的權力關係,要讀者相信權威、委託他們解決生命中的各種問題。假如讀者只聽信問答的那一套,以知識的多寡來論斷是非,忽略了思考的薰陶,就會喪失主導論辨的方向。社交網站上的隻言片語,也是一個知識的短期市場,很多人即使走出書海,也只會成為網絡公知的盲信者。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拋棄對答案的迷信?畢竟,閱讀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觀察現實的方法,若要解決問題,仍需要親證的經驗和實踐。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6年的旺角騷亂,一切全賴群眾當下的判斷,正因為沒有金科玉律,我們才要思考,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世界亦不存在一套方便的理論,可以解開所有的難題。
我們就是太急功近利,每天閱覽各種評論,缺乏反省和沉澱的時間,才無法深究一本專書的系統性論述,並為自己的粗淺而愁苦不已。而我們的確太掉以輕心,沉迷網絡資訊,直到今天才發現,社會的問答框架形成之後,再沒有容許思考的空間。
要對抗問答制度的暴力,我們不能被動地尋問,反而要在閱讀中思考,創造自己的答案。
(李伯匡,自由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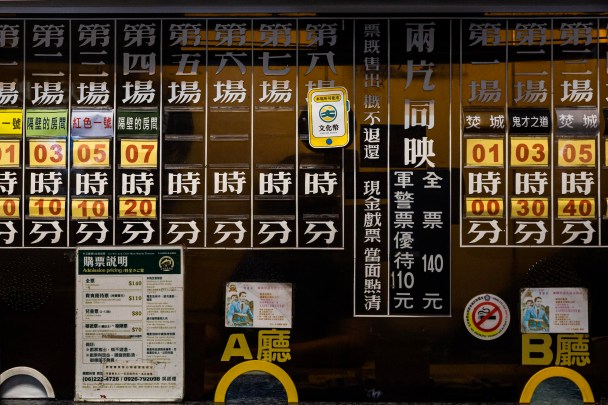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