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宥勳|自由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2016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有兩件關於張愛玲的事。第一件是書展中,有張曼娟策劃的張愛玲特展「張愛玲特展:愛玲進行式」,展出了張愛玲生前的服裝、假髮,在文化圈引起一陣不大不小的批評。第二件事則相對沒有受到那麼大的注目:承繼了張愛玲遺稿的宋以朗,在書展期間接受媒體訪問,放出了他即將出版張愛玲書信集的消息,並且以這批書信為基礎,寫一本最權威的傳記。
展出假髮和出版遺作,其中的交集是個倫理問題:作家亡故之後,我們如何處理她遺留下來的物質與精神?如何在她的自主意志和讀者的粉絲狂熱之中取得平衡?這些議題在張愛玲這麼一個具有強大商業能量的明星個案上交會,則讓問題顯得更為複雜。
我們或許需要先後設一點,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作家」這種角色的社會位置。無論作家本人的自我意識為何,也無論文學媒體如何包裝,文學出版本身就是一項商業行為,而且如同「演藝圈」一樣,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粉絲經濟」。換言之,你可以是一個思想上不染凡塵的作家,但你只要進入現代出版產業中,你的「不染凡塵」也可以兌換成商業價值。現代文學的諸多迷思之一,是強調作者與作品的「獨創性」,「某某作品,就只有某某作家寫得出來。」所以,所有「作品」的成就,最終都會回頭挹注在被神格化的「作家」身上,形成一個環繞著作家的類宗教社群。而這與現代出版產業、著作人格權和商業利益一拍即合,自然形成了「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寡占事業。
違反作家的意志」也未必是不行的,就像眾所週知的卡夫卡的案例,我們現在閱讀的每一個字都違反了他的意志,但權衡他為人類心靈帶來的巨大貢獻,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也因為上述體系,是依附在一個明星作家上的,所以當作家死亡之時,這個體系就將面臨無可避免的生產中斷——最起碼,再也不會有新作產出了。這時候,這個體系能否延續,就端看作家的作品是否能讓後世讀者願意一再重讀,這需要強悍的作品素質和不斷延續的論述,來使其「經典化」。
或者,用一種比較短視、能快速收效的方式:去操作粉絲社群,加強並利用粉絲對作家的「戀物」傾向。

根據報導,張曼娟策劃的展覽,是「從皇冠出版社借來張愛玲封存多年的遺物」,可以很明確地看到這個展覽背後,運作的是怎樣的商業操作,或至少是知情同意的合謀。而宋以朗從《小團圓》等作以來,陸續出版遺作,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商業性質。然而我並不是要說商業操作必然是罪惡的,如果讀者或參觀展覽的人,能夠從中對作家或作品,獲得更深一層的體驗、理解,這些「更深一層的東西」當然可以當作一種商品來販售,而且也可以帶來正向的文學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作家的意志」也未必是不行的,就像眾所週知的卡夫卡的案例,我們現在閱讀的每一個字都違反了他的意志,但權衡他為人類心靈帶來的巨大貢獻,這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重點不是你是否違反作家的意志,而是你處理這些遺產時,是否真的帶來了正向的文學效果,帶來了「更深一層的東西」?
假髮源自於張愛玲晚年的「蟲患」,是精神疾病重創她生活的「遺跡」,在這個洩漏病歷即是洩露重大隱私的時代,還如此堂而皇之的展出,居心簡直惡質到極點。
由此來看,張曼娟的「張愛玲特展:愛玲進行式」特展和宋以朗的書信集出版,畢竟還是有優劣之別的。「張愛玲特展:愛玲進行式」顯然以「作家」為核心,展出衣物、假髮,勾引的正是粉絲的戀物傾向。但除了話題,除了勾引,到底四頂假髮能夠讓我們多知道張愛玲的什麼呢?如同廖偉棠〈張愛玲生前最害怕的事,又發生了〉一文指出的,展出服裝或許對於理解張愛玲有其意義,畢竟這是她文學寫作中的重要焦點之一。但假髮源自於張愛玲晚年的「蟲患」,是精神疾病重創她生活的「遺跡」,這件事張曼娟不是不知道,在這個洩漏病歷即是洩露重大隱私的時代,還如此堂而皇之的展出,居心簡直惡質到極點。
就算非展不可、錯過可惜,展覽中是否提供了更多說明,讓張愛玲在隱私上的「犧牲」是值得的?很可惜,除了獵奇的展示之外,再無其他了。
宋以朗或許應該出示明確的證據,來證明出版權利的正當性。如果授權上沒問題,就算它同樣會有暴露隱私、違反作家自由意志的問題,但能夠帶來的啟發當是足夠豐富的。
而以同樣的標準觀之,張愛玲逝世後,擠牙膏式陸續出版的遺作,容或有所爭議,但起碼都還能讓我們多看到作家的文字表現。即便是殘稿、未完稿、作家不滿意的稿子,也都能成為詮釋或研究的線索,甚至在某些意義上,可能比作家修飾完整、願意出手的稿子,更有研究的價值。宋以朗預計出版的的書信集,比較大的疑慮,會來自張愛玲是否真的有對書信文字進行出版、複製的授權?如果只是「繼承遺產」,很可能只是繼承了「擁有原件」的權利,在張愛玲逝世未滿五十年、還未變成公共財的情況下,逕自出版很可能是有問題的。宋以朗或許應該出示明確的證據,來證明出版權利的正當性。如果授權上沒問題,我認為是可以樂觀其成的,就算它同樣會有暴露隱私、違反作家自由意志的問題,但能夠帶來的啟發當是足夠豐富的。
當然,在編輯出版的過程中,若能邀請專家學者加入,對這些遺稿進行初步的導讀、說明的話,也會比「裸出」更讓人期待。在評價這些遺作的出版行為是否值得時,也是端看編輯方面的處理是否足夠細膩,能否帶給讀者更多東西——比如說,像《同學少年都不賤》那樣把脈絡無關的作品打包成一本,隨意出版的情況,就是不可取的。
但問題不在遺作能否出版、遺物能否展出,而在怎麼處理出版和展出的過程。
愛財也應取之有道,特別當你是從作家的才華之中賺錢時,至少得負起「對得起作家」的基本倫理責任吧。
本文感謝楊佳嫻老師和張幸真老師的協助,但文責由本人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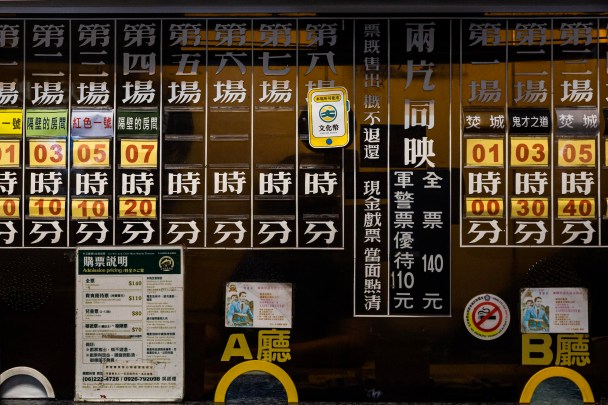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