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一個寒冷、猶猶豫豫的春天,雪已經都化了。伴著面前的咖啡,我看著手機上的疫情數據:美國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我不住在美國,也不是美國人。事實上,在我生活的比利時,疫情數據要比美國更糟;可打開《紐約時報》的應用程序看一眼美國的數據,還是成了習慣。在每天開始的時候看一眼疫情的統計數據——就像體育比分那樣,就像跟蹤美國大選一樣——帶来一種詭異的滿足感。
依據目前的數據,COVID-19已經感染了1.29億人。大約1800萬人是重症患者,已有282萬人死亡。許多倖存者的身體垮掉了,心肺有永久損傷,長期的健康影響未知。咖啡漸漸涼掉。我知道,數據背後都是真實的痛苦,可我發現,好像我無法與這個事實聯繫起來。我應該感到同情,與生病或垂死的人們一樣難過嗎?我為什麼沒有在難過呢?當我在看這些數據的時候,我「應該」帶有怎樣的情緒呢?
數據都是抽象的,我對自己說,看著數以百萬計的人生病死去而毫無感覺,這也許是可以被原諒的。數字難以產生具象,所以它們既是邪惡的工具,亦是安慰的來源。
我生活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在經歷了連續的、前所未有的限制後,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已經停滯很久。我居住的社區叫做Saint Antoine,這裏的街道上擠滿了低收入家庭的小公寓,遭到疫情的嚴重打擊。「我不知道百分比,但已經有一百個人死了,大部分是老人。」我家對面青年中心的社工伊斯梅爾(Ismael)對我說,「真的很極端,光是在我們這條街上,每週就有十個人死去!」我對伊斯梅爾點點頭。可當我一個小時後,沿着街道走回家時,我意識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依然無法感覺到附近的痛苦和死亡。
我似乎有些麻木。這意味著什麼呢?

何為哀傷?
我們並不是因為失去了某人或者某事而哀傷,而是失去了對他們的依附才哀傷。
悲傷是人們應對重大損失的過程,尤其是親近之人的死亡。被憤怒、絕望或怪異的麻木所震撼,你可能無法起床、穿衣、洗澡、吃飯、工作或與他人互動。
配偶、父母或孩子去世時,我們會哀悼,這種精神上的痛苦似乎無需解釋。但真正地理解它很重要。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們——亞里士多德、孔子、莊子、尼采、弗洛伊德——還有很多現代的社會學和醫療科學家們都試圖去精確把握它究竟是什麼。
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候哀傷、悲痛,那通常是一種全然的、毀滅性的經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似乎是真的「迷失」、然後又「找回」了自己。
很多人相信自己是獨特、完整的個體,獨立於其他人。現實、社會、或是其他人可能很重要,但都是次要的——我們自己的角度、興趣和能動性支撐並凌駕於一切之上。西蒙頓(Simondon)等當代哲學家挑戰這種自我中心的世界觀,從生物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辨析稱,我們一直在通過「個體化」的這個過程,來一再製造自己的個體性。
相似的,哀傷理論家也認為,我們是透過和人、物、事、信仰構成的依附關係,來分析並定義自己的:這些關係都是「建材」。我們有一個複合的社會身分,不是既定的、也永遠不會「完成」。我們是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多種群體的固有部分,沒有了這些,自我就失去了邏輯或凝聚力;環境不斷變化,我們也必須去適應。
舉個例子。當你意識到,你的伴侶關係和在其中的你,已經不是你相信的那樣時,愛情就失去了它的位置。悲傷和憤怒會動搖你,幫助你接受這一現實並重新梳理:也許你會獨自或與伴侶一起去接受心理咨詢,也許你會愛上別人,也許你會對愛永遠失去信任。你愛過的人還在,但對你的意義卻不同了。
因此,嚴格意義上說,我們並不是因為失去了某人或者某事而哀傷,而是失去了對他們的依附才哀傷。
專業的悲傷諮詢師總是說,導致哀傷的「損失」是沒有等級之分的。他們說,你可以因母親的死亡感到哀傷,也可以為你黃色斑點鸚鵡的死亡感到哀傷。事實上,不非得是死亡,在任何有意義的「損失」發生後,比如失去健康或者工作,你都可以哀傷。人們掙扎著因失去健康而無法與孫兒在公園散步後、因失去童貞、或因喜愛的球隊在決賽敗北受到巨大的打擊之後讓自己振作起來。
這聽起來可能有些漫不經心,其實僅僅意味著我們對不同的事物存在深深的依戀,並相應地對損失作出反應。
不過,專業人士在騙我們。哀傷絕對是有層級的。事實上,一大堆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規定了你該為誰哀傷、你被允許為誰哀傷、在什麼時候、如何哀傷、哀傷多久。
你絕對不應該像哀悼你母親那樣哀悼你的寵物。

某種程度的悲傷被認為對你有好處,但它同時也是有破壞性的。悲傷太多,沈迷痛苦並被痛苦吞噬,失能並與世隔絕太久會被認為「不健康」。參考醫學文獻和政府的各種規定,這個界線常常在6到12個月之間。在那之後,哀傷不再是「正常的」,而成為了「拖延的」、「複雜的」,或是「創傷」,一種你需要為它尋求治療、抗抑鬱藥和保險的疾病。保險公司大力遊說悲傷的「醫療化」,因為這讓他們可以賣產品。
這些所謂「健康」或者「正常」的哀傷界線一直遭到批評,因為這本質上服務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把人矮化為有生產力的個體:不該閒置太久,要由醫生判定你是「病了」,而不是懶惰。公司通常允許僱員在直系親屬過世後休少得可憐的三天帶薪假期。
根據一種流行的看法,悲傷可以被一系列的情緒階段劃分,譬如從「否認」、「憤怒」到「懇求」、「沮喪」和「接受」,與垂死之人的經歷很類似。不過,這個所謂的「哀傷的五個階段」並沒有科學依據,甚至並不準確描述人們哀痛的經歷。比起這幾個清晰的階段,真實的悲傷要更混亂,它的結構也未被真正理解。
能被經驗所證實的是,當你所愛之人去世時,了解、目睹其他有著相似經歷的人會有所幫助。「哀傷一旦被分享出來,就會開始消失,其他人、整個社會都參與到你的哀悼中。」比利時心理學專家基爾斯(Manu Keirse)在視頻電話的另一頭告訴我。
痛苦和悲傷看似私人,可哀悼卻是一件集體發生的過程,全世界都是如此。我們需要與親友一起,在瀕死之人的塌下,交談、注視、哭泣並牽手說再見,見證死亡,參加葬禮。分享哀傷是必須的,也是高度儀式化的。一樣的,這裏頭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定。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家在2020年的一份報告中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會認為,對於「善終」而言,在家裏、醫療機構和殯儀館的一些重要時刻,並以一種被認可的方式發生是至關重要的。
失去親人的人們需要一個「善終」,一個遵守這些規則的、「正常的」哀悼。這些時刻都需要身體接觸,在疫情下,這些不被允許。遏制病毒傳播的措施,迫使數百萬病人和所愛之人隔離開。人們獨自痛苦,獨自死亡,獨自哀傷。
社工伊斯梅爾告訴我:「穆斯林從不會讓一個人獨自死去。通常你會聽到許多哭泣的女人,家裡擠滿了親朋好友,在逝者家裡坐好幾天。我們都會去清真寺祈禱並送去關愛。當他死了,我們都出席,葬禮一定人山人海。」
「現在,葬禮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嘆道。無法參與最後的儀式會制止、擾亂哀傷,從而導致創傷,讓喪親者很難從中恢復。
很難恢復的,不止是喪親者。

疫情帶來的「哀傷海嘯」
我們很可能已經集體進入了一種「極度混亂和不確定的創傷狀態」。
「想像一下,幾個月內持續有一千架客機墜毀;每隔幾小時就有新的飛機殘骸從頭頂掉落,日復一日,持續數週。」2020年4月,心理專家凱斯勒(David Kessler)這樣向美國的觀眾們解釋關於2019冠狀病毒的集體性哀悼。
波音Max737型飛機在2019年發生了兩次墜毀事故,造成346人死亡後,客戶、投資者和政府才對波音失去信任——直到墜機事故不久前,波音還被描述為「全球經濟的中堅力量和美國最大的出口商」。如今,波音元氣大傷,仍在收拾殘局。
按這個邏輯,如果COVID-19疫情是「一千架飛機接連不斷、日復一日地失事」,疫情一定也在傷害更廣泛和更深層次的期望和信任。我們很可能已經集體進入了一種「極度混亂和不確定的創傷狀態,」哲學家艾丁(Ciano Aydin)如是說。
的確,專家警示,疫情下個人和集體性的哀傷組合在一起,會讓我們不堪重負,「哀傷海嘯」將會來襲——「這場大流行已經把精神疾病的個人、社會和經濟代價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19冠狀病毒帶來的精神健康後果,很可能會成為未來幾十年內全球最緊迫的公共衛生挑戰,影響數十億人的福祉。」
美國一個「喪親規模」調查得出結論,每1個COVID-19的死亡病例,就會讓9個人經歷哀傷。在2021年3月,這意味著幾乎500萬美國居民在哀傷——如果用這個等式,全球的數字是超過2500萬人。這還不包括數以百萬計因疫情而失去了健康、工作、安全感和信任的人。
導致哀傷的「損失」不盡相同。不同年齡、社群、性別、膚色、職業和階層人群受疫情影響明顯不同。
老人的生理健康風險最大,大約是20多歲的人的90至630倍。在美國,80%的死者年齡在65歲以上。很多老人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被遺棄,儘管他們需要照顧。人們在西班牙和美國發現了被遺棄的老人的屍體。在比利時,養老院的老人死亡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無國界醫生組織將其稱作人道主義危機並要介入。此外,還有很多人把限制出行的措施,歸咎於老年人的患病率。如果倖存下來的老人們再也不相信他們會得到妥善的照顧,也是情有可原。
相反的光譜則是數以百萬計的青少年,他們不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但一樣要付出代價。心理健康專家警告,大流行的宵禁和封鎖讓他們的個人和社交發展停滯,無法見到朋友、不能約會、無法上學、上大學或是得到第一份工作。他們失去了至關重要的人生時刻。美國疾病控制中心2020年6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在接受調查的18歲至24歲青少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曾認真考慮過自殺。
女性的世界是最糟糕的。面臨嚴重感染風險的醫療工作者中,70%是女性。而且,女性受疫情影響比男性按比失去更多工作,被迫回歸家中扮演傳統的照顧角色(比如教育孩子),失去了在經濟和職業平等方面來之不易的成果。聯合國婦女署的數據顯示,由於封鎖,一些國家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激增。
醫護人員的悲痛更為複雜。
2020年1月,繼武漢居民們在公寓的窗口大喊「加油」、「繼續戰鬥」,世界各地的人們的都開始為醫務工作者們鼓掌,醫生護士們被巧克力、繪畫和橫幅淹沒。那之後,醫務工作者們英勇的工作還在繼續,大眾對他們的崇拜卻消退了。最糟糕的時候,他們甚至面臨攻擊。在印度,醫生們被認為是危險的而被趕出家門,外勤醫務工作者成為暴力的受害者,一名因公殉職的醫務人員甚至被剝奪了墓地;在荷蘭,也有暴徒襲擊醫院。
況且,鼓掌和糖果不能保護醫務工作者。僅在美國,就有數十萬醫護人員被感染,數千人死亡。沒有做好準備的醫院和療養院被一波波的感染者、病人和垂死的重症患者淹沒。即使在有足夠物質資源——擁有床,病房,呼吸泵,呼吸機和防護裝備——的機構,醫生、護士、清潔人員和其他護理人士不停轉地工作,冒著被感染的風險,也承受者極大的壓力。
在不少國家,醫務人員被叫作「前線」工作人員——這是疫情時期眾多戰爭用語中的其中一個。來自印度、中國、美國和歐洲的研究都顯示,醫務人員中存在著前所未有的焦慮、抑鬱、藥物使用和創傷後壓力。
對醫務人員來說,其中一個應激源是「精神傷害」(moral injury),也是一個源自軍隊的詞,通常在一個人做了違背其堅定信念的事後產生,會導致精神失常。創立了醫護人員精神傷害(Moral Injury of Healthcare)非營利機構的精神病學家迪恩(Wendy Dean)解釋道,這些人想要為病人們提供像樣的護理。這是他們學習並且受訓多年的目的,是他們的職業誓言,但他們卻無法做到——他們也在失去對世界和對自己的信心。
沒有人知道這場集體性的心理創傷害會如何發展,又會給醫護人員或者我們的醫療系統帶來怎樣的影響。「真正的清算會在這結束了之後到來,」迪恩寫道。

「接受」
病毒在加深現有的社會斷層,種族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心理學家凱斯勒認為,悲傷的不同階段的理論,對於理解我們當下對病毒的反應是有用的。「比如『否認』,我們在早期看到很多:這個病毒不會影響我們;『憤怒』:你逼著我待在家裡然後奪走我的活動;『悲傷』:我不知道者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然後最終是『接受』:這已經發生了,我得想辦法如何繼續下去。力量存在於接受之中,只有接受了,我們才能找回控制。」凱斯勒說。
只是,凱斯勒所說的「接受」是什麼呢?是接受疫情的事實嗎——是新聞裏的數據?還是接受這場危機帶來的更為深刻的隔閡?
從英國、美國到香港,病毒不成比例地讓更多的黑人、東南亞裔公民感染和死去。在這些社會,少數族裔通常是下層階級,貧窮、無歸屬感,生活和工作條件更糟。在傷口上撒鹽的又一層現實是,這些社群常常被指責在傳播病毒。
在我生活的街道也是這樣。這裏是上世紀60年代從摩洛哥來的「外來勞工」後代聚集的社區。第一代勞工,如今已經年老體弱。媒體的頭條新聞會說,正是這些初代勞工充斥著重症監護室;又有報導說,這一點「個別醫生、護士都知道,但沒有人將其紀錄下來,害怕這是污名化。」——就好像這樣的說法,便能顯得中立。
針對摩洛哥裔比利時人的種族主義歧視普遍存在,並被主流媒體和政客滋養。媒體會報導說,正是摩洛哥裔人不遵守隔離規則,他們「在公園裏吃瓜子」的習慣,造成了又一輪傳播。「人們在商店裏看到某些群體,身子會往後縮,」研究疫情與種族歧視的費爾哈格(Pieter-Paul Verhaeghe)教授告訴我,「病毒激活了原有的種族主義,還減少了摩洛哥裔比利時人找工作或租房的機會。」
離我家不遠的街口的茶館,因疫情關門已久。但還是有很多男人站在外頭聊天。強制要求配戴的口罩在他們的脖子上晃蕩,或者包著他們的下巴。口罩不遮擋口鼻,但可以逃脫罰款。
根據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布魯塞爾的疫情規則執行是種族主義的。在我們這樣的居民區,警察不成比例地攔截、罰款和處理了更多摩洛哥裔比利時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負責這個區的警察局長最近承認,警察在疫情期間的行為擴大了公民之間的差距。
尤其是那些年輕男子,他們不戴口罩的行為似乎就是為了標誌什麼、挑釁什麼——即便這裏所有因為2019冠狀病毒去世的人,他們可能都叫得上名字。就好像口罩那一小塊布料被用來證實了比利時社會對他們是不安全的偏見,像一塊榮耀勳章。
這讓其他人感到害怕。七十五歲的皮亞(Pia Makengo)在這裏住了55年,就在我們隔壁,她是這一大片區域的第一位黑人住戶。她感到弱小,她說「這些年輕的摩洛哥裔,不戴口罩。成群結隊的,他們看著你,就好像他們……他媽的不在乎。」Pia和她坐在一旁沙發上的孫女,都因為她大膽的粗口笑了,「但我不敢說什麼。他們可能會打我。」
疫情的遏制政策奪去了這些年輕人在公共街頭以及廣場上的生活。許多人丟了工作,好幾個月無處可去,只能和家人擠在狹小的公寓裏。但是,這個社會不在乎他們的損失,只會責怪並歧視他們。對他們來說,疫情並非問題所在,而是一個多餘的提醒。他們的憤怒,正是在公開展露悲哀。
社工伊斯梅爾告訴我:「每當有可怕的事情發生時,恐怖主義、毒品、犯罪——它們就會與我們聯繫在一起。COVID也是如此。」病毒在加深現有的社會斷層,種族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可我們不是威脅,我們也是受害者,我們也會哭泣。」伊斯梅爾提高了聲音。

後記
當我開始思考哀傷、開始質問自己應該感到哀傷的時候,還是寒冬,春天來的很快,卻也在提醒著我,被疫情陰影籠罩已經一年多了。我想起伊斯梅爾說他能在街上「感受」到疫情的存在,「你看不見它,但是它在壓抑著整個街區,我在這裏長大,我能感受到!」
如今,疫情被廣泛地和戰爭或是諸如美國911的大規模暴力事件相提並論。政府和媒體經常使用戰鬥用語,這聽起來總有些奇怪,因為並沒有敵人,而是在試圖描述我們感受到的損失的重量。除了戰爭之外,我們沒有其他可以用來比較的對象了。
其實,2019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和其他所有的死亡相比,顯得微不足道——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嗎?我們不是一早就知道自己會死,別人也會死嗎?為什麼我們不總是在悲傷呢?答案也許很簡單,因為我們想要生存,我們必須就要對痛苦免疫,除了最切身的。
前幾天,街角賣啤酒的雜貨店老闆希爾萬(Sylvain)在我伸手推門離開時,突然說:「我正在失去一些東西:日子,事件,生命,而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回來它們了。很病態,我弄不懂⋯⋯好像什麼也沒發生,死亡卻在漸漸滲入。」
真的會有哀傷海嘯嗎?由哀傷組成的海嘯會是什麼樣的?我們會是眼睜睜地看著它的到來,卻什麼也做不了嗎?像是站在沙灘上,看著悲痛的浪潮滾滾而來,見證著站在邊上的別人被捲走;好像明明身在局中,卻又奇怪地感覺被移出局外;像有一個巨大的虛無的麻木感,我們像是被麻醉了。
別擔心,我對自己說,「you’re grie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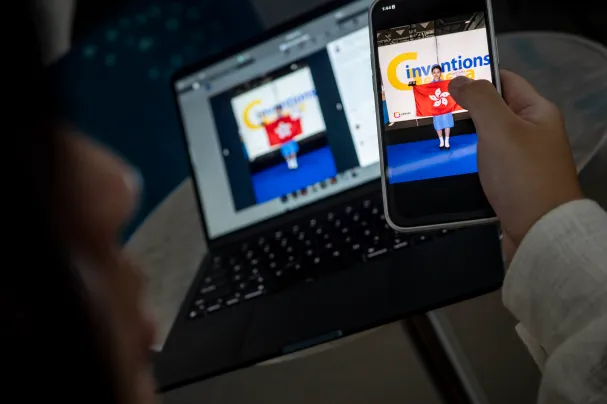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天哪,快看哭了「我正在失去一些東西:日子,事件,生命,而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回來它們了。很病態,我弄不懂⋯⋯好像什麼也沒發生,死亡卻在漸漸滲入。」「don‘t worry,you are grieving。」我似乎什麼也說不了。
身為比利時居民,昨天4/1在布魯賽爾的公園聚集了2000人party大多數是年輕人想表達自己對於封鎖的厭倦以及可以自由活動不戴口罩的‘人權’,一群人跳舞喝酒沒戴口罩人擠人,公園是個布魯賽爾不錯的社區,參與的人應該多數中產階級以上的年輕人吧,不在乎的不只是摩洛哥裔的年輕人,平衡一下報導,也覺得對比利時人不顧社會其他人的自私自我中心覺得傻眼。
截至现在,美国大概有五十七万人死于疫情,也就是不到千分之二的水平。
作为对比,美国去年总死亡人数三百余万,新冠疫情甚至只能排第三,名列心脏病和癌症之后。
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哀伤海啸”呢?倘若真有,也该是癌症的海啸,心脏病的海啸,人类所有死亡的海啸。
是的,居家隔离是武汉为世界带来最惨痛也最有价值的教训,可是欧美国家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造成今天这样,真的没有理由埋怨别人。
麻木的另一个原因,是否是对政府应对不力的无力呢?真的很难想象欧美可以应对的这么差,出台一系列无助于控制疫情却加深抗疫创伤的封城政策。相对而言,无论是台湾还是澳新,甚至从未彻底对外封锁的新加坡,都要应对的好得多……
2020确实不平凡的一年,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