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世界衞生組織指出,災害發生後,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發生率普遍增加。在疫情最焦灼的湖北,反家暴公益組織「監利縣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2月的服務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倍。在負責人萬飛看來,案情反映出來的具體矛盾80%跟疫情相關。心理壓力、無助感、喪失感,供應資源有限,社交網絡破壞,處理暴力的系統削弱,經濟受損等因素,都可能觸發更多暴力行為。不過,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的創始人李瑩認為,深層原因還是權控關係,男權文化之下對女性的歧視、貶低與物化。
端傳媒將連續兩天探討中國疫情期間的家暴問題。這是第一篇,記錄了三位受暴者的痛心經歷和艱難求助;第二篇探討家暴援助中的困境,點擊閱讀《家暴援助的中國困境:讓受害人去改變,怎麼可能真正解決問題?》。敬告各位讀者:本文部分內容涉及暴力,可能會引起不適。
「你這樣會毀了人家」
2月下旬,范范帶着傷情鑑定書和控告書去深圳市南頭派出所,自認有把握。
嚼着檳榔的調解員拆開法醫鑑定,見是輕微傷,打電話將范范男友叫過來試圖調解。范范想追究男友責任,調解員不滿:「現在人家要弄死你呢……就應該把他拘留了甚至刑拘是吧?非鬧到這個地步嗎?」做筆錄又問:「交往多久你就去他家住?他不讓你走你就不走?」范范說自己被威脅打死,調解員問:「他喝醉酒的話你也信?你就害怕了?」沒有第一時間報警,他又說:「你早幹嘛去了?」
范范一聲不敢吭,筆錄後被告知回家等通知。走出派出所,范范問男友之前是否打過女友,沒有道歉和關心的善後不像初犯。沉默十幾秒後他說打過。范范不知道口罩後面是怎樣的表情。要讓他受到懲罰,她想。當天她收到男友的微信:求你放過我,給我一次機會。
幾天前她一身傷痕來派出所,還是這個調解員,讓寫一份自述材料。見男方在知名互聯網企業工作,調解員說,「他工作這麼好,你這樣會毀了人家。」事後男友也學着說,你把我毀了。
幾天前她一身傷痕來派出所。見男方在知名互聯網企業工作,調解員說,「他工作這麼好,你這樣會毀了人家。」事後男友也學着說,你把我毀了。
隔天早上四五點醒,范范腦子裏翻滾着警方的冷漠和因疫情生出的艱難感,她想自殺。朋友寬慰她,筆錄沒做好可以再補充。范范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跑去派出所。警察說,不用老來,電話裏講就好了。被打發走。
為了找到對付調解員的話術,范范反覆聽了三遍筆錄當天的錄音,她覺得大叔調解員的話重聽下來就一個意思:你活該。難過轉為憤怒,范范在微博上聯繫女權活動者肖美麗,對方建議她寫篇文章發在她公眾號上。寫完後等不及回覆,她把文章在自己微博上發出來,轉發10萬。
下午,派出所教導員打來電話說要展開調查,當晚,又打來三四個電話催促范范去派出所「配合工作」。教導員代表派出所道了個歉。范范凌晨做完筆錄,陪同的幾位網友還在派出所門口等着她,怕她不安全,女孩之間的力量消除了一些悲觀。次日警方網上通告處理結果:拘留男方5日罰款200元。太輕了,她有些失落。後來得知男友提起行政復議後拘留暫緩執行,范范在微博上寫:惡人終會受到懲罰,但是惡人依舊不知救贖。
范范記得:
「他特別喜歡園子温導演的電影《庸才》,講家庭破碎的中學生殺死父親的故事。他原生家庭不好,爸爸經常罵媽媽,那時候我會同情他。他不是陰暗的人,跟人笑笑地說話,把他媽媽接來深圳一起生活,我覺得他還挺有擔當。
「他喜歡『賣慘』,第一次單獨吃飯後送到小區門口,我回家了。過了一段時間他發微信說,其實我還沒走,心情不好。可能想讓我陪陪他。我沒搭理。一次聚會上我看他老跟一個女孩聊天,就說了他兩句。他反過來說你也跟男生聊天,我要看你聊天記錄。我感到被侵犯,不歡而散。後來他來我家找我,摁一個多小時門鈴,我也沒見他。他說感覺自己像條狗。大事小事還是我主導的比較多。」
認識幾個月後,范范跟男友在除夕當天確立戀愛關係。疫期無處可去,兩人跳過通用的交往步驟在家做飯,互相陪伴,上漲的確診數字和負面新聞讓人壓抑又無力。之前相處和諧,突然家暴後男友沒解釋過,范范只能找蛛絲馬跡。
年前去朋友家玩,男友跟朋友因小事發生口角,從廚房拿了把菜刀說要殺死他,用刀背在男生脖子上磕了兩下。范范當下只覺得這人有點衝動。幾周後,她勸男友不要在疫期外出聚眾喝酒,被掐住脖子,被像垃圾袋一樣提起不斷撞擊牆壁。男友邊打邊問:「這樣能把你殺死嗎?」指甲斷掉四根,她被灌酒不停嘔吐,想過報警或反擊但蜷縮在牆角不敢動,一直求饒也沒有用。後來不知怎麼他突然停手了。
半個月裏,范范去派出所十次,去醫院好幾趟,事情還沒有了結。她等着派出所寄男友行政復議的回函,如果受理,還需要再等待60天才有結果。律師不建議上訴,疫期案件處理至少需要六個月,再耗上幾萬塊。律師接手的大部分家暴案件都以和解告終,女方妥協,因雙方父母怕「不光彩」而勸說或者在派出所的調解壓力下不再「無事生非」。也有拿不到判定證據的,證明不了自己身上的傷是對方所致。

「跟了我們是你的福氣」
看到有相似家暴經歷的女性在范范微博裏評論,岳越生出了抗爭的念頭,不想再得過且過。她私信范范,講述自己的受暴經歷,范范建議她做傷情鑑定。岳越說,已委託律師辦理離婚,律師說地方上派出所管不了傷情鑑定,只能自己去醫院檢查。
岳越今年26歲,是在編教師,念大學時在健身房認識同齡的丈夫,被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外貌吸引。戀愛三年後岳越遠嫁來安徽四線城市,結婚三年,因家暴離過婚,沒多久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在丈夫認錯、家人勸說下復婚。
疫期一個月,丈夫在家全天只抱孩子十幾分鍾,其餘時間就是躺着睡着或者玩手機看電視。夜裏孩子睡了又醒,婆婆讓岳越帶孩子跟丈夫分開睡,以免吵到他。保姆過年回去後無法復工,提前解約。
丈夫打斷椅子腿,繼續打,岳越坐在地上動彈不得。 她還抱着十個月大的孩子。婆婆看着,平靜地去廚房洗完碗後說:「你們的事情自己解決。」越過她,上樓梯回了房間。
過年期間就發生了三次家暴,同住的公婆已經不管了。「說穿了,我是一個外人。」丈夫家裏做生意,勉強小康,有意無意會說,跟了我們是你的福氣,不會愁吃穿。岳越被安置在獨棟三層別墅中的一層。
3月初,岳越指責丈夫不顧孩子,問他自己的孩子為什麼要讓別人(婆婆)抱。「讓我媽看怎麼了?」丈夫認為這是將他媽看作外人,掄起餐椅砸向她。她還抱着十個月大的孩子。丈夫打斷椅子腿,繼續打,岳越坐在地上動彈不得。婆婆看着,平靜地去廚房洗完碗後說:「你們的事情自己解決。」越過她,上樓梯回了房間。後來岳越聽婆婆打電話埋怨她平時不給丈夫洗衣服,不關心丈夫,把婆婆當作「別人」。
而原生家庭是「說不清的一攤爛賬」,指望不上也不再見面。從小學起,長期兩地分居的父親做生意歸家後,刻薄愛抱怨的母親常懷疑他有外遇,因此而爭吵。又壯又胖的父親揍瘦小的母親,有時遷怒岳越,順手也是一頓揍。上初中的岳越跟母親頂嘴抬槓,父親聽着不耐煩,衝進來一腳往岳越心窩上踹,又扇了兩巴掌,血從鼻孔噴出來。
母親就在旁邊看着。「可能她覺得我不順她的意了就該被打,可能父親打她的時候她也認為男的打女的很平常。連親生母親都這樣,所以當家暴出現,婆婆在那兒看着,我更不會放在心上。」岳越說。生孩子時父母都沒來,沒打過一個電話,也沒給孫女花過一分錢。父親上了年紀患病,跟母親互相攙扶着生活還欠了外債。兩人總算不打了,既往不咎。
岳越身上常有大片淤青,別人瞧見了問怎麼回事,只能說自己不小心碰到了。對方心領神會,不說破。
丈夫被溺愛,初中沒畢業就在父親公司上班,人前各面都好。在家中變了樣,暴力作為一種激烈的溝通方式被公開使用。初次家暴發生在戀愛時期,丈夫看見其他男性通過社交網絡對岳越示好,即便岳越沒回應,他仍然認為她與人有染,藉此侮辱岳越水性楊花、玩弄感情,然後動手。
道歉得到原諒,之後家暴的起因從丈夫的猜忌侮辱,慢慢變成遷怒撒氣。出遊住賓館,一個認為賓館不好,一個覺得還湊合,爭執到激烈處丈夫就上手。去年年底,孩子晚上哼唧鬧着睡不好,岳越反覆幾次試圖餵奶哄睡不成,一旁看着的丈夫一個重重的耳光扇過來:「你還喂她,你沒看到她不想喝了嗎?」岳越身上常有大片淤青,別人瞧見了問怎麼回事,只能說自己不小心碰到了。對方心領神會,不說破。
「動手的唯一理由是覺得你好欺負,打你不必承擔後果。」岳越說。有時她問丈夫,你對一個女人使用暴力覺得自己很強很偉大嗎?他說,我打你怎麼了,就喜歡打你,你就是欠打。他踹、踢、扇耳光,或者將她在地上來回拖。孩子在一旁嚎啕大哭也不停手。
有時她覺得自己是不是非常輕賤,只能這樣被人對待。懷疑這麼多年的書是不是白讀了,怎麼會淪落到這樣一個境地。有同學讀研後去大城市工作,有的常住國外,「我是不是只能這樣子?」甚至想,不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再也找不到新的感情。有過幻想、麻痺、妥協,糾纏拉扯,母女情替代這份被消磨殆盡的感情,疫期矛盾讓離婚被提前。
那天岳越在地上緩了很久,拿手機拍下現場和身上傷痕後報警。警察聽說是家暴,說過不下去了你可以離婚啊。岳越堅持讓警察走個過場,就為了留下出警記錄。以前從沒想着留證據。警察到場後說有糾紛可以上法院,看財產怎麼分割。婆婆說,他們沒有共同財產。丈夫說我知道這樣不對,但是動手是有原因的。警察說兩口子再吵架也不能動手就走了。
公公勸說坐下來再談談,還想找七大姑八大姨一塊兒勸。岳越讓不要再摻和了。離婚申請已在網上通過立案,預計走完流程要一個月,比平時多耗費一倍時間。律師告訴岳越,哪怕是女法官,遇到這類事件都很冷漠。除了女兒的撫養權、撫養費外,建議加上家暴的精神撫慰金,但不一定被法院所支持。至於財產,律師說,這種多年的生意人肯定精,做好了一切準備。公司法人代表和股東都是公公,房子是婚前買好的個人財產,車也是公司公戶。

「憑什麼我要讓你」
被哥哥家暴後,達爾在豆瓣上搜索相關帖子,想給自己一些安慰,發現大多數受害者消極甚至絕望,她越看越壓抑,就在家暴話題下寫下自己報警的經歷,想鼓勵大家維護權益。
2月中的湖北荊州,凌晨四點多,哥哥還在隔壁玩電腦,笑得肆無忌憚。睡不着的達爾衝進去問,你睡不睡覺?她念高三,當天還要上網課。哥哥說,哦,那又怎樣?達爾盯着他不動,哥哥平靜地看着她,靠近,勒脖子,一直使勁往裏拖,想關上門。掙不脱,達爾只好不停踹門。祖父母聽見聲響過來拉開,之後以大晚上別吵到鄰居為由摁掉達爾的報警電話。過了很久警察才穿過封鎖,說哥哥的行為已構成家暴,下次要第一時間報警,特殊時期不能把他帶走。調解後讓他寫下保證書。
父親在北京打工,因為疫情春節無法返鄉。哥哥放寒假就回來同住,剛開始還客氣幫忙,久了就關上房門對着電腦,早上睡,下午醒。他常感到被打擾或嘮叨,一週能吵好幾次。前不久爺爺說不如現在就把我收拾了,免得以後再煩你。爺爺拿起菜刀,推搡時手被割出一手血,報警後他手機被哥哥摔碎。奶奶在門口把警察勸走,不了了之。隔天二老照常叫哥哥吃飯、温柔夾菜。
跟哥哥對打時達爾只想着同歸於盡,「我信奉一句話,都是第一次當人,憑什麼我要讓你?」達爾還是輸在力量上,但她不服。沒有更多或者更激烈的方式能讓達爾閉嘴,大她兩歲的哥哥只好停手。他三歲才開口,不愛說話。那時家裏人怕他是個啞巴,讓達爾事事讓着他。達爾不被關注,自己拿火鉗玩,哥哥搶不過,把火鉗伸進灶膛的柴火裏然後往她臉上燙。右臉的疤痕留了很多年,沒錢看病,直到前段時間才在醫院用激光去掉,一時血肉模糊。12歲生日前,達爾跟哥哥在沙發上打架被他一腳踢得手骨折,短暫回家的母親——「她,拿一個詞來講,叫拋夫棄子」——只是邊擦藥邊罵了哥哥幾句。都說是不懂事,沒人追究。
家鄉重男輕女觀念牢不可破。後山一塊地裏常放着女嬰,路過的人願意養就抱走。有一回祖父母去地裏,一個女嬰身上已經長了蛆。
哥哥說沒人真對他好,都偏袒妹妹,以父親離婚、長輩的體罰和被送到武術學校的事為自己的暴力辯護。「難道我不是嗎?」達爾說那是渾噩的藉口。老家在重慶深山裏,直到近幾年才修了路。達爾剛出生時黑瘦,走親戚被問這是誰家孩子,母親總說反正不是我家的。原本有個漂亮的大姐,活了52天夭折,直接埋了。計劃生育時生下達爾發現是女孩,是祖父母求着才留了下來,他們迷信達爾在那時候降臨是她命好。
家鄉重男輕女觀念牢不可破。後山一塊地裏常放着女嬰,路過的人願意養就抱走。有一回祖父母去地裏,一個女嬰身上已經長了蛆。
小時候,家門正堂掛着一根長竹片,專打達爾用的,每次躲到隔壁祖父母家的桌子底下還要被拉出來打。不知道怎麼為不公平的事情爭取,比如被分到比哥哥更少量的麪條,還想要,母親說你自己這一點都吃不完還想要更多的?非要,就會被打。哭了只有父親會哄,內衣睡衣都是他買。想跳皮筋,父親取下摩托車後備箱上沒什麼彈性的皮筋給她。哥哥一直記着這事,說父親偏袒她。
哥哥生出來就白白的一團,可愛,討人喜歡。10歲開始沉迷網吧,拉着達爾去那兒讓她看動畫片,變成共犯就不會找家裏告狀。一次趁奶奶高燒說要拿錢去買藥,拿走500塊一天花完。那是奶奶在市場剝蒜一小袋一塊五、六十來歲的爺爺給人搬運貨物攢的辛苦錢。被發現後撒謊說被人勒索,爺爺捆住他,父親拿皮帶抽他。家人都沒耐性。打一頓他能安靜一段時間。
年長一些,哥哥折斷父親打他的棍子並丟掉。有時講不到兩三句話,就突然摔門而去,接下來不是吵架就是父親打他。管不住就送去了北京的全寄宿制武術學校,跟別人打。為了高考,父親又花三萬多塊將他轉回老家最好的高中唸書。總之是有求必應,家裏任由他挑最貴的電腦,再給配上高價散熱器和鍵盤。一管家裏要錢祖父母二話不說就讓達爾幫忙轉賬,因為祖父母不熟悉手機轉賬操作。逢年過節哥哥都能薅上幾百。達爾生日那天,奶奶還讓她給哥哥發兩百塊紅包怕他沒人照顧。
達爾曾經建議父親不要過多干涉哥哥上網,勸說愛上網是青春期的一種現象。哥哥想學動漫設計,家裏人覺得沒前途不讓填志願,達爾跟父親聊了三天說服了他。愛,甚至是情緒,都在拳腳中被消耗光。現在無論他講什麼,達爾扭頭就走。「沒人治得了他,無法無天。他至少還能欺負我,在他的概念裏,應該叫理所應當。」
家人對哥哥不抱期望,只能要求達爾讓着點,不要起衝突——她聽着刺耳。只有聽話才能換來家裏人的好,要是吵一次,就被說白養你了,沒教養。解封的時間一天天延長,哥哥更礙眼了,每回都在飯桌上高談闊論,從沒買過菜的他大談蔬菜買賣,發表對疫情的看法。達爾情緒低沉,大把掉頭髮。武漢連日陰雨,白玉蘭開了,可外面還是一片狼藉。達爾只想要靠考學離這個家遠一點,像逃離兒時所處的那個小山村。
父母被撮合結婚,母親跟祖父母間齟齬不斷。為了讓家裏太平一點,兩位半百老人收拾行李去被稱為「小上海」的湖北荊州。在親戚介紹下,在繁榮的江邊碼頭上一個大型批發市場裏幫人卸運貨物、剝蒜。達爾四歲多那年收成好,母親去鎮上賣菜,趁此離家。達爾感到解脱。八歲時母親回來,只為了辦離婚手續。有一年達爾高燒,獨自在家不省人事,直到被鄰居發現打電話叫回父親,祖父母聽聞後連夜買船票接倆小孩到湖北生活。房子是姑姑買給他們的。姑姑「灌輸思想」,告訴她很多事情都沒必要計較,女人必須要自己奮鬥。
「她前幾年什麼都幹過,發奮就因為想着還有侄子侄女離開了父母、住在一個破屋子裏等着她。後來不想給別人打工了,去北京自己開店。她很漂亮,在山裏的時候別人都勸爺爺奶奶把她嫁掉,姑姑求他們說要去上學,爺爺到處湊錢送她念書。讀完之後她說要出去看看,去哈爾濱當服務員、職員。待了五年之後有一回問家裏人,要不要也去城裏發展。家人商量了一下,就讓我媽去城裏打工,我剛滿一個月。」達爾說。
「姑姑教我媽穿衣打扮。後來我媽賺錢悄悄買了一個手機,但不接我爸電話。可能是一個女人經過城市裏的喧囂看不起以前擁有的某些東西了。有一回接通了不知道說了什麼還把我爸電話掛掉,我爸特別傷心,找我姑姑哭。我姑就把我爸改造了一番也讓他去城裏,他變得時髦了一些,她才跟我爸見面。
「後來他們提醒她還有兩個孩子在老家那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裏,就說你回去照顧他們吧。我媽不樂意,說要跳樓。姑父把她拉下來,後來找了一些人把她強制帶回去了。待了幾年,她還是跑了。如果我看過外面的世界,我也不願意被關在那樣一個地方。
「這個話題在我家不好惹,一提起就爭吵。她剛走的那段時間,奶奶對她恨之入骨。拿奶奶的話說,一口一口咬死她的心都有。現在哥哥從她手裏拿錢的時候開心且親密,事後就常不接電話。她問我哥哥近況,我懶得理她。」

「難道這是個發微博求助更有用的時代嗎?」
肖美麗向范范介紹了反家暴志願者林爽,讓她提供幫助。2012年因為李陽和Kim的家暴案(編註:2011年,「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的妻子Kim在微博上曝光李陽對她實施家暴,並公布數張照片。法院後認定李陽家暴行為成立,准予李陽和Kim離婚,李陽向Kim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財產折價款1200萬元),作為kim助理的林爽關注到中國的反家暴議題。反家暴法尚未實施時,個案推動困難,林爽陪同受害者去派出所常被告知,回家好好跟老公商量。
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後才會報警。
范范的訴求是家暴者得到懲罰、警方道歉及有相似遭遇的女性能從她的經歷中得到借鑑,林爽告訴她警方可能的處理方式和對策、她可爭取的權利,也觀察到她的反覆——對自身安全有所顧慮,猶豫是否要接受採訪、推進事件的討論。
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范范說男友醉酒後在次日凌晨想與她發生關係,她沒聽從,男友惱羞成怒毆打她。男方告訴南都記者,女方先扇他耳光耍酒瘋、兩人互毆,調解時曾提出賠償,但女方要求一次性賠償十萬元,要麼就走法律程序。男方認為這有惡意敲詐的嫌疑,「她扭曲事實,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男方做完筆錄後不願此前所言被報導,問記者這事多長時間熱度才能消退。記者問范范,為什麼要十萬塊。一改之前電話中的直白,范范停頓了很久,說她不想接受調解,於是提出這個男方無法答應的條件。
在林爽看來,在涉及親密關係或者婚姻的案件中,公權力系統傾向於使用調解制度,調解之下做出更多妥協的是受害者,有時施暴者沒有做出任何犧牲就能逃脱應有的法律處罰。至於賠償,「她的原意是提出大金額賠償讓此事無法用金錢解決,就算是要提出金錢賠償,那又怎樣?做錯事情總需要受到處罰。打一個可能不是很正確的比方,李星星的案例報導中,記者專門說,當事人一邊收鑽戒,一邊報案,這能證明什麼?對性侵的界定不會有什麼改變。」(編註:2020年4月,中美兩國執業律師、曾任中興通訊獨立非執行董事、傑瑞集團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的鮑毓明被指性侵未成年養女李星星三年的案件經由《南風窗》等媒體報道後引發關註。4月12日,《財新》發布特稿《高管性侵養女案疑雲》,采用大量鮑毓明單方提供的材料,導語稱,「這更像是一個自小缺少關愛的女孩向『養父』尋求安全感的故事」。報道引發極大爭議,當天被撤下。次日財新網發布聲明,稱「報道確有采訪不夠充分、行文存在偏頗之處」。)
「大家都不得不求助網絡,其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反映現在公權力介入的力度或者有效性不夠。」
如何判斷當事人所言的真偽?「首先站在相信受害者的立場,如果有實物上的出入再去跟她求證。至少我從未遇到有女性專門為了所謂的毀掉一個男性而找志願者幫忙。在性別暴力一事上,不管受害者最終是否得到公正的處理,她所受到的傷害都深刻且久遠,包括尋求公正處理中受到公權力、輿論的傷害。如果這樣權衡,(編造)是很不划算的一個生意。」林爽說,「從大的性別背景上來看,家暴事件中男性施暴佔90%以上,考慮女性求助的心理門檻和現實門檻,我們站在女性這一邊,天平才稍微平一點。」
林爽認為,服務受害者的難點之一是一旦遇到不太作為的公權力,事情難以推進。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後才會報警,如果還要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去督促公權力機構,很多受害者在這一步就停下來了,因為成本太高或者自身習得性無助。還有受害者的複雜心理,做決定要經歷多次反覆。需要志願者有同理心與耐心。范范案件的特別之處在於,短暫的戀愛暴力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同情並被認定為家暴,公安機關開始的處理不恰當但後期能夠積極作為,能作為其他公安機關的警示和參照案例。
接受採訪的三人無一例外提起網上求助後收到女性們私信、評論給安慰和建議,在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的創始人李瑩看來,「大家都不得不求助網絡,其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反映現在公權力介入的力度或者有效性不夠。」而網絡求助的門檻對女工而言更高,要會發聲、知道有流量的平台、有強敏感比如取證。

尾聲
范范告訴端傳媒,工作單位與男友的勞動合同關係已經解除,但要等行政復議結果才能作出相應處理。
岳越第一次開庭不順利,丈夫爭奪撫養權,即便有照片,丈夫也否認家暴行為,說不能證明是他所致。「小地方就是這樣,開庭感覺吊兒郎當不正規。他委託的本地律師似乎跟法官很熟悉,庭審間隙跟法官用方言聊天。」她問記者,「難道這是個發微博求助更有用的時代嗎?」一審後雙方協議離婚,岳越撤訴,拿不到撫養費和其他賠償。孩子撫養權歸岳越,但平時孩子由前夫家庭照看。律師不願接受採訪。
達爾刪掉了哥哥的聯繫方式。武漢解封後,祖父母依然早出晚歸辛勤工作,不問緣由地讓達爾給哥哥轉賬。次數多了,餘額漸少,奶奶問達爾,錢怎麼少了?達爾感到被懷疑。近期親戚來家裏,坐了片刻,問爺爺,兄妹關係是不是不大好。爺爺說達爾曾經報警想讓警察抓走哥哥,沒提家暴一事。親戚笑了一笑。在達爾眼裏,他們是在聽一個小題大做的笑話。達爾不願意再跟家裏人提起家暴怕再生不愉快,也不想他們接受採訪,她想讓事情塵封。
應受訪者要求,范范、岳越、達爾、張琦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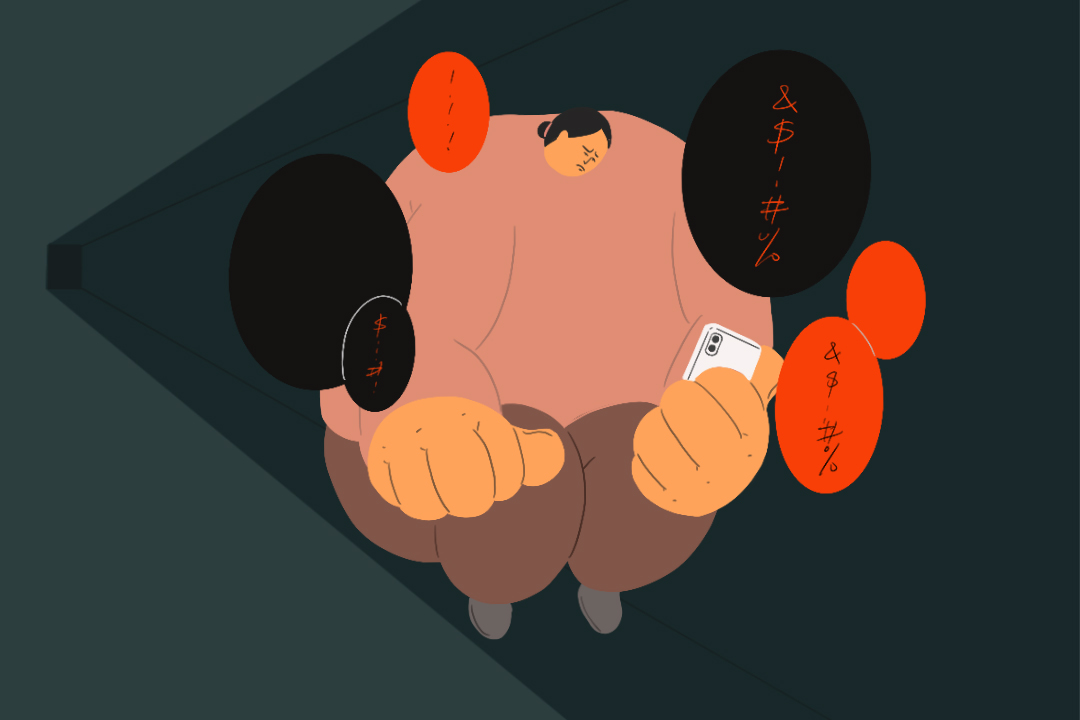




正是因为有觉得一切咎由自取的男人,才再三提醒了女性,一定一定一定要自强独立,擦亮眼睛
我連個對象都找不到,或者說不願意找。往後若有異性伴侶,會不會家暴她,我不太確定。或許他們是冤家路窄,不得不互相傷害……還有,我覺得我之前的人生遇到過很多比我壞的女性,有一些不壞或者壞的女人像是更願意尋找壞的男人交往,這世界有時就是那麼的神奇,一切或許都是咎由自取。
看完文章的感受是:家暴行为如果不能被及时中断就会是旷日持久的恶性循环。
別忘了語言暴力。
引人入勝如小說的情節劇情,在擱下手機的同時才意會到看的不是文章,而是被生活攪爛的各個靈魂。
看完只觉得触目惊心,幸好还有志愿者的努力和网友的关心,让这个冬夜显得稍微有了一点温度。
無能為力的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