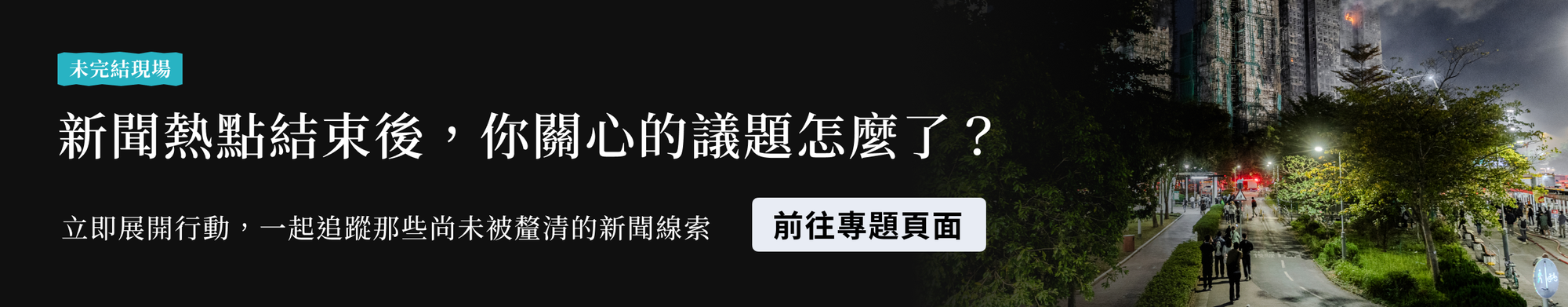速遞 Whatsnew
更多
編輯精選







/
僅限會員
失落的熱帶:香蕉種植園和不屬於這裏的人
這群中國人和越南工人,是兩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進程擁有相似處境的人。種植園將他們放置在了同一時空,是同樣沒有保障且不確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選擇,是背井離鄉過一種農民生活。

解讀
更多
評論
更多



/
僅限會員
評論| 十年《怪奇物語》:以懷舊為名,以迷因爲媒,串流時代一場大型召喚儀式
《怪奇物語》以懷舊為主調,但指向經驗匱乏時代的地下幽暗源泉,鼓勵指南針壞掉的邊緣者冒險,只留下一條規則:別讓奪心魔剝去你的好奇心。

系列
更多
欄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