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前告白]生命中那些不可捉摸、不停變幻的形而上或下的情感與性感。

「美,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可怕是因為無從捉摸,而且也不可能捉摸,因為是上帝設下的,本來就是一些謎。在這裏,兩岸可以合攏,一切矛盾可以同時並存。理智上認為是醜陋的,感情上卻簡直會當作是美。美是在索多瑪城裏嗎?」
多年以後,移居南方之城,在費心打造的、真正屬於自己的、擁有窗外一片田園風光的小書房裏,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一部第三卷第三節「熱心的懺悔」(詩體)時,簡直驚呆了。見到人性真正相通相切相對撞的部分,那原是偉大的探索者共同的興趣愛好。
世俗之謂、理智之謂,恰是最無形又最霸道的美的界定者、殖民者。誰要想移開哪怕一點點目光,探尋到一點點光,也是千重萬阻。性向上的少數,撇開權利爭取之必要,何嘗不是被額外賦予了一種捉摸美、拓闊性情的任務。追求那情感與性感上「可以合攏的、一切矛盾可以同時並存」的美,為此,哪怕降落到被視為等量齊觀的索多瑪城,也是心甘情願的。
有一次,在大嶼山長沙海灘的友人婚禮上,喝得醉醺醺之際,一堆人圍起來,樂呵呵。在暗夜的吵雜的海風裏,憂鬱怕醜的文青歌手 P,突然溫柔而嚴肅地問:「郁翔,你最喜歡的作家是哪一位?」
我知道屬同一星座的 P,這種時候其實是比平時更清醒的,是過了很多年之後都會記住那個問題和那個答案的氛圍。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於是很認真,快速而莊嚴地答道。
P 似乎滿意的沒有接話。彼此知道,雖然絲毫沒有理智或世俗的價值,但在感性或美感上,這曼妙的交會卻很重要。
世俗之謂、理智之謂,恰是最無形又最霸道的美的界定者、殖民者。誰要想移開哪怕一點點目光,探尋到一點點光,也是千重萬阻。
心裏暖暖的,對着大嶼山的海,我想起,無論從哪裏走到這裏,有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跨進大學校門,一種被放逐的感覺撲面而來。這是過了長江大橋的新開沒幾年的分校。所謂分校,就是慌亂的市政規劃配合混亂的經濟規劃,胡亂的在郊區批地開發。因為有政策優惠和經費補貼,大學城的模式很快風行全國。
石頭城大學尤其積極配合。七十年前,老校長、五四新青年羅家倫,親手訂定在紫金山麓新校區的宏偉規劃圖,不幸因日本侵佔南京而告終。到了1952年,文理學院和工學院更慘遭肢解,學脈留在文理,但搬入剛遭停辦的教會名校、賽珍珠任教的金陵大學。從此以後,「金陵」兩字因為代表着民國遺緒,也遭禁用,卸甲歸田。
有了身世的原罪,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它的校長仍然保持由民主黨派擔任的傳統。美其名曰統一戰線,實則放任自流。幾十年的打壓,讓渴望拓展校區的石頭城大學,樂意跑到郊外開墾荒地,十年建設,寧願每天校巴接送老師來回城郊、每天過江上下班。因而到了晚上,整個新校區,只剩下一群青春十八九的少男少女。這一回,連可怕的舍監也省去了。
但奇怪的是,這裏並沒有出什麼差池。無政府狀態對於年輕人,原是再適合不過的。
每個宿舍四人同住,在荒郊野外的建築群裏,更容易過得像一家人。比起高中,住宿條件好了很多。兩年的時間,有廣袤荒蕪的山腳平地,光禿禿的水泥地,一人高矮的行人樹,人工開挖的水塘還沒來得及種下荷花,一切都是原始初開的。
樣樣都不害羞,美的形態各異,頭上只有天空,腳下的路卻全憑自己去走,難道這是多年壓抑困頓的煉獄之後,我的天堂之路?
這裏的同學卻很不同。南北交會,大氣,恢宏,各樣標緻、各種神情都有。一個人就是一棵樹,這倒是與此地風物相匹配的。
難道,這裏就是無人管轄的、我的青春的索多瑪城?樣樣都不害羞,美的形態各異,頭上只有天空,腳下的路卻全憑自己去走,難道這是多年壓抑困頓的煉獄之後,我的天堂之路?
四口之家,能有許多故事和恩怨情仇。但在此之前,惶惑的我去了開放給新生的心理輔導公開大會診。
「我很困惑自己喜歡的是男生。」
「沒關係,這是許多人都會有的,青少年成長的一個階段。」
那個穿着白色醫用長褂的慈靄婦女臉上,明顯露出了尷尬。
但我知道,自己的試探是值得的。首先,她沒有把它視為一種病了。其次,她重重的關上了另一道門。這衝突會製造一個新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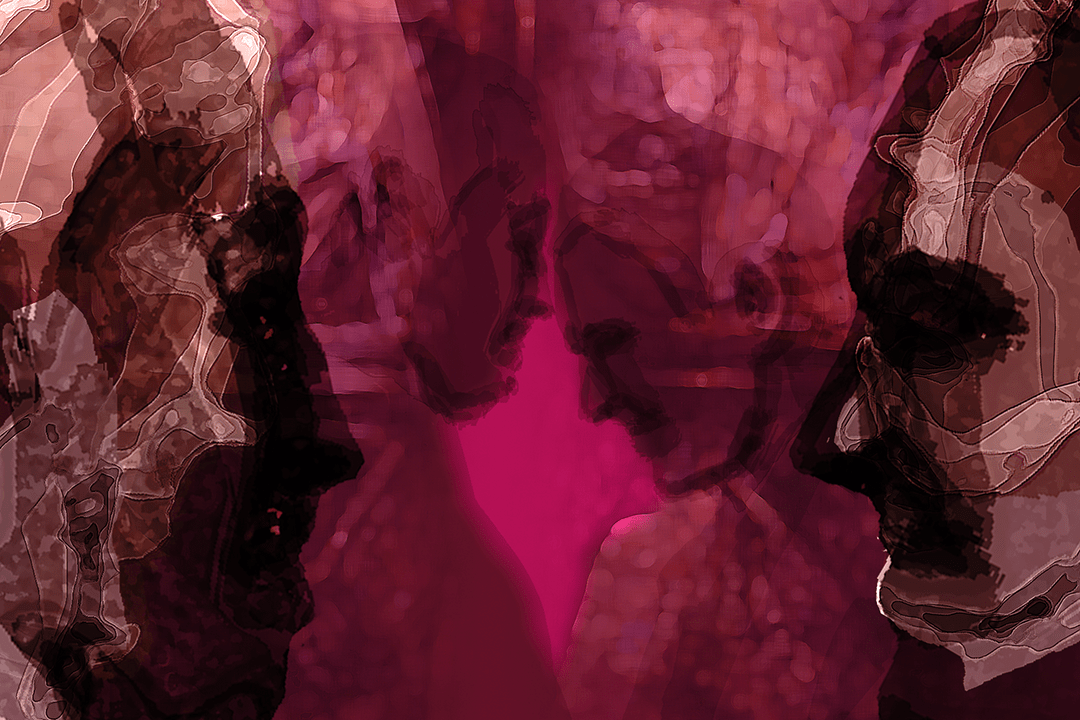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