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警察跪壓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致死以來,示威遊行和暴動在美國全境逐漸升温,警民對峙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國民的威脅也日益嚴峻。是否應該支持非裔的基本人權訴求、是否應該對警察使用暴力加以限制、在廣泛的民意訴求和被獨夫趕上街頭「戰場」的武裝之間如何選邊——這些問題無論在通常的左或右、平等或自由、激進或保守的框架之中本來都不該是問題。
但是,美、中、港的很多論者自動地首先把問題放在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框架中理解,讓它成為了相當大的問題——非裔作為美國公民的身份,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高於其作為自然人的身份,因此他們基本的生命權力放在美國複雜的對外衝突語境中,就變得曖昧不明瞭。

撐民眾還是撐國家?民族國家框架下不是問題的問題
全球化的確讓「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們有關」,但聯繫「他們」和「我們」的不是共同的苦難,而是各自所屬國家之間的衝突,素不相識的「他們」和「我們」的關係不是休慼與共,而是你死我活。
中國大陸的官媒自然選擇在新冷戰的語境裏討論這個問題,迫不及待地接住美國「遞過的刀」。胡錫進、華春瑩等代表官家聲音的個人和《人民日報》等官媒,均不遺餘力地諷刺美國「雙重標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方面官媒批評美國的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醉翁之意顯然不在美國本土的歧視,而在美國就香港問題對中國的指責;另一方面,頗為自相矛盾的是,官媒也「祝賀」美國部分示威者和趁火打劫的路人搶掠縱火的行為形成了「亮麗的風景線」,渲染治安混亂,試圖合理化警察暴力。胡錫進更是對港人提出了他自認為的「送命題」:香港示威者是和抗議警察暴力的美國示威者站在一起,還是和揚言暴力鎮壓的美國特朗普政府站在一起?
的確,部分港人同樣首先把反歧視暴動放在國家博弈的框架中理解,或者由於視美國制度(而非美國人民)為「自由燈塔」而同情美國政府,或者希望共和黨政府連任,以便繼續對華的鷹派政策,總之出於種種功利目的而選擇不支持和自己有類似命運的美國人民,於是也就難免讓自己的運動被北京指責為「虛偽」。
但其實,這個問題對於大陸主導公共話語的國家主義民眾,尤其是「小粉紅」來說才是真正的「送命題」——如果他們支持美國政府,則顯然認同「對家」勝利就是讓「自家」吃虧;如果他們支持美國抗議群眾,則在根本上違背了為中國強硬的國家主義提供合法性的國家主義原則,尤其是「主權高於人權」這一條。
於是,既憎恨美國也憎恨「暴徒」的小粉紅們在社交媒體上經歷了幾天的混亂後,最後達成的一致態度是吃瓜看戲,希望對方兩敗俱傷。微博超話#美國暴亂#中,諸如「美國警察不要停,繼續澆油」、「美國風景真挺好」、「超級大國不是吹的……傳染病毒也能搞個世界第一,暴亂再來世界第一!哈哈。」這樣的嘲諷基本佔一半比例,確是「一片歡呼」。甚至有少數華人在社交媒體展示自己趁火打劫商鋪的成果。至此,他們的行為已經不是基於某種具體的或對或錯的政治原則,而根本就是基於毫無原則的犬儒主義之惡。
這些討論中的悖謬,尤其是悖謬孕育出的純粹邪惡,讓善於反思、尤其是關注香港鬥爭的人進一步意識到國界線內部、人民追求基本權利的鬥爭和國家之間的博弈之間痛苦的關係:全球化的確讓「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們有關」,但聯繫「他們」和「我們」的不是共同的苦難,而是各自所屬國家之間的衝突,素不相識的「他們」和「我們」的關係不是休慼與共,而是你死我活。
民族國家和其人民的利益時常是不一致的——這原本是句廢話,但在現行框架中,他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成為了國家、機構、和民眾思考和行動的前提。
在美國這次示威暴動中,國家與人民利益的相悖和相關被鮮明地暴露了出來,然而這絕非偶然情況。幾乎在警察暴力發生的同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鑑於香港已失去獨立地位,美國應停止給予香港特殊經濟待遇,並同時強調「我們和香港站在一起」。雖然這種「站在一起」的方式十分諷刺,對於香港民眾的生活實際上更是打擊,但亦有攬炒派認為這種「同歸於盡」式犧牲是大國角力之下香港唯一勝算。1989年的「六四」運動代表了「攬炒」的另一種可能。在政府鐵腕鎮壓群眾後,包括美、加、日和歐共體成員在內,以西方為主的大量國家對中國實施凍結貸款、停止出口、中斷政治、經濟、軍事合作乃至一切外交往來等制裁,使本已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快速陷入滯脹。大量原本抗議政府魚肉百姓的民眾在國家宣傳部門的強力鼓動下,轉而仇恨「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勢力,結果中共的統治非但沒有被動搖,反而更牢固了。
這種調轉人民槍口「一致對外」的做法在政治學領域叫做「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大致譯作「團結在國旗周圍」效應),大意是通過將國內矛盾上升為國際矛盾,利用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感和與國家利益的被動綁定,來將他們對政府的不滿轉變為擁護。歷史上,大部分針對某國暴政的國際制裁,都被這個「rally' round the flag」化解,只有在極少數毫無民族認同的國家,如實行異族統治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等,這一策略才不會成功。
上述現象,無論是港人「務實」地支持美國政府、小粉紅在「送命題」面前左右支絀、還是抗議本國政府的人民面臨在外國制裁時被迫(從思想或至少從實際利益上)和本國站在一起⋯⋯都反映出一個事實:民族國家和其人民的利益時常是不一致的——這原本是句廢話,但在現行框架中,他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成為了國家、機構、和民眾思考和行動的前提。無論民眾是支持還是反抗國家,都逃不出這一前提的五指山,在兩種情況下,可能受益的只有國家,可能受害的只有人民。

民族國家:唯一的主體?
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被迫無限期綁定,其深層次原因,是在現行國際秩序中,民族國家是唯一合法政治單位和行動主體,而人民缺乏任何主體性位置。
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被迫無限期綁定,其深層次原因,是在現行國際秩序中,民族國家是唯一合法政治單位和行動主體,而人民缺乏任何主體性位置。這一點,學者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的論述已經獲得各界(儘管基於不同立場)的承認。目前最重要、最有力的、關乎關税、貿易、人口、資金、武器等重要「資源」的國際行動,例如援助、借貸、制裁等,實施主體是國家,接受對象也是國家。同時,人們的政治立場、經濟利益、文化認同也首先依附於國家。問題在於,「國家」這個龐大、成份複雜、定義含混的機構是如何擁有主體性(agency)的?
首先,不消說國家是沒有意識的。大陸的讀者應該都很熟悉「中央決定了,你去xxx」或者「組織上認為xxx」這種話術,也肯定明白這些發出動作的主語大抵就是某個或某幾個領導意見的綜合之意。
其次,民族國家不是,至少不單純是成員意志的總和。它不僅在客觀層面不是——否則就不會出現前述所有矛盾、不會出現主宰大半個地球的強權,所謂「民主」國家中也不會有操縱選舉、綁架民意的現象出現;並且在人們的主觀認識中也不是——儘管很多小粉紅會未經反思地認為「祖國爸爸」一定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們管祖國叫爸爸的行為本身,已經說明他們感知到了祖國對自己的外在性和權力關係,只不過一廂情願地認為這個外在的、有權力的父親一定會為孩子付出一切。
儘管在2020年人們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起源還是眾說紛紜,但幾乎沒有學者仍舊認為國家是社會契約的產物。無論源自宗教戰爭、資本原始積累還是海外殖民,國家都鮮明地表現為邊界的建立和權力的集中,並且前者服務於後者。立場不同的學者(如蓋爾納Ernest Geller、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大都承認:現代的民族想像依附在國家秩序之上,民族認同搭建在國家造就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壁壘上。無論具體的個人是否有相應的民族認同,「民族」國家都會降臨在他的頭上。
在此情況下,人民無法讓自己的利益和行動與國家脱鈎,因此也很難有和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只能在客觀上與國家結成「命運共同體」。不只是無權無錢的普通人,即便大資本都不得不依附於國家——如今資本主義和國家日漸密切的關係,已經演化為國家政策為資本運營設置門檻。新冷戰對全球市場的區隔整體上違背了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既讓華為步履維艱,也讓臉書屢次入華失敗,讓貿易戰中頂風在中國設廠的特斯拉左右為難。當「國家」成為世界絕對的話事人,曾經積極促成這一局面的資產階級就的確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那麼,到底是誰在驅動國家主體意志,誰從國家爭端中獲利呢?當然,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各國的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同時,從爭端中獲利的還有整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以及國家這個抽象概念——不抽象地說就是各國目前政權的存續。
「Rally‘ round the flag」能屢試不爽,這就提示我們國家民族主義在國際對抗的話語中才是最有效的。沒有任何機制保證國家在平穩發展和國際合作中獲得的 GDP 一定能讓共同體人民「一榮俱榮」,可是國際對抗帶來的損失,一定會讓共同體人民「一損俱損」。
「Rally‘ round the flag」能屢試不爽,這就提示我們國家民族主義在國際對抗的話語中才是最有效的。既然國家並不代表人民意志,也沒有任何機制保證國家在平穩發展和國際合作中獲得的 GDP 一定能讓共同體人民「一榮俱榮」,換言之進步不容易展現國家共同體存在的合法性。可是國際對抗帶來的損失,所有賠款、禁令、退單、制裁,一定會讓共同體人民「一損俱損」,損失的迫在眉睫更能讓危機顯示出強大國家存在併為國民減少損失的必要性,從而迎來它的高光時刻。因此,大陸「必須」要有「百年國恥」教育、要有「多難興邦」、要有仇恨動員和戰爭威脅,「有困難要上,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以便為國家的存在輸血,讓它在面臨共同威脅的國民面前呈現出正義的保護姿態。
在這種情況下,靠衝突維持自身合法性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好比大陸企業破冰、高校O'CAMP時常玩的「修長城」遊戲(一種信任遊戲):若干人圍成一圈坐在椅子上,每個人都把上半身倒放在身後人的大腿上,這時撤走所有椅子,這些人就完全靠身體的相互支撐懸在了原有位置上。與之類似,國家就是靠相互的敵意、衝突維持着共享的體系。這個體系儘管最初可能建立在某種普遍利益基礎上,但現在這個利益基礎已經愈發空虛。中國政府指責的「雙重標準」當然並不是美國特色,小粉紅答不出「送命題」也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一切自相矛盾都是「國家」題中應有之義——互相為敵,本身就是對共同的生存體系的維護。
因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斷言:如果中美的新冷戰持續升級,中美兩國和其他相關國家的民眾、企業都不會獲得什麼好處,只有兩邊的「國家」概念,和實際上承擔這一概念的現存證券能夠從中漁利。

國家興亡,永遠的輸家是人民
去殖民地鬥爭中國家民族主義的合法性是首先建立在反抗既有「命運共同體」而非構建新「命運共同體」上的——大部分新興民族國家的人民並沒如約當家作主。
必須承認,民族國家和驅動其建立的國家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確起到過積極的作用。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覺醒讓統治者不再毫不負責地將民眾僅僅視為剝削税收的對象,而開始和自己的領土建立更密切的聯繫;19世紀一系列拉美國家獨立、一戰後小國的獨立地位和殖民地的人權在文理上獲得「威爾遜十四點」承認、二戰後期殖民地紛紛擺脱奴役,獨立建國……這些顯著有利於保障人民生存和發展權利的成果,背後亦有民族主義的熱情支撐。「只有建成國家,才能保護人民」,一定程度上也曾經成立。
然而,去殖民地鬥爭中國家民族主義的合法性是首先建立在反抗既有「命運共同體」而非構建新「命運共同體」上的——大部分新興民族國家的人民並沒如約當家作主。新成立的主權國家中,和舊社會一樣的權力秩序仍在滋長,新晉「獨立」的人民仍然會被民族主義抽空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權利。新的共同體對國際體系的依賴、對爭端與對抗的依賴和來路不同的歐洲民族主義並無本質區別。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先驅,弗朗茲·法農在遺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曾經提醒後來者,民族主義的意義在於「破」,而若要實現「立」,則需要超越性的新精神。民族主義的最後階段應當是超越民族主義、超越勞苦大眾互相的敵對和隔膜。然而很遺憾,這一階段至今未能發生。
國家民族主義走到今天,其實已經抵達了自身邏輯的極限——不同民族國家的利益佔滿了整個地理空間、倫理空間和思維空間。正如本文開頭提到的,人們無論被綁架得多麼痛苦,都難以想像(更別說追求)超出國家利益之外的利益、超出對抗正義之外的正義。最後的必然邏輯結果就是:只有敵我,沒有對錯。個人和團體都必須在邪惡的敵人和正義的我方之間選邊或被動選邊。用毛澤東幾乎一個世紀之前的預言來說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互相對抗的民族國家體系對國際秩序的主導,以及民族國家的唯一主體性,最直接(但不是最嚴重)的後果之一是:國際主義援助無論對於被援助者還是援助者都不可能。一方面,援助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間時常隔着後者的國家,針對國家層面之下對象的援助會被視為對該國主權的侵犯。大陸一貫喜用「接受境外勢力資助」來污名化國內的民間社團,屢試不爽,如今美國的一些共和黨官員也有樣學樣地用同一理由給示威民眾潑髒水。
在國家間白熱化的對抗中,國民利益實際上消失了——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利益最後都被整合為國防利益,在無盡之戰中減少損失的「利益」。
另一方面,這種污名之所以有效,不止因為它穿透了被援助國的國界,還因為援助者的確不能超越自己的國家利益進行援助,而在對抗模式中,敵人擁護的就是我們反對的。例如1992-1993年,美國和聯合國曾試圖對索馬里內戰中的饑民進行人道主義糧食援助,然而援助行動遭到當地軍閥抵抗,美國部隊損失20人(史稱「黑鷹墜落」事件)。美國本來在索馬里地區的利益就不多,在本國輿論的壓力下立刻撤出軍隊,維和行動旋即失敗,索馬里人民的境況至今未能緩解。次年,當盧旺達大屠殺在前殖民者的鼓動下瘋狂蔓延,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吸收了索馬里教訓」,加之考慮到盧旺達一無戰略地位、二無稀缺資源,因此未加干涉,致使100萬人在三個月內喪生。
如果說國際援助及其失敗仍是非常態事件,建立於對抗上的民族國家體系的更嚴重的後果,則根植於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中。對於國家,道理很簡單:只有「多難」才能「興邦」。如果不發生衝突國家就不能彰顯其合法性,它必然會製造永遠的危機、永遠的緊急狀態、永遠的戰爭。在此意義上,各個版本的「大國均勢」恐怕既難以達到,也並非所需。在國家民族主義的推動下,曾經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也發生了變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以「American First」為宗旨,早已放棄世界警察的角色。如果說當年六四期間滯留美國的中國公民尚能拿到「六四綠卡」,被捕的學生也能被美國高校錄取,如今陸港兩地的抗爭民眾則不應該寄希望於類似承諾會兑現。
這部分是因為在1989年的冷戰晚期格局中,「和平演變」中國有助於幫助美國打擊其首要敵人:社會主義蘇聯,而冷戰後,中國自己填補了蘇聯解體造成的「敵人」空缺,和平演變中國的努力就逐漸停止了。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競選期間就曾經宣布: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無論其意識形態是專制的還是自由的。而在2020年6月9日,布什家族的另一位年輕政治家,布什的侄子喬治·普雷斯科特·布什則高調宣布,必須支持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是唯一站在美國和社會主義(中國)之間隔開兩邊的那個人。」
可以看出,美國國內的政黨政治越來越依賴於對國家公敵的敵意展演,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打擊中國遠比「轉化」它的民眾更為討彩。何況,作為老牌帝國,美國雖然仍有海外利益,但整體上已經不再有明確的海外(而不單是中國)的「建設」目標,只有在短期對抗中為自己續命的考量。在這種考量中,作為敵方陣營叛逃者的普通民眾並沒有什麼利用價值,更難以在民族對立中被接納為「我們」的一員。而當續命成為唯一目標,對抗成為唯一手段,各區域霸主以民族主義的短淺目光行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其最可能的結果就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爆發,世界實現最終「核平」。
在這場引向毀滅的無盡之戰中,沒能獲得政治主體性的人民是永遠的受害者。從他們自身來看,他們的利益跟國家利益並不一致,但在遊戲規則中,他們的利益卻不再可能和國家利益不一致,因為他們的利益根本就是從國家利益中反推出來的。鑑於所有問題都被放在民族國家衝突、敵我對立的框架中解釋,對國家政權哪怕最善意、最輕微的批評都是服務於境外勢力、都是「遞刀子」。在尚未過去的肺炎疫情中,大陸公眾一度對作家方方的認同、對「吹哨人」李文亮的尊敬,最後都被「遞刀子」的罪名擊敗。
在國家間白熱化的對抗中,國民利益實際上消失了——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利益最後都被整合為國防利益,在無盡之戰中減少損失的「利益」。這「國防利益」如同一筆敲詐的債務,你從來未曾擁有但卻可以失去。為了避免失去,你先要交付一切,為了國家不會在敵人面前後退,你先要在國家面前一退再退。

為了還有明天,必須超越民族國家框架
在20世紀的歷史上,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抗爭嘗試,如支援西班牙的國際縱隊、越戰以來的歐美反戰運動大多在內外交困中夭折,只有民族主義作為最省力、最有效的動員方式在一切鬥爭中屢試不爽。
沉重的現實,毫無疑問是:即便意識到了民族國家體系的敲詐本質,也很難以一人之力、一城之力,甚至一國之力與之抗衡。如同傳說中會吞噬遇到的一切生物並把他們變成自己一部分的巨獸,民族國家體系會動用先製造危險再解決危險的策略,生成層層加碼的自證預言。在這個預言中,所有想要擺脱壓迫的人民必須用國家機器來對抗其他國家的敵意;大陸民眾對美國的仇視、香港民眾對大陸的仇視……一切民眾之間的仇視都完全合乎他們的利益。然而,其他國家的敵意和本國民眾的「利益」都只有在現存國家衝突的框架中才的確存在。被這些利益驅動着彼此為敵的民眾,就像是大逃殺類型電影中被編隊趕上角鬥場的「勇士」,他們的衝突是現實性的,但不是本質性的。
現實的刀懸在勇士的頭頂,逼他們按照遊戲規則互相廝殺。在你死我活的緊迫戰事中,試圖聯合他人修改或破解規則困難重重。在20世紀的歷史上,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抗爭嘗試,如支援西班牙的國際縱隊(最後被共和政府拱手送進法西斯集中營)、越戰以來的歐美反戰運動(難以阻止任何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爭,最後往往淪為在戰前為戰後重建募資的荒誕行動)大多在內外交困中夭折,只有民族主義作為最省力、最有效的動員方式在一切鬥爭中屢試不爽。
這也是二十世紀至今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日益鮮明的現實困境。如蓋爾納所說:應該留給階級的遺產最後留給了民族國家。無產階級本來應該聯合在一起,然而在民族國家的主導下,工人前所未有地彼此為敵,高喊「America first!」或其他口號,從彼此手中搶奪作為廉價勞動力被剝削的機會。就算搶到了這些機會,又有什麼美好生活等着他們呢?
但我們還是要意識到這種話語背後的陷阱,它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二十世紀直到現在,全球範圍內的民族自治沒有幫任何國家真正實現平等、健康的發展,卻的的確確維護了在充滿對抗和壓迫的體系中,許多統治者的位子。
我們都能感受到,民族國家的對抗體系難以超越,但它越難超越,就越有超越的必要。在目前,至少去思考和探討超越的可能,是作為大國小民的你我對自己負責、奪回主體聲音的方式。或許,在現有規則下,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能在利益上實現聯合,而只能更艱難、也更自覺地尋求倫理上的聯合,不讓勇敢的犧牲淪為壓迫者的籌碼。
或許,現階段民族/地區自治仍是團結起來反抗壓迫最有效的動員話語,但我們還是要意識到這種話語背後的陷阱,它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二十世紀直到現在,全球範圍內的民族自治沒有幫任何國家真正實現平等、健康的發展,卻的的確確維護了在充滿對抗和壓迫的體系中,許多統治者的位子。這個體系,如今已經過分龐大、無遠弗屆,你我都在它的腹中,實難突破,甚至連對民族主義的反抗也大多要在民族主義的架構下進行。
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需要拿出比響應民族主義號召時更大的熱情嘗試突破它,去嘗試、至少去想像一種民族主義之外的可能。只有如此,未來的個人才有可能不受國家脅迫地生存和發展;未來的人類才有可能比此刻更好更自由地生活。只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個未來。
(李大貓,韓大狗,中國政治、輿論觀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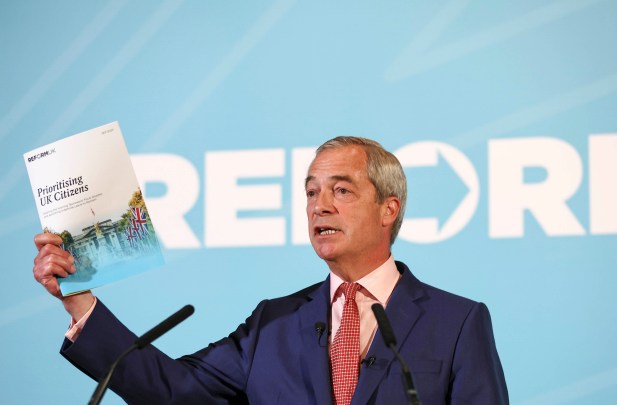

国际主义精神(注:非经济全球化)的落寞实在是让人无奈。而且似乎越发如此了。再等40年吧,或许必须令今日叫嚣让国民挨导弹来建构民族的闹剧完全退场让位给入殓师的画笔,才会从悲痛中开启下一轮文艺复兴。
这篇文章真的好,对照《国际歌》那句“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看得人心酸不已。
这钱花得值了……
就是对于六四之后民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不降反增之原因。就这样简单地归为宣传我感觉不妥,这里应该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這篇文章真的很好看!
@xzhang Virginia Woolf的三枚金幣就是以女性主義批評「國家」
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特别对于那些还在努力争取主体性的民众而言——今日公民基本权利尚未实现,现代国家遥遥无期,明日奋斗其中的民族国家框架就成了不义。民众主体性高的民族国家未必能走出这一局限,但主体性低的国家一定走不出这一局限(因不义更甚),因此对后者的民众而言,提高自己的主体性仍是当务之急。文章一直概称以民族国家,称其需要通过制造危机以彰显合法性,但我总觉得应该有国家例外于此(不知能否在欧洲的一些小国中找到例子),怀疑这一点是否是所有民族国家的性质。而国荣民未必荣,国损民一定损不正描述了统治阶层此时化公为私以利己,彼时转嫁危机于民众的过程吗——这显然是民众主体性低的国家容易见到的现象。所以超越民族国家在当下的行动,可以从继续提高本国国民主体性,使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不断进步上开始。如果说民众有可能不愿将自己的利益交给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那统治阶级更不会愿意。比如美国民众主体性够高吗?和他们自己遇到的问题相比显然不够。以上未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替代性选项,若民族国家性质如此,那民众主体性再高也无法阻止“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命运,但如果在民族国家内部尚不能实现较高的民众主体性,又如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成员意志的总和”呢。民族国家在逻辑上走到尽头和民族国家事实上走到尽头之间尚有距离,各个国家距尽头远近不一,有些国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尽头,但那些尚且遥远的国家还需要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走好自己的路。
很赞同作者前半部分的解读,尤其是“国内问题变国际问题”。最后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略有些隔靴搔痒。也无需提出明确方案,只是点出未来挑战,需要省思的问题、冲破的话语,以及这样的“全球主义”或是“国际主义”,甚至于“社群主义”的构想,和目前日益收缩的全球化趋势/愈加嚣张的保护主义之间的交互影响,就更好了。我想超越的起点可能是,重塑对于“普世价值”的共识和信心。但具体采取什么策略,联合什么力量,是我们应该继续观察和探讨的。
通过教育的方式传递“世界公民”的观念也许是一个办法?
端常有此般好文,不錯不錯
另外,我在想,国家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跟父权社会相关?我感觉在我见过的人中,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人,几乎永远是男性,特别是那种大男子主义者。民族这种跟血缘相关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跟男子气概与男权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如果父权社会的规则被打破,那么对于阿中哥哥之流的想象自然也就应该会消散,那时也许真的有可能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了。
相当难得的好文章。
我觉得不要去强求作者给出答案,毕竟这么大的问题草率地给答案才是不负责任。我所见到的最好战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他们其实真正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制度和价值是最正义的,而是那个其实与他们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国家利益,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国防利益。这样一个国防利益,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想象有没有更好世界的可能,而是恐吓我们如果不尽一切可能去维护现有秩序,就一定会带来毁灭。然而制造这种可怕后果的不是历史必然,而是民族国家自己。我觉得有些评论总是绕不出那个圈子,永远在"找灯塔",有的人找中国,有的人找美国。我从不相信这种做法最后会让人满意。找中国的,完全是眼瞎,可以无视发生在香港,新疆,还有其他地方的一切,这样的一个政权不去反对它,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找美国的,没有人注意到美国之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维持自由和平等,靠的不是美国政府的德行,而是美国社会里一直存在的质疑政府,反抗政府的人;而现在去支持川普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把自己在中国的那种思维代入了对美国的想象。现行的各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够幸免于文中说的国家民族主义,程度不一罢了。可能欧洲稍微好一点吧,毕竟吃过太多亏,但只是对比而已。
把当代中国与美国等等量齐观以所谓“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进行分析,说什么“两败俱伤”,看似理客中,实则根本不懂中国尤其是49之后的中国,抑或是装不懂,呵呵
接樓下,但是在這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的年代,不同群體之間的價值以及理念上的差異原來越大,社交媒體又為不同的群體創造了巨大的同溫層。全世界似乎已經不能接受這種要與自己理念南轅北轍的人一同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協調溝通決策的生活。最理想的情況當然就是講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國家打碎重構,讓不同膚色出生地的人依照價值理念重新組成不同的國家,然而這無異於天方夜譚。除非能把人的意識上傳到電腦方能擺脫現實政治一座又一座的難關。更現實的方法似乎是需要公民自身主動去接受異見,擁抱不同,主動溝通達成共識,但這也也不會是一條容易的路
樓下中國武漢肺炎提到普世價值應該凌駕於民族這一點,我反而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在全球化的推進以及全球各國普遍教育水平的提升之下。公民,特別是年輕公民似乎已經不太接受民族作為維繫同一個國家或者是整體的中心,也不太接納通過血緣文化傳統等建構出的民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具體的例子可以反映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年輕人主要為留歐派而老年人主要為拖歐派。相比之下現在公民似乎是更傾向以共同價值與理念作為包容與接納他者的評判標準。這有時便會出現寧願接納與自己價值理念相同的外族人也不願擁抱與自己價值理念相同的同胞。但是這一轉變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反而是與民族主義相互影響,有時甚至是需要借用民族主義的脈絡去推進。例如是港獨運動背後的香港民族建構就是在強調共同價值理念多於血統文化。台灣在蔡英文領導下建構的中華民國台灣也是通過強調在價值理念上與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差異去區隔自己。這一民族建構也是蔡英文在年初總統大選反敗為勝的關鍵。
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求仁得仁,倒不如说是文化左翼坐在树枝上砍树枝的结果。文化左翼到处搞自虐史观,结果就是解构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并导致了广泛的虚无主义。今天的美国乱局是《美国精神的封闭》所预言的产物,是《正义论》的产物。却不是《国富论》的产物。
作者最后还是落在找到更好的主义,追求更好的个人利益. 我的想法是 存在立场是因为对“利益” 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对. 资本主义哲学是人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寻求利润,从而达到某种效率最优. 社会发展需要所有人追求利益来推动. 我认为马克思没有找到更好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办法,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工具,用来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再抛弃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现在中国之所以发展快速,也是用上了资本主义核心哲学观念—发展要靠追求利益来推动.
是不是发展只能靠每个人追求利益来达到,现在看起来是的. 道家虽然提出过解决社会稳定的办法,那就是“老子”说的,从观念上放弃“好”和“坏”的定义,让大家安于现状. 但是他却提供不了发展的办法.
可笑了,不知道作者对于“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当作最国际主义的理想实践者呢?
是否把斯大林同志要求各国共产党”武装包围苏联“的政策当成国际主义?
是否把勃列日涅夫同志跨国镇压布拉格之春当作防止民族主义复辟的伟大尝试?
没有民族主义的分隔还是会有意识形态的分隔.说到底集体的出现出发点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个人利益,而需要某个集体站在自己立场去争取,可以是 宗教 ,性取向,性别等等,民族只是作为最强有力的集体,可以合法掠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捍卫自己的利益. 因此想要团结更多的人,本质上需要更多的利益. 如果人类哲学还在个人自由和私有化中打转,那么要团结全人类必须要能从另一个生物获取利益,或者人类整体利益收到侵害. 要么冲出地球,殖民外星,要么外星人入侵.
或许可以给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指明一个更贴切的名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如果喜欢古老预言,那么有一个预言场景正是敌基督骑着列维坦降临,乞求神圣许诺的代价就是抵达神赐的应许之地。怎么说呢,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可以算是求仁得仁。
这篇文章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很遗憾作者没能在最后有效的inspire我们对于一个非民族主义国家制度的想象。
不管小粉红还是民主人士,通过国际关系转嫁国内矛盾是常用手法,不是因为共产党这么做了就低级,而美国用了就高级,都是一种方法。
好文章!
一直不理解小粉紅那種「我就是國家」的精神狀態,本以為是因為他們生活裡沒有任何其他值得驕傲的事物而只好靠「國族驕傲」自慰,但現在看來似乎更像是無意識地成為了民族國家的養分。
對於文中對香港攬炒派和香港民族國家的分析,也部分印證了我在香港過去一年的感受:的確存在過以「遞刀論」不允許反思運動的人,但或許是因為教育水平不同,這些論點往往會被主流推翻,證明教育還是有一定用處的。
每一個民族國家都需要想像或現實的壓迫,習大大加速攬炒或許正正是香港民族國家所需的,但我認為民族國家之上的是普世價值,就像儘管在抗爭最激烈的時候,香港人也沒走上恐怖主義的道路(雖然大陸很努力地營造這種假象),在對分割的「國族想像」之上假如存在著普世的善念,或許能成為超越民族國家的存在也說不定。
我不抱期待,畢竟我本人的普世價值也差不多被對小粉紅的憎恨消磨的一乾二淨了。
雨月的留言說的有道理,的確國際援助取得的效果非常糟糕,並且這也是國際主義精神消失的原因之一。但需要看到的一點是,近年的所有國際干預行動(有的可以稱為援助,有的根本不是)都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進行的。即使在文中提到的93年的索馬里,聯合國的糧食援助也要藉助對政府的扶植來實施,而索馬里的無政府狀態則是國際社會歷來對索馬里困局無能為力的一大原因。科索沃、波黑的維和行動更是根本以建立民族國家政府為目標,而且實際上這也是民族國家結構裡唯一可能的目標。或許以民族國家為一切行動中心的模式才是導致國際行動失敗的根本原因。這篇文章正是指出這種困境,並希望思考一種新的可能。這個新的可能是什麼,可能需要一個很艱難的探索過程,但尋求新出路的意識,還是應該提早具備的。
我认为如何超越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是作者呼吁读者继续思考的方向,他在结尾处的说明表示,超越民族主义话语需要大家的想象与勇气,他是不想或是不能给出具体方式的。
好文,一直以来我也总是觉得现有的民族主义政治本质上非常绝望,但却怎么都无法用语言表达。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类社会很难发展出超越这个民族主义陷阱的制度——我宁愿把希望寄托到AI身上,期待有一天人类研究出真正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然后整个社会政治都交给AI去管理。
作者对民族主义的批评针砭时弊,但是问题是:如果不是民族主义,那超越民族主义的是什么?历史上有反法西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今天有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LGBTQ、反种族歧视运动。
但是前者在“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失去了动能。后者由主要关注特定团体,对于全民层面的平等自由少有帮助,有时候甚至会消解社会对关乎全民福祉的财富分配、教育医疗平权等议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国际援助被污名化,一定程度上也是援助方自己造成的。尤其是中东北非国家,在外力介入和改革/内战后民不聊生的例子比比皆是,背后的原因跟援助方的私心分不开,自然也给了“民族国家”以抵制干预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