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Fai,回應圓桌話題《當部分年輕人對六四冷感,六四對你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廿九年前香港人的強烈反應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下的「保脣」(脣亡齒寒)成分,也是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一次借機發展的自救運動(老實點來看),「建立民主中國」本身就是符合香港利益的事,這個論述涵括了當年的大多數(能有更好的中國,香港得以維繫的話是最好的結果)。而今要「去中國」,實則更像一次「斷尾」,是前者毫無希望(毫無希望的不只是中國政府,中國人本身的表現並未讓人看到國家有來自民間的、走向開明的可能)下的另一次自救運動,或身份再鞏固。要行動,先要弄清楚行動的主體,反過來說,行動主體不同,行動方式也就可以不一樣。以青年作為主體的話,可以避免處理糾纏不清的感情、歷史包袱,掃清行動障礙。在個人經驗上「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人,行動起來或更輕省。只是,政治有那麼簡單就好了,論述決定誰進場誰退場,若無能涵括大多數,少數很快會被肅清或邊緣化(中共深諳此道)。最終淪為孩童式的自我宣示(不願與目前的中國發生任何關係)或者激進的潔癖(潔癖者與政治無緣),讓人感歎「真係太純」。
再怎麼壯烈,「六四」是整個被籠罩在「國家」這個符號下的,維園集會罪在過多的、對國家的情感投射。「行禮如儀」背後說的除了「缺乏實質行動」,怕就是對「家國情懷」的抗拒排斥了。
對我來說,維園只是一個抵抗的手勢,不必對它有太多的期望,但它絕對有它存在的必要。
2. Rainbow___,回應圓桌話題《當部分年輕人對六四冷感,六四對你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我也是一位出生於1990年代的年輕人,我對六四的確也是沒什麼特殊的感情,六四對於我來說,跟其他歷史事件一樣,只是一件歷史事件,加上我本人及親屬無六四的親身經歷,我對六四的看法全部來源於網絡和一些書籍。略讀了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和吳仁華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兩本書,並且在網絡上搜索了相關的視頻與資料,讓我對中共的劣根認識更加深入,六四已經過去,想要中共為六四正名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後鄧時代不可能,加上六四發生才29年,有很多內部資料還處於機密狀態,所能夠著的史料也是極其有限的,而六四時在北京的親歷者,各有其說,也沒有非常肯定的說法,所以六四現在還蒙著一層紗,我們也只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得出大概。但這個大概也夠了,這足以說明當年中共的惡行。
對於我們,也不能一直糾結最真實的史實到底是什麼,應該追尋更深層次原因和後果,探索六四前後的社會生活方式以及中共高層的鬥爭,探索六四的來龍去脈及六四後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各階層的轉變,這些才是史學界應該做的事。
所以最終,六四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一種警醒吧,時刻提醒我應該追求的東西以及應該避免的東西。
…
那些探索和研究不僅僅是史學界應該做的是,而是所有對六四耿耿於懷或是對六四有特殊感情等等等等的人應該做的事。僅僅惦記著六四那年的中共暴行毫無益處。
3. Kuse,回應《The Name Game:聾人?聽障?為何要對稱呼執著?》
對「障礙」之是否客觀存在的回應。
這樣看吧,大部份人擁有聽覺,少部份人因先/後天原因沒有,單從擁有一種特徵(感官)與否而言,這只是一種deviation。障礙或殘障,則是disability,意謂缺乏做某些事的能力。
聾人的確難以與人通過聽覺交流,部份先天聾人在發音上也面對一定困難,但交流有多於一種方式(手語,文字),他們並非完全缺乏交流能力。
若社會配套上能助他們無礙地與其他社會人士交流溝通,則此聽覺交流能力之缺失不再構成日常生活之障礙,此時雖則他們的確缺失聽覺交流能力,但生活並無障礙,此「障」究在何處?若生活無不便,但只要無法以社會主流方式溝通即為有「障礙」,此看法本就有問題。
這篇文章在論說的正在於此,在於指出不存在所謂「客觀的障礙」。因為一種deviation是否被視為障礙,一則取決於其於日常生活有否不便,二實乃是社會主流所形成的一種觀感,兩者互為因果,而後者究為一種主觀的意見。
4. Obzeroham,回應《The Name Game:聾人?聽障?為何要對稱呼執著?》
@Rainbow 讀完你的分享,突然想到一些場境:想問一下,假如在一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際會議上,有一位使用華語的朋友需要粵語/普通話的即時傳譯,那麼你會否認為這人有障礙?
又另外一個場境:如果有位媽媽推著嬰兒車,在車站處發現原來車站沒有自動電梯或升降機,只能走樓梯。但她真的難以抱著嬰兒車走樓梯呢,那你會說是她有障礙嗎?
以上兩個處境題,相信尚說道理的人都會回答「不是他們有障礙,而是需要為他們提供設備/服務」,相信你也一樣,對嗎?那麼為什麼聾人朋友不說口語、而打手語,我們會說是他們擁有客觀存在的障礙?如果社區的無障礙資訊(如手語傳譯)做得完善,障礙就不存在於聾健群體之間。那到底這是他們的障礙,還是我們的社會未夠好、因而令他們不得不承受障礙?同樣,像你也有提及的無障礙設施,如果做得好,斜道的斜度、闊度和位置有切實考慮輪椅使用者的需要時,阻礙達致通達的障礙也不復存在。
你所提及的那句「不管是處於殘障人士的角度還是健全人士的角度,下意識地認為殘障人士是有障礙的這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看來在有意無意間把責任歸咎於「殘疾人士」,認為他們應該盡力去克服自己的「缺陷」,融入主流社會。其實,你也曾提到應加強做好無障礙設施,這很對,我十分同意。但請不要忘記,「無障礙設計」的目標是達致「共融社會」—共融,該是雙方都共同努力去嘗試了解對方、照顧彼此的需要;而並非單一地要求社會上的小眾配合我們。這樣的想法不是「融合」,這只叫「配合」,而「配合」並非文明和人道社會該高舉的價值。
5. 張生,回應圓桌話題《《創造101》王菊現象,是人格魅力的張力,還是反主流營銷的狂歡?》
從心理訴求角度看,王菊的自身形象和言行點燃了網絡女性用戶的追求獨立、不屈於傳統審美的想法,同時也迎合了LGBT群體推崇的自由、自我的價值觀。恰好這類人群在微博最為活躍,善於使用和製作生動、有趣的語言和表情包。他們是產生王菊現象的群眾基礎。
從傳播方式和效果看,「一菊兩得」、「菊內人」、 「菊外人」等網絡用語和打油詩在一定程度上使飯圈拉票活動上升到現象級跟風娛樂,連共青團微博都要蹭一蹭熱度。粉絲通過諧音替換的方式,借傳統用語的外殼表達新的意義,並將這些詞彙運用到日常交流中,現如今成為網絡用戶重塑符號能指與所指關係的常用方式,比如「一菊兩得」與一舉兩得。粉絲通過這種「舊瓶裝新酒」的語言對微博意見場進行議程設置,再基於微博的嵌套式傳播,使得不關注這件事的用戶也能收到此類用語。用戶被這種新奇、有趣的輿論氣候所吸引,同時又基於被孤立的恐懼進而形成群體模仿,再借由其他社交平台的多級傳播,層層遞進,最終成為一個現象級的拉票活動。
6. DOGE,回應圓桌話題《「SA甜蜜訂製」中國走紅後被封殺,它是「互惠」社交,還是網絡賣淫?》
產品是無罪的,用戶卻未必無罪。一定有不同需求的人使用這個app開展不同的社交功能。但從大眾角度來說,我偏向於相信網絡賣淫。因為成功人士結識伴侶的方式遠比普通人多,不太可能在這種信息精度還比較低的虛擬平台尋找目標。而且網絡帶有天然的隱蔽性,更加不確定性導致所花費的時間成本比常規線下見面社交的方式更多,對於成功人士的性價比不高,可能很難吸引他們入駐。
7. 感同身受_局外人,回應《雨傘運動得與失:「傘後」香港青年更熱衷參與政治了嗎?》
從報導的資料可以發現較深入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之後對於政治抱持著積極參與卻悲觀看待的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悲觀是對於體制及整個生態悲觀,並非對自己悲觀,相反的,這些青年在內心深處必定相信自己有可以改變社會的能力,才會有積極的力量;沒有參與社運的受訪者,可能才是對社會感到最無力的一群,與其浪費時間不如過好個人的生活,也因此最為政治冷感;至於一般(中度)參與的受訪者,對於群體的力量可能很是嚮往,但簡單轉發、分享就能表示參與,這種行為可能對於政治議題最有影響力,但也最有破壞性。
註:比較好奇採樣的對象是如何選定?是針對香港五間大專院校的特定科系發放,還是街頭發放?是如何採樣?
8. 當代大詩人,回應《從摩西到毛澤東:中國當代政治思想的神學起源與嬗替》
關於政治神學如何影響到每個人,其實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借用比喻來說,政治神學研究的是海平面下的潛流,無論是小的浪花還是大的海嘯,都由來有自,政治神學的態度是穿過紛繁的象徵符號,去尋找某種原型的東西。
當然我的困擾是,這個原型真的不是通過回溯去發明出來的嗎,我總還有一種杞人的心態,這還是一種闡釋學,最後要和人家打意識形態宣傳戰。
9. 柔夷,回應《從街頭表演到歌舞大茶飯,旺角菜街的賣藝江湖》
上面說序言書社那位:上個星期剛好去看書 問了書社老闆對於殺街的意見 答「不宜因噎廢食」。本人亦有同感。
又:菜街多中老年人和懷舊金曲怎麼了,為何不能給他們一個娛樂消遣的時間空間?難道是「年輕即正義」麼?本人91年生人,卻也很愛去菜街聽歌跳舞,也見到無數年老甚至有殘障的街坊從天水圍烏溪沙這些地方專門跑到旺角,只為這一種娛樂。我忍不住想,今日我年輕健康所以可以到處尋找娛樂活動,兜中也尚有結餘所以可以流連於酒吧歌廳,但等我遲暮之年、貧困之年又該如何呢?也許太多人欣賞不來這「光怪迷離」的旺角生態,但多一點同理心還是必要的。
10. Tautou,回應《從街頭表演到歌舞大茶飯,旺角菜街的賣藝江湖》
我也非常同意這條街目前太糟糕,表面看來惡俗、噪音滋擾、免費的公共空間卻變成大茶飯生意(就像有人用1元租金搞大排檔),問題多多;面對這個困局,我覺得單單謾罵這些歌舞團沒有意義,這不會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畢竟你一刀切關掉這個地方,但沿用同樣的思維,在同樣的社會肌理中,也有另一個地方會再成為旺角菜街。我覺得需要去理解其中的持分者的聲音,也需要看看,政府有沒有嘗試什麼新方法,民間有沒有嘗試什麼自律方法,如果都沒有,然後今天就說,好,我們關掉它就一了百了,那也可以,但我會覺得這社會也沒什麼變得更好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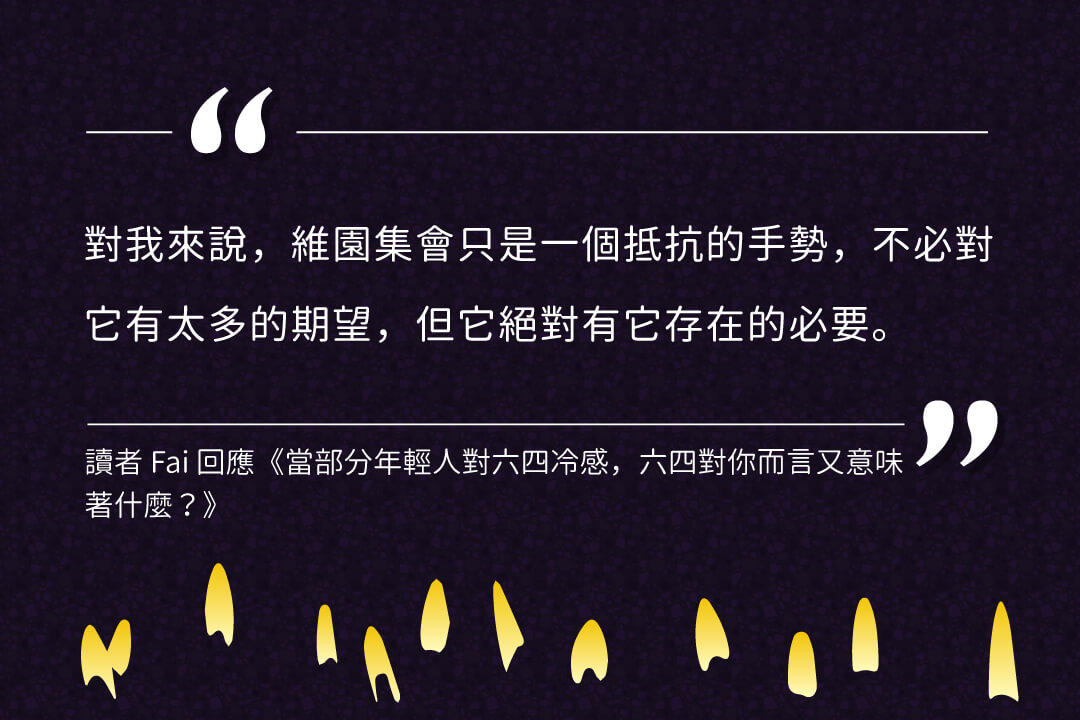
-2.jpg)
屹立廿九年,維園早已不是某種實指,而是一個寶貴的精神符號,你要做實際的事可以從千百種不同的方式,也應該從千百種不同的方式,但符號有時就像燈塔或烽火,是聚集和召喚,讓人有希望的存在。那麼容易就說要丟掉可見天真輕率得要緊。
Lee朋友说的应该是封面图罢?
標題也許說中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聲吧,起碼我也是這樣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