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534,回应圆桌话题《英语为“聪明人的语言”?语言的单一化对民族身分认同有何影响?》
刚好略懂一些,可以把客观事实和我的个人感慨分享一下。
对于在中国推广普通话和世界范围内英语霸权的问题,两者的共性是在于文中提到的客观上的语言(具体来说是high language)使用的便利和带来的实际利益。比如上世纪50年代推广普通话直接对中国普遍的文化(literacy)水平提高和中国的经济腾飞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推行虽有强迫意味,英语的渗透也挤压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实际利益在前,语言标准化是个人和国家权衡利弊的选择。
从语言学上说,语言标准化的过快扩张对语言学家,尤其是类型学家(typologist)和濒危语言研究者构成了非常迫切的威胁。因为除了纪录某种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的本质。而每种消逝的语言都一定蕴藏着帮助研究者接近语言本质答案的钥匙。比如,如果亚马逊丛林里的语言 Pirahã 如果在研究者发现它之前就因为种种原因消亡了,我们可能再无办法得知有种语言可以在各种语言学维度如此特别。而它的特别尤为重要。
我自己的感慨是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做到大家主观意识上的语言平等,可以不再去比较哪个语言“更优雅”“更美丽”。就像是不一定每一个满族人都要会说满语,但是我听到诸如“满语又用不到,研究它做什么”的言论时是真的心痛。不论政治观点经济实力,尊重和欣赏每种语言的价值和文化的美感,我觉得是每个人短暂生命里重要的一件事。
2. ketleman,回应圆桌话题《英语为“聪明人的语言”?语言的单一化对民族身分认同有何影响?》
把民族语言称为“方言”,并把他们与粤语、苏州话等真正的汉语方言等同起来讨论,是十分错误的。这不仅不符合中国国内的学术共识,也与纸面上的现行法律是冲突的。
其一,中国的民族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对民语和方言的区分,认为这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同。例如,在1955年的学术期刊《中国语文》上,面对读者的提问,编辑这样回复:从你提出的问题看,你似乎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混同起来了。这是需要分清楚的。我们的“少数民族语言”是指藏语、苗语、维吾尔语……等而说的。而方言则“是全民族语言的分支,是某一个部落、部族或者民族的一部分成员所说的话”(阿瓦涅梭夫:《方言和方言学》第1页)。就汉语说,广东话、福建话,……等是它的方言。
民族共同语的意思是“一个民族内部所有组成员共同的语言”,而不是“各民族之间共同的语言”,从来信看,你似乎也把它了解错了。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的胜利,…还没有创造而且也不能创造为世界各民族和各民族语言的溶和为一个共同整体所必需的条件”(《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51页,人民出版社)。我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社会主义胜利的阶段,当然更没有各民族语言溶和所必需的条件。因此,“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是否妨碍各民族之间的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来信所说的“民族共同语”是指“汉族共同语”,那末,我们认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是不会妨碍汉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说“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这里说明了决定一种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的是该民族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民族。当然,一种民族语言的发展跟其他民族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各民族语言可以吸收其他民族的词汇,可以参考其他语言改造自己的语法构造,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妨碍民族语言的形成,恰恰相反,它可以使民族语言更加丰富,更加完备。
其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语与方言的法律地位是绝对不同的。宪法第四条明确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民语可以作为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和推广,自治地方政府有义务支持这些行为。在有关教育的专门法规,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在第八条中明确写到: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这实际上是说,尽管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需要执行推普的政策,但民语的传播和使用依然是要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的。相比之下,各地区的方言就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来保护。
顺便说一句,在本世纪以前,学界一直认为中国在对民族语言(这里指的是那几个可以有自己学校的大语言)的保护方面,在全世界都是做的最好的那几个。藏族、维吾尔族等不仅有自己的民语学校,也有自己的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大学,地方政府的公文依然要以双语呈现,街头巷尾播放的内地电影依然要用民语配音。以至于每当有人提出小语言消亡论,我们的民族学家会自豪地反驳:中国就是最大的反例。维吾尔语言学家也会自豪的宣称,维吾尔语是保护得最好的突厥语言。只是这二十年的中央政府的强横霸道,才让人开始感到失望乃至绝望。
3. rhrm,回应圆桌话题《甘肃省百公里越野赛遇极端天气21名跑手遇难,这场意外是人为失误还是天灾?》
5月22日绝对是世界越野跑运动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作为越野跑爱好者,我有考虑过这场比赛,完赛即有千元奖金的待遇可不常见--个人经历过的唯一一次是号称全球最高难度的首届江南之巅百公里。最后放弃,改报名同一天的大连百公里(后因辽宁疫情赛前紧急取消),是因为感觉赛事实在缺乏难度和挑战性,CP4过后的几十公里赛道几乎一马平川,没有多少爬升下降,对于喜欢技术型路段的选手来说,简直是在滥竽充数。此次遭遇不幸的都是第一集团(速度慢的天气突变时尚未跑入危险地段,反而安然无恙),前20名大部遇难,而近几年参加过的比赛中,我的排名基本没有跌出前20--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自己离大灾难的距离如此之近。我所有的经验都无法解释,那几个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场如此简单的比赛如何会有如此惨烈的结局。
事后可以指责组委会忽视天气变化,没有要求选手携带冲锋衣,但这在国内越野赛组织中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毕竟无惧风雨是每一个越野跑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如此极端恶劣的天气用史无前例形容并不过分。真正不可原谅的,是组委会在应急处置上的迟缓低效。和绝大多数越野赛一样,选手都随身携带具有定位和求助功能的GPS收发器,一旦收到求救型号或在后台观察到有选手在补给站外长时间停止不动,组委会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然而选手遭遇天气突变是在中午前后,极端恶劣天气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下午就有部分选手成功通过事故路段到达CP4),而有组织的救援行动直到入夜前后才展开,中间耽误的是致命的数小时,在这期间组委会做了什么决策采取了什么行动,我没有看到任何详细的报导。我很想知道的,关键性的,位于风暴中心的CP3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及时传达天气突变的消息,是否有坚守岗位,目前也没有任何报导可以告诉我。
但是,我并不认为黄河石林越野的组委会是一个特别差劣的组委会,这样的组织和应变能力,极可能是国内大多数越野赛的普遍水平。近几年国内的越野跑行业发展极为火热,就在四五年前,百公里以上的越野赛差不多是一项极限运动,一年只有两三场赛事,参赛者寥寥无几,完成一场简直是可以吹一辈子的壮举。而现在,气候适宜的春秋季一个周末就可以有三四场比赛可以选择,距离由100公里发展到100英里,330公里甚至500公里,地点由城市周边深入到西部荒野地带高海拔地区,如此野蛮生长,无疑意味着大部分赛事的组织者并没有足够丰富的经验。线路的设计,路标的布设,补给的种类数量,是容易感知,决定赛事体验和口碑的主要因素,组织者还会多加考虑,至于99%的可能根本用不上的救援、应急预案,往往就被忽视了。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算是有相当经验和实力的越野跑者,这场灾难也如当头棒喝,让我思考,自己真的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一场越野吗?每一个越野跑手都是从马拉松跑手进阶来的(没有全程马拉松完赛记录一般是没有资格参加50公里以上越野赛的),公众更是经常把这两类比赛混为一谈(包括端的这篇文章里也出现了好几次马拉松字眼),但是,跑马拉松的时候,你大可以心无旁骛,只需要关注一件事,向前跑,越野跑则不一样,它是一项有更多风景更多变化更多趣味,却也暗含着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的户外运动。和很多越野跑者一样,我也是登山徒步的爱好者,我知道其中的风险,知道在户外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安全负起完全的责任,一定要关注天气,研究路线,带足装备,但是,当同样的路线以越野赛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我只会带上最简单轻便的装备,我相信组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需要做的就是像马拉松一样,义无反顾地向前,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我想,那一天,21名选手的心中也根本没有退赛这样“可耻”的念头,他们相信前方一定是有保障的,安全问题是无需操心的,然而这样的自信是致命的。
无疑,国内越野跑行业就此会迎来一轮整治和洗牌,但我万不希望如传言那样,对整个越野跑运动按下暂停键。过去常常被问到为什么喜欢这样如此艰苦的运动,我的回答是,跑步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事情了,世间太多事情,一个人能改变的都只有那么一点点,最后结果如何,或是看人,或是看天。跑步却是例外,不需要考虑外界,不需要考虑旁人,只需要关注脚步、关注呼吸,而所有的训练、汗水、付出,都可以有实实在在的回报。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天真和危险的,无论是赛事还是跑者,都应该更加成熟,更加负责,绝不能低估环境因素带来的风险。而对跑步的爱,对户外的爱,不会,也不应该停止。
4. Litooooo,回应《谁能定义Billie Eilish:已经自居女性主义,还可以脱衣服吗?》
提出“权力是解放还是控制”这种问题就是落入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陷阱。性别革命的目的不是以“解放”消除控制,而是以新的控制推翻与代替旧的控制,或说以“更好”的控制代替之前“没那么好”的控制。同理,认为存在一种“成为一切形象的自由”也是一种妄想,因为不可能存在没有权力与控制的“解放”乌托邦。
以 metoo 为例子,它打破挑战的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肆意凝视与侵犯,但取而代之的是对两性间应有的合理行为的新的规范,我们到达的不是“解放”,而是新的控制,但这种控制要比父权制下的控制更加符合女权主义利益。
回到 Billie 的这件事,无论穿性感服饰为荣还是穿宽大衣服为潮流都不是“解放”,而是不同形态的控制,只不过这些不同形态的控制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与情境下对女权主义的意义有所不同。放在四十年前,一线流行女歌手在公共场合穿去性化的服饰肯定可以被视为对既有性别规范的挑战,是符合女权主义价值观的,但放到今天,当挑战传统性别角色在流行文化中已然成为潮流,就很难说同样的行为还具备之前的意义,反而重新穿回束身衣可以成为一种挑衅当前权力控制的积极手段。可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我们曾经认为是“解放”的行为到头来都是一种适用范围或大或小的权力控制,只不过在特定的情境拥有的“解放”的意义与主观感受。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追求一劳永逸的“解放”,而应认为每一种 gender transgression 都是一种新的(以及在特定情境下“更好的”)权力控制,并对一切 transgression 保持警惕,在它重新成为压迫性价值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背叛它。
5. 爱国爱港爱人民,回应《谁能定义Billie Eilish:已经自居女性主义,还可以脱衣服吗?》
我觉得在这里可能要谈论某种必备的宽容:个体是不可能完全外在于建构自己的环境而存的,因为它就是从这内部生发出来的。那么“她的审美还是父权的”“她并非在成为一个女权主义的自己”一类的话语就算是苛责了。一个已经被社会建构的“女性”,即使她拼尽全力要逃脱这个社会规范,但她只要在生活,那她几乎不可能完全不带有被社会视为“女性化”的特征。
从实践来说,我还是觉得斗争策略都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先在完满的道路引领我们向前固然是最优的,可惜我们还找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求同而不伐异可能是留下最多火种的方法。如果不从自己的屁股出发,我甚至觉得对粉红女权都该多些宽容。
6. ChenMoEURO,回应《谁的双赢、谁成囚徒?遇到“中国胃口”的塞内加尔花生》
千万人口的第三世界小国如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保护和发展本国高附加值产业是对执政者能力和决心的考验。事实是,现行国际框架下绝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基本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在国际分工上被锁死在了原材料供应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香蕉共和国”。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大国可以用本国市场为筹码,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而多数小国很难有这种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7. EricChan,回应《谁的双赢、谁成囚徒?遇到“中国胃口”的塞内加尔花生》
我觉得这篇文章想要表达/带出得到隐忧在于中国花生收购商在与本土花生加工业商家竞争时存在不公平竞争优势。即图三中表明的“优惠”与不对等,令中国收购商在收购花生时存在成本优势。我个人的看法是相较于塞内加尔油厂需要将词参与花生种植的基础设施资助,并需与中间商合作,似乎中方直接将收益交到农民手上的做法更能避免农民收益被政府,企业贪腐截流。但是塞内加尔政府或许也会因此少了用于农业发展以及产业发展,专营的资金。
第二个隐忧似乎是更值得关注,那就是塞内加尔本地花生加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中国花生收购商与本土油厂存在竞争优势,间接影响本地花生油厂的发展。这部分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可能会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用中国常见的说法,这是一种产业剥削,类似于一部中国产的iphone 中共工人只能赚多少钱的故事。一旦塞内加尔本土花生油产业被打垮,本地的农民将不得不将花生售予垄断花生出口市场的中国收购商。而由于花生是一种保存期较短的作物,垄断的流通市场会导致花生农的议价权丧失。但是考虑到用作本地榨油和出口的花生还不到塞内加尔花生产量的一半,这项隐忧在实际上会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还需要更多研究和资料佐证。但不论任何国家,一项产业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总不是一件好事。
8. 鲸鱼mama,回应《杨路:从东北人口外流看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作为一个中部农业大省的中国人,说实话我对东三省的衰败一点都不同情,共和国长子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吃饱喝足,享受过时代政策红利了,现在东北的平均退休金比广东还高,对,国家拿广东人的转移支付给东北人发工资,而且发的比广东本地人还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舞台也该切换了,现在大湾区到处都是东北人,东北人也该体会一下我们中部劳动力大省几十年以来到处打工的生活方式了。
9. Carina,回应《2021年的香港人怎样笑:Mirror 同 Error,缘何在崩坏时代迷狂全港?》
喜欢文章第二段引巴勒斯坦的例子,无人可以摆脱娱乐,但我们可以选择有质素的娱乐,而自肥看似是搞笑综艺,但经常引起观众反思,尤其是最尾一集激起我们思考娱乐和电视的意义,使我们至少不会愚蠢地死去。
10. c_s,回应《万华十日记:疫情重灾区,一场对抗病毒的游击战》
万华是台北平均经济最疲弱的区域,但地方组织、串连也因应非常紧密。这篇报导倒是成了一个地方资源盘点,给对不熟万华的人算是开了开眼了吧。
说到疫情,只能说台湾政府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围堵(封锁国境实在是牺牲了多大可想而知),现在的结果变成居民只能自救,中央政府疲软无力,地方政府暗潮汹涌,最遗憾的是去年一整年完完全全地浪费了,牺牲也白费了唉。
其实最后杀手锏就是疫苗,也不能只怪政府疫苗取得不利,实在也是民众自身对疫苗兴趣缺缺,这两者还是相辅相承的。我个人是已经很看淡了,只希望在真见棺材真掉泪的当今,能够刺激疫苗尽快出现在台湾,终止这场闹剧。
方里长、芒草心等等都是于收容来自各方弱势者的台北西区长久耕耘的基层公职者和NGO了。平时,这个资源丰富的都市都交由他们担任大量的弱势照护,疫情蔓延时要期盼市府接手这个没有全国性镁光灯的工作更是奢求。
被社会制度设计刻意排挤的性工作者、逃亡移工、二年前才大幅减薪引发出走潮的市立联医......都是长年的问题,疫情以来这一年多公民团体疾呼重视也没少过,好像非要真的全面引爆才能有比较多的注视,一但风头过后又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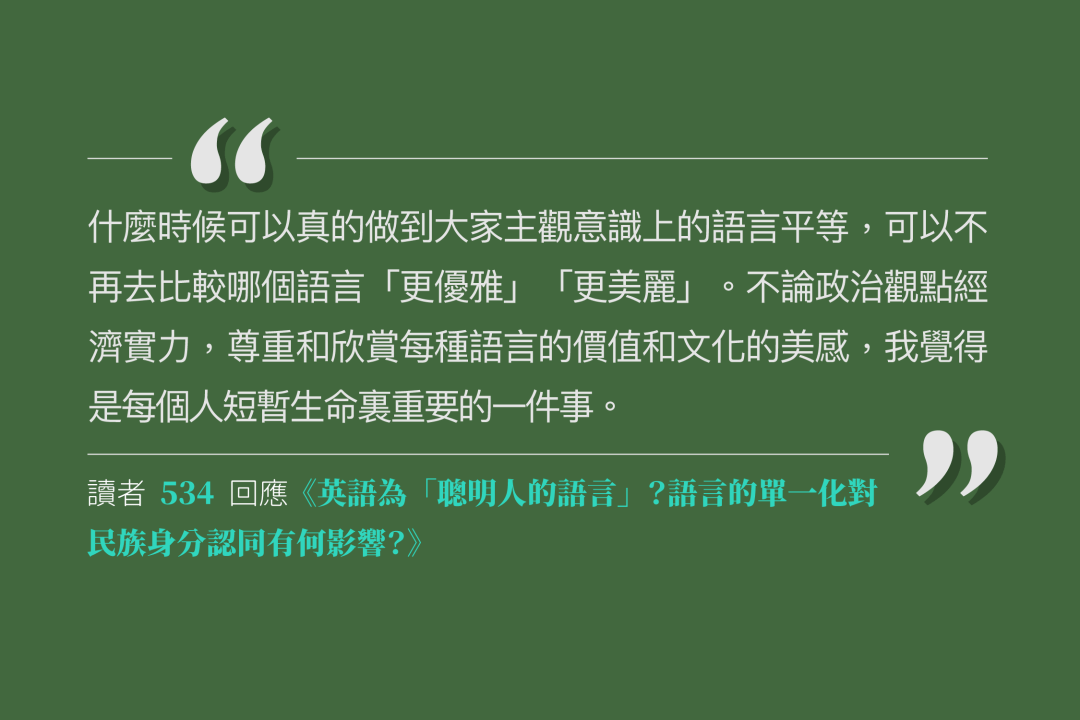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