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2月12日起,端传媒开始连载朱令案报导。这桩投毒悬案距今有二十五年,举世瞩目,真凶仍未落网。本文记者曾花数年追踪和记录朱令案情及后续发展,端传媒节选其中部分章节刊发。这些章节聚焦在:朱令案作为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的案例,曾在体制、权力围拢的层层疑雾中,由互联网撕开了一丝希望的口子。本文为连载的最后一篇。欢迎你转发、分享,并与我们交流你对此案的看法。
陈震阳为朱令做铊中毒的检验报告,当时冒了不小的风险。
因为是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劳卫所下午就不办公了,负责公章的人更是早早下班。没办法找到人盖公章,陈震阳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就个人名义了,胆子也豁出去了,我签字我负责,”他回忆。
长久以来,“担责”在中国社会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不作为总好过出错担责任。人们习惯了谨小慎微,本能地厌恶冒险。
陈震阳并不是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后果:“检测结果出去了我是孤立派,法律上出了问题,人家都说没有铊,清华说教研室就没有铊。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办?”
陈震阳告诉我,这种压力首先来自当时自己的工作单位。他记得后来所长对他颇为责怪,意思是协和医院自然会有处理的办法,轮不到他来越俎代庖。说起这些年,大家以为他因为救人受到了表扬和奖励,陈震阳苦笑了一下,“得了什么啊,我得了个红本——退休证。你赶紧走吧!”——那是1995年5月,随着给朱令开具检验报告,他的年龄也到了,便立刻被单位要求退休。
更令人遗憾的是,陈震阳和其夫人崔明珍对于铊进行的科研,在课题结题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这个领域也始终处于边缘小众的地位,到今天依然如此。由于中毒并非常见情况,中国日渐以效益为驱动的综合性大医院没有动力花费成本添置检验设备和培训人员。而与之相对的是,全球在过去一百年间仅发生过二十几例以铊为手段的投毒案件,但中国占了一半以上。
给61个阶级兄弟的药与普鲁士蓝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症治疗了。
得知确诊结果后,协和立即邀请了六名国内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广谱抗毒药“二巯基丙醇”解毒。
上世纪60年代,一篇著名的通讯报导《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报导是那个时代主旋律的赞颂“崇高阶级友爱精神”的故事。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讴歌。
故事要回溯到1960年,春节刚过,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缺乏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交通不便,药品无法及时送达。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运五运输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于是,61名民工兄弟因为党和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大爱得救了。这篇通讯很快成为了新闻写作的范文,还入选了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文章中提到的解毒药品,就是二巯基丙醇。这种药剂最早由二战期间英国牛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们研制而出,当时是作为生化武器路易氏剂的解毒剂。后来在医学中作为重金属中毒的解毒药剂应用,原理是其分子中的巯基易与某些金属或类金属结合,从而阻止其离解后发挥毒性。
“给‘61个阶级兄弟’的药,生产于50年代,二次大战时的用药,早已停产,”吴承之回忆,他当时犯了难。幸好最后他们还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这种药,售价只要三毛钱一支。
然而,通讯中的61个民工所中的毒,是较为常见的砒霜,也就是砷。对于铊的解毒,二巯基丙醇解毒并不见效。朱明新记得,一直在网络邮件中焦急关切朱令情况的留学生李新对于协和的诊治非常质疑,“他说根本就没用,甚至还有副作用”。朱明新记得李新告诉她,美国的毒物专家建议,要用“普鲁士蓝”。

不要说朱明新夫妇,就连协和的医生们之前也并没有多少听说过这个名词。
普鲁士蓝,是一种深蓝色的化工颜料,在画图和青花瓷器中较多应用。由德国画家狄斯巴赫1704年意外发现。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军队的制服颜色就是使用它,以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沿用普鲁士蓝军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更换成了原野灰。
普鲁士蓝解铊毒的原理是阳离子铊可置换普鲁士蓝上的钾后形成不溶性物质随粪便由人体排出。“重金属跟神经系统发生化学反应,是跟活性蛋白质结合。它不是马上引起你感官的不舒服,而是夺取了你的活性分子。所以只有拿更活泼的把它结合出来,就是拿普鲁士蓝。”多年后,朱令同班同学潘波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科普了解毒的原理。他告诉我,事实上,当得知朱令中毒,身为化学系学生的不少同班同学私下都有议论,探讨正确的救治方法和长时间误诊造成解毒时机的延误,以及对朱令的进一步伤害。“误诊就会造成重金属落在食道里面,会不断地从消化系统进到各个器官里面去”,潘波说。
朱明新立即跟协和提出使用普鲁士蓝解毒。她记得当时协和的药房即将放假,担心再拖又要耽误几天,便决定找熟人帮忙,于是想到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当时崔家就住在朱令家楼下,崔月犁本人还曾在60年代与朱明新的父亲朱启明在北京市政府共事,两家交情不错。
但事情结果令人有些哭笑不得,朱明新吴承之被告知化工用品商店就有普鲁士蓝出售。揣了“在当时是巨款”的2000块现金立即赶去的吴承之发现,这其实是“特别便宜的东西”。
买了一小箱、10瓶,只花了40多块,合计一瓶4块多。
在协和的医药治疗费总计是50多万,而“真正的救命药仅需40多元。”
朱令终于醒了过来
这之后的故事便几乎没有悬念了。1995年5月5日,协和医生终于被说服采用普鲁士蓝为朱令口服解毒,陈震阳持续追踪了这之后她各项指标的变化。他记得“开始的时候降得很快,后来就越来越慢,是一条缓的抛物线。非常漂亮,最后一直到零了”。
这条“漂亮的抛物线”大约画了一个月的时间,陈震阳回忆自己当时给吴承之和朱明新打气:“我不断地鼓励他们,朱令年轻,才二十一二岁,会一天天地好。”但陈震阳也很清楚,铊对大脑,神经系统,尤其是视神经伤害非常大,朱令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有十足把握。
直到1995年8月,昏迷长达半年的朱令终于醒了过来。朱明新的大事记里,记载了一点一滴的变化:8月1日 最后一次复查铊浓度;8月21日,明显听懂妈妈“闭眼”“睁眼”的要求;8月25日,听到张嘴、闭眼、笑一笑的要求,能做出反应;8月31日,彻底苏醒;9月8日,能“抱住我,伸舌头……”
朱明新曾在给美国《读者文摘》记者的信件中描述,“每天我守候在病床旁,不停地和她说话,从她的表情感觉到她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就问她:‘令令,听到妈妈说话就闭一闭眼睛。’8月底,她真的在我说完后闭上眼睛。我说‘令令,你听到了,是吗?’她努力点头并痛哭,可怜的孩子气管被切开,发不出声,其惨状真不忍睹。”
从未放弃希望的朱明新在这一刻却并没有欣喜若狂。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回忆:“我每天都在跟她说话。以前看电影,好像昏迷的病人醒过来是很突然的,实际上不是。朱令是一点点醒来的,今天会眨眼了,明天会流泪了。所以,到最后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没有兴奋,只有欣慰。”
1996年6月,朱令从协和出院。长达半年多的铊毒侵害已经严重伤害了脑神经,她再也没能恢复曾经的聪慧,视力近乎全盲,语言能力几乎完全丧失。

倒逼进了这场司法仗
回头看协和医院这个中国医疗界的头号权威和庞然大物。在中国,长久以来,普通患者无法享有与医院平等对话的权利,更不要说质疑甚至挑战了。但是朱令住院过程中几个未能得到解释的问号却是难以绕开的疑团:既然上世纪60年代李舜伟就曾经接诊清华铊中毒的案例,为何到了90年代却无法确诊?协和曾经与清华合作编纂出版过毒物手册,其中对于铊中毒有专门阐述,为何对于朱令的诊疗会拖这么长时间不做化验便坚决排除?
1996年12月,由于对协和医院抢救不当的不满,朱明新吴承之将协和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立案审理。
提起这个官司,朱明新感慨其中的艰难:“跟协和打官司(很难)。协和跟清华一样,是中国的第一,不能碰的。以前也没有人去打这种官司。”
夫妻俩起初并不想走这样的司法程序。朱明新的想法“主要是想给女儿一个好一些的医治环境,再加上我一再考虑是否将来还可能不得不回协和去治病,它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而吴承之的想法更简单,“他老是觉得大夫挺好的,像李舜伟什么的”,朱明新说,“我就说他没有忧患意识,老是从好的角度去说。”
因为再不起诉时效就要过期,朱明新夫妇最终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了官司。而这之后的听证过程中,朱明新发现协和不但不承认自身有过错,还在《卫生报》刊登文章将朱令得以生存描述为协和的功劳,“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在其提供的证据中,朱明新更发现不少与事实有出入,诸如协和要求公安开具了一份描述其救治过程中无法找到检验铊的部门的证明,而朱明新发现,这是在朱令已被确诊铊中毒之后才开具的;协和还要求陈震阳所在的劳卫所一名专家证明劳卫所无法进行铊检测,而陈震阳事后告知朱明新,这个人在检测当时根本就不在国内。
朱明新是被倒逼进了这场司法仗:“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协和一再地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我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坚决,直到后来,变成了我是家里唯一坚持要打完这场官司的人。面对的压力是他人难以想像的。”
在90年代的中国,以个体对抗集体,尤其是国家级头号权威,力量之悬殊可想而知。朱明新后来十分后悔自己当初没能复印下女儿的全部病例,“那时候就觉得挺贵的。”后来再希望去复印,已经无法拿到核心的关键内容了。尽管如此,当时的朱明新依然觉得事实清晰,铁证如山,胜诉应该理所当然。
但是事与愿违,卫生局下辖的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做出了协和没有过失的鉴定。朱明新回忆:“意思是虽然怎么着,但是也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于是,1999年4月2日,东城区法院基本依据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说法作为了判决的标准,判决书陈述:“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但证据不足……”
当年12月,朱令父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制早报》曾经采访过无偿为朱令一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几位律师,其中律师马晓刚记得,朱明新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知道二审很难打,只是想给女儿一个交代。”
马晓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证据不足,“他们是为了给女儿看病,不是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医疗单据就没有保留。”马晓刚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案子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完善,他形容医疗鉴定机构与医院的关系——“当爹的不能打死儿子吧?”
2000年6月,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检定研究所受到委托再次进行鉴定,法医刘鑫成为主要负责人。他将所有搜集到的病历资料重新进行了梳理,并重新取证,发现朱明新所说时间和人物的出入不符确实存在,这份鉴定基本否定了协和自述曾经对朱令是否铊中毒积极寻求检测资源的努力。在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鑫回忆了在他主持召开的司法鉴定听证会上,自己就此问题与李舜伟进行的一次对话。“为什么提出高度怀疑(铊中毒)?”李舜伟回答,就是因为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曾接诊过一位同样来自清华的铊中毒患者,印象深刻。“那为什么没有确诊?”刘鑫追问。李舜伟说:“确诊要靠实验室化验数据说话,临床判断只是提供一种可能。”
最终,刘鑫所在的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检定研究所做出结论:“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共10万元。
此时的朱令家,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因为官司,他们与权力、权威来了个硬碰硬的交锋,朱令家看似赢得了“庶民的胜利”。但只是惨胜。当时的律师马晓刚曾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
在回答我官司是否算赢了的问题,朱明新苦笑了一声:“没有赢。二审仅仅是作为补偿,不叫我赢,仍然是他们赢。法院的人特别同情朱令这事,但是最后结论还是——(协和)没责任。”

朱令还活着,有情感、有尊严地活着
2018年4月27日,我走进位于北京远郊的小汤山疗养院。那是一栋不太陈旧,但却昏暗寂寥,给人感觉有些压抑的病房楼,潮湿、阴冷,见不到阳光。走向前台护士站,说我来看朱令,护士的眼神稍有警惕,但打了个电话跟病房里的朱明新确认之后,便很快点头放行。
走过长长的,寂静无声,光线昏黄的走廊,我在尽头看到了已经站在病房外等候的朱明新。整洁的米白色方格马甲,一头银白短发梳得整齐不乱,表情平静和善,“令令正在做练习”,她轻声说。
病房里,我看到朱令四肢被固定在一张一人高的器械床上,在床被一点点摇直至90度竖立的时候“站立”了起来。
此时的朱令44岁,穿着干净的白领秋衣,朱红色开衫,深紫色运动裤。短发整齐,面庞干净。昔日韶华盛极时的灵动和矫健已经全然不见。但多年来媒体反复报导由于药物造成“体重超过100公斤”并不准确。眼前的她看起来行动迟缓,但并不臃肿,下肢肌肉甚至由于长时间不能站立而出现萎缩,显得比常人细弱得多。
“令令,看谁来看你了”,在母亲的声音里,她扭过头,脸上的肌肉显露出微笑的努力。但是她看不见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在长长的睫毛上,她的瞳孔呈现浅棕色,眼神有些浑浊,似乎蒙着一层薄雾,她几乎全盲。很快,练习开始,朱令脸上那一晃而过的笑意被痛苦的表情代替。
“这是每天早饭后都要做的”,朱明新说。朱令的脖子上,插进的呼吸管非常惹眼。2011年时,由于肺部感染,她的气管在喉咙处被切开,之后六七年一直未能缝合。这之前,她已经多次经历肺炎感染,更不要提先后患上的糖尿病、腹部肿瘤、呼吸功能衰竭,一次又一次,朱令被宣布病危,又一次次挺了过来。
本该处在生活和事业巅峰期的朱令,一天24小时都囿于这小小的病房之中,由此时已经78岁的父亲吴承之、77岁的母亲朱明新日夜照顾。之前两年,爸爸妈妈还会推着她的轮椅走出病房晒晒太阳,这两年父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这样的小奢侈便也越来越少了。
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父母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不卑不亢地生活。汶川地震时,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想告诉人们,朱令还活着,有情感、有尊严地活着。
在小汤山医院的一整天,吴承之和朱明新按部就班地忙碌着。该谁去为朱令做康复训练,谁去买饭,谁来喂饭,有条不紊。中午,吴承之催促朱明新带我到医院旁边的餐厅午饭,自己留下在病房“值班”。饭桌前,我说起看到朱令过去20多年的遭遇,我就再也不能相信善恶有报这样宗教色彩的预言。朱明新感触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世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这是我目睹朱令母亲一向温和的神色中,第一次流露强烈的情绪和无力感。
“所有的父母都会这样照顾子女的,这没什么,”她说。他们盼望自己“能活的久一些”。因为,“要是我们不在了,朱令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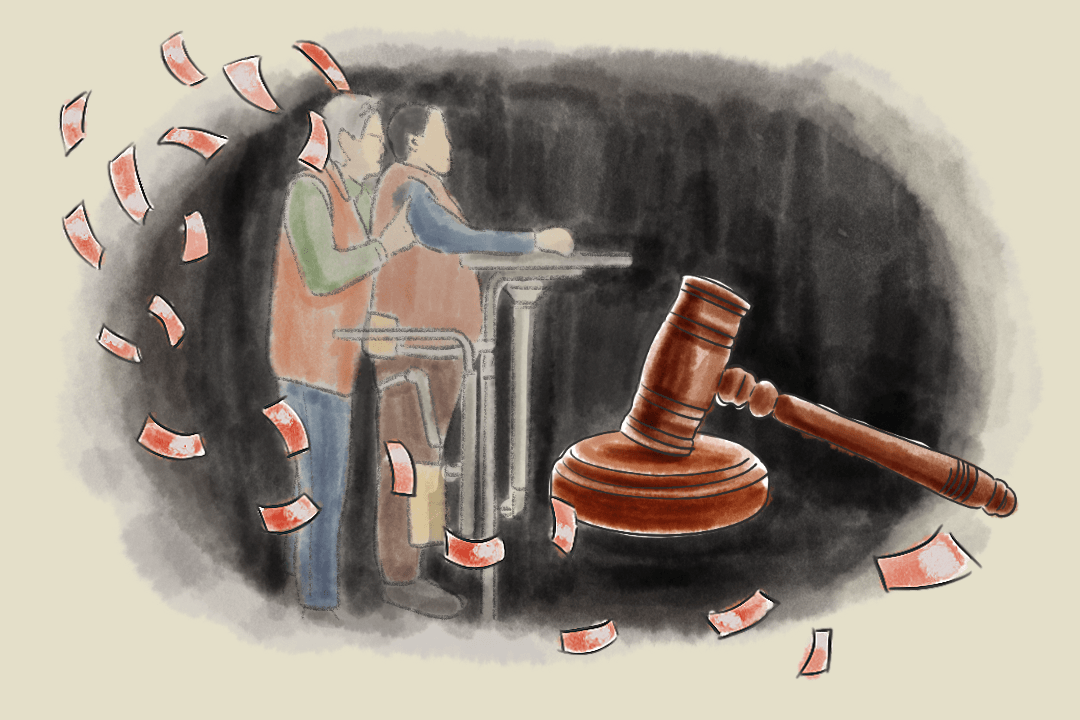




太难过了,几乎是看一次哭一次。
今天在网上看到博主祝朱令生日快乐,才找到这篇报道,看完了,很难过。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也没什么区别。出了事不能问为什么,人人都知道为什么,却只能不明不白地承受着后果。
在一个可以从网络评论就随随便便人肉出留言者的时代,竟然找不出凶手。要我是父母,真的死不瞑目。光看这四篇连载我内心就痛到不行。
感觉这个报道还没有完成,朱令到底是怎么中毒的?
太难过了 太难过了
什麼?
這就算了?
認命了麽?
認命了!就不要吐苦水!
來什麼報導!
所以協和就這樣沒事了? 這件事不能就這樣完了,應該重啟對協和醫院的責任要求,協和最少該做的是: 等到朱令的雙親過世後,負起所有醫療照護朱令餘生的責任。
朱明新的 Alipay 和 PayPal 账户都是 helpzl@163.com (信源:微博@帮助朱令)
倒是真的很担心,朱令双亲百年之后她怎么办呢
最后凶手找不到?其实也可以说找到了,凶手就是虽号称中国医疗界头号权威却漠视病人安危、延误救治的协和医院。
全文在哪里看?请问。
特别想看追踪杀手部分,可是到现在都没人被定罪。
我今天一口气读完了四篇连载报道。每每读到相似处境的事件(求助无门、不公不义),总是心痛不已,也默默激愤不已。
作为一名在海外出生的第三代华人,我对于中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对于中国的“大环境”实在不敢苟同。我希望中国会越来越有人性。嘴巴讲的身体做的“中华传统文化”,要跟真正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致才行啊。
我不是药神始终还是美国达拉斯的翻版、但这故事要能拍成电影、才真正能让中国人清醒。韩国这几年的悲天悯人的电影态度我十分敬佩、将社会的不公、悲剧在电影中放大、灌输正确的价值观、愿美好的时代早日来临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形容朱令,也可以用来形容那些追求自由但遭受种种迫害的人们。
震驚的是,犯罪分子還逍遙法外,中國的司法實在是讓人遺憾。一個品學兼優的清華女生遭遇毒手,醫院沒及時確診,她還遭二次投毒,什麼人那麼心狠手辣。司法機關還不敢追究,人大於法,讓知情的國人汗顏啊!嗚呼哀哉,我堂堂中華,有如此妖孽存在!
希望可以早日读到全文,非常感谢作者。
我觉得这次的节选连载是很好的事件梳理。因为长期以来给我感觉舆论都更多的在声讨凶手和凶手背后的强大背景,对事件背后的深重体制问题讨论的不多(当然这事涉敏感在墙内不可能自由讨论)。以及就像大家讨论的那样,现在回头看这一事件依然触目惊心,除了痛心朱令一家的遭遇之外,也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清楚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或者再说直白一点,再过若干年也是改不了的。
我印象很深的第三篇连载里提到的,美国医生"追在"后面打国际电话,强烈要求赶紧救人的细节,大概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吧。
楼上,我觉得关键在于这不是一个“讲道理”和“尊重生命”的地方,其实只要做到这两点,起码不会贻误治疗时机。
樓上,裙帶關係的可怕之處在於就算是醫院和醫療鑑定機構脫鉤,也會因爲莫須有的人際關係彼此護衛。
醫療鑑定機構與醫院是「當爹和兒子」的關係,這就是當今中國仍然可悲之處。徒有虛榮的表皮,內裏實質還是惡腐的制度。
期待早日能看到全文!特别是追凶的部分。如果因为这本书能够重启司法程序的话就太棒了
知道朱令案已经14年了,看到的大部分分析和报道都或限于舆论环境或限于调查和表达能力,写得不够清晰条理,看了这几篇报道,除了嫌疑人部分没有登出之外,对朱令案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朱家无疑是当年的北京精英家庭,可是在时代和体制之下,他们也无力在被厄运砸中后得到救济——唉,我等蝼蚁,只能祈求上苍了。
願得雪
回复楼下,他们一家在小汤山,目前还好。春节过得恬淡平和,一家人相守就很感恩。但是朱令过去几年的健康状况用朱阿姨的话说是“螺旋式下降”:气管切开不能发声,进食医生本不允许,因为担心堵塞气管,但父母仍打碎喂她,希望给她保留一点生活质量。而朱阿姨吴叔叔也已经年近八旬,一个之前做过开颅手术一个做过肠道手术,都坚强挺过来了。“再不写,可能就没机会了”,所以要记录。
To 作者:多謝持續關注他們家這個案子,原來是計劃出書!期待。
另外,不知道他們近況如何?突然看到端貼這系列,還以爲朱家是不是出事了呢。
谢谢各位的阅读和对朱令一家的关心。全文篇幅很长,超过十万字,所以端只能摘取精编部分内容。全文出版时一定会广而告之!敬请期待~
没有分析凶手,虽然疑罪从无,可惜
请问原报导怎么看呢?
不知道哪里能看到全文?
从这个系列一发出来我就在关注,今天看到最后一句话实在是忍不住,朱令父母去世之后她会怎么样呢,她的人生还有40年要走,可她已经没有未来了。而让她变成这样的真凶还逍遥法外,间接造成她这样的帮凶还是国内第一的医院,虽然很悲观,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正义永远不会到来。
自古民告官就很艰难,在中国连司法独立都做不到的情况下,胜诉只能期待官老爷的心情,就连「人民的名义」,惩治恶人也是拿比恶人更好背景和更大权力的主角来。陕西矿权案被爆出来才开始有好的进展,魏强案时隔一年才有庭审,谭秦东案,疫苗等等都是有了大量关注后迫于舆论压力才解决的。而709之后再难找到维权律师,metoo运动不了了之,工会维权中失踪的人到现在都还没回家。现在的中国,在面对社会中强者的欺压时,只能期待对方的良心发现或是上层的同情心要不就是舆论倒逼,而在思想渐渐收紧,舆论管控加大,舆论倒逼这种方法也渐渐无效了。
在封建时代,民告官只能靠上访向青天大老爷伸冤,漫漫上访路,和现在多么相似。这个社会表面上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经济强大设施现代,但内在还停留几百年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没变。
李佳佳女士沒有談論有關於兇手的信息,這點太可惜了。真的很想看看正經的分析,看看兇手究竟是不是孫維。
受篇幅所限,本文僅摘編了當年朱令確診一事的相關文字。謝謝您的關注,希望未來有機會為讀者提供更多朱令案的內容。
全文有相当多关于追凶的内容,这里限于篇幅没有摘入。
因为没有也不敢查嫌疑人
不是聽說下毒的人後台很硬,真希望兇手不得好死,全家死光
怎么没有关于案件嫌疑人的报道?
受篇幅所限,本文僅摘編了當年朱令確診一事的相關文字。謝謝您的關注,希望未來有機會為讀者提供更多朱令案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