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陈信宏在电视上看到劳动部吴姓员工因职场霸凌轻生的新闻,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经历。不同的是,对方选择在办公室结束生命,而他选择辞职重考。
那年,他在博士班毕业前夕,因家计与自身健康因素,放弃进入企业界,就赴国家考试选择当一名公务员。后来,他顺利考上,并在地方政府从基层干起;在他的想像中,公务员虽然薪水不算高但生活规律,对患有特殊疾病的自己,是一段稳定的职涯。
但现实却在第一天就泼了他一盆冷水。
在报到的第一天,主管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在这里,不要想补休,也不准请加班费,也不准请任何假、不能留加班纪录”。这样的潜规则,拥有人事法规专长的他,当下即感到矛盾与荒谬。甚至,在报到的这天,陈信宏已被交办做不完的工作;他几乎确定,自己所待的职场,是一个惯于违法的血汗机关。
之后的一个月里,陈信宏开始每周加班超过20小时的公务,“因为我年轻、又是单身男性,上头的人觉得我没家累、体力好”,陈信宏说,那个月他足足加班近80个小时。
一次,他甚至不愿配合单位撰写一份有伪造公文疑虑的书件,竟被主管从身后压著头,向欲伪造文书的对象道歉。
他不是没想过要自救,但当尝试向更上一级的的主管申诉后,他才发现,所有的申诉都原封不动回到加害者的手中。他很快明白,申诉结果只有一种:就是没有结果。彼时,甫报到就任的他,自然也没有申请转调的机会。
“整个体系就是习惯性地将申诉交给被申诉人自己处理。”他说,这不是个案问题,而是整个公部门的文化即是如此,他强调这是“文化凌驾于法规”。
在申诉后,陈信宏没有感觉到情况好转,反而让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在申诉内容交还主管、也就是他投诉的对象后,主管要求他撤回申诉,“除非你不想继续工作”。主管还对他说,“你做这些都没有用的”,并意有所指地说:“我会把你的名声弄臭。”
担心自己哪天会被抓去关的陈信宏,四个月后,他决定辞职。他带著辞呈去找主管,主管却以为他是要请假,“我不是告诉你别想请假的吗?”主管压根没想到,陈信宏真的敢辞职不干。他重新投入国考,一年半后再重新考回公务员;这次,他分发到某中部县市的基层机关,现在年资已逾七年。
这段近十年前的职场遭遇,在劳动部一名公务员离世后,他感觉自己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形容这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他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把这些人的恶形公诸于世,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在一名公务员自杀后,台湾政府大力宣示职场霸凌零容忍,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进而设立“职场霸凌案件通报平台”,作为公务员申诉职场霸凌的新管道。陈信宏看到了,他也上网去再一次申诉自己的陈年旧案;只是,十年后,什么也没改变。
近五个月来,他陆陆续续提交了数十万字的申诉文件,从人事行政总处、监察院、保训会,所有能够申诉的机关他都尝试了,但这些机关,仅是再一次将他的申诉转回原被申诉机关调查,再转交被申诉人去解决,或是收下申诉后不见积极回应;陈信宏纳闷,这能改变什么?
他想起学长对他说的一句话:“文化啊,一切都是文化问题。”即便体制在霸凌案后又新设了更多的制度,但在当前公部门文化底下,体制真的能保障公务员,而申诉亦能带来改变?或是,是让受害者承受更沈重的代价?

公部门无处不在的职场霸凌
陈信宏的遭遇,在公部门并非个案;让人却步的是,申诉未必能带来公正的结果,反而因体制内的权力结构,使调查结果不如人意,并让申诉者陷入更难堪的处境。这样的情形,使得许多公务员即便遭遇不公,也不敢轻启申诉程序。
他们只能选择沉默。他们清楚知道,申诉后的下场往往不是“问题”被解决,而是“自己”被针对,甚至彻底断送职涯——许多人最后只能默默离职,甚至有些人走上了更极端的道路。
2024年11月,一名任职于劳动部北分署的吴姓公务员在办公室内结束生命。据其同事的证言指出,吴员长期受到分署长谢宜容的高压管理和不当对待,包括在非工作时间透过通讯软体交办任务,要求即时回复,并被指派负责特定专案,但缺乏相关资源和支持,导致工作压力巨大。调查显示,事发前,吴员每日工作长达16小时,甚至假日也需加班,最终不堪重担选择结束生命。
在吴员自杀后,劳动部提出的首份调查报告却引爆舆论怒火。该报告指,主管在工作上对同仁的要求是“目的良善”,且“无法证明吴员有遭受长官职场霸凌之情事”。这样的结论,自然不被舆论买单,一波波的舆论海啸袭来,导致时任劳动部长何佩珊引咎辞职下台,其在职仅186天,创下台湾劳动主管机关首长最短命的纪录。
新任部长洪申翰上台后对此案展开第二次调查,报告认定谢宜容的领导方式已超过业务上必要且相当之范围,吴员确实遭受职场霸凌,选择离世也与职场遭遇有关。
然而,若不是这起公务员自杀事件引发大众关注,公部门的霸凌情事也难以遭受全面的检视。后续,政府展开全台公部门的职场调查,结果揭露,职场霸凌在公部门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级机关,包括卫生福利部、行政院人事总处、数位发展部等多个中央部会,都存在数起霸凌事件。
连“二乙”,与78分的潜规则
在台湾,当上公务员曾是稳定、尊严与退休保障的象征,但台湾年轻世代如今却不再向往公职。近十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幅下降,从2013年至2022年,降幅超过51%,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比率,更是骤降86%。此外,有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公务员辞职人数达到2752人,为22年来新高。少子化、就业市场多元、公职工作型态不符新世代需求,让被上一代视为“铁饭碗”的公职工作,不再如过往吸引人。
目前,台湾公务员人数约36万人,2023年数据显示,轻生是台湾人死因排名第11名,却是公务人员死因的第四名。在吴姓公务员自杀后,台湾公部门基层团体曾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并非个案,而是官僚体制的系统性问题,“公务员自杀事件频仍,霸凌更是公部门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然而,公务员林士宏指出,如果真的以霸凌标准去统计,有一半的公务员被霸凌,“为什么现在只爆出这么几件,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遇到霸凌就会去申诉。”
这是林士宏踏入公门的第12年,现于中央部会任职的他观察到,在公部门职场霸凌现象背后,与长官拥有的权力有关:包含你的考绩、是否能调职,都取决于长官一人。

公务员的考绩更与能否调职相关。林士宏解释,公务员每年都会打考绩,而甲等与乙等的差别,除了差半个月的考绩奖金外,“如果长官一直故意给你乙等,会影响到未来的升迁与转调。”
所谓的转调,虽然如同上班族求职流程——登入“事求人”平台、挑选职缺、投递履历、接受面试;但公务员们都知道,最终可能只是白忙一场。
想转调,自然首重能力,但一名公务员过去的考绩,很可能才是用人单位是否看上你的关键。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成员、担任公务员近十年的曾执辔指出,正常来说,公务员考绩都是一年甲等、一年乙等,每年轮替。不过,如果公务员连两年、甚至三年只拿乙等考绩,将使用人单位怀疑该公务员的能力,“你会连二乙,不是能力不足,就是被打压,但他们无法确定是哪一种,就会倾向不用你。”他分析道。
此外,乙等考绩也有分数的差别。曾执辔说,“正常”的乙等考绩为79分,被打79分,可能自己还会觉得只是运气不好“轮到乙等”而已;但如果被打78分,“你就死定了,这代表主管真的觉得你是个有问题的人,我要用78分来彰显你是一个烂货!”他说,这就是职场潜规则,若连三乙或是被打78分以下,“就是职涯的死刑。”
林士宏因工时长、工作压力太大,全身健康都出了问题,虽一直在密谋转调,但为了能成功调职,他现在只得在长官面前当个“乖宝宝”,所有不合理的任务都必须“使命必达”。
“公部门这么封闭的环境,可能A主管跟B主管是认识的,你在我这边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不开心,我就让你以后也过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反抗的原因 。”林士宏说,想调职时,大家都会相互打听状况,“所以得非常小心,一旦让长官不满意,就会影响到未来出路。”
林士宏提到,他身边就有同事因受不了不合理的对待,写信给立法委员,在事件传开后,他感叹道,“不会有人要收他了,他未来只能降调,降低身份调出去,再也不可能升迁了。”
而就算公务员顺利通过新单位的面试,能否成功转调,同样要看主管的脸色。目前台湾公部门的职场规则是,如果一名公务员想调到别的机关,须由新机关向原机关取得同意——原机关同意转调,公务员才能到新单位任职。
曾执辔指出,原机关可能回复“欠难同意”,或技术性地将商调期拉到半年之久,“但哪有机关能等你半年,就算你面试成功,公务员也没办法顺利调职。”
他观察到,在公部门中有三种人通常无法顺利调职。第一种是机关业务真的很忙、人手很缺,政府补人程序冗长、机关真的无法放人;第二种是能力太好,机关不想放你走;第三种则是跟机关有过节、跟主管处不好,“留下来是为了要恶整你、报复你。”
不是没能力转调,是没有权力离开。林士宏说,这就是他愿意隐忍、这么奴、这么服从的主因,他如果反抗过,之后是离不开的,想要离开,就必须乖巧温顺,这样才有可能离开,“在公部门,你只要不听话,你哪里都去不了,唯一的解方就是,忍耐再忍耐,时机到了我才能离开,才有可能好聚好散,因为只要不好聚,你是散不了的。”
有过节走不了,能力太好也走不了。过去在地方担任公职的李芷宁就是因能力优异,前两次申请调职时都被主管刻意阻挡,直到第三次才成功转调。
她回忆,当时自己已在机关内做出亮眼成绩,甚至获得奖项肯定,因此单位极力挽留,前两次转调申请都被以各种理由挡下。第三次时,她观察到直属主管即将调职,于是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调动对主管有利,从而争取到对方的同意。
她想出一套方方面面的策略。首先,得确保自己当年度的成绩再夺下第一,然后再进行调职。她说,“对主管来说,不仅可以将下属的好表现作为自己的绩效,我离开后,接替的主管也会因为失去好员工导致绩效下滑,此消彼长下,突显前主管的管理成果。”在这样的缜密计划下,这回,主管才让她顺利离开。

“铁饭碗”的幻灭
不过,公务员调职遭到原单位阻挠的现象,并非一直以来存续公部门文化中。资深公务员黄淑贞已届待退年龄,她在2011年调至现任单位,在2016、2017年两度想升迁调职,却都因原机关不同意而未能成功离开。
黄淑贞说,在她的公部门职涯中,过去亦曾多次转换任职单位,但这次却是她首度遭遇调职被挡的状况。在她眼中,或许与近十年来公部门制度或整体氛围的转变有关。她说,在过去,顶多是长官出面挽留,若挽留无效,仍会同意放人;但这次当她提出调职,对方单位的公文送达后,长官却直接将文件搁置,完全不予回复,最后不了了之。
公务员想调职,履历、能力固然重要,但放不放人的关键,恐怕在于原单位主管的一句话。
这份“否决权”,过去并未写入法规中,法律只规定要跟原单位“商量”,直到1987年才正式写进《公务人员任用法施行细则》,要求转调要原单位“同意”,等于赋予了原单位否决你转调的权力。曾执辔说,不管你去哪里面试,只要原单位不点头,你永远推不开那扇门。
尽管公务人员转调办法已入法,但曾执辔观察到,机关频繁使用否决权阻挡调职,其实是近二十年才逐渐频繁的现象。
曾执辔指出,过去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相对轻松稳定,大多公务员一做就做到退休,或至少在同一机关待上十到二十年,人员流动率相当低;若有人提出调职申请,原机关通常不会强力反对。然而,近年来随著公部门人员更迭频繁,机关内部流动率明显提高。为了留住人力、分摊日益沉重的业务压力,机关才开始更积极运用否决权,对调职申请设下关卡。
除了调职难度与过去明显不同,近年来整体公务员的工作强度,也早已和大众对“铁饭碗”的传统想像大不相同。
公务员陈彦廷任公职已有十多年,现于中央政府工作。他说,过去公务员的工作相当轻松,二十多年前他在公部门实习时,发现许多公务员的工作轻松到不太用得上电脑,这才让他留意到“大家的萤幕保护程式都特别炫”,但等他实际考进公职后,却发现情况已截然不同。如今,他一天八小时几乎没有任何空档,业务量永远堆积如山。
曾执辔也有一样的体悟。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退休,他回忆道,“小学的时候,爸妈不到休息时间就偷溜下班回家煮饭,我12点下课,到家没多久就有午饭可吃;爸妈吃完午餐,还可以睡午觉,睡完午觉再去上班,迟到也没关系。”他反问,现在有哪个公务员可以天天回家煮饭吃午餐,想到过往,他直言实在不可思议。
这样的差异,导致他跟父母讲述自己的职场困境时,父母反倒会不解地问他“工作做不完,你就丢著回家就好了啊!”“为什么每天都那么晚下班?为什么要一直加班?”
日益加剧的业务与工作量,与时代的演变不无关系。陈彦廷指出,在公部门引进公文电子化与追踪系统后一切都不同了,“以前的公文不够系统化,根本无从追踪起,就算到承办人手里,慢慢处理都可以。”陈彦廷描绘,“甚至有人会直接收进抽屉,摆到世界末日也没人理你。”他说,这也是日后民众会找上民代来“关心”案件进度的原因之一。
但在公文系统化后,加上研考单位严格管控公文与计划进度,大幅提高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与紧凑度。陈彦廷举例,在资讯系统发达的当下,过去需要一整年才能完成的业务,现在可能只给你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要求完成,“这等同于工作量暴增12倍之多。”
除了研考追踪进度,跟过去相比,公务体系的业务量明显增加,此对已是资深公务员的黄淑贞十分有感。她说,过去只要稳当完成既定工作即可,但现在更重视政绩导向,“上面想要政绩,会一直想新计划,导致公务员的工作量不断增加。”

不断叠加的工作量,也来自突如其来的上级要求。“就像是突然要我们办一个活动,还是以前从来没办过的,需要很多人力,或是经费非常拮据,”但想到这是上头长官交办的,黄淑贞只能使命必达,“你不会想说我就不要办了,没有,我们还是得咬著牙撑过去”。
曾执辔举例,以人事单位来说,过去的工作内容相对单纯,主要围绕在薪资福利等例行业务。但现在的人事,除了既有工作外,还得随时应对上级机关交办的各种新任务。
就像是,人事人员可能今天被要求统计特定职等员工子女的人数与教育补助金额;明天又有民意代表要求提出因应少子化的方案,必须搜集机关人数、职等、育婴留职等资料。再隔日,则可能轮到监察院关切人员流动率,要求提出留才策略等。
这样的变化,除了政治环境的变迁,也来自机关卯起来追求绩效的文化。曾执辔观察,公部门业务量激增,主要有三大因素:民代的质询与施压、陈情量暴增,以及政党竞争导致首长对政绩的要求。
“过去台北市政府统计过,陈情量非常惊人,可能一个局一年就有好几千件(陈情),甚至有上万件的。”他说,过去的情况并非如此,但如今民代为问政质询、或是打击政敌,会不断向公部门索取资料,公务员只能不断在办公桌前疲于整理与回复民代的需求。
曾执辔也说,机关疯狂追逐帐面的数字文化,除了证明自己有在做事,也为了防范在野党可能的政治攻讦。他提及,许多繁复的数据报表,其实并非来自在野党的实际要求,而是机关为了预防可能会有的质疑,先预备了大量的资料,以便在遭遇质疑时能在第一时间提出回应。
讽刺的是,这些辛苦整理出来的报表,绝大多数只是被归档收藏,仅在民代有质询需求时,才会偶尔被翻出使用。
他举例,一名公务员必须花上他一个月的时间,整理全台八千多个机关搜集来的数据、制作繁复的报表,“但做完后,被层层长官看完归档,没有要干嘛。等哪一天有立委问说,你那个事情怎么样时,可以赶快拿出来用。”
“这份报表从民国98年(2009年)整理到现在了,十几年过去,根本就没拿出来用过,就是整理完再收起来而已。”他说,但政府的业务只有加法、没有减法,“所以也才让大家无法下班。”

“长官就是你的天”
对这群公务员来说,超时工作已是日常,但加班费却有上限,亦为常态。
晚上近10点,中央部会大楼的灯火通明,林士宏已经工作了将近14个小时。已是小主管的他,上午八点半一进办公室就开始分派公文,同事无法完成的任务则由自己承担。中午匆匆买过饭,边用餐边工作,下午和晚上也是如此,直到晚间十点,因为办公大楼强制关门才让这一切“被迫暂停”。
但办公大楼的关门,不意味著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到家后,林士宏仍要继续处理未完成的事务。即便周末,他也难以放松,“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假日的差别,顶多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开始工作。”
去年,他罕有的休假,只有请两天特休出国、跟一天带母亲看病。但就算出国了,泡在泳池里的他,手里依然抓著手机回复工作讯息。尽管林士宏几乎是全年无休,但他实际申请的加班时数,每天只能填写一小时,周末则是“零”。
在公部门,加班从来不是用来“计算”的,是用来“默认”的。你可以日复一日待到深夜十点,周末也到办公室上工,但实际申报的加班时数,一个月40小时就是上限——而且,这还是“理论上”。
“之前有同事真的报到三十几个小时(加班),然后就被长官约谈了,说是要关心他工作状况。”林士宏苦笑道,语气中带著无奈。至于补休,虽然加班可换成补休,但工作根本做不完,林士宏也就干脆不申请了。
此外,许多公务员担心频繁加班会让主管质疑自己是否能力不足,因而索性放弃申请,选择“打假卡”、假日加班不打卡,或是就把工作带回家做。无法多领加班费、申请补休也没时间休假,公务员们选择独自揽著这些长工时下的身心俱疲。
而林士宏工时会这么长,则与他的主管的管理风格有关。其中,最令他感到挫折的,莫过于主管在文字表达上的“要求”。
“我提出的企划案架构,主管通常都没什么意见,但却可能因为一个用字遣词不够精美、文藻不够华丽,或是排版不够完美,而被退件八次、十次之多。”林士宏无奈地说。
“为了让文字更加精美华丽,我只好天天加班。”林士宏坦言,应付长官这种琐碎的要求,占去了他八成的工作时间,真正重要的工作反而被挤压到只剩两成。
林士宏感叹,公务员的工作是否轻松,一部分取决于“主管是谁”。他处理的案件,如果不用因为词藻华丽与个人的文字品味问题被要求反复修改,其实可以轻松许多;也可能有公务员本来做的好好的,但隔年换了主管就做得死去活来。
“长官就是你的天,你遇到好的长官你就上天堂,遇到不好的长官,你就完蛋了。”公务员罗凯文担任公职约八年,此前已离职公部门的他说,公务员的人生差异非常巨大,而这种差异,往往与长官的风格和部门属性直接相关。
罗凯文提及,他之前一个单位,长官不会刻意刁难、工作也轻松,他每天真的都朝九晚五。但为了升职转调到新单位后,上头两个长官,一个情绪控管不佳,成天对他破口大骂,另个则是绩效至上,就算自己病了需要就医,长官也会要求他“先完成公文才能离开”。
李芷宁也有相似的经验。她说,长官往往不会明确提供标准,让她“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问了会说,“妳怎么连这种事都要问我”,但不问,又会说“妳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让李芷宁难以接受的,在于他们提出的各种行销企划,经常被长官退回,甚至必须应长官要求将图片改到面目全非,“所有人都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努力去说服长官,反正你也不会成功,我们就像无助的老鼠,被困在瓶子里面,连游泳都不愿意,就觉得反正溺死算了。”
即使如此,面对不适任的主管,公部门的文化也如一滩死水。曾执辔说,多数主管都是年资到了就上去,上去后发现不适任,“但除非他贪赃枉法,不然只是能力不够、脾气不佳、对部属态度不好,首长通常会顾及主管的面子消极应对。”
他曾听闻过,有公务员向首长投诉长官霸凌,“首长就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啊,可是就拜托你再忍耐一下,他的职期就快到了,等他职期到了,我会想办法把他推荐到其他机关去。”职期到了,首长还是没能将主管送走,仅将原主管转调单位,结果反倒让调过去的单位人员一下走掉了八成。
曾执辔说,机关虽然可以组挡转调,但有个例外是,若公务员找到升迁职位,通常机关会放人,“这就是个潜规则,所以那单位走的八成的人,大部分都是找到升迁职位,才顺利转调成功。”他说这在圈内被称为“升迁加速器”,因为他会帮助公务员们为了逃离职场而加速升迁。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顺著这条“升迁加速器”路径逃离。陈信宏即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年,陈信宏甫于机关报到,即面对残酷的职场现实,他寄出的霸凌申诉,直接回到被申诉的主管手里,甚至不留下任何痕迹,仿佛这场霸凌从不存在。陈信宏知道自己的处境艰辛,他不想继续在这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申诉游戏中周旋下去,他选择辞职重考,再一次回到他心目的“铁饭碗”工作。
他看到了劳动部公务员自杀的新闻,直觉地感到讽刺,“作为劳动主管机关的劳动部却逼死一名劳工”,他决定起身追求属于自己的正义。
但追求正义的道路既长且阻。他说,即便自己写了数十万字的法规论述,依旧无法对抗那些无视法规的掌权者。十年后,他提出的申诉,依然由原机关收下,却未进行回避,之后再做出“不受理”的答复,形成“要被申诉者处理自己的被申诉”的怪异现象。
这像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轮回,一次次的申诉、一次次的不受理或消极应对,在他的眼中,“依法行政”终究是一场空话。
在这个体制内,制度如一座隐形的牢笼,虽然给予保障,却也套牢了希望。有人选择升迁逃离,有人选择忍耐等到长官轮替,也有人像陈信宏一样,选择辞职重考来过。但问题在于,在这个体制下,为什么公务员永远只剩下“走”或是“忍”的二选一?
(本文除陈信宏外,为保护受访者,皆采用化名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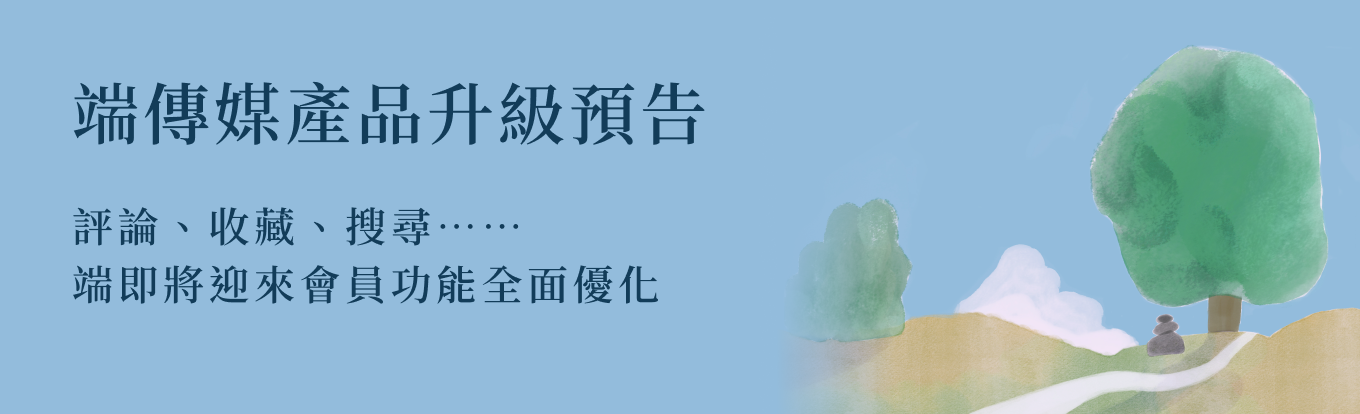


這篇報導涉及很多問題,其中事多而人力未跟上、甚至是為了配合民意代表質詢而作無用功的部分,讓我想到前陣子關於白藍刪預算的一篇報導:
『彭啓明指出,1日起開始試辦「每週五不加班」,最主要2個目的,一來是省電、二來是友善職場。他說,由於經常會應立委要求,在隔週一要交報告,之後會與委員交涉,也希望能延長交報告的時間。』
立委對行政部門的資料索求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不必要的負擔,這顯然不被認為是一個需要被關注的問題。因為在今天的台灣,公務員是連同執政黨-政府-行政部門一起被在野黨與他們的支持者踐踏的對象。
這種對行政部門乃至於公務員的輕視就會造成一種荒謬的現象:白藍在審批政府總預算時並不在乎細節,同時也無視政府業務的持續增加,直接用「總預算史上最高」一句話,就將預算大筆刪除。
「刪到人民有感」,用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是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是公僕們不計生死要完成的目標。
我曾在香港政府任職十年以上。
某部門出現一位「麻煩友」trouble maker,但在香港解雇公務員十分困難,程序繁複,公務員亦可以申訴。
於是該部門想到了一個方法趕走那位「麻煩友」~ 將他升職,因為只要將他升職就能將他調離原部門。
好离谱..
正如另一位網友的評論,覺得儘管地方不同,可是卻有很多相似之處。
真離譜…劣幣驅逐良幣
除了陈情部分是民主社会特色之外,其他其实和中国公务员的困境有点像。不知道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公务员现在什么状态,看来技术手段进步带来的不是赋能,而是更多的人被困在系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