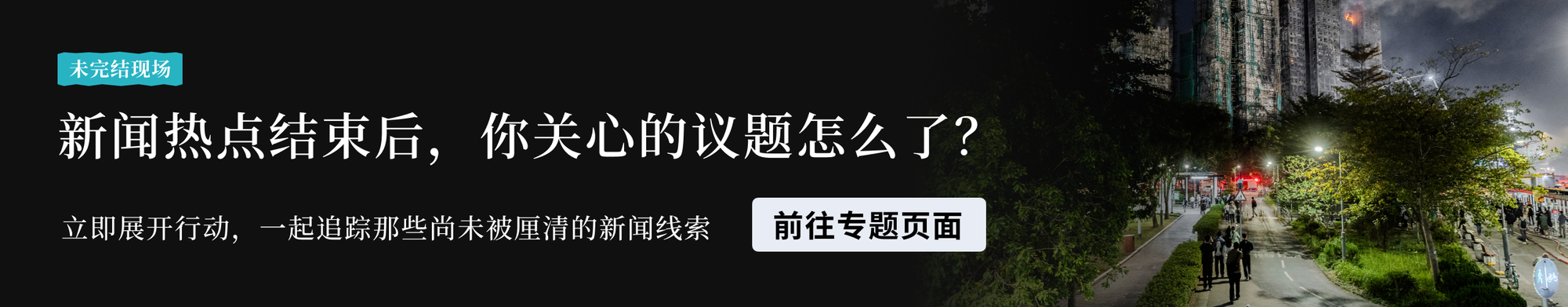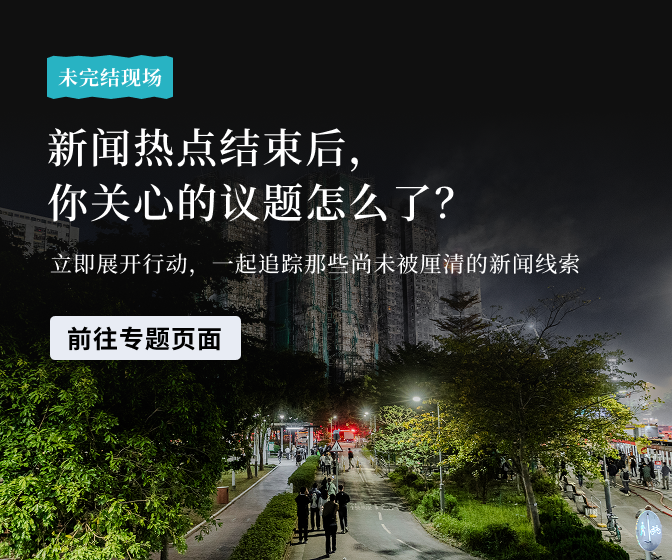速递 Whatsnew
更多
编辑精选







/
仅限会员
失落的热带:香蕉种植园和不属于这里的人
这群中国人和越南工人,是两个国家在不同历史进程拥有相似处境的人。种植园将他们放置在了同一时空,是同样没有保障且不确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选择,是背井离乡过一种农民生活。

解读
更多
评论
更多



/
仅限会员
评论| 十年《怪奇物语》:以怀旧为名,以迷因为媒,串流时代一场大型召唤仪式
《怪奇物语》以怀旧为主调,但指向经验匮乏时代的地下幽暗源泉,鼓励指南针坏掉的边缘者冒险,只留下一条规则:别让夺心魔剥去你的好奇心。

系列
更多
委内瑞拉变局-zh-hans
2026年1月,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袭委内瑞拉并抓捕总统马杜罗夫妻。这个系列关注权力如何交接、秩序如何被重组、外部力量如何进退、以及一个国家的命脉将如何被重新编写。
所有文章
栏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