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还在悼念刘晓波的时候,另一轮的政治压力已然集结。7月14日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区庆祥宣判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姚松炎、刘小丽以及罗冠聪的宣誓无效,即日起丧失议员职位以及旧任资格(简称 DQ,Disqualify
)。在这之前,同一法官已判决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宣誓无效,不得就任。
关于民选议员为何需要宣誓才能就职这个问题,笔者已在“梁游风波”时为文讨论过,而之后香港司法政治的发展,也让我们看到由暗角七警事件衍生的外籍法官风波。这两三年来香港司法政治的发展每下愈况,香港人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法治与司法独立,在北京的铁腕下似乎一点一滴地消逝。而如同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教授 Carol Jones 在她的近作所分析的,后九七的香港人常常以法治作为身份区隔的标准(他们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而当香港法治在北京的压力下不断的被突破后,香港人开始诉诸文化本土主义以抵御“赤化”。
我不打算赘述香港这几年来的政治发展,而打算从“政治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这个视角切入,分析香港这30年来司法政治以及法院角色的变化,并在最后点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已是香港司法体制捍卫自身权威与格调的最后机会。
民主国家的政治司法化
熟悉司法政治的读者,可能不会对“政治司法化”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指涉的对象感到陌生。顾名思义,政治司法化就是指行动者将政治问题丢给法院裁决;而政治问题主要是指争议的公共政策等等。
在欧美成熟民主国家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美国著名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打破了南方州“隔离但平等”的政策;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从隐私权推导出女人的堕胎权,进而确立了政府不可以完全禁制堕胎诊所的设立。在欧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判决,宣告德国的同性伴侣法与民法婚姻不符为部分违宪,进而逼迫总理默克尔(梅克尔)在前几周前再度表决并通过婚姻平权法案。
近年来更为重要的发展是,政治司法化已经不局限于政策领域,而更多的与高层政治相关,例如南非宪法法院一步步的推动转型正义,或是台湾的大法官宣告万年国大代表违反宪政秩序,必须改选,或是韩国宪法法院两次决定国会提出的弹劾案。
不论是哪类的政治司法化,论者大多认为政治司法化必须要有几个条件才会发生,第一是相对独立的法院体制以及宪法审查制度,第二是法院、法官策略性的行动,第三是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在一个连法院体制都尚未建立的地方,连“司法体制”都难以界定时,便遑论政治的司法化。而法院如同其他的政治行动者一般,会希望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取得自主性,进而在政治环境允许时,法院会倾向于自我扩权,将影响力扩及政策、高层政治领域。
但何谓有利的政治环境?近20年来的研究大多指出,当执政党、执政联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继续长期稳定执政时,他们就会愿意将政策决定的权力放给法院体系,希望可以借着法院的判决将政策延续下去。
威权国家的政治司法化
大多数关于政治司法化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老牌民主国家或是新兴民主国家,但在威权国家情况是否类似?西门菲莎大学教授 Tamir Moustafa 总结出,在威权政体下,法院也可能会积极的处理政治问题,但是这种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并不积极推动进步价值。相反的,法院可能只是威权政府的打手、威权政体内部管控的工具,或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措施。
例如在新加玻,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常常针对反对派提起诽谤诉讼,将对手告至破产,而新加坡法令又规定被宣告破产的个人无法参与选举,行动党就这样运用连环的法律攻势瓦解反对派的挑战。而在中国,司法权则扮演着处理央地关系的角色,许多针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争讼,可以有效地将地方政府的施政问题暴露给中央政府知道。而许多研究也指出,威权国家会在金融、经济领域打造有效率的法院,希望借此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市场发展。
当威权政体打造了积极的法院后,司法很可能就会成为公民社会的支点,行动者可以借由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等策略挑战威权政体的统治。但威权政体也有各种方式来限制法院的能力,常见的方式有提升司法自制、建立特别法院、摧毁法律扶助系统等等。
不论是民主或是威权政体,司法积极主义总是会面对来自司法界内部以及外部的批评。在民主政体最常见的批评是,一个没有民主正当性的机构为何可以针对政策做重大决定?而在威权政体,常见的批评就是法官不爱国、不爱党。在这样的批评下,法院也不会无限制的自我扩权,因为无限制的扩权可能会引起政治部门的报复进而斲削自身的权力。因此,在威权政体下,我们常常会发现政治部门对司法体制的攻击会进一步地引发寒蝉效应,进而让原本借由司法体制撑出的抗争空间消失殆尽。
而建立特别法院,让法院体系破碎化,也是威权政体限制法院能力的方式。例如在戒严时期的台湾,许多案件(特别是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都绕过普通法院而由军事法院审判,而军事法院的司法官又更要求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方式也有效的限制了法院的权力。
至于法律扶助体系,常常是社运团体公益诉讼的经费来源,摧毁法律扶助体系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司法体制对于威权政体的威胁。

香港的政治司法化
香港的政治司法化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进程,岭南大学学者谭伟强在他的著作 Legal Mobiliza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中指出,由于港英政府有意的扶植,香港有一个成熟且专业化的司法体制。在1990年代为了应对香港后六四的焦虑,港英在1991年通过的人权法案条例让法院有介入政治的支点;而完善的法律扶助体系(法援)又让公民团体有能力提起反对政府政策的诉讼。最重要的是,在九七主权移交过后,民主派直接参与政策制订的空间逐渐收窄,这让法院成为社会运动最新的战场:从吴嘉玲案到海滨长廊计划,法援所协助的案件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了港府的政策。而在高层政治方面,长毛梁国雄也屡次借由司法体制挑战港府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限制。
或许是中国政府发现了香港司法总是政策的绊脚石,或许是中国的国师们开始懂得操作法治的语言来遂行统治,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由下而上的政治司法化外,政府也越来越常主动针对反对派提起诉讼,除了利用《公安条例》来打压集会游行外,这一年来的发展就是利用诉讼来剥夺议员的职位。
而除了传统的舆论攻击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法院在最近这两次的 DQ 案中,服膺于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内容,并在梁游 DQ 案中,高等法院上诉庭明确地接受了北京方面的释法,驳回了梁游的上诉。而打从第一次人大释法开始,香港终审法院在刘港榕案中就通盘接受了释法的结果,并且称人大常委的释法权是一般性和不受约制的权力(plenary and freestanding power)。这也说明了,香港法院为了避免跟北京直接起冲突而展现出高度的自制;此次 DQ 案也不例外,这很明白的就是中国政府借由释法的操作来加强香港法官的司法自制。
我以前讨论过,要让法官做出符合政治需求的判决,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借由人事的变动。但在这两次 DQ 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要让法院为威权政治服务,最快的方式还是借由施压的方式造成寒蝉效应。直接的改动人事会让舆论压力落在行政权头上,但威胁利诱法院做出不受欢迎的判决,可以让舆论压力导向司法体制。北京方面的目标,很可能是在香港打造出一个在政治上服膺于政权、不受民众信任与欢迎,但在金融、商事领域仍有独立性的司法体系。
司法体系的支点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我也看不出公民社会有任何施力的支点。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脸书上向现届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注一),要求它与上届政府的立场切割,一方面可以说是务实,但另一方面他却完全没有挑战 DQ 判决的正当性。而这几天谈得风风火火的总辞,如同不少论者所说的,不但没办法瘫痪议事,反而提供建制派更迅速操作法案的空间。
当然,我们可以期待在 DQ 议题上尚未发声过的上诉庭和终审法院会重新审视议会自治原则,以及重新思考人大释法的拘束力(人大释法并没有针对个案适用法律,而是做出原则性的法律解释,终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是有操作空间的)。
但除了期待终审法院的弥赛亚时刻外,我们更该注意的是,北京以及港府是否会设立特别法庭绕过普通法院以降低法院的能力,以及是否会如同新加坡一般,借由诉讼案把反对者告致破产?还有港府是否会削弱法律援助署的经费或是介入援助署的选案?毕竟,除了街头之外,我们可能只能对法院还抱有期待了,即便它已摇摇欲坠。
(黎班,法学院打工仔)
注一:五点要求分别是:一、承诺必不会提出 DQ 其他议员的诉讼;二、承诺在四位议员的案件,不会追讨讼费;三、承诺在相关案件所有上诉终结后不超过四个月进行补选,包括梁、游的案件;不会为了合并补选,而不必要地延后补选的安排;四、表明不支持立法会在完成所有补选前修改议事规则;五、承诺不在立法会在完成所有补选前,向立法会提交具争议性的法律草案或法案如23条立法或政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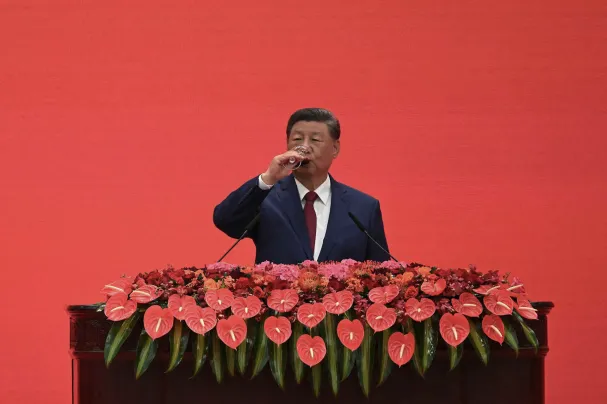

图1和2下面的小字标错日期了,赶紧修正吧
感謝讀者指正,錯誤已修正,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