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知识分子是不断为社会创造“危机”的人,萨依德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思想上之流亡者——他们拒绝主流,对权力荣耀保持距离,质疑与挑战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体系,却也没有安身立命的“故乡”,永远难以释怀。他们以生命介入社会,形成尴尬,缔造一个有危机意识的时代。知识分子位处边缘,抗拒成为“专家”,不靠依赖权力而活,不说专业意义下的术语,他们是思想上的业余者——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萨依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美式教育,后于1950年代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博士。他曾说自己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就算称不上诡异,也至少是古怪……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与矛盾”。这样复合的身份为他带来独特的思考视角——“对立”、“对抗”、“对反”、“对位”是他经常强调的元素。他最受瞩目的作品《东方主义》(Orientalism),探讨“东方”的概念是被“西方”主流学术及媒体为帝国主义服务下所生产出来的偏颇与矮化再现。
本书《知识分子论》总结了萨依德长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系列反思,由几篇1993年发表于英国广播公司“李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的演讲稿延伸而来。二十多年过去,萨依德对知识分子观点,似乎于两岸四地的我们仍有参考价值。政治权力不断膨胀且入侵诸众领域,我们总会发现有人投身权力圈,为政权之不义说项;即便有人乐于成为边缘,教育体系以专业之名而来的出版压力又使几多知识人为着职业的晋升和承认,脱离挑战群众,动员其参与民主社会之责?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社会之间,必然极具争议,却也急待探究。
端传媒将会一连两天摘载《知识分子论》,以下节选自本书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获“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刊出。
《知识分子论》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出版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萨依德(Edward Said)
译者:单德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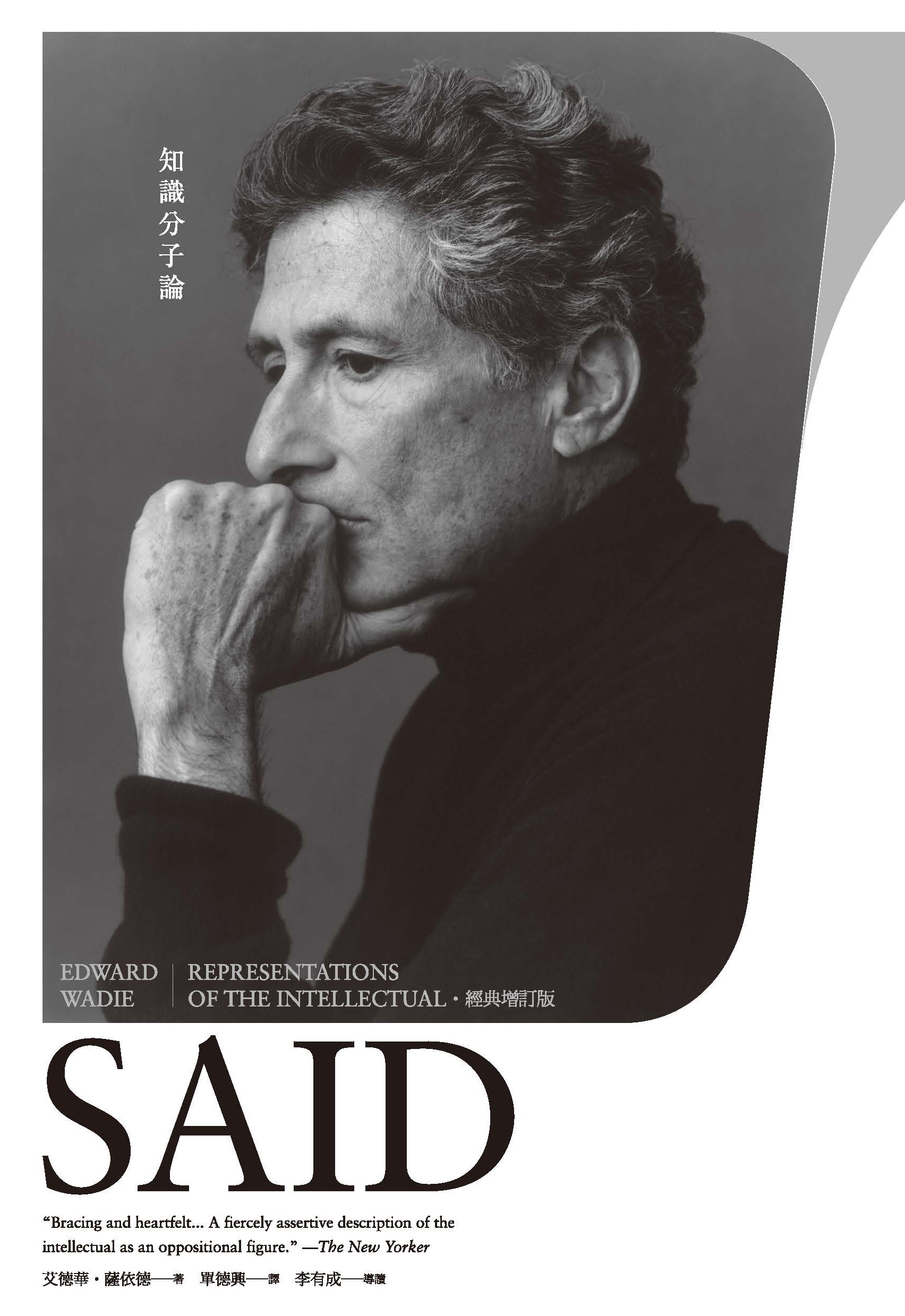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它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疯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在二十世纪,流亡已经从针对特定个人所精心设计的、有时是专一的惩罚(如伟大的拉丁诗人奥维德[Ovid, 43 B.C.-17 A.D.)从罗马被远远流放到黑海边的小城),转变成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而这经常由于像是战争、饥荒、疾病这些非个人的力量无意中造成的结果。
……
有一种风行但完全错误的认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断,孤立无望地与原乡之地分离。但愿那种外科手术式、一刀两断的划分方式是真的,因为这么一来你知道遗留在后的就某个意义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完全无法恢复的。这种认知至少可 以提供些许的慰借。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
……
政治修饰(political trimming)这种很模糊的艺术(不采取明确立场却生存得好好的技术)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的或冒现的主宰势力,是我下两讲的主题。这里我要集中于相反的主题: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论点。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流亡的知识分子的研判,来自本讲开始时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但并不限于此。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国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其次,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乐,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 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这种看法时,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惊)。知识分子也许类似怒气冲冲、最会骂人的人。
……
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样的灵巧来回避新与旧,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著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
其中一个片段——《最低限度的道德》第十八节——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义。阿多诺说:“严格说来,居住在当今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兴趣陈腐的契约为代价。”这是在纳粹主义之前成长的战前人们的生活。至于社会主义和美国的消费主义也没有更好:在那里,“人们不是住在贫民窟,就是住在小屋,到第二天可能就变成茅舍、拖车、汽车、营地或露天。”因此,阿多诺指陈:“房屋已经过去了。……面对这一切时,最好的行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虚悬的一种。……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 一部分。”
然而,阿多诺刚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便立即加以反转:“但是,这个吊诡的命题(thesis)导向毁灭,无情无爱地漠视事物必然也不利于人们;反面命题(antithesis)一旦说出,对于那些内疚地想维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
换言之,即使对于尝试维持虚悬状态的流亡者,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因为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state of in- 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这种居所的虚假在时间中被掩盖),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但是,阿多诺继续追逼:“怀疑的探究总是有益的”,涉及知识分子的写作时尤其如此。“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诺最后提到不得松懈对于自我分析的严苛:
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或写作]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结果,作者不被允许在他的作品中存活。
这是典型的忧郁和不屈。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种满足、 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人从全无“居所”的焦虑和边缘感中得到些许短暂的舒缓;但是流亡的知识分子阿多诺讽刺上述的观念。阿多诺所未言及的则是流亡的乐趣,流亡有 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真确的。然而,也有必要强调那种状态带有某种报偿,是的,甚至带有特权。因此,虽然知识分子并未获奖,也没被欢迎进入自吹自擂的菁英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惯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规、令人尴尬的惹是生非者),却同时从流亡与边缘性中得到一些正面的事物。

当然,其中的乐趣之一就是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处置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我觉得大多数西方有关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危言耸听、严重缺失的讨论,在知识上之所以惹人反感,正是因为没有和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相比,就我个人在中东的经验,这两种基本教义派都同样盛行,而且应该受到叱责。通常被想成是对公认敌人的简单评断的问题,在以双重或流亡的视角来看时,迫使西方知识分子看向一个远为宽广的景象,因为现在所要求的是 以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或非世俗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所有神权政治的倾向,而不只是面对惯常指定的对 象。
知识分子流亡的立足点第二个有利之处,就是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机缘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
最后,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会证实,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来几乎不值得。你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 失去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直待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经历失落曾经拥有的事物,更不必去体验无法返回过去生活的那种折磨人的回忆。另一方面,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曾说的,你可以成为自己环境中的初学者,这让你有一个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尤其一个不同的、经常是很奇特的生涯。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在寻常生涯中,“做好”(“doing well”)和跟随传统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剥夺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
……
对于受到调和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者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而且我在这里所想的也不是所谓的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术能力完全待价而沽。相反地,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