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学聘任我在其社会科学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国的高校教书有十多年,虽然教过的学生背景广杂,但要来香港,我还是做好被挑战的准备。
最初,我课上有香港本地学生、大陆来港学生和来自英国、美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交换生。我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和美国大学不同,香港的本科课程大多一周一次,一次三小时。学生很内敛,既不喜欢提问,也不喜欢参与课堂讨论。他们之前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以记忆正确信息为主,这让他们有些惧怕开放式讨论——怕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更怕会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样子。于是,前几周基本上都是我在问问题,等好长一段时间,期待学生能够回应。
每学期开学我都会把来自西方国家的交换生叫到一边,和他们解释,这里和他们的母校不一样,在课上说话时请先举手。不然这堂课会很容易变成交换生和我之间炽热讨论、其他学生静坐观察。一个美国学生不以为然,他批评:“你这样规定不公平。”“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本地同学来说,以交换学生利益优先的课堂也不公平。下次说话记得举手。”
每学期学生们都要花一段时间明白,我不需要他们提供正确答案,很可能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确的答案,社会科学更关心问出正确的问题。当我觉察到同学们已经逐渐对我有信任感、愿意回答问题时,我就会在他们回答问题之后一直问“为什么”,直到他们受不了为止。
“你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
“为了开拓我的视野。”
“别说得那么空。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学这个专业?”
“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
“为什么要找工作。”
“揾钱。”
“为什么要揾钱?”
“为了照顾我的父母。”
“为什么要照顾你的父母?”
“因为他们抚养我长大,我欠他们的。”
“为什么抚养你长大会成为债务?”
“求你换个人问好吗?”
我当然不是要学生不去照顾父母,我只是想展示我们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社会形塑而成。学生们也慢慢放下戒备,有时他们反问我这个美国人是否会寄钱给父母。我诚实回答很少那样做,美国社会没有这样的习俗。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很过分,我会由此出发和大家探索这些道德评价和社会常规,越谈越深。逐渐地,我不用再等著有人愿意回答问题,我可以随意点名,点到的学生已经能比较有安全感地参与讨论。
研究生班级中大部分是大陆来的学生。最初那些年,这些学生态度非常开放,愿意谈论一些我以为属于敏感范围的话题。那时候整个中文互联网也有这样的风气,《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还很受尊重,学生们常常提到这些信源。当然每个班里总会有一个同学对这些很抵触,他们坚持像《美国贱队:世界警察》(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这样的电影并不是讽刺性喜剧,而是美国政府为外国儿童制作的政治宣传片。但这样的学生并没有代表性。

我知道,作为美国人,我接受过不少对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国民先入为主的观点,就像我的中国学生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美国人一样。社会科学学者和教育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反思和解构这些偏见。有时我们会谈论在生活中实际遇到的现象——有的学生认为西方媒体总是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赞同他们的观察。分析为何如此的同时,我也会介绍西方新闻倾向于报导负面消息,不管对象是谁,这是这个行业对自己的定位。有个学生提到美国人仇视中国人——“我和家人去纽约旅行,纽约人对我们很不礼貌,他们恨中国人。”没错,纽约人对他和他的家人是非常粗鲁,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纽约人对谁都很粗鲁,包括纽约人自己和其他地方去纽约的美国人。我们双方都承认,有一些自己身份之外的视角仅靠我们自己很难想到。学生们好奇心很强,反思能力也很高,我们都会在讨论中反复思辨这些复杂的小事,咀嚼出些什么。
现在想起那时的课堂,很怀念。那时我们没有太多政治问题需要担心。事实上,十多年前,尤其是本科生课堂,大家很少涉及和政治有关的讨论,我很难让学生对宏大命题产生兴趣。本科生们目标明确——读书、揾工、买楼。研究生课堂上,我们也很少涉及3T话题(台湾、西藏、天安门),一方面我并非专家,另一方面也有学生担心他们的同学会搜集黑料、举报他们。课堂上,大家心照不宣绕过最敏感的问题,这以外的领域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和对政治完全无感的香港本科生相比,大陆来的研究生更容易谈起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心态也更开放。
本科生的政治冷感后来逐渐改变,我认为开启这些改变的是香港的通识教育。十多年前,当香港政府开始考虑将通识教育加入中学课纲时,我同时抱持两种态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好事,中学老师终于可以在教育学生们死记硬背之余,教育学生如何思考问题。这样大学老师也不会总是抱怨大学新生缺乏智识上的好奇心和热情。
但同时,我和同事们担心,批判性思维会像潘朵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香港人真的准备好让孩子们问问题吗?孩子就是这样,一开始你教他们问你想要他们问的问题,但不多久他们就会问你不想他们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结婚生子?为什么我要和你一样搏命工作?当个同志有什么不好?香港的父母、香港的政府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吗?
没过多久,2012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推动国民教育时,事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少年人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当然也许那时政治早就先一步对学生感兴趣了。学生们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知识。新的爱国主义课纲不得不暂时搁置,第一批年轻人由此得到了政治参与的一手经验。

两年后,87枚催泪弹之后,“占领中环”让世人看到香港年轻人的政治自觉。想到那几年的任教经历,有些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最明显的就是本科生和我交流时忽然谈起了政治。他们急迫想要谈论一些深刻的日常政治。这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学生了,他们开始用政治学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在的城市,谈吐的广度和深度都让人惊叹。接下来的几年,学生们越来越批判。在直接的政治议题外,学生们也卷入关于文化、社会、性别、劳工等等方面的讨论中去,这在几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同时变化的还有研究生,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在习近平强势崛起和香港抗争意识觉醒之间,来自大陆的研究生似乎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愿意谈论政治了。私下里,他们可能还是会互相交流,但在课堂和其他公开场合,大家都很安静。抱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同学解释自己前来求学的原因时,会说:“我是为了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中国的样子。”听到这样的宣言,我本能发问:“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以前,同学们会明白这些问题是思辨的出发点,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但现在不同了,交流的空间不断缩小。
2019年6月12日,香港有了点生气,让人回忆起占领中环时的感觉。人们涌入夏悫道,自发组织游行,现场井然有序,直到警察认为扔向他们的空水瓶是致命武器,并向民众发射橡胶弹和催泪弹。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场遇到的一个女学生,十几岁,坐在一架天桥上。她没有哭,但混乱的现场中她惊恐地发抖。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站在她旁边,希望这有用。只是,我心里知道并没能为她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无力。她不应该经历这一切,没有学生应该被这样对待。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是个挑战,因为抗争还在继续。警察最后来到学校,他们说大学就像癌细胞。学生则嘲笑警察,“带著水炮才敢进校园。”我那学期教的课和政治游行没太多联系,所以课堂上我没有谈及本地的抗争。那是一门本科生课堂,也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人数上他们是少数。我专门在课堂上说,如果大家对政府或意识形态不满,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攻击别的同学。回到校园的本地学生和以前比,变化太大,他们失去了某种天真——那种毕业礼上和玩具公仔合影的无忧无虑。他们中很多人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也明白曾经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是过去式了。以前的我会对玩具公仔不以为然,期盼学生快点成熟,但现在真的这样了,我却十分怀念从前。学生们成熟地太快了,短短一个夏天而已。
我的学生中没人被打伤,但不少人亲历了血腥的场面。最近我偶遇一个之前教过的学生,曾经爱说爱跳的她看上去成熟了一轮——她眼睁睁看着朋友的鼻子被警棍打烂。还有个学生运气不好,在警察围攻学校的时候没能出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另一个学生有天在旺角逛街时不巧穿了件黑色T恤,因此被捕。虽然警方没有提出指控,他被释放后整个人完全变了。本来他就不爱说话,现在他完全避免和人接触,能消失的时候绝不出现。
在美国,警察暴力一直是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警察暴力,但很少美国人会惊异于美国存在警察暴力。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暴力如此少见,我刚来的时候甚至都不习惯这样的安全。对香港人来说,对我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不习惯是反向的,而且迅速。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暴力会发生,也就没有人做好准备,更没有人想到要让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哪怕之前在美国,我曾经有朋友死于警察暴力,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现在的学生。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安全一去不复返了。

雪上加霜的是疫情,香港的大学开始线上教学,很快这成为常态。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能够熟练使用Zoom。对于那些害羞的学生来说,Zoom可能让课堂更公平,他们能够私信老师问问题了。但线上教学的短处远比长处更多,尤其是在目前的香港。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对于精神健康都缺乏开放、关怀的态度,目前的局势让一切更加糟糕。很多学生困在家里,但他们无法和父母沟通。早在2014年占领中环时,香港不少家庭因为政见不合就充满矛盾,想想看,如果一家三四个人随时可能剑拔弩张,又不得不在不到500呎的空间内朝夕相处,该有多么难熬。2019年秋季学期,我注意到不少本地学生因为情绪抑郁申请学校宿舍,他们无法处理撕裂的家庭关系。
从那个学期开始,我常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如果需要的话,要寻找专业帮助。这不是我该做的工作,但这也是我该做的工作。我和学生说,不要什么都憋在心里,难过时要去找能够交流、聆听的人。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来找我,我是最后的选择。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医生,但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人了,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也很吃力:我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学生,当他们的朋友和同学被警察逮捕了?我怎样骗他们说一切都会好的?
只有一句话,我说起来十分笃定: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
在今天的香港,作为老师,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勤思好问?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诚实自省?我们如何告诉年轻人应该好好计划将来?也许更实用的人生经验应该是:“保持沉默,努力消费,直到死亡。”我们的学生还很年轻,他们的路很长,但并不明亮。其实作为老师,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开始黯淡。

最近我教的一门研究生课上,第一次没有一个本地学生,同学们全都来自大陆,有些人上课的时候人还在大陆——这是线上教学。这门课我教过好几年,熟悉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这是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如前所述,核心教学方法是鼓励学生审视和分析生活中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这学期我第一次看到一整个班级集体拒绝这种方法。
我常常会请一个学生解释和分析他/她经常使用的某个词汇。这样做从来都不是要借此攻击这名学生,而是从熟悉的话题开展讨论。这一次的学生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方法,他们展示出很强的防御性,不但不愿意参与正常的课程讨论,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坚持这些词汇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虽然他们常常对这些词汇缺乏系统甚至基本的了解。
从有些学生的言论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用不熟悉的方法就了解和接触外面的世界。每当有机会了解其他文化,他们的选择是拒绝。一位同学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由政府直接控制文化产业,并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确如此。而当我尝试解释如何分析和审视“血缘纽带”或“种族”这样的社会概念,这门课的学生表示很难接受这样的分析。当我邀请来自中国以外国家的华人分享国族经历时,学生认为这位讲者是被她的国家洗脑,希望她能够正视自己和“祖国母亲”的关系。还有几个学生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其实得到优待,比如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时会得到额外的10分,所以真正被压迫的受害者是我的这些汉族学生⋯⋯
这门课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学生们的作业、态度和之前的学生比相差太多。一些学生能够学习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但大部分人的作业水准很低。整个学期我都想方法克服遇到的困难,试著引导学生去问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张口就说出经不起分析的口号。课下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反思到底是不是我有问题:我是不是说话的方法不对,我是不是不够理解他们。我能感觉到学生们不喜欢这堂课,但我收到学生填写的教学评估时,还是震惊了。

这次评估中,大部分对我的批评的逻辑是,因为这堂课不是按学生们希望的方法教的,所以老师的水平很差,老师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备课。这还没有让我特别惊讶,直到我看到很多人异口同声地写:应该解雇这名老师。
这样的评估让我闻到清洗“不爱国”教员的讯号。在另一所本地大学里,一名讲师被学生打国安法热线电话举报,这位老师坚信这是学生的报复行为,因为这名学生在他的课上获得较低的成绩。
这也许只是个开始,外国教员不然叩头,不然就被赶走。就好像我们的香港学生一样,走,或者屈服。反正政府早就告诉世界,他们有多么不在乎年轻人。
我们就这样看着一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和情绪被磨成粉末。新世界的教条和我们之前的教与学背道而驰,而我们唯能期望自己能够坚持,期望我们目前经历的不会一直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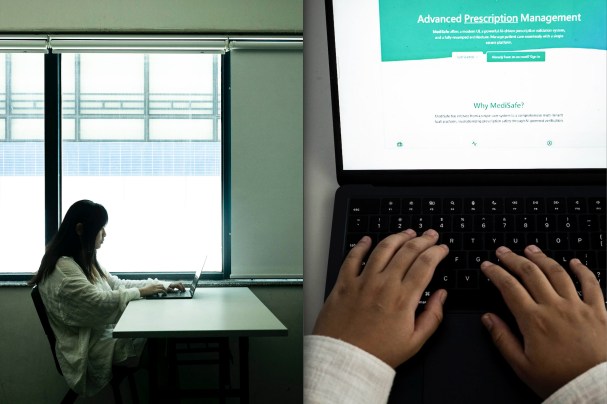
多好的文章
很可悲的是,现在香港人的确需要好好向大陆民众学习一下如何和强权相处的经验了。我认为14,19年的街头运动太多人缺乏对于北京的理解,对于自己的对手完全无兴趣
俄罗斯也有类似粉红这群人,现在分化出变种更加极端了,以俄为师的大陆应该会出现比粉红更极端的国家主义变种。我持乐观态度,人类还能经历二战那样战争吧,二战后出现了联合国,三战后能出现什么呢?
共產黨果然厲害。
令人擔憂,香港沒有通識科後,只會令下一代越來越粉紅,天朝心態更盛……
我身边也有一个案例,10年前认识一个在港中文读研的广东学生,他当时因为写了一系列关于占中运动的文章让我对他非常佩服还加入了他组织的读书组织;然而这些年我从微信朋友圈亲眼看到他一步步走向了国家主义的叙事模式,尤其是2019年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冷嘲热讽…怪感慨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年轻人的进化…
我認為@bbbbbb 說的是研究方法上,如何可以問一個好問題。問好的問題,和如何回答問題,都很重要。
我最近求职面试,面试了一个已经被体制收编的公益组织,(以前是做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现在做流动儿童)我讲出很多我知道的公益现状,负责面试的hr和业务,第一幸好她们没有反驳我,第二她们好像也没有太了解例如黄雪琴,维权律师的情况,我之前一直以为国内的公益组织起码是互联的,结果发现大家已经不太关注自己行业内的其他群体了。我表达我的政治观点的时候,也没有被反驳,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一轮,也没说我不懂事,我和我爸聊政治,他也表示很明白当下的情况是恶劣并且糟糕的。目前活跃的粉红一代,一方面是网络封闭和娱乐至死,一方面我感觉是精神无处安放,除开爱国这个价值体系,只要活着,你就能感觉到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仍旧选择如此。粉红手里也踩着加速的油门,民粹会有好果子吃吗?历史不早就证明了。当然,我就是底层,目前仍旧幸运地活着而已。
@bbbbbb
一切批判均基於“目前海外見到的中國人及中國學生粉紅親共佔大多數”這一基本事實之上。當然,若果需要一個精確的數字比例以證明“佔大多數”,這顯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一般人做不到。只能講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及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即是如此。然而,藉此否認“遍地粉紅”,進而主張無法繼續批判下去,其實是邏輯謬誤之一種,所謂Loki's wager。講得明白一點,好比威尼斯商人中,取一磅肉,那麽血包唔包?無法究竟多少血多少肉算符合約定,則約定就作廢?
既然作者已講出其觀感,評論區諸位亦基於自身體驗予以認同,你若果有相反意見,不如由你舉證以證明確實有其餘因素影響中國學生的表現結果,而非抛出問題代替論證。
感谢作者的分享,我在海外留学中也有跟作者类似的感受。中国同学真的很爱国,只是在一起玩一下还可以,但无法跟他们讨论政治问题,每次他们聊的热火朝天的中国好外国不好,我就不说话,因为知道我这样想法的真的好少,并且他们的固有观念太强,说什么反驳都不会有用。
近十年来的年轻人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各种社交媒体和视频APP了解信息,有心人自然会通过这些APP大量植入希望年轻人接触的信息,从而影响年轻人的意识和认知。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阅读经典。
感謝David的分享,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人在不同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困惑,經歷和恐懼。
包括這篇文章在內有不少軼事證據說明大陸社會在民粹化,當然這種變化似乎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普及化下的全球普遍存在的現象。那大陸的案例有什麼不同呢?對此的階段性判斷和很多人一樣,就是大陸的民粹化似乎缺少有效和公開的制衡。大陸民粹思想的商業化和泛化現象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普及看起來越來越深入,而能夠制衡他們的思想似乎處於一種比其他時期更犬儒的狀態。同時有關部門對這種情況是半放任,甚至有時候會參與分一份羹。歷史上不同時期和地點的案例都告訴我們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不受有效制約的混合演化會產生多麼破壞性的潛在社會後果,這也難怪全球不少人對此都表示擔憂,尤其是在大陸目前的國力和規模已具全球影響力的情況下。
@Cromah 很多人是為了證書 / 其他目的(e.g.居留權),而不是真的對科目有興趣
我觉得作者的观察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他面对的一直是同一年龄层的人,所以他观察到的现象比较可信。至于如何解读这个现象,是因为大陆学生整体的思辨能力降低,还是因为香港的大学变差,使得他观察不到原来那个层级的学生,还是因为社会风气变化,使得学生更谨慎,甚至有敌意,还是因为作者在香港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对香港视角越来越同情?解读的角度有很多,除了年龄是控制项,其他的方面都可以慎重考虑。那么,评论区的诸位不慎重分析,而上来就泛泛定性,又算得什么呢?
另外,其实我很相信一手经验的,这也是作者文章的可贵之处。可是我混迹评论区也有一些时间,总觉得很多人并没咋么接触过香港人,大陆人,外国人,而只是发泄一通,那又算什么呢
@Weber也许只是因为大陆上网的群体逐渐年轻
我過去十幾年在互聯網上與大陸網友互動的經驗與作者反應的趨勢相符。
@bbbbb
誰都知道五四時的中國人,六四時的中國人,還有現在的小粉紅,各有不同...談中國人,不是默認為現時的小粉紅,難道是五千年前的炎帝、黃帝?
我分不清bbbbb的留言是不是反串
我真是很佩服各位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就给中国学生和中国人定性的勇气,你们的泛指甚至没有大概的年代区分(而这篇文章的作者至少注意到10年之前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更开放),也很少有一手体验。泛泛的diss大陆群体/大陆习惯是我在端评论区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我不知道当你们在网上这样评论时,你们是怎么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协调的。你们周围有多少同事、同学是大陆人呢?你观察到的他们的言行和你在网上看到的文章相符吗?有一手经验还是道听途说呢?如果相符/不相符,那和你的背景,周围环境,日常相处的方式等等有没有关系?
Is he has written in Chinese or there is a translator helping in this article?
…我只是想展示我们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社会形塑而成。
…
听到这样的宣言,我本能发问:“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以前,同学们会明白这些问题是思辨的出发点,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但现在不同了,交流的空间不断缩小。
…
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医生,但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人了,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也很吃力:我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学生,当他们的朋友和同学被警察逮捕了?我怎样骗他们说一切都会好的?
只有一句话,我说起来十分笃定: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
Seriously…
很好的文章 ... 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些年青人如果民族自豪感如此强烈,对外面根本不感兴趣,为什么还要去香港学习社会学 ... 实际上,去到外面任何地方学习人文类学科,不都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德國為了避免再次重蹈納粹的覆轍,在教育上付出了那麼多努力和反思,直面自己的罪惡,還不斷為當年的過錯補償和道歉,才會有今天相對多元尊重的德國。
那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對當年那麼多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又做了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不去直視錯誤,經濟改革到現在國家富裕了(雖然大部分人還是貧苦,但政府確實很有錢)就開始說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還開始不斷打壓公民社會,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國度會發出怎樣的聲音。
每一個個人,在這種自由的崩壞之中,曾經如何參與,如今又到底角色如何?
每一個個人,在這種自由的崩壞之中,曾經如何參與,如今又到底角色如何?
非常好的大變局時期,大學第一線教師得手記。香港曾經那麼自由,如今又崩坍的如此之快,值得深刻反思!
我還記得快十年前剛上大學的時期在看到知乎上面許多中國人對社會問題的分析,深入淺出且邏輯清晰,心下擔心未來要與如此優秀的年輕人在世界的舞台上競爭實在是壓力山大,當下更加督促自己用功——不要在台灣以管窺天,以為週邊的年輕人不思考社會議題不關心公民政治就可以放鬆自我的學習。
結果現在快十年過去了,我發現台灣年輕一代和我這代的人們都開始關心社會議題,每個人都在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再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反而是中國那邊開始變得奇怪,知乎上關於政治社會議題的評論也都越發淺薄與殘忍:低端人口清理、新疆光榮的勞動改造、入關學、留島不留人…等,無不顯示這代中國年輕人對於弱勢族群的蔑視,以及為了達成「歷史使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殘忍。
知性的話語被冠上公知恨國黨的帽子被棄之如敝履,「民主」「自由」變成負面的詞語,「獨裁」「專制」與「遠見」「效率」劃上等號。為了政治將中醫治療COVID-19作為議題瘋狂炒作,但專業人士都看得出來這是在唬爛。
如此瘋狂的國家如果真的能在未來取得如他們主席所說的科技創新與突破,擊敗美國建設起人類共同體的話…我對人類這個物種的期許也將徹底改觀:因為這證明了人類的進步不是依靠自由與智慧,而是暴力與思想控制,這將是多麽可悲絕望?希望那天不會到來,希望。
辛苦了。
年轻人觉得什么问题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所以在网络上叫嚷着抄作业,而提出问题的人让他们感到困扰,所以支持政府阶级掉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文章的前半段让我一下想明白了这个逻辑。
形塑这一代大陆年轻人的是高压政治环境,而远比年轻人强大占有更多资源的同时代中产如果还在沉默的话,不是太有资格骂年轻人吧。中国Z世代年轻时候被形塑是不幸,当然如果将来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逼仄和极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和言语悔过负责是成年人份内事,红卫兵亦然。
這句話很感動,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知道這裡的該和不該背後有多少的思量。
「從那個學期開始,我常常在課堂上提醒學生,如果需要的話,要尋找專業幫助。這不是我該做的工作,但這也是我該做的工作。我和學生說,不要什麼都憋在心裏,難過時要去找能夠交流、聆聽的人。如果實在找不到,可以來找我,我是最後的選擇。我知道我不是心理醫生,但如果他們真的找不到人了,我會盡自己的力量。」
可以看到人是多么容易被环境所改变。他上台不过10年,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已经天翻地覆。有时我很奇怪,难道之前的年轻人们都没有记忆吗?都不记得10年前是什么样子吗?还是被迫保持沉默呢?还是已经被越来越极端民族主义的叙事洗脑了呢……
对于很多中国大学生来说政治是一个1/0的问题,中间不存在空间,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和网络环境灌输给他们的
第一次沒有本地學生的課堂那段,好笑又悲哀
極權國家才能夠洗腦人
這篇文章所言,正正反映了這些中國學生思考方式上的一些問題。不僅僅是這些學生,端傳媒見到的親共分子亦是如此。
首先,如此位教師所言,無法準確定義詞彙。譬如外國媒體講一些他們不中聽的話,就會講其受眾是“被洗腦”。其實若果以現實的媒體生態對照辭典上“洗腦”之定義條件,就會發現兩者相差千里。或者以“民主等同一人一票”作為定義,講一人一票如何差,自己畫靶來進行攻擊。
其次,缺乏一個完整的論述過程。若果需要將兩件事情建立因果聯繫,僅僅於其前面加上“因為...所以”是不夠的。需要一步步有一個明確的推論過程。而推論過程中,亦應當避免false cause這種淺顯的邏輯錯誤。譬如許多人認為“美國有槍擊,有吸毒,有種族歧視,有xx..."是因為“自由民主”,那麼如何從“自由民主”推導到以上的問題?這些人最多會舉一些例子,以說明“因為美國有了自由民主,然後這些事發生,所以是自由民主的問題”。
現在的中國人,可以很容易接觸到成套有許多艱深名詞的話術,更為神奇的是這些話術還可以幾句話解釋各種複雜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人需要勤於思考,而且不要被馴化得怕思考,這不僅僅可以防止認知障礙,亦能有效拒絕此類罐頭話術。
对世界单线条、物质化、简单化的认识,不会思考,不接受认知外的观点,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中国青年成功变成他们父辈年轻的样子,充满对抗,手段卑劣。他们口口声声说别人被洗脑,不知自己被洗脑入骨髓,他们一口一句香港废青,其实当代中国青年才是最无理想、最低质的一代。
看到同代人被如此废青代表,会不平,会痛心,也会羞耻…但回过头来,GenZ可能真的如此割裂吧,从小生长在一个有意识把你割裂和隔离的政治环境,滋生傲慢与偏狭,幸存者又有几人
只希望社会对GenZ别失望
好多错别字啊..感全感?不然叩头?
今年走在香港大學的校園里,已經完全感受不到過去的多元氣息了。
这些小留大多出身于中国的中上阶级家庭,除了习得那些物欲,他们的价值构成都来源于高中之前课堂上一些官话和套话。疫情以后这些top500的cornell、hkust的留学生跑到国内高校借读,展示出的思辨能力、学习能力甚至个人基本素质都实在让人避而远之
这才是一代废青!!!
「我們也很少涉及3T話題(台灣、台北、天安門)」
我猜第2個T應該是Tibet吧(西藏/圖博)......編輯可以確認一下原文
嗯,這位老師要聽聽黃明志的新歌《聽著玻璃心碎從聲音》,韮菜的存在價值是被收割,而不是被開化。
有同感。写得真好。
真是辛苦了。
教师还需要忍受这一代废掉的大陆年轻人,我只愿他们有朝一日为自己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