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然而这是偶然中的偶然,当时我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在第三章中已谈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杨树浦码头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转往台湾时,便深感生离死别之痛,觉得此生恐已无重见之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后,我在亲戚家中得到他们从定海托船主带回的平安讯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说他们已从台北迁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间去探望他们。
我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定居的原因。原来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湾的情势非常混乱,甚至国际地位也不确定。美国总统杜鲁门迟至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才根据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宣言,正式声明台湾归还中国。但是他又说,台湾未来在中国内战中究将谁属,美国则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契逊(DeanAcheson, 1893-1971)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更声明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不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当时不少从大陆逃至台湾的难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证;对比之下,他们似乎觉得香港不但较为安全,而且还可能提供向东南亚或西方移民的机会。
但决定在寒假期间赴港探亲之后,我立即面临一个困难问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能够得到离开国境的合法证件吗?通过和许多亲友的商议,他们都认为我必须向北京户口所属的警察分局申请离境公文。但这中间还有一层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记。在父母给我的信中,他们的住址是九龙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长辈很郑重地提议,要我在表格中只说去“九龙”探亲,不必提“香港”两字。他觉得分局警察一听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会向上层报告,极可能延时误事。我听了他的指示,果然当下便获得批准。这一张从北京移居九龙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来保留在手头,作为一个稀有的纪念,但后来因为迁居过于频繁,终于失去了。
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亲,但当时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和父母重聚一次,事毕仍回燕京读书,完全没有长期留港的念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年元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后,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近于情理的解释。一九四九─五○期间,我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因此,并未感到在大陆曾受到压迫。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顾颉刚的朋友汪叔棣将去香港,前来辞行和长谈。当晚顾为此失眠,在《日记》中写道:
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

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通感觉,但我完全没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所以我的精神变异必然是潜意识中的事。原来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许多价值,特别是“科学”和“民主”,因为《胡适文存》曾是我早年最爱的读物之一。抗战胜利后,当时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对我很有吸引力,如《观察》、《新路》等。胡适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独立时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和〈自由主义是什么?〉都是我很爱读的。大致说来,我当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和北欧式)。但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击美国《白皮书》的思想战役。《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美国政府借此表明:中国陷入共产阵营责在国民党,因为美国已尽了最大力量。不过美国对中国的最后希望却寄托在中国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它认为这些接受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知识人将来也许会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当时的攻击重点便放在“民主个人主义”这一观念上面。从中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描述来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这是我当时在理智层面所决不愿承认的。因此我相信,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我在离开北京时,原估计寒假探亲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后,当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来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过。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时日,我也实在不忍说走便走。何况我这次回大陆,以后是不是还能自由来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则是父亲此时还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协力完成不可。上一年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他的大批书籍(包括一部《清实录》)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书画等都寄存在一位亲戚家中。但亲戚即将迁居,时机紧迫,所以我陪伴继母到上海办理此事,来回费去两个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几家旧书店,把所有的书都廉价出售,而将一部份文物和书画揹回香港,交给父亲。我当时已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
父亲很高兴我愿意多留半年,当即提出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建议:他告诉我钱穆先生刚刚在离我家不远的桂林街创办了一所新亚书院。我既然这学期不回燕大,何妨暂时跟钱先生学点中国史?钱先生是我早就敬仰的史学大家,我当然欣然同意。(详见下文)我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父亲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归志已定,并未动摇。所以七月底我终于束装就道。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在离港前一个多月中,是我情感和理智互相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统语言所谓“天人交战”大概即指此而言。父母心中十分难受,但因尊重我的决定,不愿给我更多的情感压力,因而不再劝我留下。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新亚书院虽有钱先生这样大师在,但开学两三个月以后便已遇到经费的大困难,是否能办下去也在师生心中成了一大疑问。何况香港教育司只承认香港大学是唯一的大学,新亚在法律上仅具有中学的资格,毕业生只能教小学。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驱使下,我终于狠下心肠,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
然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的香港火车本来和广州北上的火车是连接的,一到广州便立即换车开行。不料火车入境不久,竟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发生了故障,必须停下来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个小时,和我的北上火车脱节,只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车了,因此心中甚为不快。但就在石龙这几小时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场极大的变动,使我根本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首先,我觉得太自私,只为个人的兴趣着想,完全没有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于未来生活的忧虑。我离港前确有感受,但未及深思。这时在石龙车站回忆以往半年与父母相处的情况,不禁愧悔万端,汗泪并下。我才领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时或可成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会安心不少。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最后,这时韩战已经爆发了一个月以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两边都日趋严格。我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我和父母与幼弟这次分手便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我在石龙几小时内的反思所涉甚广,不过以上三点是最重要的,至今仍在记忆中。总之,我翻来覆去地检讨,最后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回北京有百非而无一是。在火车未修好之前,我已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决定:到广州后,我不但不北归,而且要重回香港。说起来教人很难相信,我在做了这一新决定之后,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有一个负面的念头确曾出现:我已入团,对于“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应有所承担,这在香港是办不到的。但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种自解之道:新民主主义团员不计其数,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少我一个人似乎无足轻重。我的新决定在我自己而言觉得是情理兼到,然而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火车到广州之后,我住进一家旅馆,询问回港的办法,因为那时香港方面正禁止大陆难民入境。我的出境证依然有效,但如何取得入港的许可却成为一大问题。幸而有人指示,广州黑社会的“黄牛党”和香港边境的警察相通,只要付出一笔钱即可进入香港。第二天我便循着这条途径重返香港。
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
--
【附录】余英时生平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其父出生在清末,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赴美国哈佛大学修读美国史。1929年余父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余英时也因此于1930年在天津出生。
7岁时,余英时回到潜山官庄乡生活。乡居九年,余英时自述在地缘和血缘主导的传统乡村社会长大,同时见到佃户欺负地主孤儿寡母、有势力的地主欺负佃户等景象,他尝自言,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对他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
在官庄乡,余英时几乎没有接受现代教育,而是在私塾跟着先生读《四书》、《古文观止》等,在刘惠民先生的引导下进了作诗的大门。13岁时,余英时卷入一场“文字祸”:他写了一封控诉桂系军队一位营长的状子,在当地引起风波。
余英时形容这是他个人生命史上的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1946年夏天,余英时辗转几个城市,去沈阳读高中、考大学。当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储安平办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观察》周刊,他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
1947年,余英时考进中正大学历史系,第一次接触钱穆的学术著作,他自述,在这所大学只读了三个月(由于国共战争后从沈阳逃到北平),“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当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储安平办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观察》周刊,他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
1949年7月,余英时从上海考去燕京大学,再赴北平,但此时已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在燕京大学,余英时修读了“历史哲学”,这是他日后经常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根源;也为英文打下基础。
1950年元旦,余英时从深圳过关香港探望父母,经过几次思想变动后,放弃北归中国,选择留在香港,他形容“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由此,余英时在港入读新亚书院,并在1953-1955年间,在钱穆的指导下精读汉史。入钱穆门后,余英时选择传统中国史为终身的研究专业,同时在香港大量阅读西方史学和西方专著。
在香港的最初五年,余英时自述“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中”——一个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余英时当时的政治立场,是同情香港的“第三势力”,即希望在中共和国民党两个“专政”政权之外,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一股力量。
余英时当时参与了第三势力诸多刊物的编辑工作,比如在《祖国周刊》撰稿等。这份民主反共刊物后来也被国民党封禁,是这代流亡知识人进退两难处境的缩影。1954年,余英时在香港出版《民主革命论》。
1955年,余英时受邀去美国哈佛燕京社访问,由于护照不获批,他当时是以“无国籍”身分赴美。到访哈佛一年后,余英时开始在哈佛攻读古代史博士学位。博士期间,余英时师承杨联升,主修中国古史,副科跟随费正清和史华慈学习中国近代史,还研究了“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的欧洲史。
这段研读的经历,让余英时放弃了早先认可的胡适对“五四”的 定义。1959年,他公开质疑关于“五四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
1962年,余英时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通过审查,顺利毕业。而他也成为1950年代中国赴美留学新阶段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72年,余英时出版最为人知的著作《方以智晚节考》,从新材料与个人精神世界考据故史,透露出明末知识人物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其考证方法突破学界窠臼。
1975年,余英时香港《明报月刊》和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同时发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指出统治阶层历来多有反智倾向,在学界引起不少回响。
1978年,余英时回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访问,自此再未回过故土;他将自己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的激烈批判,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余英时公开支持学生民主运动。1989年后,余英时公开立誓不回再回中国大陆,并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1987年,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出版,将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认为二者都是“社会的良心”,对正处在“文化热”中的中国学界给予剧烈刺激。
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余英时透过网路发表〈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一文,力挺学生,忧心台湾的民主前途。同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箭在弦上,余英时接受记者提问时,回覆“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是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的表现,“虽然抗议也不会马上改变事实,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了,不然下一个又来一个命令,你又做乖孙子...最后你不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余英时在报导中指,抗争有其必要,可以让中共“有许多困难”,并指大陆也有很多地方都在发生抗争,共产党的统治“并不是很稳妥”“并不是一统江山”。
2021年8月5日,台湾中研院发布消息,公告院士余英时已于8月1日晨间辞世,享耆寿91岁。
中研院在消息中表示哀悼,并言余英时“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分子”“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受西方学界推崇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泰斗。”
香港中文大学署理校长陈金梁亦代表中大发布悼词,指余英时“余教授一生贡献学术,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其学术成就屡获奖誉。余教授与中大渊源深厚,为新亚书院校友,其后返回母校任职副校长及新亚书院院长,致力在校园推广中国文化研究,让师生裨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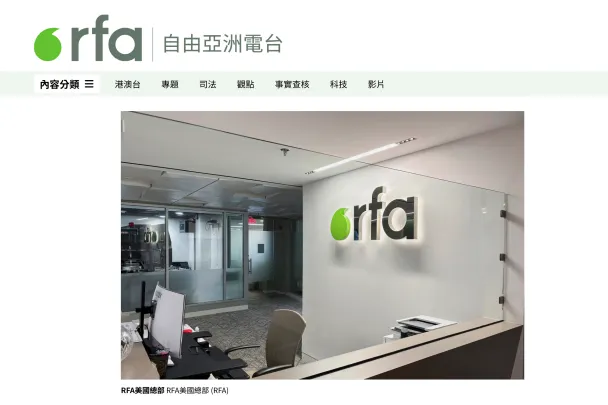
文中储安平的周刊对余先生的影响怎么写了两次呢🤨
端传媒广告好多啊,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