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无不具有争议性,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恐怕没有哪个概念比“自由主义”更容易引发误会和争论。在中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格外严重。自由主义常常被当作自私自利、无组织无纪律的代名词;有时也被用来笼统地形容一切反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主张。一些人将其等同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或者美国霸权,另一些人则用它指代在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立场偏左的欧美“自由派”,讥讽他们是“白左”、“圣母”。
这种概念混乱,甚至是刻意的曲解和污名化,使很多公共讨论沦为鸡同鸭讲。自由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学说,它从何而来,经历了何种历史变迁,产生了哪些内部流派?这正是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的新作《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旨在梳理和澄清的问题。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
作者:海伦娜·罗森布拉特
译者:徐曦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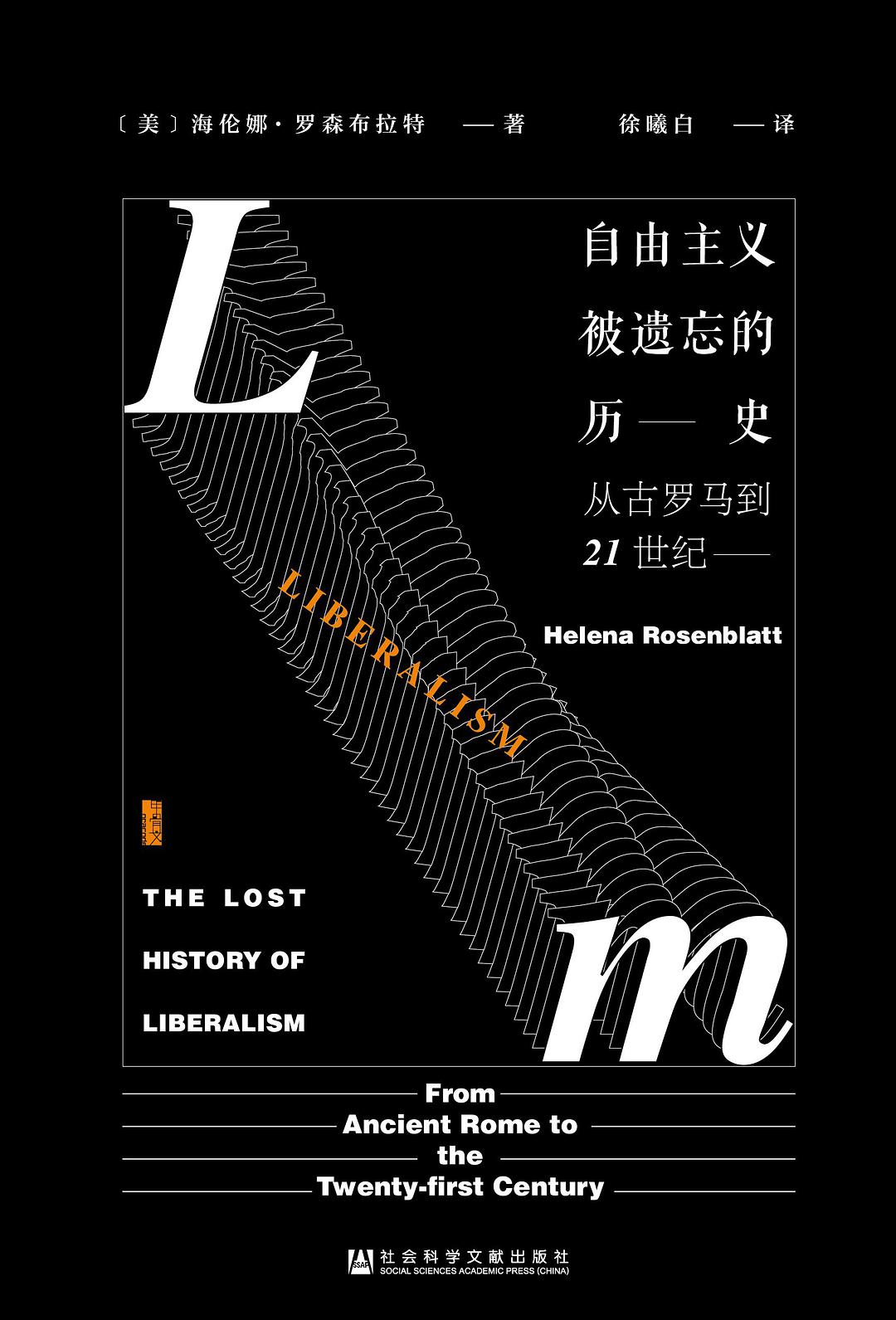
她指出,在过去几百年中,“自由”强调的是高尚、慷慨的公民美德,是社群的共同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毫不相干。历次法国大革命在推动这种注重道德的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德国则在19世纪下半叶强化了这一点。然而,这段历史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逐渐被人遗忘。自由主义被塑造成一种主要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学说,与美国的全球霸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面对当下的思想危机时,需要拨开历史迷雾,回到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去找寻、理解和阐发那些被遗忘的核心价值。
“自由”概念的演变
为此,作者把我们带回到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讲述了自由(liberal)一词如何脱胎于拉丁文的liber(慷慨)和liberalis(生而自由的身份)。在那时,自由意味着具有公民身份,不是奴隶,也不屈从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同时,自由的公民需要践行慷慨、互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和享乐。自由的对立面恰恰就是自私。这种贵族式的自由理念随着历史演进发生着细微变化:基督教的出现为它增添了仁爱、慈善的内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扩大了它的内涵,除了人身自由,还需要自由的情操和理念,自由人应当消除偏见,变得更开明,更绅士。到了18世纪,宗教宽容逐渐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之一,尽管这种宽容仅限于基督教内部。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作为反抗和斗争的学说,自由主义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它在历史时刻中经历的具体斗争。在美国,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不再是英国君主可以随意收回的赏赐,而是所有人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的。自由而慷慨的民众自行立法组建政府,政府的权威完全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在法国,斗争的对象则是代表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以及和它勾结的天主教会。在革命者眼中,法国的自由原则是保卫共和体制,保卫人民主权,防止反革命复辟,推进法治、宪政、代议制政府和政教分离,并保护各种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不过,对美德的讨论从未缺席。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就指出,天主教会使法国人迷信、软弱、麻木,要把人们从这种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恢复慷慨、大方、宽容的自然状态。寻找一种新的、开明的自由宗教,并通过建立公立学校体系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这成为贯穿法国近代史的主题之一。除了与天主教的长期斗争,在19世纪的历次法国革命中,自由主义还遭遇了各式劲敌,无论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还是拿破仑三世以人民之名所行的专制(也称“凯撒主义”)。在这些斗争中,自由主义不断壮大,其含义也逐渐显现出多样性。
实际上,自由主义从来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存在根本分歧。比如,应当支持暴动还是应当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如何应对贫困和工人福利等社会问题?是否应当给予更多的人投票权?如何看待奴隶制?女性权益的边界在哪里?她们是否也应该获得投票权?自由主义理念能否和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相容?
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往往认为19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其核心主张是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然而,那时并不存在古典自由主义,虽然也有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这样的极端自由放任主义者,但大部分自由派并不把自由放任视为教条,也不推崇财产权或者追求自利。
相反,很多人明确提出政府有权力监管各个行业,也有义务保护工人利益。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认为在私人的慈善之外还需要公共慈善。斯密(Adam Smith)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政府干预都有过正面评价。晚年的密尔甚至认为贫穷与工人的所谓“道德缺陷”无关,而与社会制度的总体失败关系重大,因而需要更多的社会变革,留下了遗作《社会主义论章》。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与分离
然而这些文字似乎被很多人遗忘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自由主义的历史往往是后人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人为建构出来的。比如“古典自由主义”,就是把几位差异颇大的思想家组合在一起,忽略他们对慷慨、美德和政府干预的论述,只突出他们对个人自由和自利的论述。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针对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融入了不少社会主义理念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罗森布拉特指出,这种新型自由主义最早可以在拿破仑三世那里寻到端倪。正是他的独裁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工人生活的社会改革和大规模的公共事业计划。后来的普鲁士政府也进行了类似改革,为工人提供强制医疗、工伤、退休和残障保险。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兴起,主张国家有义务致力于公共福利,后者不但不是不可避免之恶,还是国家的最高使命之一。这自然引来了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把德国的自由主义贬低为可憎的国家主义,强调公共慈善只会助长工人的懒惰。法国经济学家纪德则反驳说,自由放任主义者提倡的是毫不关心公共利益、不道德的自私,也许应该在他们的自由主义名号前加上“古典”二字,以表明他们活在过去,不愿意面对新的现实。
德国的思想很快在英国生根发芽。英国的自由派开始主张政府对贫困问题进行干预,不仅应当赋予人们自由,还应该赋予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而不是一味允许资本家无限度地剥削弱势的工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出现了深度融合。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就断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旨在完成,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的理念。连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说,自由派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标签,因为只有这种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才能使社会发展更加平等。自由党的事业就是要帮助那些被丢下的人。
在当时的美国,自由主义仍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政治术语。直到20世纪初,进步知识分子才开始向美国读者译介自由主义。他们当中很多人曾在德国留学,引进的自然也是在德国和英国流行的“新型自由主义”。这个传统后来逐渐成为了美国的主流,最终在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中发扬光大,以至于不再需要“新型”二字作为修饰语。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说,自由主义存在“两大流派”,一种是为大工业、银行业和商业服务,致力于自由放任,另一种则是更加人道主义的,接受政府干预和社会方面的立法。美国的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或者个人主义毫无关系,而是代表了“慷慨和宽容,特别是精神和品格方面的慷慨和宽容”,其目的就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促进平等,打击财阀统治。
一战的爆发强化了英美同盟。德国成了敌对国,学者们开始避谈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德国对自由主义的贡献逐渐被遗忘,顺带连法国的贡献也被弱化了。自由、民主几乎成了西方文明的代名词,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似乎成了这些理念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二战进一步抹杀了德国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德国成了“极权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总源头,而欧洲也被视为自由主义运动彻底失败的地方。
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发表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明确反对政府干预。他警告说,英美的社会自由主义如不加以制止,必将重蹈德国的命运,导致极权主义的复兴。柏林(Isaiah Berlin)则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保护个人自由,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或侵犯的消极自由才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强调能够“去做”的积极自由许诺的是某种“集体的自我指导”和“自我实现”,这通常与极权主义或者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相关,最终反而会以自由之名剥夺个人自由。
正是在这样的批评中,原本有机相容的自由主义被切割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甚至相互敌对的传统。一种是保护个人权力和消极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另一种是强调平等、干预,旨在实现积极自由的法德自由主义传统;后者成了暴力、混乱和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就连罗斯福的新政主义,也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标签。正是在这种冷战的学术氛围中,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转而强调个人权利,不再谈论平等、干预或者改革,试图以此撇清身上的极权主义标签,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几百年来对慷慨和美德的追求,以及法德自由主义在国家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都被一笔勾销了。
自由主义的左右钟摆
作为高举法德自由主义传统的矫枉之作,《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还原了法德两国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只了解英美传统的读者来说,无疑具有醍醐灌顶的意义。但对不了解自由主义历史的读者而言,搭配偏重英美传统的作品对比阅读,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限于篇幅,作者对德国的描述明显比法国更简略,一些重要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康德、歌德和洪堡竟都没有出场,不免令人遗憾。
该书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当代自由主义部分。美国的“自由派”可能很难接受作者的观点,认同自由主义已经沦为主要致力于个人权利的学说。他们会反驳说,那只是大众化和庸俗化的理解,或是自由主义的某些批评者加诸的错误指控。在当今美国的语境中,“自由主义”指的恰恰就是反对自由放任、支持政府干预和收入再分配的主张,或者说就是“大政府”的主张。这正符合杜威描述的那一支强调慷慨、公德、共同利益,反对财阀统治的自由主义。2016年和2020年桑德斯参选总统带来的关注热潮就是明证。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青年政治家也已接过衣钵。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传统在美国稍有衰微,在它的故乡法国和德国,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兼顾社会平等、公正的自由主义传统仍然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
此外,虽然书的副标题是“从古罗马到二十一世纪”,但作者只写到二十世纪中叶,并未提及二十世纪末“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和本世纪初以来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如果将这部分补齐,读者就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个人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宗教与世俗化的冲突、自由放任vs政府干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激烈争论的议题,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历史有如钟摆一般,在19世纪末,摆向了以政府干预和再分配来修正自由放任主义的“新型自由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欧美工人阶级的境遇,避免了马克思预言的那种暴力革命,并一直延续到罗斯福新政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诞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的传人们重新发明出“新自由主义”以对抗政府干预。历史又开始向回摆,削减公共福利、减少市场监管,放开资本流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这也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平等,直接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其恶果今天仍在不断浮现。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被金融资本主义吞噬的产物,正因如此,自由主义为人们带来自由、平等和繁荣的许诺无法得到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森布拉特为当代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仅仅重回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资源,找寻关于慷慨和美德的理论——恐怕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更大胆,更激进的想法,需要夺回“新”字,发明一套“新新新自由主义”。这套新新新自由主义需要坚守核心的自由价值,比如公民权利、宪政、法治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抗拒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侵蚀;它需要保持对普世和平等的追求,能够强力制约全球资本主义,并以必要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不平等,创造平等的机会;它不能仅限于某种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应当如书中所说,注重社群和公共利益,并给人们带来必要的归属感。
罗森布拉特向读者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多面性。它不是单一自洽的学说,而是庞杂到有些混乱的思想拼盘,或如施克莱(Judith Schlar)所讲,是由 “不同传统构成的传统”(tradition of traditions)。这当中既有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也有平等主义、改良主义和普世主义。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达成妥协或者平衡,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和争议甚至超过了自由主义与其他竞争理论的分歧和争议。自由主义的历史就是秉持自由信念的人们不断试图推翻过去的压迫和枷锁,寻找在自由的条件下和睦相处之道,应对每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挑战的历史。罗森布拉特这部跨越数百年、内容无比丰富的政治实践史也将为我们应对时代挑战提供无价的理论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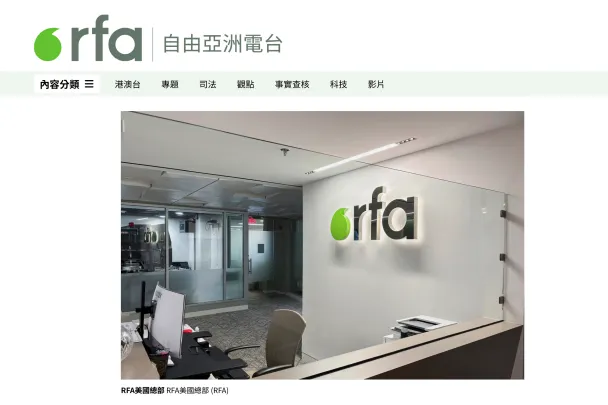
相當精彩,反覆讀了幾次。但一邊閱讀也一邊浮現一個問題想請教作者:
自由主義的起源來自於自由民的貴族與奴隸,感覺偏向人身自由、一般人的自我保護與政治參與、與統治合法性等等偏向當代人民與政府關係的領域。既然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種身分,自由並不理所當然包含平等,而是權力分配或者權利與相應責任的關係。後來延伸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感覺都是這個「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的脈絡。
可是,雖然文中提到羅馬時期有慷慨、高尚的公民美德傳統,這個公民美德不知是否曾經制度化?如果沒有,這個美德可能就和宗教戒律一樣,雖然是社會機制的一部分推動人際往來,但並不是強制性的政府分配或法律執行。如果慷慨停留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是私德,這樣的公民美德是否可以視為「公德」,被統治者強制要求,確實討論的脈絡就不一樣了。慷慨要擴展,超越個人,可能是慈善的施捨或貴族的恩賜,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其實和社會整體的財富重分配意義還是不同。這種「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和前一段提到的「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感覺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與制度討論,彼此並不必然相關。
如果我們接受「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和「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彼此不必然相關,那就能理解法國和德國在專制政府的制度下,一方面限制言論新聞自由(「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一方面卻推動照顧工人與貧困階級的制度(「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如果這區分成立,那推動「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不一定是自由主義的內涵,也不一定是自由主義追求的目標,更可能不一定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本文和羅森布拉特的書對話,順著她的敘述邏輯,或許「慷慨互助」對應「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身而自由的身分」對應「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但如同前面提到的,慷慨互助感覺並不一定能上升到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關係(又或者,這種慷慨互助在希臘羅馬也有邊界,不包含奴隸、女性、非我族類)。
或許當我們回顧歷史上的「自由派」,我們必須留意這些思想家政治家學者是基於什麼基礎,被貼上「自由派」這標籤。如同前面所說,如果慷慨互助不能上升到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關係,不能放在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脈絡下討論的話。這些人的「自由派」可能只是他們面對政治權力的態度,不一定代表他們的社會經濟態度。
這樣一來,即使極權國家為了有效率運作也可以講究「公共利益」,在管制言論新聞自由限縮政治參與時推動一定程度的社會經濟重分配。就像文中的拿破崙三世時期的法國、帝國統一的德國一樣,現在中國不也正在踐行這條路線號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歷史脈絡,反而反證了「政治參與專制」和「公共利益」不完全衝突,「經濟層面的社會總體重分配」和「政府權力合法性與人民賦權自我保護」彼此不必然相關。也因此,自由主義並不理所當然包含這兩個領域。
雖然我理解本書作者原本真正想對話的,是八零年代新自由主義之後的全球化與跨國資本的肆虐,但因為資本已經跨越國界,在一個超國家的荒野空間流動,有時候已經不能純粹用一國之內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來討論。所以我很喜歡您結論中提到的「新新新」的嘗試,但我覺得這是否還要講這種倡議稱之為自由主義的一環,硬是塞進這個脈絡有點疑惑。
不知道作者怎麼看待呢?
新自由主义真是文科学者的福音,靠着批判这个靶子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学者.....
在 斯諾登 (Edward Snowden) 的自傳《永久檔案》(Permanent Record,2019年) 指出,個人私隱的保護是現今數碼世界中「自由」的重要構成部分。
很好的文章,感谢作者和端。书也记下了,准备有时间读一下。我觉得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自由派完全把新自由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特定版本当成了自由主义本身,导致其政治想象力僵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也完全缺失,这实际上也是直接导致自由派脱离群众、始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最终在近年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自己也是后来接触到卢梭、黑格尔才逐渐意识到法德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和在中国流行的英美传统截然不同。
自由,自然創造了內部思想的分歧,但是也詮釋了自由。
关于这个话题,推荐看 Philosophy Tube 关于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视频: https://youtu.be/VlLgvSduugI
好文章。
權利是需要制衡的,不論這個權利是來自政治還是資本。不受控的獨裁政權和大財閥對社會所帶來的破壞同樣巨大。自由作為一種權利,在權利不平等的情況底下,絕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而在獲得了權利的當兒,每一個公民,也需要被制衡,這就是自由的邊界。
文章中大力推崇的所谓“新型自由主义“从命名学的角度就不难发现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但完全不是一回事的东西,而观其渊源,连作者也承认所谓”新型自由主义“源出更加专制的法兰西帝国与普鲁士
好文。
我觉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很重要,如果放任消极自由就容易使资本或其他优势群体侵犯到弱势群体的积极自由。就像 Amazon 靠着自己大平台的优势打击了其他规模较小商家扩张市场的权益。所以政府的介入有时候是有必要,但如何能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方案就需要反复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