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医院停留的时间越长,遇到各式各样的病人就越多,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受到疾病带来的疼痛所折磨。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叫,也有人选择独自哑忍。可疼痛却是如此地难以捉摸,来去无踪,有时只在身体局部地出现,有时却持续性蔓延到全身,而疼痛本身也有不同类型之分,如肌肉撕裂的痛、网状式神经痛、针刺穿透的痛、皮肤灼烧的痛,乃至是癌症等病理性疼痛。其可谓是疾病对身体的介入最为显著的知觉体验。在人类文化中,病和痛,总是相伴而生,疼痛被看作是疾病不可避免的衍生症状。
当我做完手术的时候,医生就明确告诉我,一旦觉得痛就可以用止痛药。始终没有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因此我并没有服用任何止痛药物,后来护士告诉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能听到我痛苦的呻吟。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知觉呢?
常识中认为人类身体有五种知觉,但疼痛并非简单地作为一种与五大知觉并置的生理性感觉而存在,有时也是一种情绪的展现。如果疼痛确实存在,无论清醒还是昏睡,它应该都能被觉察,然而它却可以在某些时候逃离人的感知,那么,必然是受到人主观意志的约束。更准确地说,疼痛是人作为生物性存在中综合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体。
在西方,疼痛是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存在。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肉体之痛开始,疼痛便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中世纪的时候,疼痛被基督教义视为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是惩罚也是奖赏的方式,折磨身体的禁欲方式以及苦行僧的自我鞭笞都是将身体作为靠近神的献祭品。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大量地描绘了信仰者在遭受痛苦时呈现出满足的愉悦。相对于精神追求,身体并非当时信仰者关注的重点。把疼痛“神圣化”为非人自发的感觉,而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这种观念直到十八世纪才被经院派哲学家所否认。但泛灵论式的疼痛观念在人类文化中的社会意义被未消除。
疼痛成为了赋予新生命的力量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疼痛治疗对医学的重要性也不断得到重视,以痛制痛、电击、止痛药、外科麻醉等治疗理论和方法随之出现。其中以启蒙时代的以痛制痛治疗方法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它展示了一种矛盾的论调,用人为制造更大量的疼痛来减少疼痛。用萨德(Sade)的话来讲,这就是一个虐待狂和受虐狂的世界,对生命的狂热和感觉的放纵达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疼痛成为了赋予新生命的力量。
如果说医院是每个小孩的童年噩梦,那么打针绝对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护士拿着注满药水,又长又细的针筒,笑嘻嘻地说不会痛,妈妈也抱得紧紧地,说护士姐姐只是轻轻一扎而已。这分明是人世间最大的谎言。针刚扎到肉,立马嗷嗷大哭,人肉又不是猪肉,怎么会不痛?当小孩要大哭抗议上当受骗的时候,护士和妈妈都使出杀手锏:勇敢的孩子是不怕痛的。最终,每个孩子都是在这样半哄半骗的泪水和口水中蒙混长大的。虽说我们早已脱离了部落社会的生活,但社会成员特别是男子以承受巨大的肉体折磨作为成人标志的意识依然存在。倘若小孩还有怕痛的权利,那么成人怕痛,就成了懦弱的表现。
隔壁病房的男人三十来岁,每次扎针都叫得像杀猪一样,连护工阿姨都背地里笑话他不知是不是个男的。而我,面对扎针这件事早已习惯,两只手的手背上静脉针孔可以画一张中国地图,估计屁股上也可以画个日本了。每次我会自动得把屁股送给护士,打完后在捉弄地说她的技术不精,逗得大家都乐起来。
我一直在疑惑,到底年龄对疼痛的感知是否有影响的呢,是年龄越大的人越不会痛吗?无论针头的大小、护士下针的力度和技术以及药物对肌肉的刺激等是如何被缩小到忽略不计,这也只是影响疼痛的程度而已,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完全不痛的情况,除非,知觉系统出现病变,或者是死肉。既然,在疼痛必然存在的情况下,年龄的疼痛感知差异就更多地是来源于社会和文化的规训。
疼痛成为了修行
在集体意识中,建立在“先苦后甜”的观念之上,疼痛的苦难被认为是有好处的。从各位家长的口头禅“勇敢的小孩不怕痛”,到各种历史英雄故事和不同文化中修行式的宗教实践,忍受疼痛的能力都是作为个人意志力对抗生理性的标准,只有能够忍受极端生理上极端疼痛的人才能最终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忍,被解读为在心中插一把刀,体现了中国人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的一种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这里清楚地可以看到,人类文化中精神力量高于一切身体感知的观念,尽管两者从未也不可能分道扬镳。
显然,疼痛作为连接身体和精神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节点,疾病为身体带来的疼痛(pain)和精神上的痛苦(suffering)也是难以清晰地区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前者更为倾向客观地陈述一种状态,而后者更加强调受苦的主体,即病人自身的感受。同时,也是横跨多个学科的研究主题。尽管从古典时期开始,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试图为疼痛准确地下一个定义,但从未成功。哲学家、生理学家、医生都有各自的诠释:哲学家探索其作为感觉的地位;生理学家视其为身体机制的刺激反映;医生则以描述疼痛,治疗病症为目标。
住在我隔壁床的是患有神经元运动疾病的女人,她经常会出现胃痛、腹痛等症状。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医生都会判定为胃造瘘手术后的适应问题。
“你是哪里痛?”医生问道。
“胃痛!”女人回答。
“是做手术的伤口痛吗?还是哪里痛?”医生追问。
“不是,是胃痛,而且经常胀气。很不舒服。”女人不耐烦地说。
(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没有胀气呀。”医生惊讶地说。
“可我就是很痛啊!”女人愠怒地回答。
“......那给你开点止痛药,痛了就吃点吧。”医生无奈地说。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女人还是会不定期地痛得直嚷嚷。任凭医嘱上都写满了各种止痛药也不奏效,久而久之,女人也不再愿意吃药了,结果还是继续痛。
我不敢轻率地断定这是现代医学的缺漏,但相对于病人强调自我的感觉,医生更加关注疼痛这个客观事实,或者说,在这个医学系统内,疼痛是没有主体性的,只有把这个事实客观化之后才能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对医生而言,病人只是一个待完成的项目编号,而非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而病人却只能通过自身的主观感受来衡量疾病的发展态势,甚至直接作为疾病的表征,是一种身体本能反应,预示着身体更为严重的崩溃。
就这样,隔壁床的女人一直在疼痛的折磨中度日,而医生亦并非置之不理,但解决问题的态度相对不够积极。
“你老说痛,可是又不吃药,怎么会好呢?”医生不耐烦地说。
“可是越吃越痛啊,都没有效果的。”女人不服气地回答。
“最好的药都给你试过了。”医生无奈地说。
“那你们得想办法啊。”女人愠怒地回答。
“痛,这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原来的病,神经元运动疾病是不会痛的。等你以后习惯了那条管子,饮食跟上就会慢慢好的。”医生劝说道。
对现代医学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根治疾病。在这个进程中,疾病才是医生面对的主体,而非病人,甚至在这个终极目标面前,病症还有主次之分。只要最终达到治愈,恢复身体健康,疼痛作为衍生物亦会消失。在这种逻辑之下,病人的感受便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有时在找不到缘由的情况下还会归结为心理问题,也就是再次把这个烫手的山芋还给病人。疼痛,既是一个短暂且局部性的身体感受,也是一种具有时间演进和扩散能力的痛苦体验。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特质使得医生和病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疼痛成为我存在的证据
要用何种态度面对疼痛,恐怕只有遭受过疼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由于我本身所患之疾病从未得到疼痛的恩宠,对于疼痛反而有一种期待,因为感受到疼痛于我还是一种存在的证据,身体在无声无息之间腐坏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这肉体的疼痛。
由于插管伤口自然愈合不理想,于是我主动向医生提出缝针的要求。只有短短三厘米的伤口缝合术在床边即可完成。耳鼻喉科的医生使用了短效局部麻醉的药物,在缝针的过程中他特意和我聊天。我心里自然明白他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于是也趁机问了他一些医学问题。整个小手术总共缝了八针,在完成第四针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疼痛,针刺进皮肤后,线在肉间穿行的痛,我一边抱怨,一边继续和他聊天。我没有选择再打一次麻药才接着完成缝合术,因为,扎针,也是会痛的。疼痛不可避免,我也只能面对。
我并不赞美疼痛,也不视其为罪恶的象征。与其说我如苦行僧般将疼痛作为精神升华的工具,不如说是以此来了解自己。
正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他的《随笔集》(Essais)中记录了大量自己身体真实的疼痛体验时所说的,解除身体疼痛属于个人哲学观的问题。除了保持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在遭受疼痛折磨时并无其他事情可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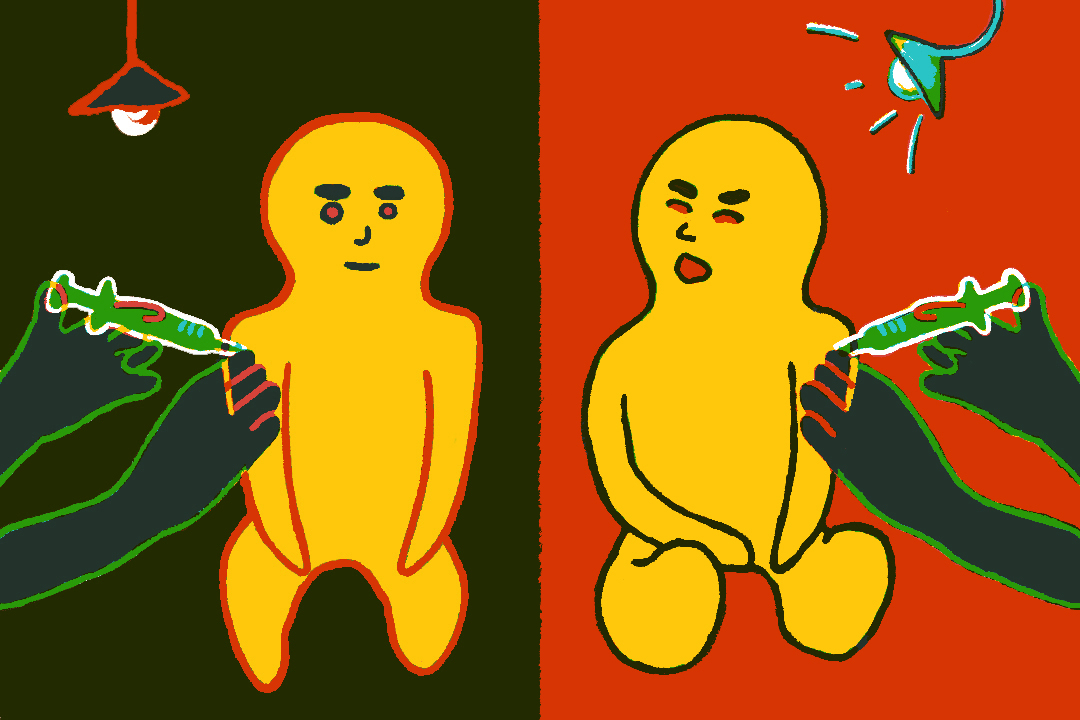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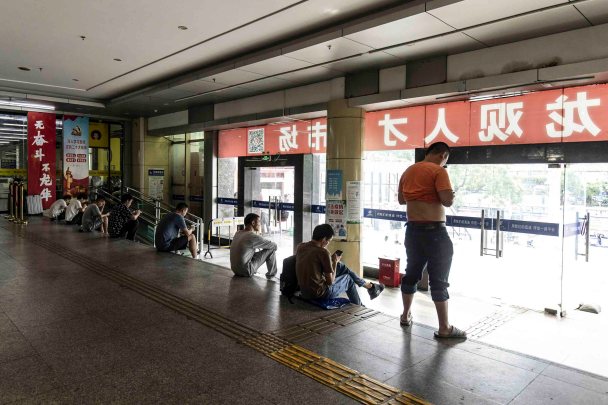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