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很多外地人搭建的房屋上都有褪色的“拆”字。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与其说是一个临近的威胁,更多像是一个个假火警。但今年小雪节气的几天,这些火警仿佛同时起了作用,上百万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可能戛然而止,余下的是一个个灾区似的城市角落。与此同时,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幼儿园都再次面临拦腰截断的命运。一场史无前例的“清理”和“驱逐”,令三十年来不断缠绕外地务工群体的噩梦终于发生,让北京的寒冬格外铭心刻骨。
学界研究移民问题的都知道,2008年被称为“城市化分水岭”(the urbanization divide)——不仅全球城市居住人口超过乡村,跨国界移民活动也史无前例地增多。那一年,我是康奈尔大学社会系的博士生,回中国做关于城市贫困的田野调查。在中国,到2008年为止,大约两亿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社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尽管人类社会存在着各样的歧视,但是在当下,很显然户籍制度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场域,直接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型和变革中,可以用马克思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曾经,提供人们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地缘和业缘、单位制,在20年前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却并没有提供给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归宿。拆迁不断,不变的是继续往北京外环扩展的外地打工者聚集区,和层出不穷的寻租手段。
2008年夏天,我曾与一位资深NGO人士马姐访问北京刘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区。马姐属于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从安徽进京做保姆,后来在外地民工聚集区创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开展一些妇女和儿童的社区活动,让原本封闭在家中带孩子的妈妈们有个去处。马姐说,她从1982年到北京之后,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记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区的一堆拆迁瓦砾面前,她无奈地感叹说,“这里曾经生活过这么多人,但多少年之后,哎,谁会记得呢?”
##民工子弟学校的恶性循环##
每隔几年,北京就又开始一轮拆除外地打工者社区和农民工子弟小学的政策。民工子弟学校被强行拆迁已经不是新闻。我想到当年与很多NGO朋友们在密云区做公益夏令营时的那些孩子们,估计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如何了,他们的孩子们现在又漂流到了哪片土地上?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第三代,还在经历着与祖辈一样的不公正对待?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发展逻辑:私立教育的制度限制(不许募款和登记),让民工学校不得不按“黑色市场”的规律发展。在一些民工群体中,没有教育背景和资历的商业投机者进入私立教育市场,让很多学校在设备、师资和管理上存在问题,不能提供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很多家长认为,一些学校甚至比不上农村的公立学校。官方因质量低下为由强拆学校,当然成了理所应当的。但正是同样一种自我实现的逻辑,不停重复着民工学校换场地重建、又被拆迁的剧情。
在1990年代,进城务工群体当中有一些在农村学校担任过教师职位的人(他们在凋敝的农村教育体制里的工资报酬一直偏低,很多是编制外的代课教师),因看到少数随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需要上学,而家长们又愿意支付学费让老师教授,就出现了最早的私塾式“流动课堂”。后来十年之内,教育需要越来越凸显,有一些教师们开始租赁场地,把教学规模做得大一些。然而,当这样的模式变成可见的收益机会时,便吸引一些缺乏教育理念或资历的人,也进入这个潜在的教育市场,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校长一般被称为“老板”,把经营学校作为一盘生意;有时一个家族的亲戚都可以靠一间学校全部就业。
而且,我在调研中观察到一个细节:每一间民工学校都会有一个零食小卖部,仅这一项收入就非常可观。在一些午餐比较寡淡的学校里,很多孩子更愿意花钱买辣条之类的低营养甚至伪劣零食。学校乐意经营,家长无心关注孩子在校的饮食质量,造成很多孩子营养不良。我在2010年与现暨南大学教授冯帅章合作的民工学校问卷调查项目中,设计了测量孩子身高体重的问题,也证实了这一点观察。
很多民工学校招聘来的教师们,工资都不会高于一般工厂工人。农村户籍的年轻人愿意考虑这样的工作,因为比工厂中流水线工人的“包身工”经历要自由一些。但他们很快也发现,“老板们”的苛刻、家族垄断、权力斗争,也让这些地方的人际关系变得货币化、贪腐,以至于令人窒息。民工学校教师们的流动性非常大,也成为家长们普遍的不满,因为孩子们往往刚熟悉一位老师,人就因为不明原因辞职不干了。长期以来,学生们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依赖被切断,连课堂里的师生关系也变得冷漠,甚至常常敌对起来。因此,可悲的是,不管民工学校外部的制度管治,还是内部的管理,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无法改善。
民工子弟学校所在的社区也有很多对儿童健康的隐患,其中一个就是黑网吧和黑游戏室。孩子们一放学就会钻进一个他们都熟知的小胡同,掀开一家人的布门帘,在主人吃住摆设后面隔一个木板,就放着按小时收费的几台电脑或游戏机。
台湾大学教授蓝佩嘉对民工社区生态的研究,细致刻画出这些也是真实的人所生活的地方。而有人的需求,就会有市场。设置制度壁垒,只会将需求导入“黑市”。政府因其“黑”的性质,用强拆或驱散的方法,只能雪上加霜。正如一些新闻图片所呈现的,打工者社区有自己的生态环境,从餐馆、学校、小作坊、旅馆、职业和婚姻介绍所到娱乐设施,应有尽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写到的,这些由居民自发形成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不可抵挡的“自发秩序”,因为人们将生活需要和创造力都用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给这些虽然凌乱但真实有机的社区赋予了强大的活力。她批判一些僵硬的城市规划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可以制造出整齐划一的街道和街区,却无法复制社会交往的一种生命力。而用强制手段拆除这些社会交往网络,尽管是借助清理“安全隐患”之名,仍是一种对社会整体有害的、短见的做法。毕竟这些社会关系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机生长出来的,人们投入了他们的情感、梦想和期待。

##移民权利与经济贡献##
移民权利引发的讨论如今也成了全球政治危机。在美国,特朗普(川普)的移民禁令以及各种排斥性措施,激发大众发出各种反对意见,“移民是祝福,不是负担”的标语比比皆是。在全球,也大约有两亿人在跨越国界地迁徙。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涉及地理边界的冲突、国家安全、人权、国家主权、自然法和民法、公民权和社会伦理。
在不同社会制度中,一些想要为移民问题寻求出路的主张,都普遍基于一个被认为很强有力的根据:外来移民撑起了本地的经济繁荣,因此他们应该被接纳,不应被作为权利被剥夺的一个隐形群体。很多学者或权利倡导者会以此逻辑为移民的平权发出声音,例如说,因移民对本地经济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上享有同等权利。是时候对这种思维进行反思了。
将移民的价值与经济贡献联系在一起,它本身不就是问题的根源吗?从何时起,人被作为一种资本,而一个人的价值也被等同于他或她所能生产出的经济效益?这点让人想到了E.P汤普森在谈论英国工人生活说到,“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几十年中,劳工完全被遗弃在历史上最有辱人类的一种教条——不负责任又毫无节制的竞争理论,几代人就死在这个摧残中。”移民权利的被剥夺,也是从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和资本化开始的。这是当人类社会进入一种以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中心的秩序后的结果。移民问题的平权逻辑,需要从最根本上回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19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变革。欧洲从一个农业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如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洞见地指出的:“社会的一切都被经济因素所约束。”当他抽离出自己的时代来看时,更忧心地评价说,这种以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秩序,是“只有在极少情况下被人类社会历史所承认的一种动机”。托克维尔也在研究《济贫法》的时候指出,工业化带来一种结构性的贫困,这将是很多国家此后要面对的一个持续问题。他甚至说,“在欧洲羡慕的那一副繁荣面具背后,一定隐藏着极大的悲惨。”
当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时,曾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很大伦理争议。人可以被简化为经济生产力的单一维度吗?对教育的投入,只是为了增加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提升生产力吗?其实贝克尔提出的理论并不是新的,因为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指出工业生产力不仅依靠机器设备和资本投入,也包括人的生产能力。贝克尔的一点贡献在于,他从50年代开始用量化方法考察教育投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们都习惯于将人直接等同于劳动力,就是一大群没有面孔的工人,甚至只是他们数据模型上的那些数据点。
##迁徙自由与权利逻辑##
2009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访问到正在冷冻食品厂打工的小康(化名)。这个与我同龄的江苏籍年轻人已经品尝过很多艰辛,换过无数份工作,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重复流水线上的工作。小康曾经想去南京试试运气,结果钱包被偷,露宿街头好几天,后来靠给人洗车赚了些路费,又回到了上海郊区他原来工作的工厂。2009年经济不景气,很多打工者都回乡了,所以他觉得能留下来,不管怎样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小康每天具体的工作,就是把流水线上一些半熟的冷冻鸡腿装箱。他说到一个让我听了就忘不了的细节:
“唯一不好的是,老板给的饭菜没有肉,只是素菜。”我问为什么。小康说,“是这个厂的规矩,因为老板假设每个人在装箱的时候,都会拿冻鸡腿吃。”我问他,“你有吃过吗?”他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后笑笑说,“饭菜那么清淡,谁不吃啊?……就是得小心一点,被抓住要罚款的。”那两年,我听到过很多打工妹和打工仔的故事,但这一个是最让我心酸的,所以一直记得。
另外一个场景,是我在2007年夏天第一次进入上海漕宝路附近的一个民工聚集区。在那里,上海旧棚户区的狭窄空间又被木板分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出租屋。做小餐馆生意的小贩在摊位上面又搭盖一层,可以和家人住。也有人把床铺(一般像个封闭的盒子)悬挂起来,用布隔开,外面就是卖小炒的厨房。我在这个狭窄的市场通道中穿行,眼光观察周围的居住环境。看到右手边一个房东正在和新房客谈价钱。年轻的打工者很犹豫地低着头,一看就是初来乍到的。我瞟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个“房间”,有些吃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四五个平方米,像一个盒子,没有窗户,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凳子之外,只能站下一个人。我想像一下自己躺在那张床上关上门,就倒吸了一口气。房东试图在说服那个年轻人,一个月三百元这样的价格,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已经很便宜了。
十年前与小康的那段对话和这个出租屋的场景,让我更想探讨关于人的尊严的维度。人是寻求自我尊严的造物,而平等的尊严是仅仅物质层面不能给予的。当我们在讨论给移民平等权利时常常忽略了对人尊严(human dignity)的讨论。诚然,制度性的歧视、社会排斥以及不平等工作权利,都会威胁人的尊严;但同时,打破这一切是否就能完全实现人的尊严呢?究竟什么是尊严?这又是一个回到人本身是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迁徙自由的时候,是否只用权利的逻辑就有足够说服力了呢?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为城市移民弱势群体呼吁平等权利的人,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谈论人口、教育不平等、拆校舍每一个话题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真实的生命,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醒我们注意到“劳动力”这个词背后真正的问题——“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同时也处置附在这个标签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的‘人’。如果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
**(马丽,康乃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加尔文大学Paul Henry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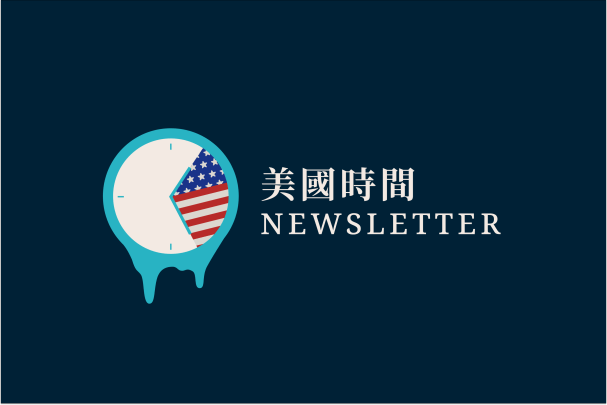

北京户籍是天龙星户籍,哪里有你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份(笑)。
好文章!
@張小泉 「選擇性失明的中國讀者」,是有定語的。我無意以偏概全,讓你誤會了,我致歉。
對你們這些選擇性失明的中國讀者真的感到很煩厭,一堆批評特朗普批評台灣的文章都看不到,只要說說中國,就是不行。這種大國自信我也是醉了,中國媒體可以瘋狂批評外國,但就是不容許其他地方談論中國。
--------------------
有几个人觉得不行?是不是内地读者读完文章必须留言告诉大家自己没有生气?
开地图炮在内地互联网是很缺乏教养的表现,可能人口差两个数量级的地区理解不了这种多样性的社会吧。
来,打滚,继续打滚
我小學沒畢業,文化水平低,真心問一下,“出街”是什麼意思啊?100多萬出街是這麼多人都住到大街上了的意思嗎?那可不好,這麼多人,總住街上也不行啊,妨礙交通啊,天氣太冷凍感冒了怎麼辦?違法建築都拆掉了,又有幾百萬人想住便宜又安全的正規住宅,怎麼辦啊?
某个人自我审查后还来做媒体审查啊,在首都赶一百多万人出街那么大的事,做个专题也算炒作,还真是中共思维。
排华行动一共要持续40天呢,昨晚还在赶,在某些人看来,进度都还未到一半就不能再跟进了啊
唉!我也覺得自己挺沒格調的, 都只會玩口活兒了,還要不分對象。
依然瞎!
一幫玩口活兒的,還挺理直氣壯。。。
@马路:我说台湾发生了蜗居房的火灾,现在要强拆违章建筑,难道不是实事?北京的事难道不是被放在“中国因素”里长篇大论的讨论?我提一下就是“居心叵测”?!就是“装”?!我也觉得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去找个心理医生比较适合你。
還好意思說我給你定罪了,「不过经常读端的内容就一定会知道,这种事情肯定都是“中国因素”在作怪」,這是不是定罪?繼續裝吧,已經沒興趣再跟你糾纏下去。
@马路:“居心叵测”?“掩饰自己的意图”?是不是接下来就该给我定罪了?!你不识字吗?我哪句话说了“一定要认同我的看法”?请你给我找出来。你说你也是醉了,我就当你是醉了吧。
*你別以為你現在寫得好像「客觀中立」就可以掩飾自己的意圖。
你別以為你現在寫得好像「客觀中立」就可以掩飾自己的意圖嗎?當大家是傻子?端真的做了比較,肯定又會被你們這種人說在黑中國,反正什麼都可以說成是端有目的黑中國的。這個「類似」只是你自己說的,我也說了從規模到處理方法都不一樣,這種比較意義不大,但你又無視了我的看法,所以媒體就一定要認同你的看法,兩件事有可比性才成?不認同你的,就是居心叵測?你也太看高了你自己了吧。
@马路:请你仔细看一下,我有说规模一样、处理方法一样吗?至于有没有可比性,这个要大家自己去判断,随便一搜就有报道,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替别人瞎做主。另外,我已经回答你了,这里的文章几乎全部围绕两岸三地展开,为什么对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类似事件不能谈论呢?这个倒是你要来说明才对。
對你們這些選擇性失明的中國讀者真的感到很煩厭,一堆批評特朗普批評台灣的文章都看不到,只要說說中國,就是不行。這種大國自信我也是醉了,中國媒體可以瘋狂批評外國,但就是不容許其他地方談論中國。
@AlexZ 我剛才就說出了兩者不同的地方。先不論規模,連處理方法也不一樣,這樣要比較起來,還不是更顯得北京的粗暴?比較了你更可以說端黑中國了,對不對?而且你還是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耶,為何一定要拉其他國家下水,去證明中國做這種事是很平常?為何批評地方政府的政策,就一定要是黑,不能是關心這個地方?端那些批評香港和台灣的文章,例如批評一例一休的,又是黑台灣了?是不是又要拿中國來比比?
@马路:是你看不懂还是我表达有问题呢?我只是指出来有这样的事情,又不是编造的,你接受不了吗?每个媒体都有一定的立场,端的立场很明显,指出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在一个号称提供两岸三地视角的地方,谈一下台湾社会近期发生的,有一定可比性的事件,有问题吗?
@shuimeiren 很期待知道你做了什麼實在的事幫助這班數以萬計的被逐離者。
@AlexZ 請問台灣有暴力即時驅趕違章建築內居住的人,要求他們幾天內要遷出嗎?好了,退一萬步,當台灣跟北京一樣粗暴,那就代表了中國正確了?什麼時候才可以脫離比爛的邏輯,每當有時發生了,你們就最愛說,美國更爛呀,台灣更爛呀,什麼什麼地方更爛呀,悶不悶?追求一個更善的社會,就先應該放下被害妄想症和比爛的邏輯。其他國家的爛,其他國家的人也有在批評。
解決辦法:繼續說。越是有人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去抵銷這種言說(的意義),就越要繼續說。《端》千萬別停,我會鼓動更多人訂閱你們的文章。謝謝!
要说起来的话,最近台湾也刚好有蜗居房发生火灾,据说是有人在违章搭设的套房纵火,每套3-5平,一共烧死9人。本月8号之前还要强制拆除200个类似的违章建筑。不过经常读端的内容就一定会知道,这种事情肯定都是“中国因素”在作怪。
無補充。
@kx
那個不讓我說話的結論來自於我一上來,就有人罵我,你沒看到?哈,你說你沒看到我對這件事本身有啥見解,那就對了,因為壓根我也沒說啊。對了,你把這件事挖的夠深了嗎?挖出水了吧?看得出你是如此見識廣博還憂國(中國)憂民,說說你的見解吧,重要的是說說解決這件事的方法,我們都聽聽。
@Fai
哦,你說你也不知道端傳媒是否樂意扮演什麼角色,這麼說你也不夠了解端傳媒,那何必急著替它辯護呢,我也就是對它發發牢騷,表達一下看法。還有,因為我說對低質量的文章看膩了,你得出結論,說我對生死、苦難缺乏尊重什麼的,那就更過了,我對火災燒死的那19個人的同情與悲傷絕對不比你少,而且我可以為他們做一些實在事,你做了嗎?你們在這跟著端傳媒一起高端黑(沒錯,我就是評價端傳媒的),反反復復各種角度墨跡這件事這麼久了,以你對中國的憂國憂民之心,以你具有的比我高許多的學識智慧,那麼,對這次火災後,北京拆除大規模違建的行動,造成違建的租戶必須限期搬離的這個矛盾,有什麼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呢?咱誰也別玩嘴皮子(這一點我也不厲害),不用說你們的看法,低端黑高端黑歌功頌德表態支持的看法都不要,我就想想聽聽你們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人的尊嚴並不是被忽視了,而是被刻意摒棄了。
無知而無愧,卻又嚣嚷。
我無心傷誰,但有些行為不用「喝止」就顯不出你的驚愕,就像有留言者說她最初對「低端人口」這詞語無感一樣。可怕的是有些冷漠麻木已入血,需要棒喝來敲醒。
我不知道端是否樂意扮演這種角色——很多不同種類的「大事」放在架上出售的賣場。反正你的發言是讓人咋舌的。
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我想哭。這個國家要斷送在笨蛋手裏嗎?我還要很理性地跟你說道理,義務教育你何謂正常人。正常人是對生死、苦難表現敬畏和尊重。你沒有,你明明白白告訴別人你要的是新鮮的東西。而對這件事的重量的評估,我覺得簡直與你如處平行宇宙。
好吧,給你一個你想要的理性回應。你讓我又對這國家悲觀了一些,就是這國家裏的人會把生死之事當成會「膩了」的消費品。其實,你更劣於五毛。不自知,不是瞎還能是什麼?
@shuimeiren //不是所有不黑不罵中共政權的人都是你們嘴裡的五毛,那樣會讓人覺著你們很裝13,話說哪有那麼多五毛啊,別不讓人說話。// 這個結論又是哪來的⋯⋯佩服。說真的,也沒人生氣,都覺得可笑。將一個問題深挖到底,做到見微知著,也是媒體需要做的。不知您一直說這個議題不值得反覆炒作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您對這個議題又有何見解?以及廣泛一點,指的又是什麼?
沒別的,就是瞎!
@kx,,得了吧,你可省省吧,你怎麼得出我有意讓這個媒體宣傳所謂“正能量”的結論呢?笑話啊。這裡不可能正面宣傳中國,時不時到這瀏覽幾眼的人都能看得出來。你在這個媒體看到過正面宣傳中國的文章嗎?
仔細理解一下我的意思再說話不遲,希望所有喜歡留言的人別先入為主自以為是,記著,不是所有不黑不罵中共政權的人都是你們嘴裡的五毛,那樣會讓人覺著你們很裝13,話說哪有那麼多五毛啊,別不讓人說話。我故意說幾句這個媒體的壞話,你們就開罵了?說真的,我沒生氣,我只是覺著可笑。
中國的社會問題多了去了,別的國家其實也是問題一大堆。既然是這個媒體、許多文章作者和諸位留言者都是發自內心的為了中國人民好,有意救中國人民於水火,何不廣泛一點,別盯著一個問題,很讓人絮煩的,弄得我都不想充會員了,呵呵。關鍵是這個事件並不值得報道起來沒完沒了,批評力量用的不是地方,否則西方大牌媒體會比這個媒體積極的開火的,還有,與那幾篇大牌媒體的文章比,這媒體上關於此事件的文章水平也是真的差了不少。
@Fai,,打錯一個字=瞎,好吧,你上來就罵人,然後你把這叫理性,好啊,你真牛逼,領教了。
哇哈哈……還是瞎!(我沒沒爆(出)口,雖然我覺得爆粗更理性)
@shuimeiren
1 天下大事這麼多,媒體要兼顧廣度和深度的確很難,何況只是一家你口中的小媒體。
2 中國大事那麼多,已經有那麼多“媒體”在關心正面新聞,若你有需要補充正能量,大可移步。
3 已經從多面向”天天報道一件事",卻還沒能讓讀者意識這個議題的重要性,真是可惜。
@Fai
我勒個去,,我就說了幾句話,也沒爆出口,只是沒順著你,沒罵中國政府,呵呵,然後,你就罵我瞎,你是一直這樣暴躁嗎?哦,那好吧,我知道你是個什麼貨色了,你就是垃圾狗一樣的東西啦,懶得理你。
呵呵,持續“關注”吧,關注到你姥姥生日去。對了,是關注,不是炒作,哈哈,這還是一般的矯情嗎?天下大事那麼多,僅僅中國大事那麼多,即使只關心中國偏負面的社會新聞,也有好多好多啊,天天報道一件事,是不是沒說過癮呢?你們不絮煩啊?關鍵是你們也沒嘮出啥有用的東西來呀。😊😊
這樣大件事,媒體通通不予以持續關注才有問題。說這系列是炒作的那位真夠虛偽,不僅讀了,還要評論,這不是故意吸引注意力助長「某小媒體」炒作嘛!用心險惡,居心不良,還不趕緊把中文全忘了,學這些允許你看懂「炒作」的知識做什麼?
回S字頭者的,特此說明。
瞎!
回復那幾位反對把報道說成是炒作的回復者。。。。。。。。。。。。。
這個世界,每天發生重大的事件太多了,但這個小媒體單單選擇這件事,連續多天鋪天蓋地發文關注一個事件,不是炒作是什麼?而且配圖有的是PS過的假圖,翻來覆去的那幾個人云亦云的詞語,文字內容有明顯臆造的段落。。。。看得多了都膩歪了,請再多說幾句,這個媒體不是炒作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任何提出所謂「生產力」的邏輯有一巨大漏洞與academic bigoty,就是生產的產品給誰用?生產的意義?從一開始為什麼要生產?
因為生產者亦是消費者,購買力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工業社會裡勞動是獲得購買力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所有經濟學書籍(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忽略了這一點。美國大蕭條就是因爲資本家開始減薪,勞工沒錢,沒錢則不購買,進入今天世界經濟進入了的惡性循環,越沒錢買越減薪獲利,還不停生產,可是勞工沒錢吃東西,更別提購買了,最後就全垮了。
“As mass production has to be accompanied by mass consumption, mass consumption, in turn, implies a distribution of wealth -- not of existing wealth, but of wealth as it is currently produced -- to provide men with buying power equal to the amou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nation's economic machinery.” Marriner S. Eccles 1934-1948年間美聯儲主席/首長
還是國父中山先生那句-人類的進化靠互助。
「所有的不平等,在政治經濟學上而言,都不是本質地存在,而是因應不同的生產需要,而產生出不同的壓迫。有了因生產需要而出現的不平等,才有階級的分野。為此,「人是不平等的,所以清除低端人口也是無奈」只是一個不當論證,貿然接受豈不是等同自暴自棄?正如馬克思所講:「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沒有改變世界意志的人,讀了政治經濟學,也不會改變什麼,只是為所有不平等找原因。只有願意改變世界的人,政治經濟學才有力量,成為瓦解不平等的利器。簡單來說,無奈的是欠缺意志的人,而不是世界本身令人無奈。」——李達寧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E4%BA%BA%E4%B8%A6%E4%B8%8D%E5%B9%B3%E7%AD%89-%E6%89%80%E4%BB%A5%E6%B8%85%E9%99%A4%E4%BD%8E%E7%AB%AF%E4%BA%BA%E5%8F%A3%E4%B9%9F%E6%98%AF%E7%84%A1%E5%A5%88/
@muyadada: 确实有日本,我一下子没想起来。不过,安倍政府一直宣称日本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是活在美国宪法和军队的保温箱里。如果排开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性来讲,日本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上有很深的门阀色彩,但是在其他方面走西方模式走得很成功的例子。
再指望中共不啻等待末日。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發展思維(強調中央調控,單一角度的發展規劃)可以是與世界潮流(微型經濟、本土經濟加科技引入)違逆,我們別再去想有一個單一權力用一種單一的現成方法可以拿來解決如此複合的問題,而是要從在地出發,用現代科技和思維set examples。
看评论真是……比烂很骄傲吗?
日本也算过亿的好吧...
如果目前沒有任何力量迫使政權轉型,民間要開始做轉型,起碼在意識上、方法論上、思考上。
在民怨一觸即發無可收拾的當口,有沒有可能由民間提出可供政權自動轉型的方案和選擇?
感觉这是国家大事,确实值得更多学者来研究。但是我个人非常反感很多评论将政府和社会直接对立起来,或者把矛头完全指向执政党。这根本不是谁执政就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今天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抬头,但是政治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最终都要落实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来,无非就是在尽量提升财富创造能力的同时还要争取社会正义,全世界的课题都一样,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而且政府用公权力强制调整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印度的政治模式和我们完全不同,但中国有的问题可以说印度都有,甚至更严重。其他在政治上符合自由派理念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拿来比较,但是现实是,这些国家普遍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上真正能按西方标准正常运作并且保持相对富裕的国家,全部加起来可能只有二十来个,而且都不是人口很多的国家,人口过亿的可能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如果俄罗斯算的话。
我們沒有政策倡議的位置,就不能再假裝有。評論與分析若是另一種形式的諫言,在目前根本對象不明。所以,類近的文章到底是要對誰說話?我們嗎?有這個需要嗎?媒體如果在這種時候有什麼作為,不是再去探討政府應該怎麼做,如何做,而是民間可以怎麼做,如何做。把能動性放回到民間來,能捕捉中國社會情勢的質性變化,及早結集專業和學術力量應對中國的處境,對為民者近乎功德。
支持继续发北切
恭喜你已習得中共邏輯,報導評論就是炒作,呵呵。
回复第一层评论,这不是炒作。
我们之所以持续谈论此事,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不止事件本身具有显著重要性,为城市做出奉献的群体正在被城市无情地驱赶,同样,这件事也成功把曾经置身事外、为盛世鼓掌的许多人卷进了事件中,他们不得不去谈论这些话题。
事件持续在发酵,没有人是局外人。
謝謝端。
除了端,上周我在台灣時,主要媒體我看不到一條與北切相關新聞,端是唯一有好好地記錄、探討這次的切除。我付費就是為了看在其它傳媒看不到的真相。
成天發稿炒作這件事,我覺著挺打臉的,差一步二就得了啊,否則就變成法輪大法那班人弄的媒體一樣嘍,那樣的話,還能有幾個願意付費成為會員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