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5年,台湾教育改革浪潮下,苗栗卓兰山上出现了台湾第一所体制外中学:全人中学。这是一所标榜自由、反对权威、反对填鸭考试的学校。为了不让下一代承受相同之苦,一群不满体制教育的大人放弃原本安稳的人生,开启实验教育之路,寻找另一种教育改革的可能。作者刘若凡,是全人中学第一届学生。虽然后来回到体制内学校,但这段受教育经历,对她的成长有重要影响。长大后,为追寻自己成长的秘密,她重返全人中学展开研究,以大量的田野访调与资料搜集,爬梳全人20年来从违法设校到合法立案,实践自由教育的历程。
成为你自己,是自诩开明的家长、教育者最常说的话。如何成为自己?可以成为怎样的自己?这本书揭露了理想教育的艰难。书中呈现的不是体制外教育的天堂,而是一群怀抱理想的教师,他们的挫折、矛盾与焦虑,以及一群在自由教育成长的学生。他们如何与大人冲撞,在说理、吵架与妥协的过程中,“成为他自己”。
自由是有边界的。但这边界绝不是一条整齐划一的直线,而是曲折模糊,在学生和老师的一次次互动中产生的。全人中学的故事,是台湾教育改革的重要路标,更是值得所有关心教育者、受教育者值得一读的故事。
成为他自己:全人,给未来世代的教育乌托邦
出版社:卫城出版(台北)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作者:刘若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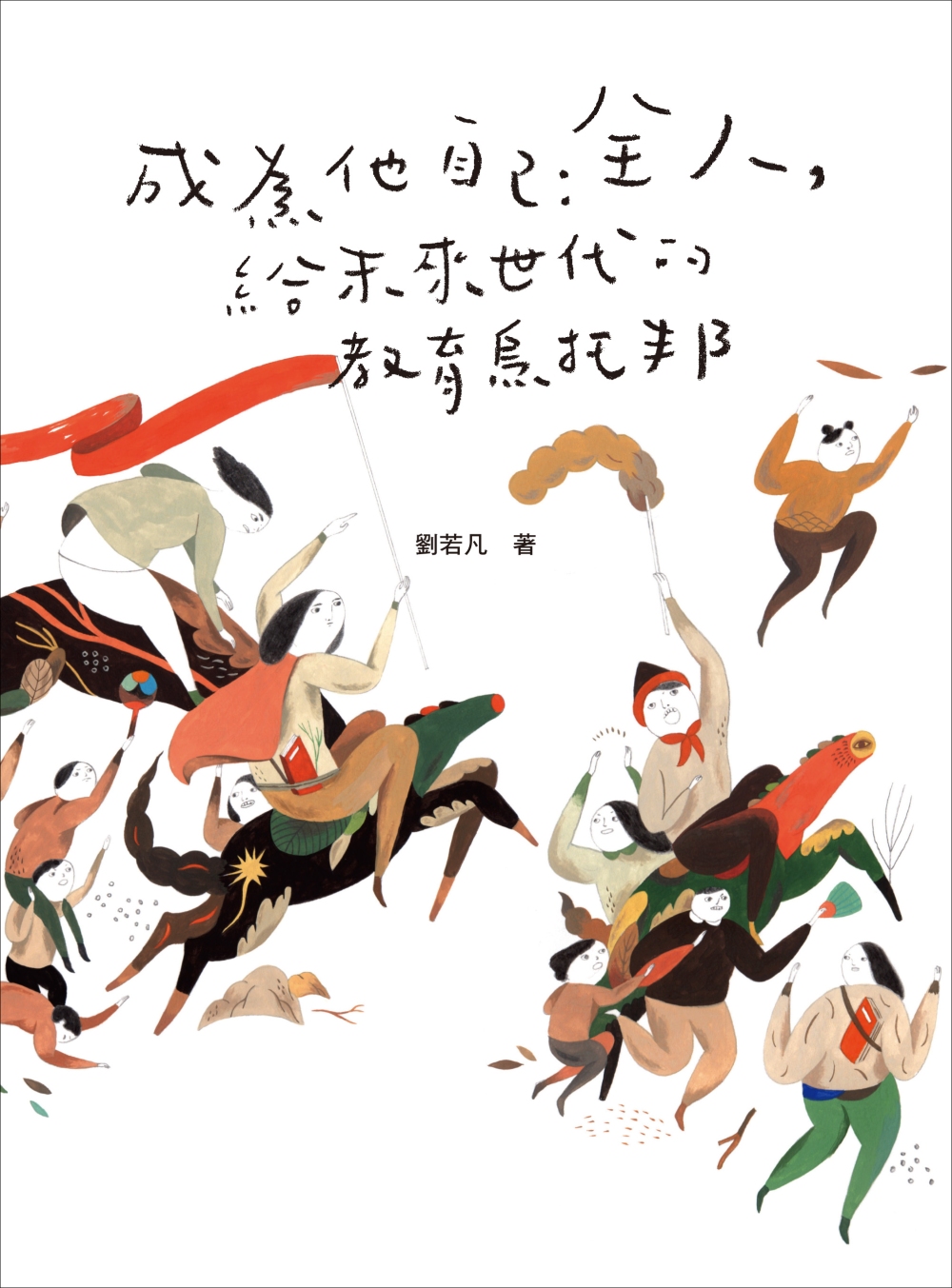
一开始我们想做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总是很羡慕别人的教育,比如北欧、荷兰或芬兰的教育。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教育?所以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乌托邦的故事,但其实这是1994年到现在,全人中学20年来的真实历史,也是我的研究。
我今天来这里之前,遇到一个男生分享他读这本书的心得。他觉得看这本书很像在看《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读了就停不下来。
重新回到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小学四到六年级读的是全人中学,是台湾第一间体制外的学校,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是跟一般学校不一样的学校。这个学校有很多独特之处,比如有学生自治会,所有的校规都是学生投票决定,包括要不要穿制服、要几点睡、学校能不能养猫等,大大小小的校规都是透过自治会来决定。第二个特征是,学校并没有一张帮你拟好的课表,所以全部课程都要学生学习自己选择。
后来我回到一般的国中念书。我是1986年生,所以回到一般国中时,还是女生长袜要穿到膝盖的年代。一进校门就有教官在旁边拿着一张单子,检查你的白色球鞋有没有色彩的那个年代。
因为一般学校要求很多,要穿白的球鞋、不可以在走廊上奔跑,不可以不遵守规则。所以我从全人中学回到一般的学校,常常忍不住回头去想,全人中学要教给我什么?它似乎从来没有给答案,可那是否也是一种答案?只不过不像普通学校,它是用其他方式告诉你。所以,我就回去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学生的样貌。有很多教养书都是在跟家长讲话,告诉家长要教出怎样的成功小孩。可是从来没有一本书是在跟学生讲话,或者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中,学生的样貌如此不同。
所以,这本书中的学生有顽皮的、会爬山的、不喜欢上课的,你会看到他们的身影。我觉得自己回去跟这些校友做访谈的时候,像是一个采集青春的蜜蜂,把他们的青春的记忆酝酿成了这本书。
我想简单地通过四个故事,来讲这本书的四个章节,也就是全人中学20年的四个阶段到底是什么样。

第一个故事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原本我念一般的小学,有一天爸爸载着我驱车走到苗栗卓兰山上的一个果园,进果园的路上两边都是橘子园跟葡萄园。然后车停在一个平地,爸爸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学校。
可是我没有看到学校,只看到一片被铲除的果园跟泥土地,天上有大冠鹫翱翔。我很好奇这个学校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在这本书后面,你会看到我搜集的这所学校的历史照片,就是一开始我看到的那个光秃秃的学校的样子。
一开始,这些大人,像我爸爸,是怎么想像全人中学这样的学校呢?他们在苗栗卓兰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家长跟老师在那个房子阴暗的灯光下,讨论学校要教出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这些不同身分的人就开始谈,认为学生该怎么学习,如果不是填鸭教育的话,学习应该从哪里开始。
当时就谈出很多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人可以先天被定义,学生应该有权力去自我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教育的起点不是别人告诉你要学什么,而是你要慢慢地自我察觉,决定要变成什么样子。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想法,是一个非常本质化的想像。他们开始思考,教跟学的起点必须从学生开始,而不是从老师在台上灌输。假设必须要从学生开始,那应该怎么教,可以怎么教。所以他们就想像出了另外一个老师的样子。
这个老师要想办法诱导学生发觉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不能简单地告诉学生,你应该喜欢什么,而是要带领学生发现,你喜欢这个吗,你喜欢那个吗,你到底想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这种教育方式是很迂回的,必须承认它很浪费时间。可能有的学生6年都在打电动游戏,然后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毕业了,这也是有的。在他们这样的想法下,学校在苗栗卓兰的小村庄到了9月就开学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那时收到的一封开学信。《哈利·波特》第一集就是哈利·波特收到一封被叼来的入学信。信上写了他要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长袍、魔杖等等。1995年,我开学的那一天,也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信上说,我们学校有自治会,所有规则都要你自己决定。不要穿太漂亮的衣服,因为学校在山里;要有脚踏车和登山背包,因为我们要去爬山;你要想自己要学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帮你安排你的课程。
这封信寄来之后,就正式开学。全人中学是住宿学校,也是混龄制,所以大大小小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都住在一起。开学的第一天分宿舍,我压力很大、很慌张,就会想要跟谁住,跟谁好。
在实行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要多问一个问题是,当老师把他们的手放开,取而代之的机制、理念是什么?当学生从一个什么都管得周到的学校,来到一个大部分事情都被放任的学校,我们能形成什么新力量?所以在第二个故事,同侪的身影就开始出现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这时,全人中学运作已经到一个阶段。大家慢慢习惯自己选课学会自己制定规则。制定规则的场所很像小型的国会,例如一条规则你一定要投票表决,二分之一通过还是三分之二通过。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从头学习,因为以前我们并没有可以替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
到了这本书的第五章,我写到学校开始慢慢发现,当拿掉外力控制,学生自主、自治的环境,并不那么容易就可以形成。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学校里有一群男生在卓兰镇偷了别人的车,被抓到警察局,之后学校的老师才知道这件事情。
但他们选择的处理方式跟一般学校的老师不同。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惩罚那些学生。1998年的那一天,老师们持续讨论,当老师放下了控制的力量,学生不是应该自主地遵守规则吗?但为什么他们还是选择了违规?
他们不断谈这件事,谈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最后校长选择带着学生去道歉,还有其他因应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很真实地看到老师,也就是学校里的大人怎样去面对秩序的崩解,怎么去面对放手之后的代价。
现在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回去看1998年的资料时,有一个老师的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老师曾经是一般学校的老师,后来在全人待过一阵子,他说:“他们的处置方式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在一般的学校,这些学生一般是记大过或者警告,最后想办法让他不要留在学校。可全人中学并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的是,当你的学生越界的时候,跟学生沟通,解释为什么这条规则要存在。”
为什么有些行为必须要付出代价,怎么弥补跨越这个界线之后的问题。也就是,当你发现仅仅给学生自由并不代表一切的时候,老师们开始透过许许多多的事件回头思考,假设放手并不是教育,我们要教出怎样的人?
假设他是一个自主的人,他要长成什么样子?他是温柔的呢,还是理性的?他喜欢知识还是喜欢习作?这些思考,是书中的第六章,就是在谈这些老师反省之后,怎么慢慢地思考人的价值,思考如何取舍。
我会特别提及价值的冲突是因为,我现在也在一些学校现场、立法院观察现在学校的改革。我发现许多改革是不断要求学校要多做什么,可是没有真正去面对价值的冲突。所以第四个故事就是,全人中学里出现了两群不同的老师。
一群是非常雄壮和阳刚的男性,他们喜欢读柏拉图《理想国》,喜欢用批判性的言语来跟学生对话;另外一群老师,男女都有,他们是辅导组,他们跟学生的互动方式是邀请学生来家里泡茶,他们不聊柏拉图,但聊谘商理论,聊家庭,他们想了解一个学生的家庭如何影响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学校也有两群不一样的学生,一群是比较强势的,他们在自治会是学生领袖,学校里人缘很好,这种学生就跟那些很阳刚的老师感情很好;另外一群,生活上比较不能自理的,比较柔弱,他们就跟喜欢聊家庭的老师关系比较好。
这两群老师有不同的样子,所展现出来作为一个人的姿态也差异很大。所以在书的第六章,两群老师和两群学生开始形成了很激烈的争执。他们的冲突是什么?难道这些东西不能并存吗?
可是因为这个学校这么小,所以他们要争,到底谁是值得被我们赞扬的,被全人中学定义为成功的人。这个成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这个学校所想要教出来的理想的人的样子。
最后全人中学做了一个选择。它选择了比较阳刚的、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喜欢探险、登山的人的样子。当全人中学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是2007年了,从1995年到2007年是从一个无到有的过程。
从不要过去的教育、填鸭式教育,不要只有规则的教育,慢慢地寻找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个比较民主的,让学生可以自己制定规则的,一个把学识融入生活当中的,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要学和不学什么的教育。
所以,第四个故事是书中的第七章。事实上要教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始终在全人中学被讨论,也并没有完全解决的一天。20年来,全人中学不断思考要教出什么样的人时,不断地碰到新的问题。尤其在寻找这样的人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的问题:升学压力。
很多人都经历过自己喜欢的科系和父母想要我们念的不一样。全人中学是一个体制外的学校,似乎不会面对升学压力。但其实对所有体制外的学校和学生来说,升学压力跟主流价值,从头到尾始终伴随着选择另类教育的学生。
因为当你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于是2009年,全人中学看起来找到了一个他们想要的自主自治的人的答案时,他们也要回头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2009年,我在全人中学做田野调查,那时全人中学已经选择要立案要有学籍。一个教官打电话到全人中学问,请问你们要教官吗?全人中学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教官,因为它是个学生自治的学校,不会有教官去管理学生,所以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过了两天,那个教官就来了。他来的时候穿海军的军服,走到全人中学的行政室,他问行政他要怎么报到。这时候,手上拿咖啡穿着短裤和T恤的校长从长廊那边走过来,看着这个教官。后来教官就留下了。
开学时教官已经不穿军服了,他开始跟校长一样穿短裤和T恤,陪学生一起登山。这段插曲让我很讶异,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全人中学的选择:选择立案、要合法、让学生可以升学,虽然这并不是全人中学要教给学生的价值;
另一方面内部也在讨论,有一位老师这样形容自己,他说:“并不是我们自动放下了威权,我们才选择来全人中学,而是我们来到这个环境,我们主动自然而然地把身为老师、教官的权力放下了。”
在最后的阶段,全人中学还是很挣扎,假设它要教出一个理想的人的样子,这个人就是没有学历、文凭,他没有证明自己的东西拿到劳动市场上去贩卖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妥协?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两全的方式。同时,他们还在不断思考台湾的这种另类教育跟升学体制的关系。这就是全人的最后一个暂时性的阶段。
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成为他自己:给未来世代的教育乌托邦》。我的答案是乌托邦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很理想美好的“理想国”,而另一种是当我们要前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通过的那些荆棘,挣扎的,甚至价值冲突的过程。
而我觉得全人中学正是在展现这冲突的过程。这本书真正的价值,是诚实坦然地把全人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在教育上面对的挣扎写出来。很赤裸裸的现实、价值上的挣扎,每一个学生在成长中的际遇,都在这本书。
一个只有20年历史的学校,一段过去的历史,为什么我要说是给未来世代的?因为近年来我发现,全人中学的故事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般中学在改变,而全人中学也在改变。两者分别从体制内跟体制外,或者主流和另类的差别,慢慢地越走越近。
而我们即将面对的问题,也会是全人中学过去面对的问题,例如怎么教学生选课?假设学生什么兴趣都没有,就喜欢打电动游戏的时候,你要等他多久?例如,现在我们倡导师生平等的关系的时候,当教育还是要有权威、老师还是要有权力的时候,你怎么去拾起教师的权威?
当一个老师不只在课堂上执教,只是把这堂课上完,赶进度,当他开始对教育学生有不同想像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们能够讨论并彼此达成共识?这些我们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在全人中学都真真实实地发生过,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这本书既是20年的历史,也是给未来的乌托邦。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找到更好的答案。
(本文为作者刘若凡在2016台北国际书展演讲全文,演讲题目为:教育青春梦,全人中学20年。经作者授权刊载)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