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台湾总统大选刚结束,隔一天最新的人事异动消息,不是关于内阁院长,也不是立院龙头,而是华视总经理,据传将由辅选有功的艺人余天出任。虽然余天在第一时间否认,但媒体人事成为政治酬庸的阴影,却在新政府上任前,重新笼罩在公共与国营媒体上头。
说到“国营媒体”,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有“国家通讯社”地位的“中央社”,中央社遭政治介入及干预的问题,在媒体圈时不时就浮上台面。
政府主导人事 国营媒体高层热衷经营关系
成立于1924年的中央社,一开始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过去甚至背负收集“匪情”(中共情势)的功能。它成立的初衷,更接近“宣传机器”而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新闻机构。
在两蒋时期中央社甚至能“上达天听”,派驻地方的军事将领,都少不了要拜会中央社驻地记者,以免自己做了什么被记上一笔,传进总统耳里。这个角色类似今天中国新华社记者撰发的“内参”(只供高层领导在内部阅读的讯息)。
1996年,立法院订定《中央通讯社设置条例》,中央社正式改制为“国营通讯社”,人事任命权由行政院决定。条例中还规定“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董事总额二分之一。经费来源则有4种:中央政府补助、捐赠、提供服务收入和“其他”。但国家补助仍然是最大宗,目前1年编列近3亿元(新台币,下同)经费。钱与人事掌握在执政者手中,也注定了中央社为执政者干预操控这一难以翻转的命运。
党营转国营的中央社,内部组织和人事与党政关系勾连过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还尚未显现。但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背景亲民进党的媒体人开始进入中央社内并位居主管职务,与中央社原来的成员的观念产生冲突,矛盾逐渐浮现。
“当时的中央社很多都是国民党文工会(“文化工作会”,后转型为文传会)来的,我们那时进去,都被说是‘台日帮’(过去曾在亲民进党的《台湾日报》工作过的人)进来了。”曾任中央社副总编辑的庄丰嘉笑了笑。回忆起那段日子,庄丰嘉说,当时攻击抹黑的黑函从没断过。庄丰嘉在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离开公营媒体,之后参与创办网路媒体“新头壳”,目前投身培训地方青年“自己采、写地方新闻”的新媒体工作。
政府主导人事的恶果之一,就是中央社内不乏藉着建立关系来巩固位子的主管。“2000年那时要变天了,有一天主管会议上,一手由国民党栽培出来的社长在会议上说着要如何因应未来政党轮替。”曾在中央社任职30年的胡宗驹说,一间媒体的社长竟想着怎么因应政党轮替,让他气愤不已,随后便走出会议室递了辞呈。
想起这一段,胡宗驹感叹:“主管觉得他若不去讨好政府,可能会被换掉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也凸显台湾民主的不成熟。国外的老牌媒体想的是怎么靠转型活下去,哪有在靠讨好政府活着的!”
2013年亚锦赛期间,中央社意外流出一则“亚锦赛错称中国台北,抗议无效”的新闻,刊头出现“总编裁示不发”6个字。事后中央社紧急撤稿,隔1小时再发出的校正稿,却是改成“中华男篮今午凯归”,而内文中对于正名的抗议内容也大幅缩水。
现任中央社记者的黄倩(化名)也直言,“虽然社长是任期制,任期时间并不与选举一致,但政党轮替后(董事长)通常会辞职。毕竟颜色不对很难做下去啦!”黄倩感慨,中央社的预算要靠政府给,仰人鼻息争取预算,当然就不能让党政关系不好的人当高层,“否则要得到钱吗?”
也因为高层人事与政治密不可分,“政党轮替后,社内中阶以上的主管就会有一股大搬风,政治新闻的主管大多会有调动,有些会换下主管职,或转到闲差去。另外选举前也已经出现小幅度的调动,一些跑政治的资深记者就先被升到主管职卡位,这样选后人事要进行调动时,至少让他能在主管这一水平平调。”
但人事随政党轮替流转,也让胡宗驹感叹,媒体因此沦为执政者的工具。空降的高层,与政府之间属于利益的结合,有了这层关系,免不了影响新闻内容,像是打电话给总编辑,干预新闻内容。一位离职的中央社员工就透露,中央社曾经出了一篇关于总统民调的新闻,“新闻内容是研考会做的民调,那时研考会还提供几个学者让记者采访,只是其中一位学者提到,民调抽样可能有误差。结果那篇新闻出了以后,社长接到来自府方的关切电话,急着深夜就要编辑撤下新闻。”
此外,在总统竞选期间,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因为“带职参选”而引来批判声浪时,中央社也“适时”密集推出了一篇又一篇国外政治领袖“带职参选”的报导,让外界对中央社的角色为之侧目。
这几年中央社也常被质疑“报喜不报忧”,像是编辑台压下“国际盖洛普民调——台湾是亚洲最悲观国家”的资讯,引发争议;或是2013年亚锦赛期间,中央社意外流出一则“亚锦赛错称中国台北,抗议无效”的新闻,刊头出现“总编裁示不发”6个字。事后中央社紧急撤稿,隔1小时再发出的校正稿,却是改成“中华男篮今午凯归”,而内文中对于正名的抗议内容也大幅缩水。压稿、改稿一事,让中央社遭外界讥讽“已成新华社分支了吗?”

关系比专业重要 媒体本业谁在乎?
文章开头提到余天可能入主华视的传闻,提醒外界公股占多数的电视台也是人事酬庸的管道。此前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艺人江霞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大力辅选,那年陈水扁上台后,江霞成为台视董事。2004年总统大选,江霞同样卖力声援,选后华视董事会无异议通过江霞担任华视总经理的人事案。彼时江霞虽遭质疑能出任华视总经理,全是出自酬庸,但面对这样的批评,江霞回应:“就算是酬庸,也酬庸得很有道理。”
“执政者不是不能对媒体高层有想法,毕竟执政者若有政策目标,当然得选择适当的人入主,让政策能够被有效执行。”政大新闻系教授刘昌德说道。可惜的是,过去几次政党轮替,换上的媒体高层,总不符外界的期待,甚至为媒体本身带来不少伤害。
“江霞来华视后,有天晚上许多业务部主管在接获通知后打包走人。”曾在华视任职8年的蔡瑞珊回忆道。
江霞上台后除了人事异动外,由于华视的节目多是“外包外制”,那时她选择停掉一些收视率不错的节目,再新开其他节目,并外包给另一组自己熟悉的团队制作,也引发不小的质疑。媒体经营者能藉着外包制作,有意无意的建立与巩固自身的人脉关系。但也因为节目存续得看总经理人事,“所以那时我们去签约都不敢签太久,总经理任期两年,所以我们节目制作大多只签两年,主持人多半也签两年。”蔡瑞珊说道。
只能签订短期合约,直接冲击的便是节目品质。蔡瑞珊解释:“制作一档综艺节目要搭景啊,你如果签的是5年约,制作团队当然愿意花钱在布景制作上;但是两年的合约,两年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布景当然不会花这么多成本做。”另外节目的主持人与团队,也总处在充满不确定的危机感中,因此当遇上更好的工作机会,便毫不眷恋的离去。
两年一任的总经理任期,加上人事酬庸风气盛行,让华视内部相较之下“关系”远比“专业”重要许多。“每到总经理任期后半年那段时间,你就可以感觉很多人在‘夜奔敌营’,到处打听谁可能升官、谁可能接任,然后不停地送礼、请吃饭。”蔡瑞珊感慨。当“搞关系”成了稳固工作机会的途径后,媒体的本业自然也就被晾在一边。
随着华视在2006年以后并入公广集团,人事任命得依据公广集团的相关规定办理,总经理也得经过遴选机制产生。但貌似公正的机制,蔡瑞珊却直言,“遴选有传说都是假的!都是内定好的!”即便已转型为公共媒体,但“关系”仍旧决定了一切。
不过,在扁政府时期曾任新闻局长的立委姚文智为江霞缓颊,他认为江霞本身作为一个专业的艺人,熟知媒体产业现况,虽然任职华视总经理时引发不少争议,但争议却是“有好有坏”,例如江霞任内大力推动本土戏剧,就能看出她担任电视台总经理努力的痕迹。
“过去威权体制下,电视台的戏剧总是偏向商业考量,本土内容很难有空间。江霞大力支持本土戏剧,当然就引起一些争议。但在我看来,她引发的争议,其实是台湾走向改革过程产生的‘阵痛’。”姚文智直言。
2008年民进党在立法院仅仅只剩27席立委,公视董事的审查可以说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随后新增的8名董事,可想而知是一份亲近执政党的名单。但政治力如此直接对公视进行干预,随后也导致内部新、旧董事相互提告,新董事对公视董事长提出不信任案等荒谬状况。
公共媒体成为政权转移之际,政党恶斗的牺牲品,最经典的案例要数2008年的公视董事会之争。
当时国民党上台之初,立法院先是冻结了公共电视一半的预算,同一时间欲修法扩编公视董事人数。强行修法过关后,新闻局(现已解编)随后招开审查委员会,增聘8位董事。
由于公视的董事提名遴选机制,规定由新闻局提名,再按照政党立委人数比例来推举组织审查小组;但2008年民进党在立法院仅仅只剩27席立委,公视董事的审查可以说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随后新增的8名董事,可想而知是一份亲近执政党的名单。但政治力如此直接对公视进行干预,随后也导致内部新、旧董事相互提告,新董事对公视董事长提出不信任案等荒谬状况。
那段时间公视的董事长郑同僚与总经理冯贤贤也曾大动作在四大报刊登声明抗议政治干预,但立即成为攻击目标。回忆起这段经历,冯贤贤仍旧气愤不已,“那时候中央社整天出刊攻击公视的文章,内容却几乎没有向公视求证!”冯贤贤说,中央社对公视之争的报导,往往援引攻击方的说词,有一次终于有中央社记者打电话访问她,“我在电话里就跟对方说,你们每篇文章都没有求证另一方当事人,这样还有专业可言吗?”
对于中央社成为执政党攻击异己的工具,谈起这段往事,冯贤贤声音愈显高亢,“攻击的模式往往就是先由中央社发出一篇负面的文章,为议题设定风向,随后其他媒体再跟进报导。”此间执政党总是透过中央社为议题定调,藉此遂行目的,“可见中央社就是党国体制下的产物,根本应该废除,否则哪有转型正义可言!”
整肃最惨烈时,甚至有董事直接下公文要查特定节目的帐目,质疑该节目藉着聘请顾问酬庸特定人士。虽然最后都在经理和总经理手上挡下,但彼时人事恶斗的压力可见一斑。
另一边,公视彼时董事长郑同僚则是针对8名新增董事,向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随后新闻局也作出反击,向民事法庭声请解除郑同僚董事长职务,双方刀光剑影,那段时间新、旧董事的司法攻防,看在许多传播学者眼中,无疑是政权移交过程中,公共与国营媒体内各自的政党势力大乱斗,
公视的纷争延烧5年,期间冯贤贤遭解聘,更引起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关注,“自由之家”提出呼吁:“我们希望最近的解职行动不是因为台湾公视屈服在具有争议性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呼吁台湾的政治决策者确保公视不会沦为政治冲突下的受害者。”但一直到2013年,人事争议暂告一段落,难产多时终于顺利诞生的第五届的董事,也于同年7月召开首次的董事会议。但此时已距离第四届董事届期任满超过3年,延宕已久的人事浑沌,也让公视运作几乎停摆。

万年经营团队 毫无企图心
公共与国营媒体成为政治的工具,追根究柢就在于这些媒体过去“转骨”没转彻底。以中央社和华视来说,长期以来与政党关系紧密,许多人事与党政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党味”如此浓厚的组织,与媒体该有的反叛与创新格格不入,也因为这样的组织特性,让政治酬庸的人事能够在媒体内遂行他们的意志,少了内部的阻力。
“当年我进华视,身边全是一些年资二、三十年的工作者。”蔡瑞珊笑着说,里头的人死气沉沉,一滩死水,对于年轻人的提案无法理解,有时还觉得是年轻人不懂华视“文化”,想要推动变革相对困难。
这样的体质,即便出现想做事的总经理,例如小野与陈正然,但华视内部原有的军系背景,以及僵固的人际网络,再再都强化“关系”与“升迁”间的因果关系,“专业”反而毫无用武之地。这样的环境,让创新理念难以推行,“以前我开会,10个人里面有9个就跟公务员一样,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们觉得你太年轻,不了解华视。久了真的很沮丧。”蔡瑞珊感慨,毕竟“有关系”就能安稳度日,谁还会有斗志。
“我还记得陈正然那时想把日本综艺节目‘全员逃走中’搬到台湾,他挑了一些相对年轻的人,每周进行教育训练,带我们去阳明山亲身玩一次‘全员逃走中’。”蔡瑞珊回忆,那段时间华视似乎有机会注入活力,但最后,这些培训的年轻人几乎全数离职,“待不下去,有理想的人很难待在里面。”
从党营媒体转为国营的中央社,同样承接了僵固的人际网络在组织内做事的习气,“过去在里面,有时下面的记者会来问你某条新闻该怎么做,但他这样问不是真的要跟你讨论,很多时候是想了解你的态度,作为他以后处理新闻的依据。”庄丰嘉笑着说,这种“看上面做事”的风气,在其他媒体几乎很难存在,但在中央社里却到处弥漫。
而公视虽非党营事业,但创立之初,新闻局底下广电基金会员额直接并入公视,里头还包含了早期行政院新闻局公共电视节目制播小组,也让刚出生的公视,甫成立便显得老态龙钟。加上近似公务体系的升迁保障制度,“像我们里面就是‘万年经营团队’,经理从这里换到那里,升迁与加薪都比照公务员,只要不出大事,就能稳稳地做。”公视内部同仁嘲讽,这样的稳定成了双面刃,一方面让想做事的人有空间施展,不怕大展身手后遭到开除;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墨守成规的空间,“里面不要说是‘保守’了,根本是‘毫无企图心’。”
公共与国营媒体内保守僵固的体质,以及长年累积的人事酬庸陋习,如今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过去民进党即便没有这么严重的伸手干预新闻,但是对于公共与国营媒体的态度一样消极,把它们当成安插人事的单位,对于公共与国营媒体毫无想法。”冯贤贤说,如今新政府又传出为酬庸而将人安插在公共媒体的风声,“但到了2016年,台湾应该要重生了。过去许多因循苟且的东西必须一脚踩破。”而公共与国营媒体能否彻底转型,正是一道考验。
不论公共媒体将朝何处改革,新政府首先得跨出的一步,必然是对人事权放手……第二步则是得要针对高层人选有个完整的对外说明。
但究竟该怎么改革?对此庄丰嘉、冯贤贤不约而同的提出,应该让中央社等媒体与公广集团整并。
以中央社来说,1995、96年间立法院为了《中央通讯社设置条例》吵得不可开交,彼时便已出现担忧中央社为执政者把持的声音,外界也质疑台湾是否需要一个由国家资助的通讯社?“20年后我们更该问,中央通讯社还有存在必要性吗?”冯贤贤感慨,中央社的设置条例中明订它具有“国家对外新闻通讯业务,促进国际对我国之了解”以及“加强与国际新闻通讯社合作,增进国际新闻交流”等功能,但如今仅在21个城市派驻20名记者,国际新闻内容称不上多元丰富。加上网路时代来临,中央社在提供资讯上的功能早已式微,中央社是否还有存续的理由,值得好好思考。
对于国营的中央社或许已不符时代需求,庄丰嘉建议,“中央社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多外派记者,如果并入公广集团,可以扩增公视的国际新闻内容与品质。台湾不是整天在说缺乏国际新闻吗?那就应该好好运用这些人啊。”
除了整并,担任公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多年的陈信聪也提到,必须回头检视公共媒体在当代的角色与功能,公共媒体新的功能与任务分组,有机会引进更多人才进入公广集团,也才有机会让一滩死水的内部产生扰动,产生出新的可能。当然这些改革免不了涉及组织的重整,冯贤贤提及,公共与国营媒体本身的组织文化,与媒体应有的反叛背道而驰,过去党国关系导致的僵固非得重新洗牌,否则改革难以向前。但涉及内部员额的变动,如何能妥善安排人事,也将会是一大考验。
另一边曾担任中央社社长的胡元辉则认为,中央社作为国营媒体,对外仍有它的功能性,例如过去他曾遇上外交官员询问,能否在非洲各国都有驻外记者,因为这些与台湾毫无邦交的国家,或许台湾政府能够透过中央社,进一步了解当地,甚至因此有了非官方的交流机会。胡元辉认为,要不要整并进入公广集团都可以再讨论,但怎么保留并强化中央社的特殊功能,需要好好思考。
但不论公共媒体将朝何处改革,新政府首先得跨出的一步,必然是对人事权放手。胡元辉说,新政府得先做到尊重公共与国营高层人事的任期,“中央社、公广集团董事长都是有任期保障的,执政者至少要先尊重他们的任期,不能一上台就想把前朝的人换下来。”如此一来等于是让人事嬗递回归法定程序。姚文智也同意,政治力面对国营和公共媒体,必须有所“节制”,“政党的手不能伸进去(媒体),是最基本的认知!”
第二步则是得要针对高层人选有个完整的对外说明。“例如公广集团的董事长,你为什么选这个人?要达成的目标任务是什么?都应该有所说明,让大家知道你是有媒体愿景,而不是只拿这些位子当酬庸。”刘昌德说道。
回顾过去16年,由于缺乏媒体长远政策,加上执政者在党国思维下,只想牢牢掌握媒体工具,不思这些媒体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功能性,导致国营与公共媒体半死不活,既没影响力,也无法成为产业的领头羊。新政府上台后,外界也睁大眼盯着看,这一次执政者能否走出旧思维,让国营与公共媒体脱胎换骨,“否则公共与国营媒体,只作为政府的传声筒,公广集团和央视、中央社与新华社又有什么两样?”蔡瑞珊叹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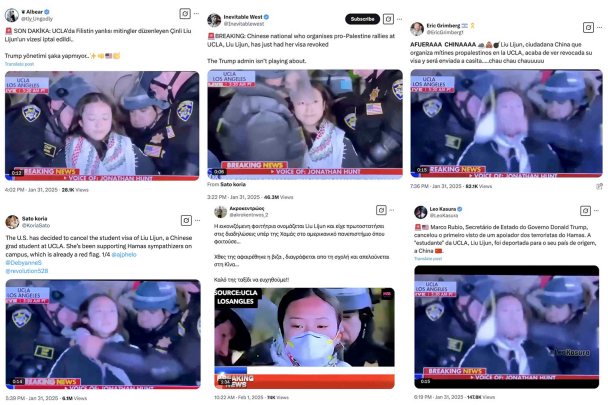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