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173期)文章。端傳媒與《二十一世紀》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經雜誌與作者授權轉載。本文不代表端傳媒立場,但端傳媒期待透過此一契機,重新檢討當代中國社會公共輿論及思想狀況,後續將有多篇回應文章,敬請期待。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版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性質:學術雙月刊
當期雜誌:2019年6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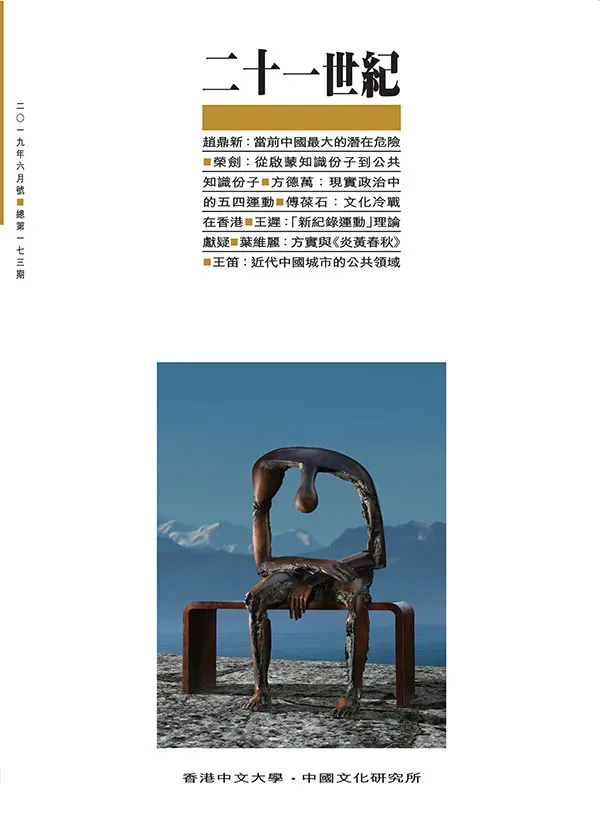
一個正態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在短短幾年內就遭到大面積破壞,導致中間聲音在社會上日趨衰弱,左傾聲音衝高,以及激進的自由主義聲音在社會上重新獲得廣泛同情並且重新被道德化。

【編者按】: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173期)文章。端傳媒與《二十一世紀》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經雜誌與作者授權轉載。本文不代表端傳媒立場,但端傳媒期待透過此一契機,重新檢討當代中國社會公共輿論及思想狀況,後續將有多篇回應文章,敬請期待。
版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性質:學術雙月刊
當期雜誌:2019年6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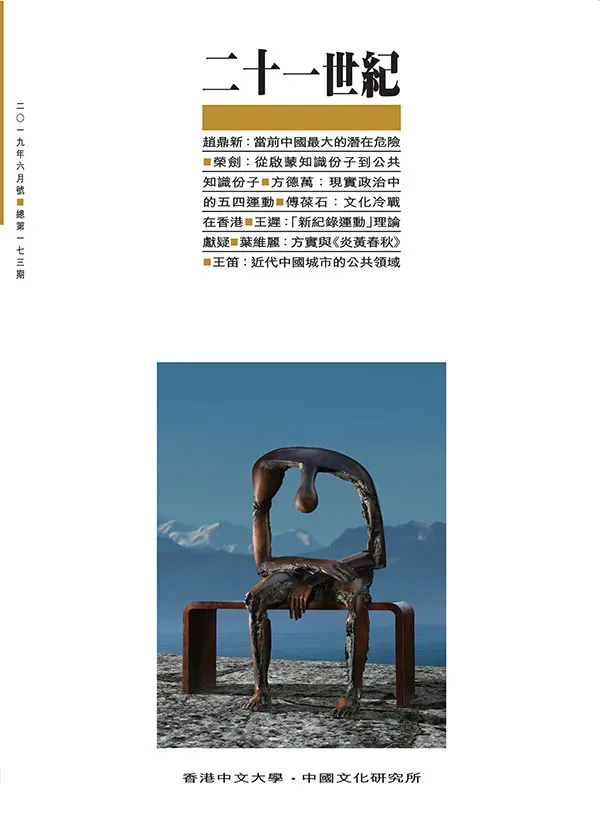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 端傳媒編輯部 或相關單位所有,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