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6月号(总第173期)文章。端传媒与《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经杂志与作者授权转载。本文不代表端传媒立场,但端传媒期待透过此一契机,重新检讨当代中国社会公共舆论及思想状况,后续将有多篇回应文章,敬请期待。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版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性质:学术双月刊
当期杂志:2019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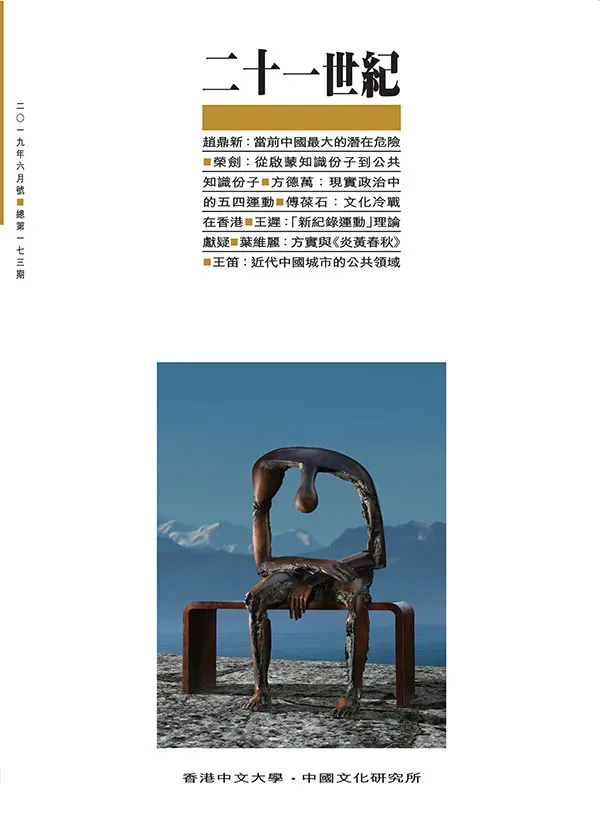
一个正态的公共舆论空间分布在短短几年内就遭到大面积破坏,导致中间声音在社会上日趋衰弱,左倾声音冲高,以及激进的自由主义声音在社会上重新获得广泛同情并且重新被道德化。

【编者按】: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6月号(总第173期)文章。端传媒与《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经杂志与作者授权转载。本文不代表端传媒立场,但端传媒期待透过此一契机,重新检讨当代中国社会公共舆论及思想状况,后续将有多篇回应文章,敬请期待。
版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性质:学术双月刊
当期杂志:2019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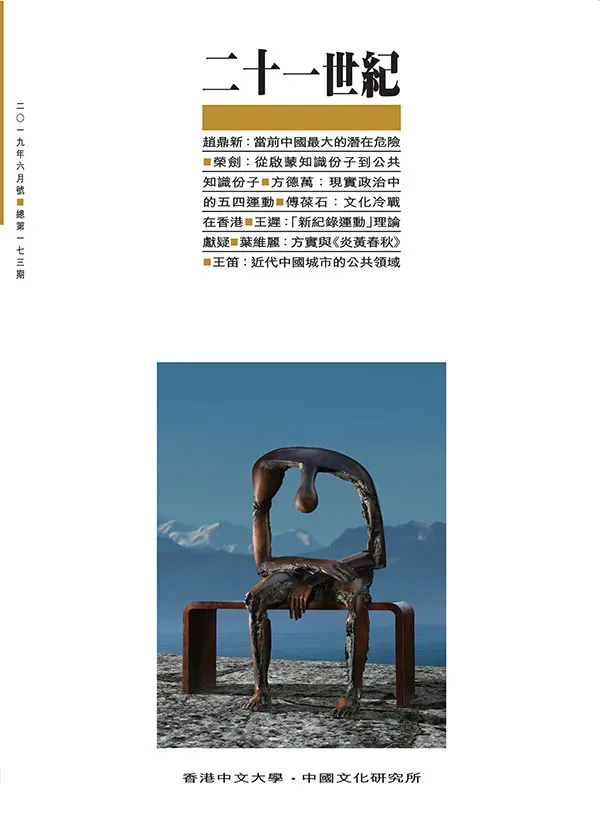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 端传媒编辑部 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