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 (Donald Trump,川普) 在輸了普選票下贏得選舉人票,「令人意外」地擊敗民主黨的希拉莉(Hillary Clinton,希拉蕊),得以入主白宮,成為第45位美國總統。儘管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榮克)及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墨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先後禮節性地祝賀特朗普贏得選舉,但歐盟傳統政治核心法國及德國,對特朗普仍不太客氣。
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歐蘭德)表示,他按民主國家傳統向特朗普表示祝賀,但同時亦指出:特朗普當選將開啟一個「不確定的時代」(a period of uncertainty),更直言法國會以獨立姿態與美國合作,不作妥協。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梅克爾)在發表講話時亦強調,美德的緊密合作,是建基於民主、自由、法治及人的尊嚴等兩國的共同理念,而且該是不分出生地、膚色、信仰、性別與性取向和政治理念地一視同仁,似乎也是針對特朗普在選戰期間的言行舉止。
從不同的外交渠道及媒體報導得知,歐盟內部對於特朗普普遍持不信任,歐洲各國外長在得知特朗普當選後,更召集特別會議,商討如何回應「後奧巴馬時代」的特朗普政治。事實上,歐洲傳統精英素有支持民主黨的傳統,現任總統奧巴馬在歐洲的支持度長期維持七成以上,而支持希拉莉的也有近六成。反之在相同的調查中,有近八成五受訪者對特朗普表示不信任,認為他沒能力勝任美國總統一職。
事實上,歐洲媒體對特朗普當選的報導,也反映了歐洲主流社會對他的不信任︰法國報章《解放報》(Liberation)以 ”American Psycho”(美國精神病,也恰好是2000s年電影《美國殺人魔》的英文片名)為封面標題,報導特朗普當選;而德國大報《世界報》(Die Welt)則以「世界反轉了」為題,將封面上下倒轉,一方面似乎形容自己跌破了眼鏡,另一方面也暗示特朗普將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歐洲領袖對特朗普最終勝出感到躁動可以理解,但單純認為特朗普上台對歐盟弊多於利,則過分簡化跨大西洋關係(Trans-Atlantic relations)。畢竟正如資深記者 Patrick O’Gara 指出,特朗普現象對歐洲而言是一個「奇觀」(spectacle),歐洲媒體以至政客在意的不是特朗普是一個怎樣的總統,而是如何透過特朗普現象,建構有關歐盟與反歐盟的論述。
美國,歐洲認同的「他者」
歐美關係錯綜複雜,在於這段大西洋關係既有實質外交操作,亦涉及彼此身份及歷史建構。借用知名美國學者蘭普頓(David Lampton)形容中美關係的詞彙,歐美關係大抵也是另一個「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美國立國本來就是要與歐洲切割;立國初期所提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就是以美國不介入歐洲戰爭及政治事務,換取歐洲國家不干預美洲事務的外交思想。而美國在戰間期(interwar period)的不干預主義(non-interventionism),也是針對歐洲一戰後紛亂局面的回應。
若非二戰後國際秩序形成美蘇角力的格局,柏林圍牆將歐洲一分為二,西歐在經濟困頓下接受美國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成為所謂「西方社會」(the West)的一員,美國與歐洲本來就不屬於同一種文明體系。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發表研究報告,綜合多年民調的數據,點出歐洲與美國五個不同之處︰
- 美國人較歐洲人更強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相信個人能力可以扭轉命運;
- 美國人重視個體自由不受國家干預,而歐洲人普遍認為國家有責保障國民生活所需;
- 針對種族及宗教的冒犯言語(offensive speech),歐洲人的容忍程度較美國人為低,更傾向認為人無權在公開場合發表上述言論;
- 宗教信仰對於美國社會的影響力比歐洲社會為高;
- 美國人與歐洲人的道德標準不盡相同。例如,美國人對婚外情及越軌的接受度,比歐洲人低。
後兩項差異主要針對個人行為,在歐洲社會亦是言人人殊,而在歐洲一些國家(如波蘭及愛爾蘭),天主教信仰是不少社會政策的基礎──儘管以宗教理由制訂的政策,認受性近年每況愈下。反之,前三項差異是歐美兩地在「國家 – 社會」關係及「自由 – 權力」關係的結構差異,也是構成對國家甚至超國家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對於歐洲社會而言,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國作為歐洲「他者」(The Other)的典型象徵︰一個強調個人能力的資本家,一個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精英,一個不時以言論挑動族群及性別矛盾的素人政客。
美國作為歐洲「他者」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及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德希達) 這兩位在思想上南轅北轍的歐陸哲學家共同發表文章,一方面批判小布殊的伊拉克政策,另一方面提出以「歐洲共同外交政策」回應伊拉克問題的方式。當中哈伯瑪斯及德里達強調,歐洲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以超國家系統,締造跨越傳統民族主義管治方式,以及在不同階級、宗教的紛爭,從與「他者」對話間建立歐洲身份認同。
儘管不少學者如霍夫斯特大學(Hofstra University)政治學系教授格連(David Michael Green)或維珍尼亞大學教授古瑪(Krishan Kumar)認為,以美國作為歐洲「他者」來建構身份認同不甚可取,在數據上也沒有充分支持,但從以往戴高樂將軍(General De Gaulle)所顯示的反美(以及反英)情緒,到默克爾對美國「稜鏡」(Prism)及互聯網世界監控的不滿,均反映在這些歐洲政客眼中,歐美政治差異實為歐洲人在建構何謂「歐洲」的重要參照。
事實上,特朗普當選後,歐洲執委會容克已立即提出:歐洲需要思考,歐盟是否需要建立共同軍隊,令歐洲國家可不再依賴華盛頓的力量,維持歐洲地區安全。軍事整合從來都是歐盟內部一個重要但困難的議題,涉及國防甚至國家主權爭議。假如特朗普的出現,竟令歐洲國家「痛定思痛」,重啟上世紀50年代已放棄的軍事整合計劃,對於歐盟整合而言未必是壞事。
特朗普的勝利,歐洲右翼的強心針?
另一方面,法國總統奧朗德之所以如此高調批評特朗普,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指桑罵槐,借機抨擊國內正在冒起的激進民族主義情緒。
從制度分析,歐盟制度與美國的聯邦制度有很多相似處︰歐盟主席是由間接選舉產生,而有能力選舉歐盟主席的國家元首,則是由歐洲國家民眾直接產生,這種情況猶如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歐盟的立法機關有代表國家的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也有代表人民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情況也與美國的參眾兩院相似;歐盟整合涉及中央集權的歐盟政府,即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及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及歐洲國家各自政府,看來也像是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翻版。當然,在細節的權力結構上,歐盟制度與美國聯邦制仍有一定分別,但對於部分歐洲民眾而言,華盛頓的「威權管治」與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並無差異,而當下歐洲政治精英也如特朗普口中的希拉莉一樣,早被視為腐蝕不堪的一群。
事實上,特朗普的成功經驗,早被歐洲右翼視為重要的強心針,法國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領袖馬琳蓮.勒龐(Marine Le Pen,馬琳·雷朋)被國際媒體視為下一個可以贏得大國總統寶座的右翼領袖,而荷蘭自由黨領袖威爾德斯(Greet Wilders)更視特朗普現象為契機,希望藉此鼓勵民眾在下年3月的國會大選中支持自由黨,從布魯塞爾及一眾傳統政客手上贏回荷蘭。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容克在演說中也強調:歐盟不會變成「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歐盟不會是美國的翻版,其弦外之音更似是回應歐洲近年右翼思潮的批評,這又是一個以「他者」強化歐洲身份認同的明證。
對外經貿協議,關鍵仍在歐盟自身
展望將來,歐美關係會否退到一個無可挽救的地步,目前言之尚早。學界近日對於特朗普的分析,多強調他的「商場主義」及「現實主義」面向,認為部分對他的指責過於誇大──例如稱他會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潛在傀儡。美國國會在外交事務的參與,以及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不滿,也可能形成足夠制約,防止特朗普如脫韁野馬橫衝直撞。事實上特朗普也明白,選戰與治國是不同概念,否則他不會在當選後立即致電南韓總統朴槿惠,強調美韓軍事同盟不變,一改選舉期間的「撤軍」說詞。在與現任總統奧巴馬見面時,他也亦表現得十分謙卑,甚至對選舉期間戮力攻擊的「奧巴馬醫改」(Obamacare),也願表示部分認同其政策。
歐美關係在特朗普年代的重點,相信仍是後冷戰時期的三個層面︰
第一是兩大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協定。日前媒體已報導,總統奧巴馬放棄在任內向國會爭取,通過早前簽訂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這意味著國會已為未來特朗普年代的美國保護主義作準備。儘管相對於TPP,美國與歐盟商討中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簡稱TTIP),並未成為特朗普競選時的主要攻擊對象,但大西洋兩岸的媒體及政府成員,均對在未來幾年落實協議感到悲觀。
例如,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ECIPE)總裁 Hosuk-Lee Makiyama 指出,即使在小布殊及奧巴馬年代,往往要到第二個任期才著手處理國際貿易議題。因此他預估:特朗普上任後首兩年,TTIP 不會是要優先處理的問題。不過,正如歐洲執委會貿易事務專員Cecilia Malmstorm 提醒的,現時評估特朗普上場對 TTIP 的影響言之尚早。
其實,歐盟與加拿大簽訂《全面經濟及貿易協議》(CETA)也是一波三折,當中困局在於:現時歐盟沒有一個有效的法理框架,處理這類同時涉及歐盟(如國際貿易)與成員國政策範疇(如文化產業合作)的混合式自由貿易協議。現時歐盟要求,這種協議需要全體28個會員國一致授權,而如某些國家又需要來自地方授權,導致光是比利時瓦隆區左派政府的反對,就幾乎拉倒整個協議。這個例子足以顯示,歐盟與合其他國的談判進程的最大風險,還是在歐盟成員國自身的政權取態,而非其他國的政權更替。
歐洲軍事整合,與北約的命運
第二個層面是歐美軍事合作,以及應對東歐、中東及全球恐怖主義的問題。
對烏克蘭而言,特朗普在選戰期間的親俄姿態,與其對克里米亞問題的立場,自然是基輔政權的惡夢。不過從另一方面,美國媒體提供有關特朗普內閣的名單,國務卿熱門人選金里奇(Newt Gingrich)與烏克蘭的關係友好,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會支持對烏出售具殺傷力武器;美國國內烏克蘭社群對民主共和兩黨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正打算在下年初訪問華盛頓,希望了解特朗普對烏克蘭及克里米亞的政策。
美歐關係的另一個重點,是美國在北約的角色會否改變,以及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態度。特朗普在選戰期間,多次批評歐洲國家依賴北約,卻沒作出相對貢獻。他甚至揚言,今後考慮美國僅在有合理回報的情況下才保護歐洲──即便這本質上違反北約第五條有關「共同防衛」的原則。不過,奧巴馬在本周出訪雅典前的記者會提到:特朗普及美國均會維持北約,也將持續參與保障歐洲安全穩定的努力。
大家較少留意的是:本年4月奧巴馬接受《大西洋》(The Atlantic)訪問時也曾明言,不少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搭便車(free-riders);他也曾警告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要增加軍費開支,否則會影響英美「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奧巴馬在訪問中指出,他總統任期其中的一個政策方針,是鼓勵其他國家以自己的方式,捍衛自由世界及國際秩序,而非每每等待美國領導才作配合。由此觀之,特朗普不過是將奧巴馬的政策公諸於口──這亦是他的可愛之處。
與國際經貿問題一樣,歐盟在共同國防及外交政策上,內部問題遠比外部問題來得重要。《金融時報》日前提到,原本歐盟同德國想就特朗普問題召開緊急會議,但法國、英國及匈牙利均表不會出席,可見歐洲各國至今在對美國立場,仍沒有一致共識。
但樂觀地看,歐盟成員國的外長及國防部長在11月14號召開聯合會議,會後發表《歐盟安全及防禦戰略執行綱領》(Implementation Plan on Security and Defence),暗示歐洲軍事整合的方向。九月意大利國防部長 Roberta Pinotti 及外長 Paolo Gentiloni曾提出建立歐盟軍隊(EU Army)的構想。雖然在這次執行綱領尚未成型,但當最強的反對者英國早晚會脫歐,歐盟軍事整合似乎不再遙不可及。
一旦歐盟在軍事整合上取得成功,北約對歐盟的實質利益將大幅降低,考慮北約終結與否,關鍵其實是:歐洲國家是否仍願意為美國其他軍事行動負責。事實上,現時歐盟現在最應該擔心的是,假如特朗普真的要滿足他的競選承諾,即在不通知媒體甚至其他盟友的情況下,開展他的「100日消滅伊斯蘭國」計劃,歐盟國家是選擇共同參與戰爭,還是如伊拉克戰爭般各自為政?這種情境將直接挑戰歐盟內部團結。
歐洲的2017,比今年更精彩
最後,也是最諷刺的,是美歐雙方不同議題的差異下,衍生的身份認同政治。當面對著一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特朗普,歐盟如何提出具吸引力的條件,吸引他將美國資源「投資」到歐洲經濟及軍事安全之上。而當美國單方面行動時,如何善後其衍生的「界外效應」,將是歐盟未來4年要面對的外交問題。
特朗普越是冒進,歐盟政治精英愈有能力利用這個歐洲「他者」,來鞏固歐洲身份認同,打擊歐洲正冒起的右翼思潮,甚至促成以往視為不可能的政策合作。特別是當其唯一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文明體系的盟友英國已被邊緣化,法德核心或可將歐盟整合推到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達成真正的歐洲聯盟。
當然,這是假設來年5月及9月兩國不會換了一個疑歐派政客掌權。世事難料,對歐洲而言,2017年其實將比2016年更精彩,而問題核心從來不是特朗普上台與否,而是歐盟支持者是否能為自己爭一口氣。
(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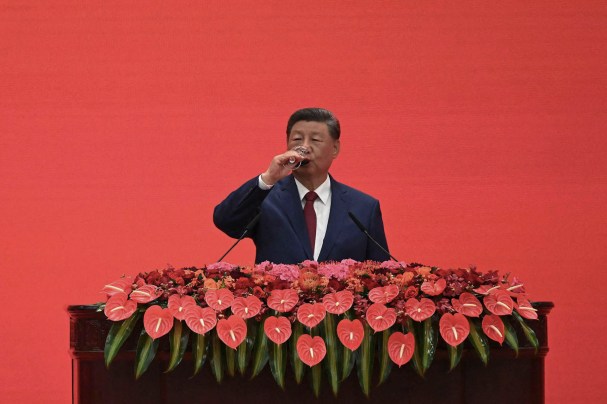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