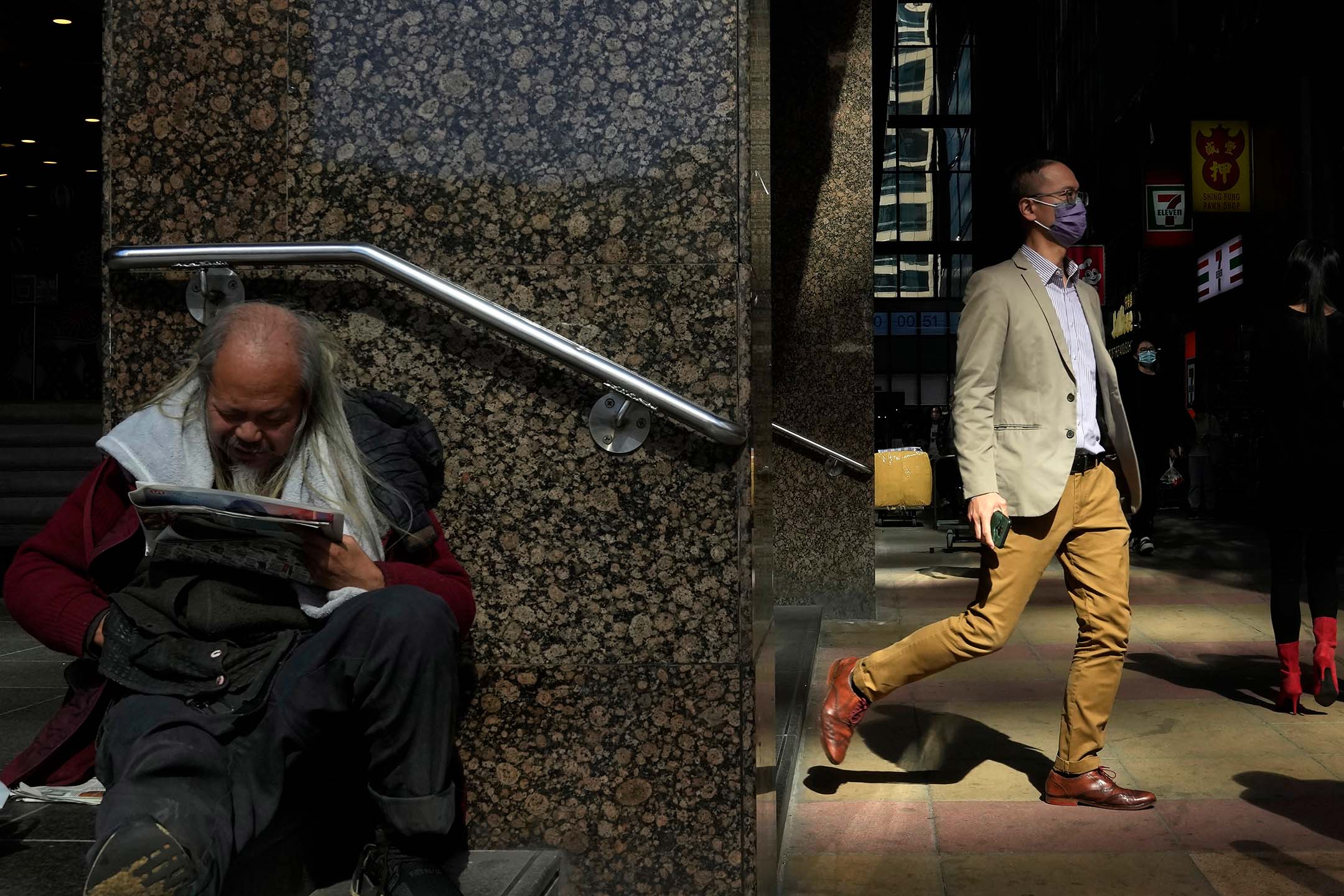我首先要為「香港文學館」正名:它不應該是商品,不應該有所謂「專利」和「盜用」的問題。事實上,當香港作家聯會(作聯)會長潘耀明近日「忽然」宣佈正式籌建「香港文學館」,更是迅速地擬在明年4月開幕時,整個香港文學界均大為錯愕、嘩然,正說明了一個關於「香港文學館」的歷史現實:
「香港文學館」由早不是一個抽象、空泛或言人人殊的概念,而是近十多年香港文學、香港文化乃至香港社會政治論述中,一個極為重要、豐沛且影響深遠的論題,我們早就有大量跟「香港文學館」相關的討論,涉及香港文學價值、視野、文化意義、文學展示和推廣的理念、實踐方式和可行性等等,不勝枚舉。但歸根結底,卻是一個關乎「文學公共性」的問題,而這亦是多年來倡議「香港文學館」的過程中被討論得最多、也說得最成熟的一脈。
本文不擬花筆墨重述有關論述脈絡,筆者只想簡單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在2009年因應香港西九文化區重啟公眾諮詢而成立的「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才是有關於「香港文學館」論述與倡議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起點。小組後來因西九管理局的冷待,而改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繼而成立「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以「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名義經營民間文學策展機構,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具認受性的文學機構之一。「端傳媒」於2016年的報導文章〈一場「無」中生「有」的文學抗爭: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故事〉已有非常詳盡的介絡,亦在此不贅。
「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多年實踐,恰恰應合了整個「香港文學館」論述的核心命題:文學具有公共性、文學應立足民間,而偏偏潘耀明所宣佈要成立的所謂「香港文學館」,卻全然背棄了上述的歷史脈絡。
這當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聯」「成功爭取」的成果,而是經歷三年多的政治洗清,政府跟親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攜地控制公共資源,而無需經過輿論的監察和公共論述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