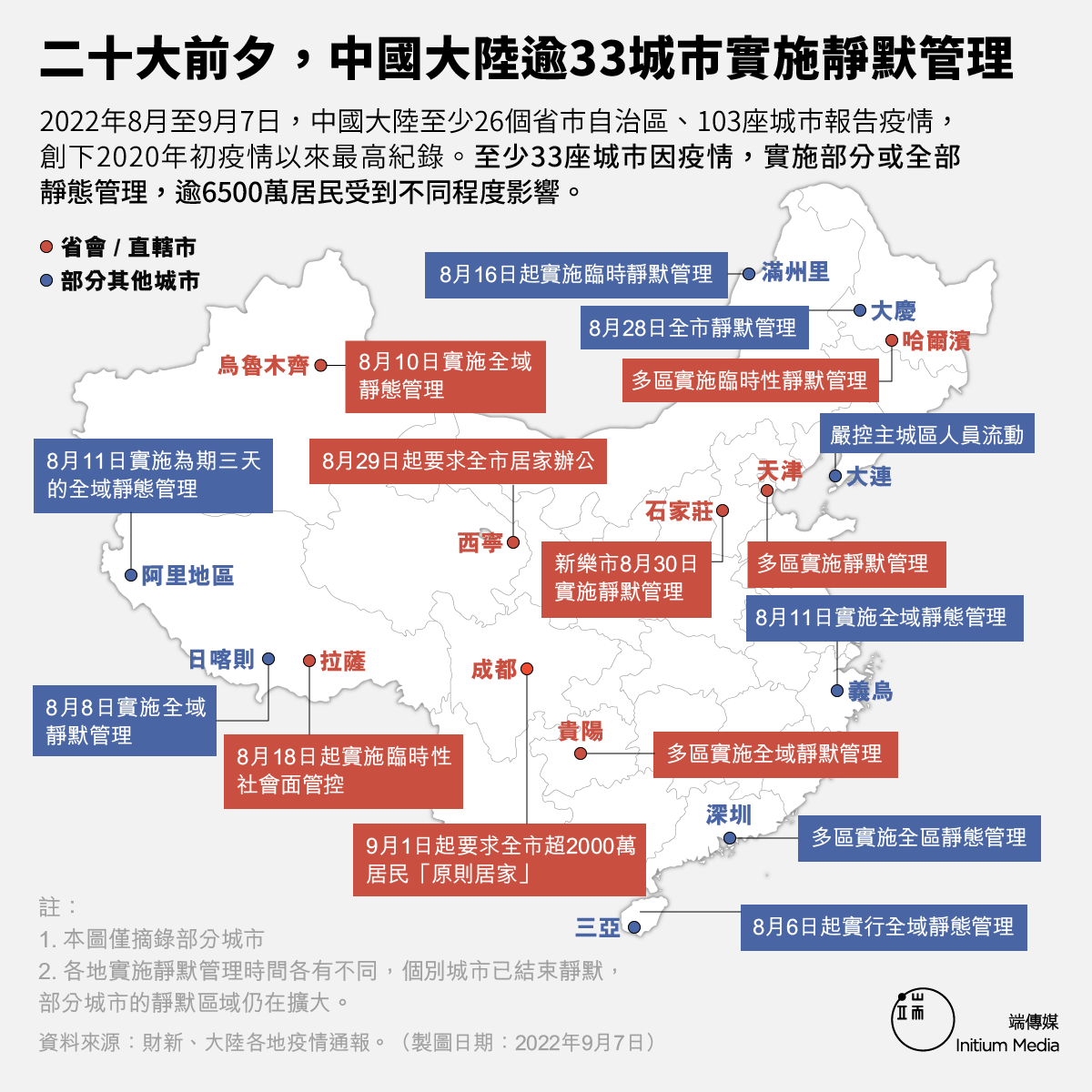【編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劇仍在重演。8月,三座熱門旅遊城市——海南三亞、新疆烏魯木齊、西藏拉薩——先後爆發疫情,並採取了不同程度的「軟封城」措施,曾僅見於一二線城市的核酸檢測點,兀然出現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隨後,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廣東深圳、貴州貴陽等數十個沿海和腹地城市。
誕生於疫情初期的「大白」,從居民歌頌感謝的對象,成爲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衝擊對象。「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自戕式的憤怒與決絕,並無力撼動當局清零的決心。從健康碼、行程碼到核酸常態化,面對致病性越來越弱的Covid-19病毒,爲鞏固虛幻的抗疫勝利敘事,中國政府正以犧牲經濟和民生的代價,將所有人拖入疲憊和荒誕。
劉力峰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奔赴戰場了。
這是劉力峰第一次摸到實體的白色防護服,一股新鮮感湧上身。不過,沒人教他穿配白色防護服的步驟,他盯着不遠處的醫護人員,一邊上網搜索注意事項,按部就班變身「大白」。他先在場地內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膠清潔雙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將身體裝進白衣,最後再套上一層手套、鞋套和護目鏡。在白色防護服內,一呼一吸都變得不同,面罩因水氣凝結起霧,讓人看不清手機屏幕。
2022年3月,上海捲起兇猛疫情,劉力峰作為一名選調生公務員,在年初剛被派到浦西(註:上海核心地段,廣義指黃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區域)駐村基層鍛鍊。穿上白色防護服後,他負責協助核酸採樣,掃描採集信息,日日與居民見面。有時,附近的居民會認出面罩後頭的劉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時候,是劉力峰認不出別人,「我像一個無情的掃碼機器,也懶得去看他們的臉。」
「大白」,誕生於2020年初爆發的疫情,彼時,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護服的防疫工作人員,也是白色防護服的代稱。由於全白、隔絕式的防護服鮮明、直觀,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線,民間和官方都不約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員。
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醫護人員會穿上大白。隨着防疫政策層層加碼,白色防護服內裝着的身分也變得多元:政府公務員、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警察、從社會招募的志願者、僱用的安保人員,都有可能成為「大白」。
一開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徵。人們對大白態度親切,抱有寄望,積極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嚴苛的防疫政策束縛逾兩年後,大白與市民的衝突愈發頻密地出現在公共視線中。有大白強行進入確診者家中消殺,往私人物品、傢俬和冰箱噴灑刺鼻的消毒液;在街頭,有寵物因主人被確診,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間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髮,以示懲戒⋯⋯
疫情覆蓋超過1000天,更多的人成為了大白,更多的權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