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資訊戰,多數人會自動與「假新聞」畫上等號。用虛假訊息混淆人心可能從人類有戰爭開始已經存在,假新聞也非全新的現象。然而社群工具的出現,卻讓資訊戰脫離過去所有我們了解的戰爭形式,成為可以精準到針對個人量身定做、打擊的奈米級武器,也徹底改變了這場戰爭的本質。
在大數據出現之前,操作者並不真的知道投放出去的訊息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能多有效,直到搜尋引擎和社群工具為了解人類的嚮往與慾望、如何形成價值取向和選擇意向這個暗房,點起了一盞高瓦數日光燈。
在這場戰爭中,敵人並不(只)是特定國家的政府,而是握有海量數據的科技巨頭,和任何能花得起錢去購買它們服務的人。理解這場戰爭如何直接在你腦海中開打,才能完整認識這場戰爭的性質、找到解方。
假客戶,真商品
廣告主面對的也不再是「三十歲經濟獨立的都會女性」這種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費者,而是這樣的帳號:「OOO,三十五歲、台北人、外商業務、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間、希望與伴侶各自財務獨立,寧可養寵物而不是小孩,未與父母同住,每週上健身房兩次。」
社群平台的服務幾乎都是免費的,使用者並不是他們的真正客戶,廣告主、劍橋分析、政治公關公司、政治人物競選總部才是,而我們,其實是被販賣的產品。社群界面裏每一個按鍵、每一個功能,不只串連著你的人際關係,成為你與工作夥伴、親友最重要的連絡方式,同時也扮演著改變慣性甚至想法的作用,包括將原本你並沒有的念頭灌輸給你。
臉書用戶已超過24億,等於中國與印度的人口總合,YouTube 的使用者超過10億,推特活躍用戶數超過一億,谷歌的 Gmail 活躍用戶數超過15億,還握有全世界最大搜索引擎,累積了22年人類意向的數據庫。這早已不是單純販賣你的個資(個人資料)給詐騙集團或是銀行業務,廣告主面對的也不再是「三十歲經濟獨立的都會女性」這種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費者,像臉書這樣的社群工具能透過收集到的數據,能明確找到這樣的帳號:「OOO,三十五歲、台北人、外商業務、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間、希望與伴侶各自財務獨立,寧可養寵物而不是小孩,未與父母同住,每週上健身房兩次。」
是的,你每天使用的社群工具,就是這麼了解你,Google地圖比你的主管更能掌握你的行蹤,Uber Eats 比你的伴侶更了解你的飲食喜好,臉書比你更知道自己是否口是心非。所有資訊,都是我們或自願、或毫無察覺時透露的。這些公司不只知道你是誰,還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甚至能進一步透過對你的理解,創造原本並不存在的「需求」、改變你的想法。
或許有人覺得跟所換得的便利相比,這麼一點小小的資訊交換根本微不足道,但當這些被運用在選舉上呢?運用在政治宣傳上呢?我們仍覺得無所謂嗎?這些「數據點」,遠比過去任何極權政府對人民的政治監控檔案更細微。
這使「溝通」一詞變得極其諷刺,因為任何在社群平台上進行的溝通,都難逃由演算法與出錢的廣告主共譜一場大型操弄的命運。我們或許有博士學位,或許是律師、醫生、核子工程師,會設計半導體,卻不一定知道身為一個人類的心理機制是如何運作的,而這正是這些科技巨頭得以掌握重大財富的關鍵:將所有說服、改變人類行為的心理知識,融入進他們的設計。

被偷走的選舉與民主
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早已超越「跨出同溫層」的呼籲,不是小心填寫個人隱私就能解決的。
從2016年起,已經有學者、獨立記者開始注意到這個現象。社群平台起初的目的是將人串連起來,然而面對「如何營利」這個問題時,幾間巨頭不約而同走向利用手中數據、透過設計來壟斷人的注意力的路線,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自願為其勞動、生產。
深諳人類心理機制的設計師們,透過操作著間歇性增強、從眾、渴望被認同等效應,讓我們無法自拔的深陷在滑動與各類通知中,誰家的 app 可以讓用戶停留的時間更長,也就越有商業價值,因此設計者努力讓你得到更多正向反饋、覺得被認同,你開心了,就會付出更多時間和注意力。以心理健康的觀點來說,這就是一種數位毒品。
劍橋分析的離職員工所曝光的文件指出,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數據來建立分析模型和演算法,將10,000種不同的廣告精準地投放到不同的族群當中。而臉書至少涉嫌洩露5000萬筆個資,且最晚2015年已知情,卻未採取任何補救措施,導致大西洋兩岸的兩場重要投票遭到了外力的不當介入。
劍橋分析在2016年歷經英、美國會的聽證會與司法調查後,已自行停業,臉書也在消息曝光、股價大跌後,保證會修改其隱私政策。然而根據英國《衛報》、《Channel 4》與美國《紐約時報》合作持續進行的調查報導指出,除了川普和脫歐陣營外,至少還有十幾個國家的政權和候選人,與劍橋分析有過接觸,曾試圖或已經購買過類似的服務,並且透過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數據,將大筆資金投入社群廣告,其中有陣營或政府涉及煽動暴力與種族迫害。在他們所列出的資訊地圖裏,台灣也赫然在列。當任何競選陣營透過購買這些數據,或委託社群平台進行透過數據分析的精準投放時,等於是在民主制度裏作弊。
除了川普和脫歐陣營外,至少還有十幾個國家的政權和候選人,與劍橋分析有過接觸,曾試圖或已經購買過類似的服務,並且透過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數據,將大筆資金投入社群廣告,其中有陣營或政府涉及煽動暴力與種族迫害。
即使科技巨頭們承諾改進隱私政策,也增加打擊、查核假新聞的力道,此刻卻少有國家的法規,能跟上新科技的發展趨勢。況且,當臉書開始禁止或要求政治文宣有一定透明度,有需求的人們就轉往難以追查來源的 Line,以及尚未有明確管制政策的 YouTube 平台上。因此,數據權是此刻最迫切需要被明確納入保障的基本人權,民主國家也需盡快補強與選舉相關的法律,強制科技巨頭們在設計與開發流程中,建立如同醫藥類實驗的倫理規章與監察機制,才能扭轉這場不對稱戰爭的局面。
但法令能防範的畢竟有限,只能還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抵抗基礎。社群平台誓言對抗假新聞的行動也不算順利,一來人工通報、查核,遠比不上透過既有人脈網絡往外擴散的速度,二來查核的基準也經常為人所詬病,甚至因為缺乏覆核和制衡機制,還可能演變成新型態的言論箝制,或激起更嚴重的對立,例如推特或臉書刪除特定立場的帳號和貼文。
對於公共討論裏那些「被傷害的情感」和仇恨,我們甚至必須追問這些情緒是如何產生的?是屬於自己內在的,還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確實存在,卻被更挑起放大,到我們不願也無法跟差異者共存的地步?
因此,在法律未竟之處,需要更多人願意透過不斷練習,去察覺、破解這些操弄手段,彼此提醒,讓公共性與公民社會重新成為可能,包括直視那些最困難的提問、辨識自己在其中的反應,是基於政治理念與原則的辯論,還是「被傷害的情感」。這並非否定情緒在公共領域出現的資格,但情緒不會自動讓你的主張有正當性。我們甚至必須追問這些情緒是如何產生的?是屬於自己內在的,還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確實存在,卻被更挑起放大,到我們不願也無法跟差異者共存的地步?

台灣公共討論的毀滅
新興的各方意見領袖們,或許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卻早就從經驗中體會到越是簡化二分、激烈指責、選邊表態的言論,特別是讀完能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憤的圖文,就能獲得越多的按讚、轉發。
我們由此進入另一個階段:認清這場戰爭完全不對稱的本質,和它發生的場域。當演算法打造了無數分裂版本的「真實」,原本已經因為大眾媒體各擁立場的資訊轟炸而瀕臨崩潰的公共討論,和民主社會仰賴的不同社群相互理解、協商的公共性,直接被這場土石流沖毀。
過去,我們尚能抓住事實作為辯論基礎,例如氣候變遷的傷害是真實存在的,但各方對於是否改變生活方式(茹素、少用油與電)、限制碳排放與開發綠能各自的比重之間有不同看法。然而,現在我們卻要爭吵「氣候變遷只是自由派傷害經濟發展的陰謀」。當我們因此而失去辨識事實的能力,甚至否定事實的存在,「公共」也不復存在。
新興的各方意見領袖們,或許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卻早就從經驗中體會到越是簡化二分、激烈指責、選邊表態的言論,特別是讀完能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憤的圖文,就能獲得越多的按讚、轉發,看到他們的成功經驗,不少政治人物和議題性粉專也紛紛跟進,忘卻身為民選政治人物或被任命政務官的責任,開心當起帶風向的旗手,為自己「社群行銷」成功而沾沾自喜。
一旦情緒被挑起,特別是在恐懼和憤怒這兩種情緒下,多數人已沒有心理的餘裕,不論是去看見他者的苦難,或是思考恐懼的成因。在進入媒體識讀之前,我們需要搞清楚自己為什麼憤怒、為什麼恐懼,而在這種憤怒與恐懼中,我們放棄了哪些,忘記了哪些,否定了哪些,又為什麼改變了想法。
我不同意將這股底層的情緒簡化為狹義的國族主義,但我們確實必須正視這股集體的情緒,這情緒已在我們的公共討論中蔓延許久
舉一個近期在台灣極具爭議的例子:公視晚間新聞製作了一則有關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內容是中共官媒拍了一部記錄片試圖改變外界對此事的看法,也轉述了美國國會和相關人權組織對其的批判。官方粉絲頁在分享這則新聞的文字稿時(有附該則新聞完整影片),僅截取了一段文中中共官方對外宣稱的說詞,並未加註譴責字眼,此舉引來網友的誤讀,並在相關社群傳開,公視粉專瞬間被洗版,也有KOL下場參戰,指責公視的報導手法,是「在邪惡納粹政權面前假中立」。
批評公視的論點大約可歸納為三個面向:一、新聞標題讓人以為是在為中共宣傳;二、公視接受大筆政府補助,怎可播放敵對國家為慘無人道的種族迫害行為洗白的記錄片;三、內文只有並陳雙方說法,沒有批判中共,是假中立,有違媒體道德。
事實是,公視的新聞下標使用「官媒」、「續宣揚」已清楚點出批判中共的立場。公視也僅於該則新聞使用一小段記錄片畫面,不足一分鐘,事發數天之後,卻仍有不斷湧入的留言指稱公視播放「整部」影片。而第三點看似有理,卻搞錯了「呈現報導」和倡議報導或評論的差異,前者是敘述「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後者是「我們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記者在此篇用字譴詞的細微差異,也顯示「並陳」不等於沒有立場,不等於「平衡報導」,且長期且揭露新疆集中營慘況,只要往前翻幾則報導,立刻都能知道。
唯一可稱為瑕疵的,是公視小編的政治敏感度不足,但讀者的誤讀,並不是該篇記者或公視這個製作單位的錯,讀者「不讀」就亂批,更不是公視的責任,但這個應被指正的風氣,在這波爭吵中反而被「正當化」了。
數日後,中央社製作了一則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線上演說內容的報導,全篇完全只有摘述講稿內容,並無任何「平衡、譴責」,但前幾天指責公視的KOL們都安安靜靜的,義憤填譍的網民們也都不見了。如果他們前幾日所主張的「媒體倫理」為真,為何中央社不必被質疑是為帝國主義喉舌,而公視新聞就是在為極權政府「洗白」?
立法委員王定宇譴責公視的貼文:「不願幫台灣做國際宣傳、卻為中國央視做大外宣」,具象的呈現了整個事件裡情緒蓋過事實、迫使理性讓位的根源:網民真正不滿的不是新聞該怎麼報,而是兩個月前,公視董事會拒絕文化部以專案委託執行方式,扮演國際宣傳一事。在台灣急切向世界宣傳防疫成績與民主成果的此刻,此派憂慮公視因此失去公共性的意見,無疑觸了主流民意的逆鱗:「身為靠納稅人(拿我的錢)製作節目、發薪水的公視,拒絕為台灣宣傳這麼光榮的任務,本來就欠修理,還跑去報導中國央視拍記錄片的事?」這才是公視事件炎上的主因,也是這些粉專、KOL、網民們可以如此雙標、濫用新聞倫理詞彙的原因。
我不同意將這股底層的情緒簡化為狹義的國族主義,但我們確實必須正視這股集體的情緒,這情緒已在我們的公共討論中蔓延許久,並從兩年前民進黨地方選舉敗選後急速惡化,「韓流」所造成的恐懼、普遍籠罩的「亡國感」,在總統大選裏因抗中激情而更加匯聚,然而在台灣社會裡涌動的這股情緒,並為隨大選落幕而逐漸遞減,反而因為疫情更增添了人們對中國的憤怒,而來到新的高鋒。

屬於台灣的特殊性:亞細亞孤兒那受傷的情感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團結、結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權」很容易被工具化,當它可以用來區隔對手或敵人時,就樂於擁抱所有進步的修詞,當觸碰到我們的情感邊界時,還對理念的堅持就被劃入「危及生存、不切實際、不顧國家安全、要害死我們」那一邊了。
除了個體去正視、覺察自己的情緒來源外,我們也必須正視如今盤據在台灣集體意識中的情緒。這是屬於台灣的特殊性,身為亞細亞孤兒那受傷的情感。我們在一個又一個殖民政權中跌跌撞撞,在被人壓迫、也壓迫他人(原住民族、族群械鬥)的歷程裏,逐漸形成了一個「台灣人認同」、艱難的完成了民主轉型。然而一切並未隨之幸福又美好,我們仍活在中國威脅下,惶惶度日。這個「台灣人認同」,與其說是被什麼號召,不如說是透過一個又一個共同敵人(日本、威權、中國),透過「討厭什麼、不要什麼」而形塑出來。
即使不談歷史,在缺乏共同宗教指引,家庭、婚姻和任何社會關係都不斷變動的現世,投向一個身份認同(例如女人、同志、客家人),確認一份「共同體」(台灣人)的關係,特別是在全球經濟秩序重組、外有疫情與中國威脅之下,選擇成為「我們」,於一份被主流認可的認同中尋求安全感,似乎成了最當然、也最理性的選擇。
然而,當公共討論裏的風氣從渴望找到「我們」,渴望表達「我們是一樣的」,漸漸擴張成為「指責那些不一樣的人」,甚至演變成「他們竟然敢不一樣」、「那些不一樣的人會害死我們」的時候,我們與可怕的國族主義之間,就不存在那麼遙遠的距離了。
社群時代,更多人學會了的是如何用看似理性的語言,來包裝自己情感先行的選擇。情感先行、直覺先行不一定是錯的,甚至它是人類之所以能在演化中存活勝出的關鍵,然而當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體,就有必要理解並意識到自己是用什麼在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團結、結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權」很容易被工具化,當它可以用來區隔對手或敵人時,就樂於擁抱所有進步的修詞,以表示「我們不一樣」,然而當實踐它或回應它本質性的需求,觸碰到我們的情感邊界時,還對理念的堅持就被劃入「危及生存、不切實際、不顧國家安全、要害死我們」那一邊了。
我們要把公共性,建立於何種根基?
數月前在台灣社群廣為流傳的報呱網站專文《德國研究中心分析:為何台灣防疫經驗不易複製》,幾乎一眼就能辨識出這是有問題的內容農場文,然而在「台灣之光」的光榮感加持下,難以計數的言論領袖、知識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學者,都轉貼了該文。
很多人並非真的不知道是非或自身的雙標,但情緒先行、選擇立場以後,「媒體識讀」的技巧,只會被工具性使用。以數月前在台灣社群廣為流傳的報呱網站專文《德國研究中心分析:為何台灣防疫經驗不易複製》為例,幾乎一眼就能辨識出這是有問題的內容農場文,然而在「台灣之光」的光榮感加持下,難以計數的言論領袖、知識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學者,都轉貼了該文。
當疫情喚起台灣人在SARS中被世界孤立、放棄的絕望感,被中共打壓的憤怒、對大型傳染疾病爆發的恐懼疊加爆發,台灣人空前的團結,但公共討論的健康度也來到近幾年的最低點。
自今年一月以來,關於引入數位監控、透過手機定位找出感染者行動軌跡、將健保資料庫對接口罩實名制系統、禁止特定職業離境等措施,是否有侵害人權疑慮、有足夠法律授權的討論,都成了公共輿論中的「敏感詞」,就算想善意提醒、建言者,開口前也必須以「政府做很棒、支持防疫原則以保護台灣人優先」當起手式。
台灣人空前的團結,但公共討論的健康度也來到近幾年的最低點。
正因為對中國長年的不信任,台灣提早應對一切,成為疫情中少數正常運作的國家。然而,很多人在自豪於這份如先見之明的同時,也將情緒轉移到個體的中國人身上。九個月來,在台灣的中生、中配、中配的孩子們,不論他們個人政治或國族認同為何,都集體承受著這股不被信任、不受歡迎的情緒,甚至被認為「那就是他們身為中國人活該承受的」。而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言論鋪天蓋地的程度,連新住民社群都深感恐懼,畢竟他們也屬於隨時可能被質疑的群體。
在中國輿論界為方方出版封城日記陷入混戰,甚至有人稱其是「為西方帝國主義遞刀」時,台灣的社群討論裏,也有許多人被類似地質疑。提問政府為 COVID-19 提出的特別條例第7條是否真有那麼大法律授權的人,被指責為人權膠、不顧台灣人生命安全,即使多年來都站在第一線對抗威權、一直是民進黨最佳盟友的學者和公民團體,只要認真討論對是否包機接台商回國,以及中配及「小明們」入境資格,也都必須承受巨大的網路言論暴力。
那段時間裏,恐怕我們討論的並不是公民或居留資格該怎麼認定,也不是如何維持防疫成果,而是比賽著誰比較恨、誰比較討厭中國人。如果我們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這裏應該辯論的是資格,而不是他們的言行與內心認同「配不配」。在這一題,顯然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認為既然中國流氓,我們也能理所當然的拒絕辯論與承擔。

相似的情緒也展現在近來對待香港政治難民的態度上,不少人堅信越嚴格、名額越少越好,免得中國派間諜假裝政治犯混進台灣,社群風向普遍也覺得香港的前途必須靠港人自己努力,台灣並不欠他們什麼。我們好像忘記了,就算沒有反送中運動逆轉民進黨一度低迷的選情,台商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第一批大舉登陸、幫中國賺進第一桶金、走向大國崛起的功臣之一,賺到人民幣的,並不是只有藍營支持者。
除了譴責民間人士的救援「沒有現實感」外,KOL們宣稱「救援標準不宜明確化、規模太大有違國家安全」究竟有沒有事實基礎?在港澳條例框架下,什麼是台灣所能做到最大程度的救援?我們有否打算藉此向國際展現作為民主陣營最佳盟友,台灣不只能輸出防疫經驗,同時也懂得承擔國際責任,而不是只想把香港難民送往歐盟、北美?
我們或許沒有餘裕去支持、去為他們發聲,但台灣的委屈和苦難,並沒有給我們貶抑、輕視他人所受壓迫、還為自身政治利益將其正當化的權利。
台灣人的情緒近來甚至外溢到BLM運動上,認為這是在扯「最挺台灣的總統川普」的後腿。我們可以對BLM中個別失控的暴力表達不認同,甚至確實可能有中、俄勢力在其中試圖激化運動,但這並不改變BLM運動的本質,是嚴重的種族歧視、司法、社會、經濟的長年不公。你個人可以期待川普當選,可以去向有投票權的美國朋友拉票,但不該加入那些種族歧視陣營的論調,認為黑人就是暴力、活該。
我們或許沒有餘裕去支持、去為他們發聲,但台灣的委屈和苦難,並沒有給我們貶抑、輕視他人所受壓迫、還為自身政治利益將其正當化的權利。
回顧過去兩年,正因中國威脅的陰影面積實在太大,於是我們先對內自我審查了起來;DPP的支持者,甚至民代、幕僚開始戲稱自己為「沙包黨」,認為選民什麼都要找他們負責、要求他們做好,是不公平的,即使多數公民團體在民進黨執政時抗爭力道已經非常客氣,甚至是多所期許的態度,還是會被稱為「中共同路人」,意思是「就算沒有直接與中國勾結,但你們的批評與反對會造成同樣的結果」。
梳理這種大家都不想面對、不想承認的情緒,是很不討喜,但卻也是此刻很必要的過程。學者 Bernard Yack 曾在《沒有幻想的自由主義》一書中,改寫霍布斯的話:「民族主義是討人嫌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則是討人喜歡的民族主義」。除了修辭和程度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其最後的結果,並沒有那麼天差地遠。
不論是愛國(國族)主義還是民族主義,信仰的都是「我們」的信條,意思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只是民族主義是丟掉鑰匙、封上大門,只有已經在裏面並被認可的人才能擁有相關權利,愛國(國族)主義在表面上看似比較包容,更懂得怎麼使用包容、多元的語言,但卻把責任丟給那些要求要被接受成為「我們」的人:是「你們」要向「我們」要證明自己。
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不是透過上述兩者的教條、資格的設定來建立的,只能透過生活裏彼此尊重、互助、協商而來。此刻,我們會選擇將這個國家建立在哪一種根基上呢?
究其根本,兩者都不接受人們珍惜、保持、甚至發展出更多差異卻仍就彼此相屬,不相信人可以無感、淡然、不憎恨敵人卻仍願利益與共。然而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不是透過上述兩者的教條、資格的設定來建立的,只能透過生活裏彼此尊重、互助、協商而來。台灣人渴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已近百年,此刻,恐怕也是我們終於能遠望到終點的開端。我們會選擇將這個國家建立在哪一種根基上呢?
(喬瑟芬,基督徒性別運動者,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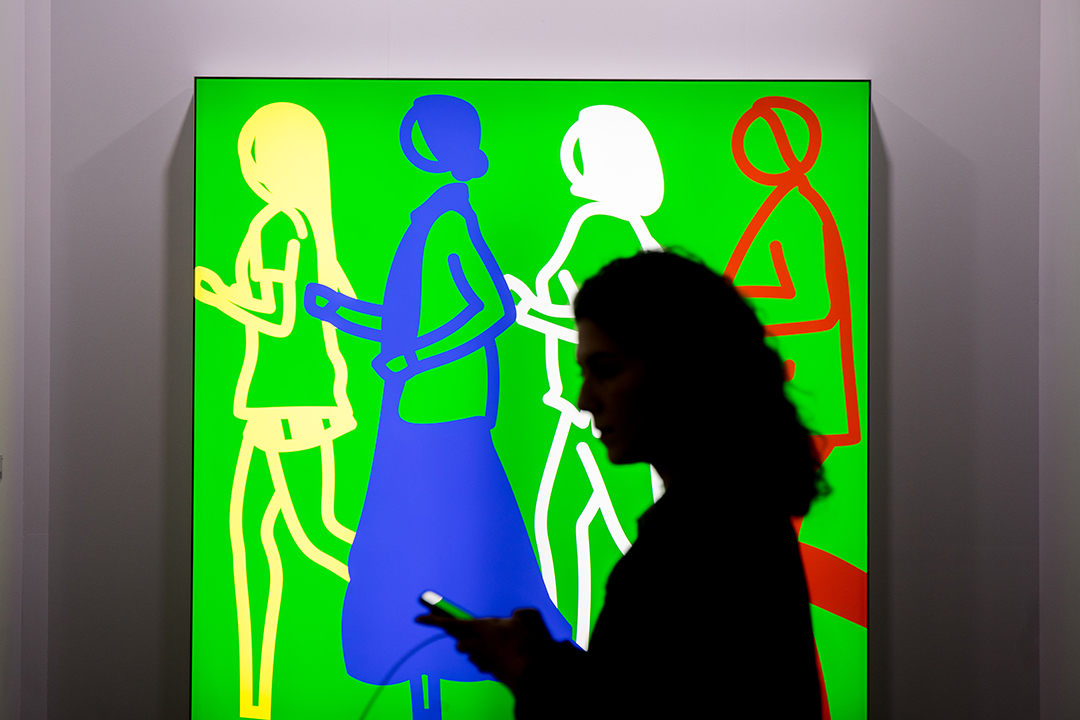




謝謝端傳媒,謝謝喬瑟芬
「XX未幫過我們,我們也不該幫他們」這真是我近期最常看到的滑坡。請問我何時說過或認為不該幫助不該支援香港抗爭民眾了呢?!
對於自由膠跟左膠來說,或許民間的自發行動都不是行動都不是支持吧。一定必須是連可能接近半數港人都不支持的台獨/華國政府官方發起的支援行動才是真的在挺香港。至於會觸發多少兩岸衝突、敵對、挑釁,以及全面戰爭的風險,我就想問,你們這群自由左膠在意過嗎?
所以就如我先前說的,對各位來說,民間的支持力量你們根本就都不放在眼裡啊。
講句難聽的,在台灣的人權機構大聲疾呼,喊著要台灣中央政府通過難民法的同時,你各位香港人哪,你們甚麼時候出來大聲疾呼也要你們的特區政府好好實施難民法好好受理難民申請了?各位不是最支持人權跟政治庇護這種冠冕堂皇的說詞了嗎?
附上Wiki對香港難民申請機制的說明,希望自由膠跟左膠們好好閱讀、好好思考:在國際政治以及地緣政治的框架下,台灣官方到底哪裡來的力量跟政治利益可以作為單方面實施對香港政治難民認定的依據。
"保安局表示,聯合國《難民公約》從來未曾適用於香港,現時在香港因各種理由提出免遣返聲請要求不被遣返的非法入境者或逾期逗留人士,無論其聲請的結果如何,他們都不會被視為難民。即使他們的聲請獲得確立,他們亦不會在香港享有合法居留的權利。聲請被拒絕的人,必須盡快被遣返至原居地[2]。
至2018年3月,尚未完成的酷刑聲請個案還有4,420宗,同時已有16,977宗酷刑聲請個案完成審核,其中獲確立酷刑聲請的有120宗,可見不足1%的個案能符合酷刑聲請資格[3]。"
文中台灣民間的輿論和人民的情緒/立場
跟香港反送中運動一年多演化出的很相似
而這其實又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無關係
在資本/資訊爆棚,algo橫行的世界
人們(或說是人性吧)要繼續互相提醒
喜歡這篇文章。有時候都不知道側翼是不是真的側翼還是中共同路人,帶領風向發表一些有違很基本價值的言論。我認為台灣人現在不管在內部(韓流的後續、民進黨穩定取得多數且防疫成績優良、國民黨主流路線趨向統一、新住民、第三勢力的崛起與轉化)、外部(中國對香港、新疆、西藏、蒙古政策收緊、共機頻頻擾台、中美之戰等等)都面臨前所未見的改變。在輿論場上大家需要一邊重新辨認你我、釐清彼此所有可能的情感或身分認同、另一邊卻必須思考所謂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價值,會不會為台灣帶來威脅、有沒有讓共產檔滲透的空間(看看台灣的媒體政治經濟)。這段時間可能言論會激進化,但希望激進之後,群眾中還是不乏理性之人重新帶回健康的輿論風向。
說得太好,謝謝作者。作為一直有follow台灣不少知識份子/學者的香港人,近一兩年確實愈來愈感受到,很多人明明已經有了權力,卻仍然在受害者的身份裡過得安然,還永遠好像在經歷存在危機那樣--好像沒有太多對現狀,對權力的反思。很感謝作者寫出來了。在港台兩地都有對BLM運動的質疑和惡質批評,還有對川普的盲目崇拜,確實我們都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貼小白左標籤看來是鬥爭的第一步。想強調限縮人權與民主發展,支持鬥爭才是解決之道,不必舉例英美,自古以來的改朝換代,大小混戰華人打得還少嗎?各種假民族復興或窮苦人翻身之名,獨裁局面結束了嗎?鼓吹台灣人毀壞民主基石,浪費精力時間去鬥爭那些煙霧彈跟紙偶,好給共產黨更多空間與話語權去操控局面?打這什麼算盤。這種落後狹隘鬥爭思想就是毛與習以人民為矛盾的手段。拿幾百年前英美戰爭為例,試問人類的智識、人權概念、訊息傳遞科技、文化、軍事發展已日新月異的如今,何必師法舊觀念?以小國來說,不認為台灣有時間餘裕與國際空間走錯路。
「共同体的边界是共同体存在的先觉条件」邊界可以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民粹主義,一旦共同體惡質化便失去存在的價值,留人話柄,使人輕視,與現在的共產黨無異。統一在台灣幾乎沒有市場,主因是我們看到了兩種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的不同。共產黨繼續集權,台灣堅定發展民主,差距會愈拉愈大,邊界便明顯清楚;反之,仿效共產黨,鼓勵民粹,審查思想,縮小兩者之間差距,邊界便不存在,那麼統獨將不再是問題。
小白左同志还是搞不清楚共同体的边界是共同体存在的先觉条件。台湾的一切统独斗争,乃是国本斗争,而不是民主共同体内的人权进步竞技。如果英美在英国内战、美国内战都要像台湾一样分不清敌我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英国和美国了。
確實一直以來香港不曾為台灣做什麼,甚至更多是譏嘲與冷眼;然而若要把(最近也被瘋狂出征罵左膠的)民間團體的協助嫁接到公部門承諾施行的政策上,未免也太好意思。
倘若主張「XX未幫過我們,我們也不該幫他們」,何不省下各種國安問題的詭辯藉口,正大光明對國際社會坦承不打算幫助香港的立場,誠實地撕毀兩公約施行法和人權國家的道德光環,敢作敢當之外還可以避免表錯情的流亡者與陸配親屬前來。
同樣邏輯,向來對各國基於對人權與民主的支持應捨棄對中利益挺台的倡議也可免了,台灣人跑去主張孤立主義真的是我見過最蠢的事之一。
感謝這篇文章。Refreshing。
有人質疑作者抄襲,但Netflix 記錄片也不是全然原創的,大量引用別人的概念與調查結果。例如 Shoshanna Zuboff 創造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一詞。中譯本剛上市。
刀口向内,值得尊敬。
這篇文章的前部分內容跟Netflix的影片「願者上網」是如此的相似,是否有抄襲的嫌疑呢?
作為香港人,聽你提出「請問香港官方為臺灣做過什麼、在國際上為臺灣發聲過嗎?」,還真想爆粗。
明明香港人本身就厭惡香港政府,就係因香港政府逼害,才成為香港才有政治難民,你說成香港政府代表香港人....
台灣是無義務接受香港政治難民,是事實。但香港墮落到有政治難民,香港人不傷心嗎?有選擇誰會做政治難民?希望有一個公開準則關於如何處理難民,不過份吧?
這是一篇必須和及時的好文章。
在講這種話之前,請問香港官方為臺灣做過什麼、在國際上為臺灣發聲過嗎?
如果沒有,憑什麼講得好像是臺灣官方欠港人什麼?
此外,民間自發的協助難道就不是協助嗎?
那之前的物資、防毒面具、甚至人力跨海支援到底算是什麼?
別說的好像如果台海發生戰爭,香港官方就會大大方方的開放接收臺灣難民好嗎?
還是對左膠來說,國際政治就都該是大家比誰人品更好,沒有半點阿諛我詐跟利益交換?
別鬧了好嗎。
好文,我的想法是扭曲的舆论是因为心中的不忿和对一切的怀疑,近年来,感觉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偏激,戾气越来越大. 我想症结有三,
第一 ,大家对各种价值观都有了一定质疑,社交媒体的存在让道德和普世价值的标准因为部分人双标而被质疑,同时太多的人因为做坏事获利,因此他人的卑劣让自己获得了下作的理由.
第二,因为无底线的媒体和社群的恶意剪辑和无中生有,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任何事物保持怀疑论,这样的人普遍喜欢阴阳怪气,起手式就是批评而不是肯定. 对任何肯定的人质疑其身份,立场.
第三,就是对不公的不忿,世界政治流行以强凌弱,美国欺负大陆,大陆就欺负台湾,台湾就欺负陆配小明,强者欺负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
感謝此文作者,提出現在臺灣內部被扭曲的公共議題討論環境。
在對抗中共大外宣的時候,民主臺灣的反制不應該是大內宣和那些與小粉紅無異的對異見標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