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我們摯愛的人類學家和無政府主義夥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終年59歲。這樣的年紀,以思想家來說,死得有點太早;以行動者來說,死得有點晚。儘管我未有機會和 Graeber 碰面,但對我這樣一名人類學學生和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行動者來說, Graeber 的理論與實踐一直是重要且罕見的思想及行動資源。不論 Graeber 走得是早還是晚——都是可惜和難過。
作為人類學生:在佔中時讀《為什麼上街頭》
本著「We Are The 99%」(佔領華爾街口號,Graeber也參與了這口號的創作之中)的精神,重新「佔領一切」,其實是一種最直接的行動,去奪回本來屬於99%的社會,然後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無政府主義感召的NGO組織者、人類學畢業生及運動者。在香港佔中運動爆發的時候,我和同學無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觀地想:到底人類學的知識和方法,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去理解運動?在佔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情況下,在香港NGO界及社運力量被壓抑、消耗而渴望爆發的那個當下,怎樣使得「佔領」這種運動模式發揮它最大的潛力,而不只是一次動員力的展演?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味道濃厚的論述,可否為香港帶來什麼啟示?而人類學,是否能提供什麼答案?
順著這些思路,我們很快找到了 David Graeber 的思想,那是2014年,從接觸時間來說,不算走在「潮流」尖端,但自此他對我的影響很直接。因為 Graeber 剛好踩在運動和人類學兩條線上,並跟我們一樣,希望在知識的行動及行動的知識中,改變我們覺得具壓迫性的文化、社會、國家及經濟結構。只是, Graeber 對我來說更具備另一層意義——他是無政府主義革命路上的小夥伴。
人類學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互相契合,似乎是順理成章的。首先,是因為人類學的學院氛圍一直都有一種開放性:既然人類學在面對復活島石像、亞馬遜獵頭族、薩比亞部落的口爆成人禮等「千奇百怪」的文化行為時,都可以深刻共情並冷靜理解,那麼被當今普遍的社會大眾認為是不可思議、甚至是瘋狂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在人類學所遇到的其他研究面前,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第二,人類學中大量的考古學資源和對部落文明的研究都指出,以「現代國家」為單位的世界秩序並非古今如此,而在現代國家遍佈全球的當下,還是有許多不服從於國家和資本主義秩序的社會及文化秩序存在。在人們大量研讀這些案例的時候,無法不一次次地敲問資本主義、國家主義、以至於現代性的正當性及必然性,這都使得人類學多多少少有一種原始無政府主義(primitive anarchism)的氣氛。
但與此同時,人類學卻並沒有指出任何的「道路」去抵達另一種社會秩序。我們對原始文化似乎只能是崇敬、「懷舊」,但卻無法從中讀出任何的指引。於是問題變成,對被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印刻的「現代」人來說,這些社會及文化可以有什麼參考價值?如何參考?參考的基準在哪裏?
當「訴求」不過是繼續承認著國家及資本主義的霸權以及暴力、當「訴求」的過程必然地會產生出某種身分政治並排除了某些人的參與時,更直接的作法就是「不再訴求」。
一個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模糊地尋找答案的人類學學生,譬如我,當年是抱著這些基礎去接觸 Graeber 的思想——從《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開始。這是一本平易近人的橫向民主組織攻略,它沒有直接回應我那些糾纏在一起的人類學思想與運動發想,而是提供了一堆實際的彈藥:「行動!不只是追求民主!也要民主地行動起來!」、「民主的內核不是投票!」、「民主是一種基於平等的信念,允許人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並且去集體決定事務」。Graeber 以運動參與者的角度,分享了行動中取得共識的操作原則,以及如何在資本主義及國家霸權中,創造一個「平行時空」般的公共空間,建立起平等的自治生活。
這本書至少解答了我和朋友心中的第一條問題:佔領不只是「公民不服從」或坐在那裏等警察來抓,「佔領」就如同「拒絕工作」(但這並不等於罷工,罷工經常性是為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或工資,抵抗工作是為了完全取消工作為主導的關係)、直接民主及推動共識過程等,均為不同程度的「直接行動」;重點不在於公民不服從或抗議,而是「不理會國家」,使得國家自行失效。
如此,我們反過來讀懂了加州的佔領行動,讀懂了為何會有「Demand Nothing, Occupy Everything」(不再訴求,佔領一切)這句口號。因為當「訴求」不過是繼續承認著國家及資本主義的霸權以及暴力、當「訴求」的過程必然地會產生出某種身分政治並排除了某些人的參與時,更直接的作法就是「不再訴求」;而人們首先被佔領了,幾乎被國家及資本主義佔領了一切,使得資本有系統地流向1%的人口,而那無權無勢的99%必須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大眾。本著「We Are The 99%」(佔領華爾街口號,Graeber也參與了這口號的創作之中)的精神,重新「佔領一切」,其實是一種最直接的行動,去奪回本來屬於99%的社會,然後另立秩序。

但接下來,或許你也可想而知:帶著這種對佔領、直接行動、群眾大會、共識機制等渴望,參與到2014年的佔中運動中的我們,到最後感到了多少困惑和失望:我們該如何面對非以群眾大會所產生的金鐘大台?該如何面對不願意乖乖坐著等被抓的蒙面行動者,在用行動打破了「佔領=公民不服從」框架後,被謾罵是「鬼」(有意把事情搞砸的人)、是亂衝?該如何回應之後的「捉鬼潮」及「捉左膠潮」(後來演變成所謂的左膠vs本土勇武派的紛爭)?然後,在群眾撕裂中,我們這群既是「左」,也鼓勵直接行動的人,被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如何「佔領一切」?
但這些不是 Graeber 那個脈絡下可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只能盲目地摸著石頭過河,盲目地「幹下去」。
2014年的佔中運動以後,我與許多運動的朋友一樣,有不同程度的社運創傷。於此同時,我也開始懷疑 Graeber、懷疑99%的精神,也懷疑佔領的實踐是否過分溫和。佔領與黑人暴動中的打砸搶(looting)可否結合起來,成為一條更武裝的運動道路(這種想法其實是我對當時「捉鬼潮」的反撲)?有很多個夜晚,我都覺得我在和心裏的 Graeber 吵架。那本《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最終被我不知道丟到哪裏去了。
作為無政府主義者:讀《債的歷史》、《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
如果說,Graeber 這種對債務神話的拆解,仍來自於人類學火藥庫裏各種債的文化概念,使他能去敲問當今的債的文化的正當性,那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就是他更明確、直接地整理出人類學的基進性和改革社會的潛力。
之後有幾年,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 David Graeber 的書。我是到了2016年才有機會靜下心來看他的《債的歷史》與《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看畢,一方面意識到自己之前臆想 Graeber 可以如同神召問米般去回應自己的求問,是一種不負責任及去脈絡化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卻也覺得有某些關於人類學與運動結合的問題,被 Graeber 解開了。
畢竟 Graeber 的專長就是價值理論及人類學,《債的歷史》以經濟人類學的角度,把過去數百年間資本主義形成的一些經濟學理論,放置在更久遠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嘗試論證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一些社會組織或交換模式的合法性或啟發性。
《債的歷史》開宗明義就說要破除經濟學家塑造的神話,也要破除「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概念。這個神話是這樣說的:「從前,原始人以物易物,後來為了方便交易,發明了貨幣,繼而發展出銀行和信用⋯⋯然後開始有『債』的概念——我們變成了現代人。」
Graeber 有不同意見,他說:早在貨幣出現前,人類就已經有債的概念;而信用的本質就是「債」。他指出所謂的「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是一種被資本主義塑造出來的文化概念,去維穩當今的經濟制度;同時這是一套雙重標準:當我們要求個人及小國立刻還債的同時,世界上有一些「債」(譬如美國的公債)是從來不需要還的。一方面向他人借貸(發公債),另一方面生產欠債文化,像底層問債卻不向上討伐,導致了眾多社會問題及戰爭。
如果說,Graeber 這種對債務神話的拆解,仍來自於是人類學火藥庫裏各種債的文化概念,使他能去敲問當今的債的文化的正當性,那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就是他更明確、直接地整理出人類學的基進性和改革社會的潛力。
這是《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的問題意識:若我們想實現一個由人民自治的世界,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理論呢?他就此提出,「無政府主義」就是那個「社會理論」。簡而言之,他把人類學和無政府主義連結起來,並認為這種理論/學術/實踐,正是實現人民自治的社會運動(譬如反全球化運動)的關鍵。
《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是 Graeber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最為肉麻的一次告白。
《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是 Graeber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最為肉麻的一次告白。在書的第一章,他就以克魯泡特金(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想者)的主張打響頭炮,勾勒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看法:「這個社會的和諧,並不是靠法律或者服從於某一權威來維持,而是各個團體、區域和專業通過自由協議來進行。生產和消費也相應自由形成,以滿足文明個體無限的、相異的需求和熱誠。」Graeber 接著澄清,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分別在於,前者是傾向於一個關於革命策略的理論性或分析性的論述,後者則傾向於一個關於革命實踐道德倫理的論述。也就是說,無政府主義者最關注的是實踐的形式,認為目的和方法必須呼應。
那 Graeber 所認為的無政府主義需要的人類學,又是怎樣一種人類學呢?他認為,人類學對人類的可能性(human possibilities)的關懷,一開始就和無政府主義相當接近,因此人類學更容易儲存無政府主義所需要的理論資源。他透過把人類學名著(譬如 Radcliffe-Brown 和 Mauss 的書)中對某些群體的「無政府主義」實踐的諸多記述抽取出來,以佐證以上的看法,即無政府主義與人類學在歷史中經常相遇,只不過是以「沒有自覺」的、「碎片」的(而非專門的系譜)形式存在而已。
在此基礎上,既然人類學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軍火庫,記錄了一堆「另一種社會實踐」,那麼,當今的運動者要怎麼樣參考?參考的基準在哪裏?就如同我們這群香港的人類學學生,已經選擇了當時覺得比較「相近」的美國佔領運動作為參考,結果在面對運動時,還是遭遇瓶頸。那是因為我們參考得不對嗎?我們參考的發想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我們可以用更實際和具體的語言去形容我們的瓶頸——「沒有做好組織和輿論工作」,甚至是更直接的自我批評:「我們就是一群不夠貼地氣的象牙塔左膠」。但說白了,如果說我們意識到人類學的我們與「大眾」的距離,這種距離除了可以用實際和具體的語言去超克以外,我們可否首先理解那個「距離」是怎樣被造成的?用 Graeber 的話來說,在那無權無勢的99%之中,也存在著1%(我們這些「象牙塔左膠」)和98%(大眾)之間的圍牆,那麼這個圍牆,是長成什麼樣?

讓那名為「現代」的圍牆現身吧!(然後炸毀它)
現代與原始的截然二分的想法是來自於,人們以為「現代性」使得社會出現一個清晰的斷層,使得現代性出現前後,世界有了根本性的斷裂。但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想法呢?
用 Graeber 的話來說,那98%認為「另一種社會是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是象牙塔」、「只有本土主義是出路」(卻也開路給本土主義的國家主義)等,很可能是中了「現代性」的毒。第一,受現代性的影響,只願意肯定「國家」或「民族國家」是唯一成立(legitimate)的社會單位,無視例如巴黎公社、西班牙內戰中的具規模的無政府主義實踐、並貶低所有原住民抗爭和有色人種抗爭為「不文明」,以至於合理化白人至上主義、美國對原住民的掠奪、帝國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侵略。第二個後果則是和第一個相連的,就是那98%把部落看成是「原始的」,與現代社會「斷裂」的,因此否定了現代社會向這些原始的「無政府主義」部落學習的可能。
Graeber 針對了第二點中「原始」這個概念進行了 Derrida (法國解構主義大師)式的解構。他認為,現代與原始的截然二分的想法是來自於,人們以為「現代性」使得社會出現一個清晰的斷層,使得現代性出現前後,世界有了根本性的斷裂。但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想法呢?因為我們以為現代性是繼兩個「革命」而生的──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什麼是「以為」呢?因為能稱之為「革命」的東西,總會讓人覺得是清晰的範式轉換,可是,現實中的「革命」,卻並非如此清晰,範式之轉換,往往也要很多年的時間。
同樣以現代性為例好了:法國共和政府之建立並沒有使得英國突然也變成共和政府,工業革命所發生的背景恰恰是中世紀味十足的英國憲法,也就是說,儘管在現代性核心的英國,我們想像的現代性模樣(譬如自由放任經濟學配上共和政府),也非一步到位的。現代性有帶來原始/現代的斷裂嗎?有使得我們變成和之前截然不同的生物嗎?當 Graber 把現代性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永遠都未完成的(特別是當我們幻想中的所謂的完成是那麼的「平整」的時候)、漸進的過程時,他帶出了一個非常具衝擊性的結論:我們從沒有現代過——我們和 Piaroa 和 Tiv 這些部落沒有根本的差異。
Graeber 這種對現代性的批評,是非常有人類學和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因為人類學101會告訴你,歷史並不是進步的,文化並不是進化的,而只是在不停地演化,沒有要朝著「進步」的方向線性發展。但這也使得我們在讀人類學的時候,一方面對原始的文化有了崇敬之心,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國家主義有痛恨之感,另一方面,也容易落入原始無政府主義的陷阱——認為我們必須要回到原始的狀態才能實行無政府主義——卻也只是跑到了「進步」的對立面,以「退步」的原始文明為立腳點,卻沒有從根本解構成就了「進步」和「退步」之對立的框架。
而另一個人類學經常碰到的問題是,比起社會學那種更為擅長使用科學語言的社會科學,當人類學要面對活生生、硬邦邦、凶巴巴的政治體制、社會機構、經濟結構等時,往往會提出要研究「文化」,而這看起來就很遜、很軟、很不搭、很不「大氣」。甚至,人類學家也會懷疑自己對文化的切入會否不夠「唯物」。
人類學容易落入原始無政府主義的陷阱——認為我們必須要回到原始的狀態才能實行無政府主義——卻也只是跑到了「進步」的對立面,以「退步」的原始文明為立腳點,卻沒有從根本解構成就了「進步」和「退步」之對立的框架。
於是我很喜歡提 Graeber 常說的一個例子:北美洲東北部一群住在森林裏的原住民,在十六世紀時遇到了恰好有很強的平等意識的歐洲人,被發現他們的社會比歐洲人自己能想像到的最平等、最個人主義的社會都要更平等、更個人主義。當時的歐洲人就像某些原始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嘗試這樣去解釋——「原生的狀態就是最好的吧,原住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因為他們很貼近自然,自然是很平等的」,並得出「這就是他們的文化——原始文化」的結論。然而,當人類學家真正去研究這群原住民的歷史時會發現,附近的密西西比河河谷曾經有過顯赫的城市文明,這城市文明存在上千年了,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暴力的現代國家很像:有層級系統、有人祭、有大規模的戰爭,後來這個文明衰退了。
也就是說,在城市文明毀滅五十年後,這些白人眼前所見的這群原住民,其實可能是推翻了原來的大型國家的革命者,或者是從層級系統中逃出來的後代。而他們的「文化」中所具備的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很可能是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
這也是為什麼 Graeber 會說,「有很多我們叫作文化的東西,其實是成功了的社會運動」——儘管這不代表所有的文化都是好的,就好像不是所有的運動都是帶著平等的理念那樣。但我們還能說文化沒有用、沒有力道(或反過來說,不可怕)嗎?
人類學對自己學科潛力的退縮和沒自信,造成兩種結果,一是人類學家不願意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是新的可能,而會使用譬如市場邏輯這些大理論去解釋現象,而不願意相信眼前的人其實在實踐一種制度的翻轉、挪用或重新理解。第二個結果就是,人類學家傾向把事例僅僅解讀成個別的、本土的,而不去想這些事例可以成為民主轉型借鑑的對象,最終導致了人類學成為全球「認同機器」中的齒輪,變成對「認同政治」搖旗吶喊。舉個例子,Zapatista會因此被看成是一群要求本土獨立的馬雅人而已,而不是馬雅人正在向全世界宣讀政治聲明,告訴世界民主的可能。
面對這個困境,Graeber 開出的藥方就是要人類學多與無政府主義親近,這不僅會讓無政府主義獲得適合的「工具」,也會讓人類學發現自己的強項,因此變得更為自信,最終承擔起他們可以負的責任。

作為同行者:在 Graeber 死時讀《狗屁工作》
這本書的問題意識也很簡單直接:是怎麼樣的文化機制和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在大量生產無意義的工作崗位,而人們又為何「心甘情願」選擇「戇鳩工」,成為「返工狗」(社畜)?
後來幾年 Graeber 徹底紅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了——《狗屁工作》大賣。《狗屁工作》是根據〈「戇鳩工」現象〉(憨鳩是粵語,指傻、呆)短文擴寫而成。這文曾經一度成為網絡現象,其傳閱熱度甚至曾一度把刊載它的網媒伺服器壓垮。
《狗屁工作》有著脫口秀般的銳利和幽默,讀的時候讓人不時哈哈大笑,暗忖真不愧為暢銷書。這本書的問題意識也很簡單直接:是怎麼樣的文化機制和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在大量生產無意義的工作崗位,而人們又為何「心甘情願」選擇「戇鳩工」,成為「返工狗」(社畜)?
凱恩斯早在20世紀30年代預言,21世紀社會的自動化科技可以取代大部分毫無價值的工作,人們一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然而我們今天還是成為了返工狗,此時,Graeber 發現,戇鳩工的爆炸式增長完全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這本書就是要去戳破這個增長有多麼的不合乎邏輯,那些戇鳩工有多麼的戇鳩——戇鳩到連執行者都覺得自己戇鳩。進而,他要分析戇鳩工帶給人類的集體創傷,它們使得我們妒恨(妒恨別人在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自卑(認為自己做的工作毫無意義,還談什麼勞動光榮和無產者革命?)、繁忙感(生命已被佔據,庸庸碌碌),而其造成的客觀效果是,人們沒有時間和心思去理解和渴望另一種社會的可能了。
《狗屁工作》作為〈「戇鳩工」現象〉的擴寫,用了足夠篇幅去解釋戇鳩工是如何大量繁殖:那是一種官僚主義思維的延伸, Graeber 用的框架是「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而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是工會運動者,都會覺得「更多的就業是好」的時候,其實是延續了一種「巧立名目」,透過「戇鳩工」佔據人類時間,使人類一直處於無間地獄之中。
那要怎麼打破這個困局,特別是對於相對有條件的發達地區?Graeber 提出了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UBI),也就是一個使得勞動和雇用勞動制脫鉤的建議,讓人的勞動不再受限於資本主義市場或管理封建主義的需求。和「人人有工開」這種傾向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不一樣,「人人有工開」始終無法解決勞動背後的支配權的問題。當然,Graeber 也不反對可以雙軌並行。
UBI 乍聽起來或許像是另一次的語不驚人誓不休⋯⋯然而,只要你跟隨 Graeber 的無政府主義道路和人類學資源,或許就會明白為何他並沒有被這種憂慮壓垮。
UBI 乍聽起來或許像是另一次的語不驚人誓不休,因為我們都幻想「鐵飯碗」只會使人懶惰及缺乏生產力(這也是在蘇聯解體以後,一種還沒有「去冷戰」的普遍想法)。然而,只要你跟隨 Graeber 的無政府主義道路和人類學資源,或許就會明白為何他並沒有被這種憂慮壓垮。因為,在人類學研究中,我們讀到的往往是人類驚人的可能性和創造力,而這些也不必然受市場和官僚主義所驅動。反而,社會越不信任人的自主勞動和創意,越要去高壓管理,越可能會弄巧成拙,造成一種集體創傷和絕望,使得人想要逃避勞動。這樣看來,UBI其實是要去打開資本主義市場和管理封建主義所加諸的冷酷封印,同時也是有大量人類學證據去支持的路線。只是,路線的道路必須是透過運動去逐步摸索及開拓,並且透過文化邏輯的分析去評估它的進度。
Graeber 死掉了,就像消失了的手足,我們再也沒有可以一起抗爭的機會。但 David Graeber 也許沒有死掉。
遺憾的是,從現在開始,我們再也沒有辦法和 Graeber 一起,在這個時空去尋找那條道路了。
但既然活著就是在無間地獄,自身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因為自身所身處的文化與信念也是前人留下來的果,那麼,為了我們的存在而前仆後繼的先人,及將會被我們所影響的後代,我們可以塑造一個更公平和民主的社會嗎?Graeber 死掉了,就像消失了的手足,我們再也沒有可以一起抗爭的機會。但 David Graeber 也許沒有死掉,就好像北美洲原住民成功的社會運動以文化的方式流傳——他帶來的思想與文化影響,會一直烙印在同行者的心裏。
——和你抗爭,我很愉快。
(劉璧嘉,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生,現於台灣攻讀亞際文化研究碩士,研究興趣為香港70年代社會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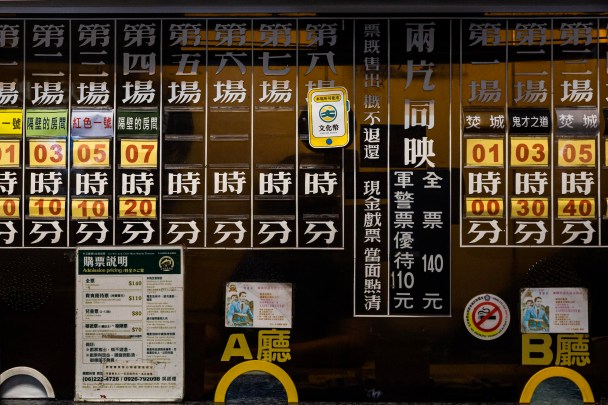
謝謝 劉璧嘉,希望有更多文章講解 無政府主義。
作为一名刚刚开始学习社会学,且同时抱着对当今国家、社会集体机器、政府的莫大怀疑与敌意的学生,非常庆幸自己无意间点开了这篇文章。
谢谢作者的这篇文章,你让我能够从这个从未了解过,思考过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
如果有余力,我非常希望并且期待能学人类学 w/
2014年的佔中是因為要求普選特首、取消功能組別等訴求而發起的,跟無政府主義無關。而2011年滙豐總行的「佔領中環」可能會比較貼近你的説法。
在自動化的改革完成後,UBI的確能最直接回應「異化」,讓人類不再受生存資料的束縛。但我很懷疑在人類變得空閒後,會否再產生更多的問題。
Graeber的想法很樂觀,我以前也是。但我在看了《衝吧!烈子》第二季後(沒錯是動畫)有所反思。會不會也有人滿足於只是接受命令,不想多作思考的戇鳩工。我們讓他們自由支配時間,反而會令他們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痛苦之中?
之後有時間會再拜讀Graeber的作品,感謝作者分享。
@端小编
安卓端app做不出本文截图
感谢作者和端。我自己是多年前由学校的人类学老师介绍知道了Graeber(这位老师Thomas Gibson同样是位对于激进政治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在学校也开设激进政治课程,并且自称和Graeber很熟233),虽然买了Graeber的书但是至今还没来得及拜读,没想到他就去世了……
无论如何,作为试图去想象和实现另一种可能性的激进左翼同志,我会继续走下去
非常前卫的讨论,期待更多这样的文章。
很好的文章。不过开头那句话,有待商榷 - "作为行动主义者,死的有些晚" ... 似乎行动主义的行动,都无可避免地走向牺牲。这是人类学社会学中的共识吗?
感谢作者,看完很感慨。想要去看看David的书
好文
感謝作者!深深感到Graeber描繪的正是心裏孜孜以求的非暴力的、多彩的、人的世界,而非現在這個單一的、暴力的、國家主義的世界。很開心,還有一群人有這樣的理想和追求。
謝謝Lala好文
一直覺得世界被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收束了,而這是無可奈何的,但今天看完這一篇,算是對人類的可能性再次燃起了希望,感謝作者
P.S. 我會去找Graeber的書來看,希望它們對外行人friendly一點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