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6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向中國出口貨品徵收額外關税、正式打響中美貿易戰開始,這場戰役至今已經超過一年。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在角力和妥協的交織中艱難推進——談了又停,停了又打,打了再談,幾經反覆。在陷入僵局後一觸即發的硝煙中,兩國最高領導人兩度面對面會談後出現轉機,時隔不久卻又會再次劍拔弩張。
8月,隨着宣布中國未履行購買美國農產品的承諾,特朗普耐心耗盡,將中國直接定性為「匯率操縱國」。中美貿易戰何去何從,再添新的變數。
面對這場政策大轉變,美國國內也有激烈辯論。今年七月初,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等人牽頭起草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彙集了中國問題專家中的温和一翼,批評特朗普政府的魯莽政策轉變,並強調,華盛頓的政學商界在對華政策上並不存在一個強硬共識。
著名政治學者、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數十年來專注研究民主轉型,曾於包括大中華地區的全球超過70個國家實地研究。在新近出版的著作《妖風:從俄羅斯瘋狂、中國雄心和美國自滿手中解救民主》(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中,他警示了中國擴張對於自由民主世界及其價值體系帶來的威脅。書籍甫一上市便備受關注,學界與評論界人士最大的爭議是——中國真的這麼可怕嗎?更有書評作者稱,針對其中某些論斷,恐怕是最強硬的對華鷹派都難以意見一致的。
近日,戴雅門接受端傳媒採訪,深入探討他對當下中國充滿警惕的原因,以及對未來中美關係走向的判斷。
耐人尋味的是,這位外界眼中的「鷹派」坦承,自己其實同意《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中70%的內容,但同時指出,它低估了中國帶來的潛在危險,甚至不乏「天真」。他在面對華為的態度上有一種不容分說的決絕,但針對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笨拙、過頭、專橫,甚至有些挑釁性」的舉動,戴雅門同樣發出直言不諱的批評——
「天哪!美國官員們真的需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第一課,永遠不要侮辱這個國家,她已經承受了太多。」

端=端傳媒
戴=戴雅門
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最終會尋求全球霸權
端:在新書《《妖風:從俄羅斯瘋狂、中國雄心和美國自滿手中解救民主》中,你聲稱中國在尋求對整個亞洲的霸權,並以本世紀內稱霸全球政治為目標。《紐約時報》書評作者Gary Bass說,即使那些最強硬的對華鷹派,也會對這一論斷產生異議。你能否解釋為什麼形成這樣一種判斷?
戴:因為我會觀察中國的行為。首先,即使在海牙仲裁法院拒絕之後,近年來中國依然在南海限制其他國家航行自由,並要求這片巨大水域的單獨裁量權。當你去觀察中國在南海區域的軍事化速度,比如從無到有地填海積淤建造軍事化島嶼,並建造軍事跑道、空軍與海軍基地,當你觀察中國海陸空軍隊外加衞星等領域這種軍事擴張和現代化的速度,當你觀察那些涉嫌從西方不當獲取的科技如何在過去三十年被迅速應用於軍事目的,當你觀察中國在全球的迅速滲透與控制,你很難不擔憂。
當你觀察那些涉嫌從西方不當獲取的科技如何在過去三十年被迅速應用於軍事目的,當你觀察中國在全球的迅速滲透與控制,你很難不擔憂。
很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從澳大利亞、新西蘭,到加拿大、美國和歐盟這樣的成熟民主政體,中國都在使用「鋭實力」途徑影響西方社會、高校、智庫以及大眾媒體等等。如果看看中國官方在全球宣傳機器所投入的資金規模,在全球語境「講好中國故事」的努力,使用經濟肌肉對於批評進行審查和威脅的做法,就會了解這一點。
當你把所有這些因素疊加起來,就會看到一幅令人憂心的圖景——很明顯中國希望把美國「推出」亞太地區,這對其意味着能掌控台灣局勢、並削弱美國對於協防臺灣在無挑釁情況下被強力統一的能力,最終意圖是將美國推出第二島鏈,使得該區域之內全部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
把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因素疊加起來,除非太天真,否則不難看出這些情況發展的方向。
端:這有些類似於多年來的「中國威脅論」,尤其是在當下中美可能出現「新冷戰」的背景之下,美國對華態度日漸強硬。但也有很多人認為,目前的中國已經「太過強大而不可能被遏制」,或許尊重其崛起的事實,會更有利於使之貼近既有國際秩序。你怎麼看?
戴:必須明確,我們絕不否認中國現在是當今世界的一個超級強國,美國再也不可能充當全球唯一的霸主。但是自由的普世價值仍然是需要捍衞的。我們應該以集合的力量,在經濟上、地緣政治上、道德上——希望不至於到軍事上——與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抗衡,以保護自由世界國際秩序的基石。
我們絕不否認中國現在是當今世界的一個超級強國,美國再也不可能充當全球唯一的霸主。但是自由的普世價值仍然是需要捍衞的。
但我並不是說不歡迎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或不允許中國發聲。如果中國希望調整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話語權,當然應該談。如果中國在國際機構的談判桌上希望獲得更有權重的地位,他們有權被傾聽得更多。
但是如果你希望在全球治理之中成為同等重要的利益相關者,那你必須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但當下中國在南海、新疆、香港的做法,以及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有新殖民主義色彩的債務陷阱——以商業貸款利率大舉放貸(卻稱之為外國援助),又在這些國家無力償還的時候拿走其戰略資產來抵債。所有這些,都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應有的舉措。
歷史一再證明,這樣的威權國家——尤其是如此傲慢、不透明和難以接受監督的威權國家,起初會尋求區域霸權,最終會尋求全球的霸權地位。那麼,其政治特性也不會局限於國境之內,而是流出其內部體制,向其國際舞台上的行為延續。
如此傲慢、不透明和難以接受監督的威權國家,起初會尋求區域霸權,最終會尋求全球的霸權地位。
我在去年11月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與亞洲協會共同發表的報告中、以及《妖風》一書中都指出,我們並不希望發生一場新冷戰,我們也不希望激怒挑釁中國。我要再強調,我不贊同台灣獨立或香港獨立。這些地區的年輕人應該十分謹慎,不要打「獨立牌」。這非常危險、非常具有挑釁性,並最終只會給所有人帶來悲劇。
我不贊同台灣獨立或香港獨立。這些地區的年輕人應該十分謹慎,不要打「獨立牌」。這非常危險、非常具有挑釁性,並最終只會給所有人帶來悲劇。

中俄結盟純屬權宜聯姻
端:新書中的另一個主題是「俄羅斯瘋狂(Russian rage)」,在冷戰後二十年之際,這種「瘋狂」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具有破壞力了,究其根源是什麼?
戴:「俄羅斯瘋狂」一部分是由於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在國際地位和綜合實力上的嚴重衰落。人們會從自己所處、所擁有身份認同的群體或者國家獲得一定的自我價值,因此當俄羅斯人感到自身被削弱,加上經濟崩潰和由此帶來的傷痛(俄羅斯的經濟衰退比美國1929年大衰退時期還要劇烈和持久)。所以普京出現了,用今天的話說,他承諾將會「使俄羅斯再次偉大」。
但同時,普京對於權力、和聚斂由權力帶來的財富非常迷戀。整個克里姆林宮統治集團都不僅是狂熱民族主義者、對於攫取權力十分多疑,並且極為腐敗。所以他們需要一個妖魔化的稻草人來轉移人們對於他們統治的道德和政策失敗的注意力。這個稻草人就是西方——美國、歐盟,乃至整個自由國際秩序。
俄羅斯人口中不斷增長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城鎮和年輕人中間,並不接受克里姆林宮的論調。
然而,我認為必須強調一點,俄羅斯人口中不斷增長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城鎮和年輕人中間,並不接受克里姆林宮的論調。許多俄羅斯年輕人除了普京根本不知道其他以前的領袖。他們(正確地)認為體制是腐敗的、墮落的、憤世嫉俗的、傲慢的,而且對民意缺乏回應。這恰恰是普京和其他克里姆林宮精英所畏懼的:草根階層對於更好政府的渴求。
端:近年來中俄的戰略接近,會從深層徹底改變世界圖景嗎?會不會不可避免地重蹈冷戰時期兩大集團對抗之路?
戴:在我看來,中俄之間的結盟純粹是一場出於權宜的聯姻,現在比冷戰時期更加如此,當時至少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共同的忠誠。
俄國和中國的政權的共同點其實是一種恐懼:對於普世價值、對於人們自發走上街頭要求權利的恐懼、對於腐敗和治理失誤被曝光的恐懼——比如當下正在莫斯科和香港發生的。因此他們將整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正常化和制度性框架拒之千里,宣稱民主制度並不適合自己,「人權」是危險的概念,不可以討論。
中俄之間的結盟純粹是一場出於權宜的聯姻,現在比冷戰時期更加如此,當時至少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共同的忠誠。
事實上,這是非常負面和防禦性的。他們可以說七國集團(G7)、歐盟和北約制定了世界規則。但事實上,這些是普世價值,也是中國人和俄羅人一樣需要的。
端:除了中俄之外,正如你書中和演講中提到的,2006年以來,民主在世界範圍出現了衰退,到了2017年百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之中只剩下51%還是民主政體。同時極右、排外的領袖人物在匈牙利、波蘭、土耳其和菲律賓等國家崛起,並攻擊民主體制。面對這種趨勢,你認為民主體制的擁護者可以做些什麼?尤其對於中國呢?
戴:民主的擁護者們需要不斷地發聲,闡述民主價值,並加入其所在國家對於透明選舉、民主權利、法治的追求。諸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Viktor)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這樣的威權領導者,或者諸如菲律賓的杜特爾特(Roa Duterte)和波蘭的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這樣的早期獨裁者必須要明白,違反民主規則、破壞比如司法獨立這樣的民主制度會有後果。
在許多國家,人們需要在地的實際幫助,財政和技術支持,以幫他們堅守這些原則,並向國民傳播關於法治和民主的知識。但我們也不該低估清晰道德表態和外交聲明的價值,以及對於人權侵犯和經濟犯罪實施者進行《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類型制裁的力量。
對於中國,我相信某個時點會出現變化。習近平和他的政黨在過去三十年所專注的就是經濟增長。毫無疑問,那是令人矚目的奇蹟般的成就,但也有很多人被拋在後面,他們的人權受到了侵犯,高速經濟增長也有可能隨時減緩。
在未來一些年,中國領導人需要給予人民更多的尊嚴、更多的發聲表達、更多的權利,因為僅僅通過經濟增長來噤聲已經很難做到。
在未來一些年,中國領導人需要給予人民更多的尊嚴、更多的發聲表達、更多的權利,因為僅僅通過經濟增長來噤聲已經很難做到。人們會逐漸要求獲得更多的權利,互聯網管制、人臉識別或其他壓制手法也難以奏效。除非他們基因編輯使得人類物種變得徹底不同(老實說我還真有些擔心),這個問題都會存在。尊嚴是每個人遲早需要的東西。

《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低估了中國的威脅
端:最近,有數十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中國不是敵人」。你怎麼看他們和你的這種分歧?
戴:我同意公開信中70%的內容,但信中還有一些元素我認為太過天真。我同意中國不是「敵人」的說法,因為你必須心中有數,「敵人」意味着距離軍事衝突、兩方作戰只有一步之遙。上帝保佑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這對於中美雙方都是悲劇。
具體舉例來說,比如公開信中的第一句。「我們相信北京不是一個經濟上的敵人」,我同意;但要說「也不是廣義的國家安全威脅」,這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當下正處於日益具有壓迫性的「新極權主義」統治之下,以前鄧小平建立的一些政治制衡機制的基礎——比如任期制——也被取消。因此我認為中國在很多重要領域確實對民主世界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在地緣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具威脅性。
中國在很多重要領域確實對民主世界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在地緣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具威脅性。
但是我也同意「中國不是鐵板一塊」這個表述,我們的目標應是將領導層中理性的元素分辨出來。
這封公開信迴避了當下中國政權中的一些實際本質,並忽視了很多關鍵特點。對於諸如在新疆針對維族等少數族裔的對待、在香港拒絕給予民主等等這些近年來領導層管控的收緊,公開信未置一詞。而這種忽視是很嚴重的,甚至具有低估威脅的潛在危險。
我沒有被邀請聯署這封公開信,當然即使受邀,我也不會簽署。我注意到有一些我非常尊重的學者聯署了,但仔細觀察的話,你會發現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之中,也還有很多響噹噹的名字沒有出現在聯署名單上,這一點同樣令人注目。
端:你是否會說,這些參與聯署的學者習慣於以一種「玫瑰色的濾鏡」觀察中國?
戴:確實有天真的成分。學界對於中國對我們的自由和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我覺得有一種危險的低估。當我說「我們」,我指的是全球的民主政體。
但我不打算為那些聯署了這封公開信的學者貼標籤,或者去質疑他們的動機。我相信他們是真誠、清醒、意願良好的人,只是在對於情況的判斷上和我有分歧。
我相信公開信聯署者是真誠、清醒、意願良好的人,只是在對於情況的判斷上和我有分歧。
事實上,這些學者中的大多數比我知識儲備豐富,這也不是誰需要對於有關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知識儲備進行調整適應的問題, 而是一種對於現狀的判斷,我覺得這一點同樣至關重要。
美國對華政策須轉變,但應超越情緒與衝動
端:在書中,你似乎為特朗普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進行了辯護,因為你提及「中國肆意竊取、挪用、或強迫轉讓美國的高科技,是導致特朗普加徵關税的主要原因之一」。你是否認為美國當下的一些敵對手段加速了雙邊關係的直線惡化?
戴:是的,某種程度上我是這麼認為的。我支持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策略總體方向上向更加警惕、更加公平、更加有反制能力的雙邊關係的轉變。這也確實驅動了特朗普政府就任以來的對華政策。但是我認為這種政策的具體實施有些笨拙、過頭、專橫,甚至可能有些挑釁性。
我完全同意特朗普政府關於「華為構建全球5G電信網絡可能帶來挑戰和威脅」這個判斷。我對那些相信華為是一家「純粹私企」、能夠抵禦中共要求其提供數據的想法感到很遺憾。我認為這不但天真,簡直是太天真。
我對那些相信華為是一家「純粹私企」、能夠抵禦中共要求其提供數據的想法感到很遺憾。我認為這不但天真,簡直是太天真。
自由世界無法容忍一個「新極權主義」國家來構建和提供全球電信基礎設備,那會成為一種可怕的「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情況。這不是一個貿易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和人權問題。
所以我對於特朗普政府非常認同的一面,主要集中在科技研發及科技轉讓領域。但是即使着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也應該謹慎地超越情緒和衝動,進行有策略的分析。
端:但同時你也認為,特朗普政府宣布限制中國學者的簽證是個錯誤的做法?
戴,是的,阻撓中國學者來開學術會議,取消其簽證,這樣的做法不僅是反效果的,也是很不幸的。
首先,你不應該這樣對待他人。我在書裏寫了這個故事:1946年,美國國家政策顧問、著名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從莫斯科發出的長電報中發出警告。在當下,重温他的充滿智慧的建議非常重要,因為他被視為冷戰之父,他的長電報也被認為是為冷戰打下基礎的影響深遠的文本。凱南說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我們的民主價值與規則,我們不能變得像對手一樣——這裏他指的是蘇聯——我們不能降低到他們那樣的欺騙、傲慢與殘酷,否則我們會失去我們的道德高地,我們也將失去我們最珍貴的財富。
因此,當一位中國學者或研究者來到美國,受到羞辱或者被報導中那樣大聲吼叫,這不是我們應該有的樣子,至少不是我們致力於成為的樣子。我不在乎假如我飛去北京會在機場被如何對待,我只是不希望將這樣剝奪尊嚴的事情加諸在我們的中國同行身上。
我不在乎假如我飛去北京會在機場被如何對待,我只是不希望將這樣剝奪尊嚴的事情加諸在我們的中國同行身上。
如果我們拒簽,那就拒簽;如果我們作廢一張簽證,那就作廢;如果我們問訊訪客,甚至是長時間的問訊,我們就這麼做——但以一種尊重和文明的方式。我們應該明白,這些學者來到這裏,拿到博士學位,他們可能在中國的智庫工作,這些智庫可能和中國政府有一些合作關係。但他們可能對於美國有着更加圓融和複雜的觀感,我們也不希望失去一些能在中國表達的理性聲音、以及本可以在社會傳播的良好信息,也可能促使雙方緩和各自的行為。因此,我們應該謹慎處事。
所以你看,這種分歧更多是在風格、調門、方法,而非實質層面的,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天哪!美國官員們真的需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第一課,永遠不要侮辱這個國家,她已經承受了太多。
美國官員們真的需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第一課,永遠不要侮辱這個國家,她已經承受了太多。

無論下任美國總統是誰,「對華警惕」都將延續
端:從中美關係的角度,你認為近期在貿易和其他層面會出現什麼變化嗎?
戴:我很不擅長進行預測。我曾經以為到了現在這個時候——2019年下半年,雙方應該已經達成協議了,因為如果被拖入一場漫長持久的貿易戰,政治上誰都不會得益,更別說經濟上了。
但就如你提到的,現在這種對話談判似乎陷入僵局,似乎一場曠日持久的對抗已經無法避免。現在對於達成協議解決貿易戰,我認為機率是50/50,需要在未來八個月左右之內進行。你知道,在美國,很難將大選政治與其他政策分開,所以關鍵在於特朗普是否會連任。
在美國,很難將大選政治與其他政策分開,所以關鍵在於特朗普是否會連任。
端:你覺得他勝選連任的可能性有多大?
戴:很難講,目前看來是50%的可能性。美國的經濟狀況很好,這是他的加分項,但是他的管制風格、不可預測性、無情、對於憲法約束缺乏尊重等等,都使得很多美國人厭惡,也不抱希望認為他會改善。
端:如果特朗普真的勝選連任,會不會在對華政策上更加有恃無恐?中美關係是否會真的全面惡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戴:我不會嘗試去設想這樣的情況。特朗普顯示了他對於「不可預測性」的執著,如果他判斷貿易戰會導致他連任失利,他可能會嘗試將其迅速終結;但是是的,假如他當選,他可能會加碼。這真的很難預測。
我能說的是,目前國會裏兩黨都在一致對中國施加壓力,源於他們認為中國在竊取美國的敏感高科技。普遍來說,跨黨派的共識是,中國在美國進行了不正當的、隱秘的動作,以削弱這裏的言論和學術自由,這在美國變得越來越不能被容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對華警惕的新時代,我想無論未來的美國總統是誰,這種狀態都將會延續。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對華警惕的新時代,我想無論未來的美國總統是誰,這種狀態都將會延續。
端:那麼整體來說,你對於2020大選有什麼判斷?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們有什麼樣的對華政策?
戴:我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對華問題上的分歧,可能遠遠小於外界的猜測。國會中對於關於中國的議題有很多擔憂,就是我提及的那些問題——軍事現代化擴張、區域主張、滲透和不當影響力、在全球的各種項目等等。對於其國內人民人權的不尊重也日益令人擔憂。這些擔憂在民主黨內,尤其國會的民主黨議員之中都非常受重視。
我想,如果最終是民主黨總統入主白宮,對待中國很有可能不會像特朗普總統那樣充滿對抗性,但也不會像奧巴馬總統那樣充滿安撫性。我們很有可能會進入中美關係的一種中間路線新紀元。
(李佳佳,媒體人,非虛構寫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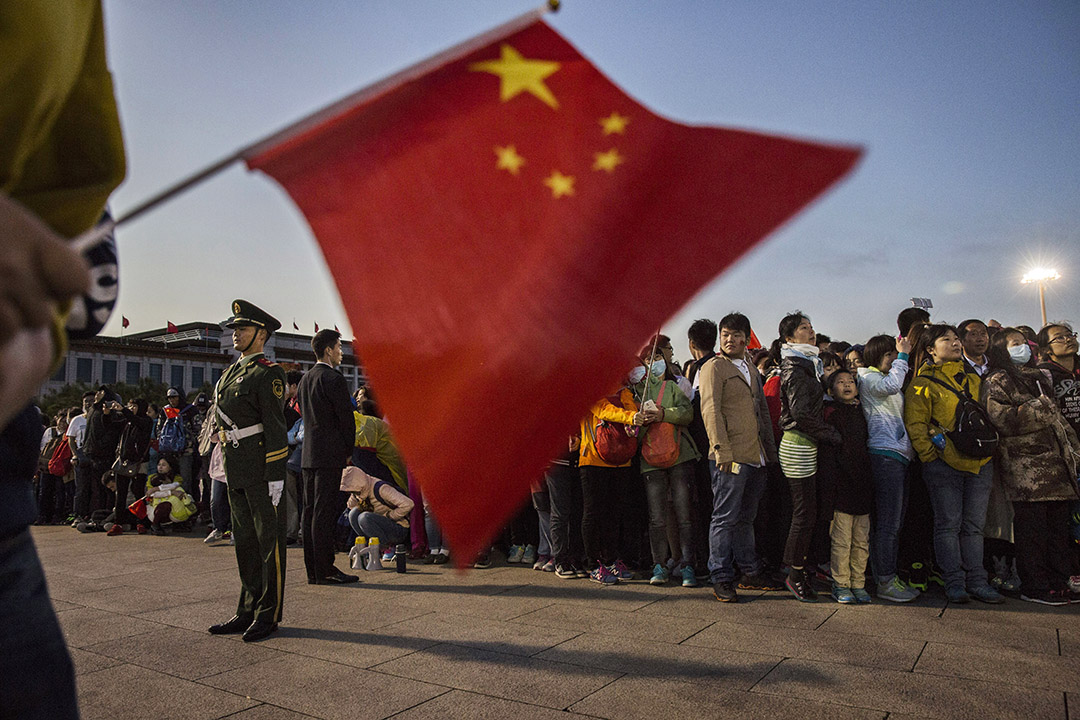




第一課,永遠不要侮辱這個國家。第二課,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第三課,國家也一樣。
總算有個清醒的學者,但不過比起那幾個聯署公開信的沒那麼天真。最簡單一點就是你沒辦法與魔鬼講規則,如果自由聯盟沒有辦法成功對抗,人類所捍衛的普世價值必定破碎。
@yanchchina 中国崛起这么快,而且还和现在国际秩序主导的西方意识形态那么不同,当然会引起很大的惊恐。美国是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逐步将自己的利益和欧洲结合起来,建立自由主义新秩序,让欧洲依赖自己,让对方逐渐习惯其影响力。这可并不是双重标准那么简单的。
看完這篇,感想是:Diamond先生,你在美國也許相對比較不天真,但從我的角度看...你還是太天真了
我同意中國學者應該受到尊重,但要藉此引申到「永遠不要侮辱這個國家」未免也太過。中國一直以來也用極為粗暴的方式侮辱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並且將表達不同政治觀點都視為「辱滑」,這個情況下談「不要侮辱」,難道是把中國當巨嬰?
不論意識形態和政體,每個國家當然首要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但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絕對沒有「分享國際領導地位」的空間。如果美國和中國各自維持現在的政體和意識形態,那麼全世界就注定只能在中美之間二選一。現在已經不少學者認為,這不僅是一場貿易戰,而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
自由世界無法容忍一個「新極權主義」國家來構建和提供全球電信基礎設備。那可以容忍一个美国监听世界的电信基础设备?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堂而皇之的都是丑陋的借口。
我對中國自上而下的改革跟自下而上的變革都報以悲觀的態度。一個極權國家發展到長期間內,他的人民無法改變現狀 集權國家向世界稱霸了野心將不斷上昇。所以支持中國威脅論,希望信仰普世價值觀的西方一眾國家可以提前對這個集權的龐然大物,做出預防甚至是制裁。
認同tw2323的見解。受訪者相信人民終有一天需要尊嚴,並導致制度改變,這是典型親華派的立論基礎;誇談民主的普世價值,自己又心口不一地警告台港年輕人不要挑釁⋯⋯當中國人民向政府要求尊嚴的那天,我們是不是也該要求人民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擾呢?
全篇读完,看得出来Larry Diamond教授真的是对Liberal Democracy有热枕的一个人,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走上他认为的这个”普世”价值政体,全世界形成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一起好好发展。甚至大胆猜测下,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好的liberal democracy,Diamond教授是会愿意支持中国成为Liberal Order世界的领袖。所以我更认为他不那么是一个鹰派,而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好人。
可是世界终究不是这样的世界,尤其是国际政治,美国也是宁愿牺牲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也不会愿意主动放弃世界霸权(Global Hegemony). 这些国际自由主义的理念很可能是morally right but socially/strategically irrelevant,因此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realism)的世界中,推荐大家读一下去年Foreign Affairs 7/8月刊普林斯顿大学Stephen Kotkin的文章 Realist Worl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8-06-14/realist-world 因可能需要订阅无法读全文,摘抄2段,和大家分享
“It chose instead to advance its interests more through voluntary alliance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free trade. That choice was driven largely by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rather than altruism, and it was backed up by global military domination. And so the various multinational bodies and processes of the postwar system are actually best understood not as some fundamentally new chimera call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s mechanisms for organizing and extending the United States’ vast new sphere of infuence.”
“The issue of the day might seem to be whether a Chinese sphere of influence can spread without overturning the existing U.S.-created and U.S.-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that ship has sailed: China’s sphere has expanded prodig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revival has earned it the right to be a rulemaker. The real questions, therefore, are whether China will run roughshod over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it can— and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global leadership, because it must.”
沒被洗腦過的人第一反應: 國家≠黨
簽(簽證)跟籤(求籤)不要混著亂用啊⋯⋯
“颱灣”?
西方学界和政界今年年初基本已经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比较清晰的时间线就是继中美贸易战后今年三月的《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如果不在西方国家学习政治学,即使长期在西方生活也很难理解他们口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变得愈加不受西方的钳制,在西太更具侵略性的“卷心菜战略”。习近平掌舵下的中国的野心让众多国家紧张,即便中国政府一直尝试扮演友好建设性的角色,但有时也难免事与愿违。中西的对抗到底是利益的对抗还是价值观的对抗这是我一直迷惑的问题,我学习过美国宪政,对他们的建国之初的宪法民权精神也异常崇拜。有些时候也很怀疑“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我理解不了它到底是什么。如果经济下滑,人民权力又受限制,这个政权还能依靠什么维持稳定。
在内,中国多数民众的强权民族主义思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极端。国内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对话的体制和氛围会让这种情况演变的更加危险,未来执政党面对的不仅是对华更加紧张的国际局势,还有89以来信奉“稳定发展论”且更加情绪化的公众,他们拒绝妥协对话,主张对外、对港台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这些人虽然无法参与中国的政治操作,但是带来的社会氛围更加可怕。未经过民主培养的人民有一天突然登上了最高权力舞台,他们会将这艘大船驶向何方。
可以预见的是,低于7%经济增长率会让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以后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如果这次香港能在PLA不插手的情况下慢慢消停,那也算是执政党及中央政府的关键胜利了。
錯字滿多的
不過,也難說,或許他就是要侮辱。反正,現在的中國,以特朗普的大嘴巴,還是要小心處理。
哈哈哈哈哈……想想DG,那還不是立心要侮辱都被解讀成侮辱。
永远不要侮辱这个国家,教授你是在讲冷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