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即禁忌。在中國牆內的互聯網,你搜索不到這個樂隊的任何相關信息。即便在香港,樂隊的名字也堵死了它實現商業化的任何可能。作為六四樂隊(寫做「VIIV」)的創始人,林律希深知這一點。六四樂隊本就是為了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的演唱而召集的,他喜歡這個直白的名字。在這組羅馬數字之中,他看到了對稱與平衡之美。名字還是個隱喻,正如逝去的民運領袖司徒華說過的,「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VIIV」中前後的V就代表勝利,夾在中間的I代表我。
林律希喜歡隱喻。六四樂隊最出名的那首歌《民主會戰勝歸來》中,他埋下了大量隱喻。那首歌由他多年朋友Anthony Kwong作曲,林律希是填詞人。《民主會戰勝歸來》在2012年維園集會首次唱起,引起巨大反響。隨着後來在不同社運場合的廣泛傳唱,它已經不止是一首為紀念六四而作的歌曲,歌名成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口號。
在六四樂隊鼓手「阿嬌」印象中,林律希是個音樂痴人。「他寫的歌有詩歌的味道。你和他相處時,他就像一個小朋友,他的世界很簡單。」
數年前,與記者見面時,林律希曾感歎馬上將成為父親的生活壓力,也表達過對更大舞台的渴望。2015年後,他新組了一支名為「地球人」的樂隊,在時政之外更豐富的領域進行歌曲創作。因人員變動,六四樂隊名義上停止合作。但他的作品始終在。「阿嬌」繼續着每年維園集會的樂隊召集,「把他寫的歌,繼續唱下去。」
音樂之外,林律希一生與病魔做鬥爭,他自幼患有抽動症,後又罹患其他疾病,需要大量服藥。不過他從未放棄。2017年7月27日,劉曉波病逝兩個星期後,林律希為劉曉波和劉霞夫婦創作歌曲《落霞之歌》。
2019年6月,林律希病逝,年僅37歲。他為人低調,離逝的消息並無獲得太多關注,直到7月中,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發布林律希病逝的消息。以下為林律希的自述,對他和Anthony Kwong的採訪在2014年6月進行,此次為首次公開。

關於《民主會戰勝歸來》:我寫的東西要感動到自己才可以公開
大約2004年,我在澳洲讀大學,我那時參加我學校的業餘作曲比賽,我需要人幫我唱歌,有人介紹了Anthony 給我認識。之後我們就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有辦中華音樂社,有做一兩個音樂劇。
2010年聖誕,我和Anthony在味千拉麵吃東西,就談起六四的事情。我們就說每年都想晚會有些新歌,但我想不到新歌。然後他就說,我有一首歌讓你聽聽,他就拿了一隻MD出來。我一聽就覺得這首歌很好,就問他介不介意讓我填詞。他就說好。他還擔心這首歌有一點「老土」。看你怎樣做,舊歌舊詞都可以有新的演繹。舊不是問題。
(Anthony Kwong:其實這首歌的demo 是我06、07年寫下的,完成了70%,我野心很大,剩下那一段,我曾經寫過很多的版本,但始終都不滿意,所以擱置下來。後來我2010年澳洲讀完書回到香港時,都有一團火想做一些事情,才完成另外30%。這首歌是想向顧家輝致敬的,我想嘗試模仿這位大師,所以加了很多武俠的元素。其實有些詞,我自己都做了一些框架。我會不斷哼,看看有什麼詞適合,剛好哼到「民主會戰勝歸來」就寫下來,就覺得不錯。我是要這首歌有一個主題,就拿了最重要的一句出來。)
我跟他分開之後,我走了兩步,我就站在街上開始寫。只是寫在廢紙上,隨便拿一些宣傳單張來寫。因為我很有興趣,我很喜歡這首歌。我寫了兩段,就想不如回家,在地鐵站也是一直寫,一直寫到回到家。回到家就睡不着,就繼續寫,一邊喝檸檬茶。我一喝檸檬茶就睡不着。我就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停寫。寫了一天多,二十多小時。
我比較有趣的是,我有信仰,我創作之前會祈禱,很快很順利就可以創作到。寫歌時我會動情,會落淚,我寫的東西要感動到自己才可以公開。我不會隨便完成。
「民主會戰勝歸來」這一句不是我寫的,是Anthony講給我的。他又再想了一些,比如說「青苔」。我一想就想得到那個意境,大海啊,激起千重浪那些東西。我第一句,就是想「青苔」可以聯繫到什麼,就想到石頭。之後又跳到「白頭浪」那一段,白頭浪就是想比喻丁子霖那些老人家,就創作出來。
之前我還想,這首歌會不會太長,一模一樣的曲,重複的音樂,不如就刪減一段。還好Anthony說不行,這首歌要這樣唱,這麼長才好聽。我就不改他的段落。我反而可以寫更多東西,推動我想更多更多,怎麼樣能寫好,但內容又不重複,真是想到腦袋都抽筋。
(Anthony Kwong:因為當時我很掙扎。最後我決定這個段落是要要宏大一點,就長一點就沒有所謂。)
我一向都很喜歡方文山,我很深入研究他作詞的方法,我研究到「爛曬」。我就是用他的作詞方法去寫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整首歌只有兩個韻押來押去、調來調去。我還用了很多比喻、暗喻。我看了方文山那些詞,他的詞是很有距離的,他說一樣東西不直接說,我就學了他這個方法。
現在大家都好似很明白歌詞,但其實大家都不明白。我特意把歌寫到好像密碼一樣。例如有一句,「我插下和平旗幟,我指尖成為號角」是什麼意思呢?因為那時候「苿莉花運動」,我指尖成為號角,就是指計算機、互聯網。「天有光」那一段,是說民主黨那一陣子做得很差,不得民心,就不是跟大眾在一起。其實那一段是勸喻泛民,有事你就要堅持去做。
另外,在音樂上都有密碼。你會發覺中間有一段音樂是「6拍4」,我在編曲時加了這段音樂,即是六個四分音符,六四。

關於六四樂隊: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
六四樂隊成員,有七八個。我是作詞、編曲,Anthony 是作歌,其他的就玩樂器。家弘是主音,最重要是他,他又帥嘛。樂隊有一個帥的很重要。
沒有六四樂隊之前,只有我和家弘兩個人,一直都是兩個人。2004年的七一遊行,我做了一首《七一精神》,家弘幫我唱。其實再往前推已經有很多歌,但都是不成熟的歌,好像是給他們選舉宣傳的歌。之後發現有些歌,兩個人不行了,就叫了Anthony幫忙彈琴。
六四20週年時我們有一個音樂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然後我們認識幾個玩音樂的音樂人,就覺得我們很match,就成立這樣一個樂隊。之後一年我們就出了專輯。
Sunny吹口琴,他高大帥氣,也很擅長處理問題,所以他是我們的manager。他處理問題很棒,要約人(排練)我就跟他說。因為我曾試過約人,我會發脾氣。家弘是一個很沉默的人,但很有影響力,有決定我們一定要找他,他以前是支聯會司儀。彈琴的叫Ivy,她比我們小一點。我們要什麼,她就彈什麼。Brian是Ivy男朋友。有一年除夕晚會很有趣,我們上台之前,「你男朋友?新認識的?玩bass?那不如一起即興演奏吧!」馬上他就上台,和我們玩。除夕晚會比較小型,無所謂。
打鼓的是阿嬌,身形很大的阿嬌。阿嬌是男生,是外號,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認識他是搞社運,大學不知道什麼組織,叫我們去參與他們的音樂會,就認識了。 我們沒有鼓手,他說我打鼓,就一起了。
Kennief 本來是採訪我們《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的學生。音樂的理念我們很配。他知道我想要什麼。我也知道,他還沒彈我就知道他要什麼。他之後和其他成員有些爭吵,就離開了。如果你要寫,就寫我欣賞他,他的創作和他的熱情。
以前(維園晚會的音樂)都是播帶,(六四)17、18週年開始有live music。我認識裏面的人,有個叔叔說你學音樂又會作曲,來幫忙吧。最重要是他信任我,因為這麼大的事,沒有信任是不會讓我做的。
六四晚會這麼多年需要新的元素,但我也看見除了音樂,它不可能有新的元素,我都計算過了。除了我這部分,沒有東西可以變。儀式難道像嘉年華嗎?拜祭先人就是送花、鞠躬,拜山你會不會開派對,拿着啤酒??不會嘛。真是一個儀式。儀式是重要的。你去靈堂,就要尊守儀式,但靈堂音樂可以改。我在20週年(晚會)看到很多年輕人,特別多。之前我不敢,之前不會有樂隊,我不會讓他們上台,但我看到20週年的形勢。 哇。
他們已經接受了有現場音樂,有樂隊當然做了。我們都考慮過要不要上台,「你們這麼大批人當然上台了」,那就上台咯。他們其實也要評估風險,台夠不夠位,放哪個位置,會不會有人不喜歡。他們一定有考慮的,但他們信任我們。我們會看時勢做編曲,看情況去做任何東西。我考慮到有老人會批評,所以節奏不可以太快,大家唱的時候跟不及。
我是教音樂的,我教鋼琴、樂理。家弘是在社福機構出作。其他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工作。《聖經》也有說,「你要馴良像鴿子,也要靈巧像蛇」。不能單單向前衝,要有計劃。司徒華也說過,「你要做民主事業,你就要有一份工作,不能全身投入。你要做這件事,你就要有一份正職。」
平時很難湊時間,所以我們不常練,很難七個人湊在一齊。有時候一兩個沒來就沒關係。
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你試試叫TVB找我們,我一定去。
我們沒有賺過一分一毫。我們的CD所有收入都捐給支聯會,捐給六四的活動。我們去六四的所有演出都沒有收任何錢。
我們很專注在音樂,很少宣傳。還有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歌詞,都是講和平、講理想、講大愛,不一定說六四。例如有一個歌是關於關心同性戀的,叫《愛是大同》。有一些歌是寫給在流亡的人。其實不一定是政治,我們的歌不一定是偏激的。我們不是一定要推翻共產黨,這多少跟信仰有關。
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你試試叫TVB找我們,我一定去。但之前有一個小插曲,我們有一首歌叫《八十後》,大陸一個電視台曾聯絡Kenneif,說這首歌很好聽,但不能用六四樂隊這個名字。Kennief就代表我們說,不出六四樂隊這個名字,就不給他們用。
擔心被人秋後算帳嗎?我們都已經開始了,你說要捉,就算我們停了,也可以捉我們。我們曾經寫了那麼多歌,我們現在不演出,也可以捉我們。沒事的,我們做的事是為這個社會發聲,除了《FUCY》(一首反梁振英的歌),那時有點生氣,但其他歌我們都沒有怎麼罵政府。我們想推動政府多關心我們。

關於自己:我想鼓勵病痛中的人,我明白有病的痛苦
我個人很政治的,我整個家庭都跟政治人物很熟。我父母都是教書的,也是教協的義工。我媽媽有幫司徒華工作,做助手,幫他搞很多活動。在未創作歌曲前,我是幫忙助選的。我十二三歲時,我幫李柱銘助選,幫忙貼信封,洗樓(上樓宣傳)。之後有一個叫黎志強的區議員,當時我在澳洲,我就說不如我改一些詞幫你助選,作了三首很搞笑的歌。到六四19週年,有一首叫《家》的歌,就是我正式為六四晚會做的第一首歌曲。
到六四20週年就有另外一首歌叫《20年》,是把《歷史的傷口》這首歌,改成廣東話。司徒華看了就覺得很好,但他提醒了我一樣東西,很重要。就是你作詞時,如果人家有給你一個原曲,你最好不要改人家任何一個音都可以作得好,就叫做好了。還有中文字有節奏,每個詞都有不同長短,你押韻時,不要勉強縮短那個詞的長度。他教我很多中國文化的東西。那時我見到他一個小時不到,就把這些全告訴我。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維園晚會,坐在草地上,以前的草地可以進去玩,現在不行。我很小,坐在那幾個小時,也不會喊尿急周圍張望。坐在那裏,很專心唱歌,很喜歡聽那些歌。他們會叫「打倒李鵬」,一開始四年,「打倒鄧李楊」、「打倒袁木」,現在沒有了。以前會喊人名,批鬥。
無論你有什麼病痛、什麼困難,其實困難也會幫助你,困難很寶貴。
我年年都參加晚會,除了去澳洲無法參加。父母一直陪我參加六四集會。一家人,參與25年。這件事很特別。六四是理想,不是口號。
我在澳洲八年。中三就去了。因為病,我讀不了書,香港壓力大。我有一個沒和別人說過的病,叫抽動症、妥瑞症。這個病小時候很厲害,現在好很多。因為多巴胺太多,要吃藥。莫札特也有這個病。我想鼓勵有這種病的人,沒什麼人鼓勵他們。無論你有什麼病痛、什麼困難,其實困難也會幫助你,困難很寶貴。病的特徵是想東西會想得很深入,有些強迫症。抽動症的人創作很棒,思想很快,藝術方面很快。因為我有病,我很明白有病的人的痛苦。我最近學氣功。也不是氣功,學呼吸,好很多。9點睡,6點起來,很精神。
我寫政治歌,包括詞和曲,加起來有30-40首。關於六四、社會。我覺得很悶,有一首歌《獅子山下》,我最近作了首《獅子山上》,都是正面鼓勵大家追尋理想。我還寫了首還未公布的歌叫《梅蘭芳》,我很喜歡中國文化,我不寫情歌的。
我也嘗試用國語寫歌,有段英文歌詞,是特意的。我希望有國際關注。我知道六四25週年是有影響力的,我不知道奧巴馬會不會看,可能有看,我特意要今年引起世界關注這件事,我特意寫得內地也可能聽到。我遲些可能想打入國際。不過慢慢來。
我也想有給音樂公司寫歌的機會,想賺錢,但沒有。接下來我會參加CASH的比賽。寫了一首《後世界杯之歌》,你不要登喔,可以提一下。關注世界盃之外,關心貧苦的人。我爸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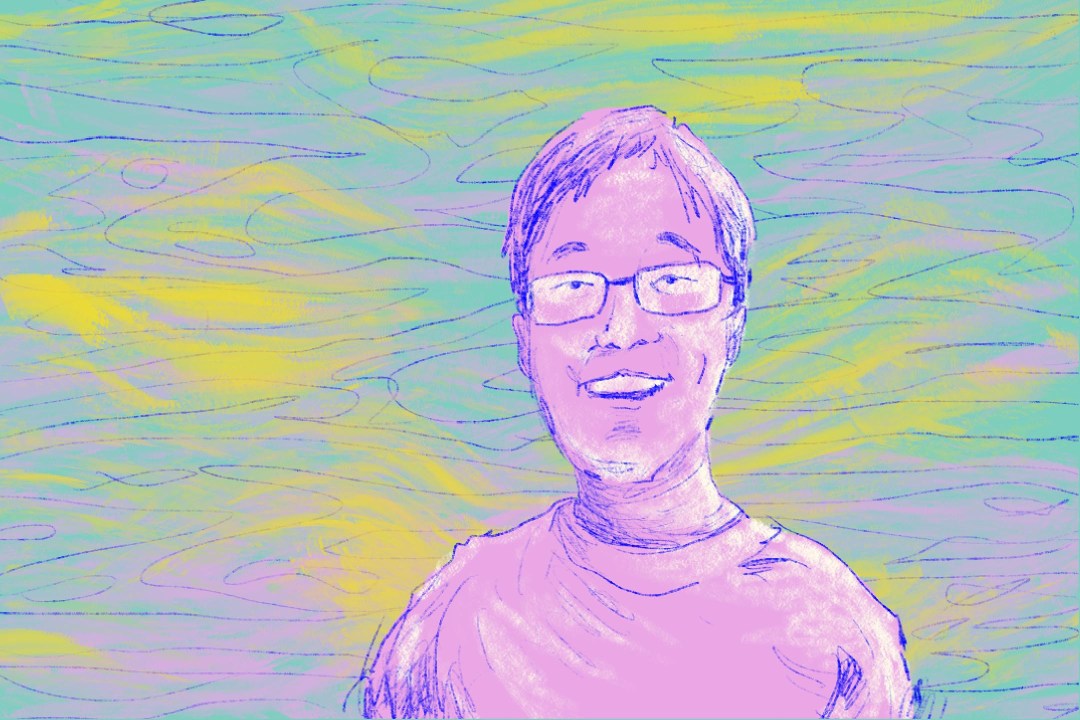




GOOD MEN, REST IN PEACE.
感謝林律希,民主會戰勝歸來,主懷安息。
@Windgoeson 謝謝你的說明,我相信閣下也不是要為防火牆辯護或是洗地。
在這個充滿謊言與猜疑的時代,「資訊準確」是我們讀者迫切渴求的事物,也因此我覺得你也不算是真相潔癖,只是以讀者的身分提出改善建議而已,這點對於媒體(特別是端這一類的),是相當重要的聲音。
只是,在專制國家的語境下,「資訊自由」與「資訊準確」同等重要,甚至在其之上。大部分端的讀者,不是從內地翻牆的自由網民,就是自由面臨直接威脅的香港人與台灣人。加上最近網軍猖獗,因此我們對此非常敏感,很容易群起攻擊「可能是」反對資訊自由的聲音。我相信閣下認為「扣你帽子」的人也並非惡意,而是對你的用意有所誤解而已。
既然這篇的重點也不是防火牆,其實也可以考慮先回覆文章主旨,然後再PS加上對於文章細節準確性的疑問。這樣評論區會少掉很多無關題旨的爭論,有助於我們真正的讀者交流意見,算是多贏,希望你可以考慮考慮。
抱歉佔了評論區的版面,關於正文我會另開評論。
額,沒有想為惡狡辯啊,可能我知道算法應該不會漏掉這樣的情況吧。
要驗證起來很簡單呀:
1. 你用一個正常的微博帳號,發布下帶有「viiv樂隊,民主」的一個微博。
2. 登出你的帳號,(因為有時他們會讓有些內容只被你自己搜到來隱藏),去微博首頁搜索「viiv樂隊」,看下是否能搜到?
3. 你可以再回去試一下發帶有「六四樂隊」的微博,這個是直接不讓發的。
搜六四樂隊搜不到不是因為這隻樂隊而是因為六四兩個字。
誰都不喜歡大陸那種高壓環境,不過可能我比你多一點對事實真相的潔癖要求,就事論事,只是希望作者在寫東西時更基於事實,卻被惡意扣帽子,也是挺無奈的。
洗地姿势太低了吧,这微博里只能搜索到一条13年的微博,百度里只能搜索到三个真的和viiv樂隊有关的条目,显然是没被算法概括进去,倒是你为恶狡辩时真的有点恶心人
我觉得倒更可能是这个名字VIIV还没达到需要过滤的火候,只不过是在微博上实在是无人关注而已,这跟其他敏感词,比如你搜六四只能出六四手枪,是不一样的。
楼上的我搜了啊,只搜出一条微博。这肯定有做屏蔽和过滤啊。
於淵是鄒思聰吧...
到現在VIIV的CD還是我最愛的專輯,謝謝林先生為我們填了如此美好的詞。
作者说,“在中国墙内的互联网,你搜索不到这个乐队的任何相关信息”
不用注册,打开weibo.com搜索一下「viiv樂隊」你会发现这并不是敏感词。
我不是很理解,一些挺好的人或事,为啥一定要用些false statement来试图加强。
脑子里想写一些话的时候,先去求证一下不好吗?
彷彿看到了在《亞洲週刊》時的夢遙。
謝謝謝夢遙老師!看完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