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從事現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者來說,香港可以說是一塊「福地」:這裏距離中國大陸足夠近,是近距離觀察這個東方神秘巨人的前哨站;但同時又距離北京足夠遠,即便在九七之後、尤其是2008年之後日漸逼壓的氣氛中,學者們仍然能相對自由地收集資料和發表研究成果。更不必說,在兩岸四地乃至輻射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格局中,香港始終處於信息和人員交匯的樞紐地位。
在這種格局下,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自1974年開始學習中文後,他在1976年到1977年間先後去了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正逢毛澤東、蔣介石等政治強人相繼辭世,兩岸都醖釀着新的變局,從此他和遠東結下不解之緣。從1994到1998年,高敬文負責建立並主持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台北分部,隨後在1998到2003年間,回到香港擔任該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主持中心季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2003年以來,他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自2007年起,又赴香港浸會大學擔任政治學系主任。
或許是出於「台灣女婿」的緣故,講一口台式温良國語的高敬文,曾在1990年代開始更多關注台灣政治體制和兩岸關係,但最近十年間,他的學術研究重點明顯更加轉向中國大陸和更加宏觀的論題,先後出版了《中國的國際政策》(2010)和《中國政治制度:邁向一種新的威權均衡》(2014)。而今年4月出版的法文專著《中國的未來:民主或專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e ou Dictature*,中文版預計於2018年末在台灣出版)則將重點放在了習近平執政之後的政治/社會演進。
《中國的未來:民主或專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ce ou Dictature)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出版社:Gallim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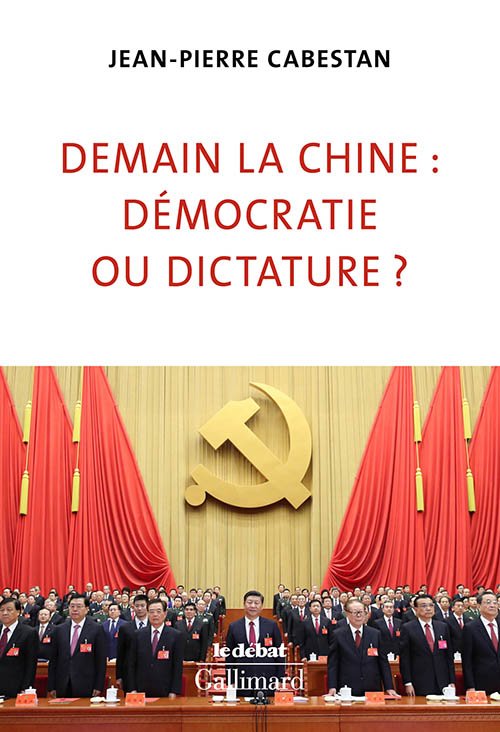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新著延續了一個「古老」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在冷戰之後,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歷史終結」卻最終落空,在這一教訓之下,中外嚴謹學者們對這種宏大敘事越來越持謹慎和懷疑態度,他們開始意識到,即便未必能斷言「中國問題」已經全然跳脱政治學一般規律,但至少,相對於蘇聯解體之後的樂觀情緒,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已經超乎人們想像。
但或許正因這一問題充滿魅惑,不斷吸引着學者們以學術聲譽為賭注,冒着落空風險,做出一次次預言式的判斷。高敬文以英文世界此前的同主題著作為理論假想敵,特別點出了早至福山、章家敦、黎安友(Andrew Natha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和裴敏欣等人近年來的論述——這些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無論着眼點是意識形態還是具體政策,都斷言中共黨國體制難以為繼,正在走向衰落、甚至崩潰。
然而高敬文質疑的問題是——中國體制真的處於危機之中嗎?在他看來,上述悲觀論者指出的經濟減速、政治僵化、腐敗叢生等弊端,北京並非不知情,但運用政治、行政、司法和經濟等各方調整措施,至少到目前為止成功應對了危機,並且逐步改造官方意識形態以適應經濟發展,使得一黨體制免於遭受挑戰。在全球民主力量相對衰弱的背景下,中共還進一步展現出自我調整、並長期掌控局勢的能力,同時讓大部分的社會階層認可其壟斷政治權力的合理性。
在2014年的著作《中國政治制度》中,高敬文提出「新的威權均衡」概念,而在新著作中,他重申了這一概念,並將其作為理解當下中國的框架,同時為它限定了一個時間範圍:在未來二三十年期間,這種均衡態勢可能將一直維持。即便這一體制此後趨向放鬆,仍將很大程度上帶有「威權的、精英的、父權的、帝國的」色彩。他多次重申上述四項特徵,並悲觀地警告,中國的民主轉型很可能是遲緩、混亂且不完整的,伴隨着改革力量的失敗嘗試、保守力量回潮甚至危及國家統一時軍方出手干預的可能性。和許多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研究者的樂觀期待相反,在高敬文眼中,經濟全球化未必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扮演積極角色,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經濟和外交上的相互依存,反而可能會削弱轉型力量和外部不穩定因素的生成。
但與此同時,高敬文的研究也絕非為「中國何以成功崛起」而背書。在信念層面,他甚至用篤定的語氣寫下:「很顯然的是,中國的體制並不比蘇聯、北韓或台灣威權體制更加永恆不朽。」「長遠來看,這一體制毫無疑問註定要讓位於另一種體制,中共註定要麼消失,要麼轉型,在一個更為開放的體制下同其他政治力量角逐權力。」
也正是從這一信念出發,在諸種理論駁難之後,他最終選擇重新同黎安友、沈大偉和裴敏欣等人站在同一陣營,從捍衞民主體制為出發點,共同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抱「絕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或許正是這位「兩岸通」學者的信念、理論和現實感相結合的底色。
端傳媒專訪了高敬文,以下是訪談摘要:
## 中共的「適應能力」會有極限嗎?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近年來出版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的著作,包括對宏觀政治體制和對外政策的介紹,今年的新著又涉及到中國的未來是「民主還是專制」這個經典問題。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您對中國的看法有沒有發生什麼改變?**
**高敬文(以下簡稱高):**應該說沒有特別大的改變。習近平上台以來致力於集中權力,中國往更加威權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程度更強,這和我當初的預想基本一致。
但我想中共也沒有其他選擇,一方面,它必須鞏固自己的專政,如果不改善、調整治理模式,它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制度上實行開放,它又必須朝民主化方向發展,很難開放到一半停下來。所以,要麼強化威權主義,要麼進行民主化改革,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我想中共領導人很清楚這種選擇的困難程度,但目前看來他們選擇了前一種。
不過,他們鞏固專政的方法很聰明,一方面繼續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更加細密地「維穩」,打壓要求民主化的力量,例如現在正在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我想這也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城市化帶來的挑戰。目前,中國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已經高達約60%,而且還在繼續增長。如果有70%的中國人住在城市裏,會對穩定造成更大的挑戰,因為對現狀不滿的人會更容易組織起來進行抗議,當局對此特別擔心,所以要提早進行準備。

**端:您在書中多次強調一個概念,就是中共的「適應能力」(capacité d'adaptation),您如何定義這種能力?它在哪些方面展現出來?**
**高:**這種適應能力的首要方面,是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現在所謂的「五年計劃」是指導性、而不是命令性的。在這個大方向下,市場和私營企業發展得很快。
其次,政府的運作方式也發生了相應轉變。到目前為止,中國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個「服務型政府」(尤其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但在相當程度上,中國政府的確是在為那些有能力賺錢、創新並推動經濟增長的人進行服務。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40年(1978-2018)為長週期來看,中共的適應和調整能力是很可觀的,很多方面已經完全不一樣。和40年前相比,政府部門已經公開得多,但黨務系統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透明度。比如在針對高級官員的腐敗案件中,我們沒有辦法通過獨立來源核實涉案金額的可靠性。
**端:這種適應能力會有極限嗎?**
高:當然會有。我在書中用了一個概念——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同樣也使用了,就是 atrophy(法語為 atrophie,沈大偉著作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被譯為《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但 atrophy 或 atrophie 還包含「衰老」、「萎縮」或「損耗」之意——編者注)。
第一個表現是意識形態的弱點。官方理論——從馬列主義到習近平思想——和民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雖然現在中國官方重新大力弘揚馬列主義,但誰會真正去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而且另一方面,指導思想的內容越來越空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難說有一個官方的明確定義,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更是如此。
第二個方面是反腐敗。雖然習近平上台以後大張旗鼓地反腐敗,一度遏制了公款消費和境外旅遊,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運動後繼乏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澳門賭場,此前從2013到2015年,的確去澳門賭場的人數驟降,但我觀察到最近幾年又開始慢慢回升。另外一個導致反腐敗成效有限的因素,是政治權力和發財機會密切聯繫在一起。我不否認有些人是白手起家創業成功,但同時高層領導及其家族也的確憑藉優勢地位大發橫財,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無法建立,這就是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一個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方面,是中國高層政治中女性地位之低,她們的角色可以說幾乎等於零。在經商、科研等領域,很多中國女性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十九大之後產生的25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一名女性(孫春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裝點門面的考慮,實際權力比重並不相符。從這一點上,當代中國政治在男女平等問題上的保守程度甚至超過了毛澤東時代,回到了更低的水平。當然,我並不是說毛澤東時代的男女平等是真實的,但今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退步。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國社會的民主思潮目前影響很有限,但長期來看還會繼續發展。相比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現在民主思想的影響其實要大得多。六四前夕的青年學生對民主有美好的夢想,但其實並不了解民主本身,看法很模糊,有很多幻想,而現在不太一樣,真正了解民主政治的人當然還是少數,但也比當年多得多。
## 中國社會關係緊張的源頭是什麼?
**端:您在書中提到城市化是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內部緊張加劇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看到,2017年底以來北京發起針對「低端人口」的驅逐行動,顯示出當局可能會用強力方式來控制城市化的走向,但即便手段粗暴,似乎也並沒有激起大範圍的反對。**
**高:**沒錯,對於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天堂,但當局不能完全把民工趕出去,因為不管哪個城市,都需要民工提供服務,所以當局會盡量保持平衡,既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數量,同時維持基本服務來保持穩定。
從北京大興火災後續來看,社會事實上有一定反彈,可是反應有限。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這些民工顯示出逆來順受、聽天由命(fatalism)的一面,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但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中產階級這次有新的反應。我之前在寫書時認為,中國中產階級通常比較自私,不關心民工群體,希望民工走人,但這次大興事件發生後,出現了一些社會團結跡象,中產階級對民工發出支持聲音,認為北京市政府太過分了,雖然這種批評聲音來自於很少數人,卻是一個新現象,值得觀察。

**端:您提到另一個可能導致社會壓力加劇的因素是不公平的狀況,尤其是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對於法國學者來說,這種不公平很難忍受,可是中國社會卻似乎更容易接受這種不公平?**
**高:**的確,和法國相比,中國社會更像美國的情況,人們更容易接受社會地位差距。但我的看法是,中國人可以接受「差距」,但不能接受「不公平」。比如政府做一個決策,讓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損,馬上就會有反應,會激發怨恨,他們對這個很敏感,但是對社會經濟地位差距不敏感。看到別人發財致富,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相反,法國人不喜歡看到別人發財,別人發財了馬上會想辦法徵税、或者施加輿論壓力等方法。而在中國,富人更像是一個榜樣,會激發更多的競爭精神。
但是,當社會差距變太大時同樣會出現問題,一個例子就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房價問題。早先在體制中佔據一席之地的人,包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可以通過單位補貼得到好處,而現在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如果父母沒有錢的話,憑自己能力買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的作為不夠,比如廉租房開發得太少,進展太慢,因為地方政府從這些項目中得不到好處、賺不到錢。這種差距持續下去,會起到階層分化的效果。
**端:這就涉及到您在書中提到的第三個緊張來源——對政府的期待。您覺得中國人對政府有很高期待嗎?或者說,和歐美福利國家相比,中國人似乎習慣了政府提供一個相對較低水準的公共服務?**
**高:**是的,中國人的處世觀念很務實:如果他們知道廉租房數目有限,就會想更多的辦法動員其他社會資源,例如向親戚朋友借錢去買商品房,而不去問責政府為什麼不蓋更多廉租房;如果農民工覺得城市生活無論如何都比留在鄉下好,那麼他們願意花更高價格去購買教育和醫療資源——雖然往往不能如願——但很少要求政府提供平等待遇。雖然很多人不滿意,但總體上還是「聽天由命」更多,很少有比如民工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事情。
## Is Democracy Dying?
**端:近年來在歐美——包括在法國,民主的運作遭遇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這會影響一部分中國人對民主體制形成正面看法嗎?**
**高:**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書裏的結論也談到這個問題。目前民主政治遭遇很大的危機,這一點毫無疑問。危機的原因很複雜,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政府不敢做重大決策,福利社會模式面臨危機,同時全球化導致社會差距加大。民粹主義當然是民主政治的負面因素,但在我看來,民粹主義並沒有走到建立專政、挑戰民主制度的地步。
民主制度的弱點和目前現狀,給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提供了機遇。中國正在利用這次危機,第一保衞自己的制度,第二輸出自己的模式。雖然中國否認這一點,但事實上正在將「中國模式」作為一個解決方案輸出,試圖影響其他國家,所以現在仍然存在着一場意識形態競爭,甚至是戰爭。
但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不會永遠持續,十年後的情形肯定和今天又有所不同。就目前而言,繼續深入發展和鞏固民主,是應對民粹主義的唯一辦法。
**端:您在書中直接使用了一個法國政治語境中的詞彙——lepeniste,指的是法國極右翼政治人物勒龐家族的支持者。這讓人想到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很多旅法華人、甚至中國國內很多人傾向或者支持勒龐(Marine Le Pen),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高:**這種現象並不意外,但目前還沒有人深入研究華人/華僑的政治行為這個問題。
Lepeniste 這個群體的基本特徵是強調安全高於自由,並且對外來移民(在中國語境中則是針對民工)持歧視態度。
事實上不管在中國、法國、還是在非洲,這個群體的模式都是類似的,都強調自身的安全,例如前幾年在巴黎北郊 Aubervilliers 被殺害的張朝林案件後,很多中國人出來遊行,抱怨治安狀況,要求改善安全。我完全可以理解這種訴求,但同時應當看到,這種訴求是和中國人對黑人及阿拉伯人的歧視是重疊的,認為法國的「外國人」太多,應該進行限制,但卻忽視了自己也是「外國人」的事實,只不過在法國的中國人比較聽話守規矩而已。
**端:但中國人會認為,自己是比較守規矩的少數族裔,所以即便勒龐上台也不會拿中國人怎麼樣。**
**高:**是的,而且極右翼也在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想利用華人的這種心態來拉票。比如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曾經多次去一戰華工墓地祭拜。
中國人比較保守,他們要賺錢,要求治安保障,不想要「亂七八糟」的人,相對左派來說,他們對治安問題特別不寬容;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大部分中國人支持死刑(當然今天雖然歐盟成員國已經廢除死刑,但很多法國右派仍然支持死刑)。這種對「法律和秩序」的重視,和很多旅美華人給川普投票的邏輯是類似的。
**端:川普上台及其一系列政策,對中美關係和歐美關係同時形成挑戰。從政治角度來看,您如何評估這一事件對民主體制的影響?**
**高:**川普的上台,是美國民主衰落的結果——自由主義的精英和普通民眾的距離太大,很多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下降。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另一方面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佔據主導地位,華爾街掌控了這一體系,工業資本被邊緣化,很多工廠從美國遷出,搬到中國大陸或者東南亞國家。雖然美國本土還保留一些製造業,例如航空航天等和國防相關的產業仍然有較高水準,但相比德國等競爭對手,許多產業缺乏創新、因此缺乏競爭力。
我當然希望美國的民主能保持並改善,但是接下來具體走向很難說,不是每一個民主體制都註定成功,也有可能會失敗。
但是另一方面,應當看到,20年前整個拉丁美洲基本都是獨裁國家,而今天除了個別幾個國家(如古巴)以外,大部分都是民主體制國家,當然其中並不是沒有問題,有些國家腐敗嚴重,但畢竟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了,而且得到民眾擁護。
**端:這就涉及到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演化進程會隨着所謂「第三波」或「第四波」的浪潮共振,還是它太特殊了,獨自成為一個世界,必須得單獨對待?**
**高:**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歷程,不能輕易比較。但我依然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有兩個原因,一是東亞傳統的儒家思想和民主化沒有根本矛盾,台灣、韓國、日本都是例子;二是隨着中產階級教育水準的提高,民眾的期待也隨之變化,他們要知道政府怎麼使用税收,這個邏輯最後會導向類似當年美國獨立戰爭時的「無代表,不納税」——當然現在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中共適應能力也會在這個方面體現出來,它會給新的社會精英(如企業家)一點空間,通過人大、政協等渠道讓他們說話,聽取他們的意見——當然大部分情況下是假裝聽取意見。但同時應當看到,雖然目前這種議事渠道被新貴階層充斥(例如政協),他們還是嚴重依賴政府,小心翼翼不挑戰中共的領導,但是畢竟形成了一種經濟力量,並且獲得了一定的談判能力,當局不能完全忽視。
## 習近平的夢想是「新國父」?
**端:您的書中多次用 paranoia(偏執狂)來形容習近平的執政風格,您真覺得這是一種和他個人經歷相關的心理甚至病理現象,還是中共高層現階段的一種執政思路?**
**高:**主要是制度的問題。當然習本人有自己的偏執的一面,比如反腐敗運動,主要是從鞏固個人權力角度出發,但這種反腐敗運動激起反彈,在政壇高層製造出很多敵人,從薄熙來、令計劃一直到郭伯雄、徐才厚,這又迫使他一步步加大力度,以保證自己的安全。
我之所以用這個詞,主要是基於一種可笑的矛盾,即中國政府一方面已經將社會控制得很嚴密,但另一方面還是有巨大的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種偏執狂式的做法。
我對這種偏執狂提出的解釋,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很大,相對而言黨的能力有限,因此發展出一套「維穩」措施來保證穩定,最新的發展則是建立了「社會信用體系」進行控制。
**端:從這次修憲來看,您認為習會在多長時間內把持權力?**
**高:**我認為會到2033年,因為目前半官方的說法是到2028年,也就是比原定多一個任期。官方的說法是,即便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也不意味着終身制,但我認為他可能會一直做到2033年,也就是他八十歲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新的「國父」。
但這種預測是以他身體始終保持健康為前提的,畢竟現在他的健康狀況很不透明,如果出現癌症等重大疾病,當然要提前指定接班人。他表面會採用黨內協商醖釀的形式,但最終還是由他自己指定,不會用什麼黨內民主的方式。

另外,我所謂的2033年退休,其實確切說應該是「半退休」,就像當年鄧小平的做法一樣,仍然對政策保留極大的影響力,扮演垂簾聽政的太上皇角色。雖然目前來看陳敏爾似乎是他的政治接班人,但如果真的要到2033年時,陳也有73歲,因此還存在很多變數。
**端:您在書中還使用了一個詞——Nomenklatura,這個詞原來指前蘇聯的官僚集團,您現在借用這個詞來分析中國的官僚集團,那麼官僚集團在中蘇兩國有什麼異同?**
**高:**相似之處在於二者選拔晉升的方式,都是上級提拔下級,上級的「組織部門」對候選人進行政績考察,交給高層領導人來做決定,沒有什麼民主選舉的因素,在這一點上是一樣的。
但對於今天的中國官僚集團來說,他們和蘇聯時代最大的不一樣,是他們現在很有錢(笑)。蘇聯官僚集團雖然也享受很多特權,但當年畢竟是計劃經濟體制,經濟總量規模有限。而中國的官僚集團雖然自己不能下海經商,但家人很多都在經商。「巴拿馬文件」、紐約時報、彭博社都披露了最高層的狀況,在這種示範效應下,整個集團都上行下效,雖然廣大中層官僚不可能攫取天文數字的利益,但操作模式是類似的。可以說,他們在經濟轉軌期間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兩種體制所能提供的好處。
## 中國未來將走向民主化嗎?
**端:所謂的「黨內民主制」,會是一條可能的轉型出路嗎?**
**高:**中共的問題是,從創立一直到現在都保持着某種秘密會社的作風。很多決策是完全不公開、不透明的,不要說普通公民,就是一般的黨員都完全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2007年胡錦濤曾經提出發展黨內民主,但到2012年卸任為止並沒有取得太大進展,到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沒人再談了,沒取得任何結果。
在我看來,一黨制和民主化之間存在根本對立。也許最終會證明我錯了,但目前看來,二者之間存在深刻矛盾,(在中國)Party 和 State 二者沒法分開。

可能有些人曾經對黨內民主化抱有希望,但他們很快就面臨了激烈的矛盾。因為如果涉及到黨內信息公開,會涉及到很多決策過程、選舉過程、以及領導成員的財產狀況,這會帶來很大的風險和挑戰。
當然,不排除習近平在加強控制之後,會採取一些「放」的措施,但這仍然是統治手段,而不會導致中國走向民主化。1986-1987年那時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機會,但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切。從那之後我就很悲觀了。不光是鄧小平,而且是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大部分人對蘇聯解體的教訓都感到恐懼。要維持一黨專政體制,就得一方面加強調整的能力,另一方面繼續打壓異議者。
雖然福山的論斷曾經被人嘲笑,但他的一些理論還是有道理,比如他說如果沒有「民主人士」就不會有「民主化」,精英群體的角色很重要,不光是要支持民主,而且要有實際行動,否則不會有民主化,目前中國也有這種人,例如許志永,但還是少數,而且被打壓得很厲害。
**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雖然體制的本質沒有變化,但普遍的感覺是控制正在鬆弛,所以有所謂「後極權主義」的說法,但是到習近平主政之後,黨對社會的控制重新收緊。但問題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收緊似乎也一樣可以行得通,並沒有激發強烈反彈。**
**高:**我寫書時儘量試圖超越習近平執政的時代因素,雖然並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退休。但從局外旁觀者來看,中共如果想保持一黨專政制度,必須懂得「放」和「收」兩手,這也是中共領導人此前一直用於保持穩定、改善治理的方法。
現在看來,到2008年是胡錦濤時代「放」的一個高峰,雖然《零八憲章》一出來就受到嚴厲打壓,但在當年這樣一份聲明能問世,本身就表明有一定空間。而現在絕無這種可能。
我的結論其實比較樂觀,還是認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會成功。尤其是,中國人最終會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被一個秘密會社式的政黨所領導,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問號。
## 香港的選舉模式和大陸選村長是一樣的
**端:您長期在浸會大學任教,對來香港的大陸學生有什麼觀感?**
**高:**因為我是政治學系主任,所以接觸到的內地學生也多是這個領域的。我個人覺得大概分為兩種非常不同的類型:一種學生之所以來香港讀政治學,是因為他們知道在內地很難做真正的政治學研究,只能做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這些領域,所以這部分學生比較有獨立意見;而另外一種來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則是有錢家庭的孩子,這種人對政治沒有興趣。他們之所以來香港,主要是為了留夠年頭然後拿身份證。
**端:以您在香港的實地觀察,如何評價雨傘運動的成功和失敗之處?**
**高:**應該說是失敗了,因為沒有取得什麼直接的成就。北京對香港普選的既定政策沒有改變。按照目前的選舉模式,本質上和中國大陸選舉村長是一樣的:由黨支部醖釀提名候選人,然後村民進行投票。
但與此同時,我覺得這場運動也有成功之處:香港人的政治熱情被激發出來,公開的政治辯論範圍擴展,人們更傾向於公開地表達想法。但目前北京誇大了「港獨」運動的影響力,並將其作為打壓民主言論的一個理由。
**端:一方面「港獨」的影響力被刻意誇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的確看到六四紀念問題上,香港人的熱情在下降,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高:**是的,現在在不同代際間存在一種意見分裂。老一輩的人仍然堅持關注大陸民主化,要求平反六四,但很多香港年輕人已經對大陸民主化沒有興趣,他們更關注如何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推動本地進一步民主化,但香港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是由北京中央政府決定的,我們對此不能太樂觀。
但至少,香港年輕人可以捍衞自己的自由,保持公民社會的獨立,我認為這應該是當下最重要的目標。在這方面我倒不是太悲觀。因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強韌,非政府組織很多,不管是和政治或者和教會有關,不可能被統統取消掉。
無論如何,香港將繼續會是全中國最自由的地方,也會持續影響中國的政治未來。


法文的“民主”一詞為démocratie而不是*démoratice*,疑似文中拼寫錯誤?
这篇文章倒是跟我的观点有点差不多。中共下台,中国民主是必然的事。可是时间不会那么快,我想最快也要在2030年或者是2050的前后
我總是很好奇,在中國要做政治研究,目前應該還是受到一定箝制,雖然作者Jean-Pierre Cabestan是身處香港學術圈,但距離皇城遙遠,他的研究來源跟推論是否真的有一定立足點?不過這篇訪問還是給我一些啟發
民主的前提是宪政,是将权力关进笼子之后的结果。反观现时的中国,一人的权力是完全凌驾于所谓的宪法之上的,同时也凌驾于某党党章之上,连其党内都无法实现“宪政”,更何况全国。
Cabestan的受访内容很多都是从很实际的事实出发,进而做出判断,特别是在谈到習与党内民主制的问题上,结论基本都是短期内不看好的观点,同时从八九事件、党内财产公示、香港占中等一些历史具体问题出发,也基本认可了体制内存在很强自我纠“错”的能力,可以说是一种长期不看好的表态,但不知为何最后又表现出一种未来会更好的姿态,跨度有些偏大,缺乏说服力。
受訪者對中國的認識,完全停留在表面上。習近平只是個兒皇帝,權力基礎根本不穩。並且就在最近幾天,習的權威已經被大大削弱了。雖然習最後有一定概率會反殺,但無論結果怎麼,中國都注定在幾年之內進入一個長期的動蕩時代。
自由主義只是民主的衍生品,隨着後者的進一步發展,前者必將被拋棄。爲什麼所謂自由主義的精英們都害怕民粹呢?因爲民粹就意味着普通民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權力,這樣的話這些精英們也就沒有了特別的話語權,也就失業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總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卻從根子裏排斥普通民衆的權力。
Cabestan的觀點跟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觀點相比要務實的多,因為他看出來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意識形態的不重要,也看出來了中共的變通性,佩服!
跟端之前的幾篇學者專訪一樣水準的好文。每次閱讀都會幫我梳理和解惑。
我本來想說中國怎麼會沒有啟蒙的歷史。但後來想想,還真是沒有。因為無論誰在台上,啟蒙對於掌握權力都有絕對威脅。而民間對權力的適應能力又太「良好」。所以,要對中國人公平,他們還不完全瞭解碟子上可以有什麼選擇。
这篇专访真得很好,学到很多。感谢! 期待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
一党执政的民主也还是有的,看看胡温时代。谁曾想习一上台就如此的收紧,简直了!
维稳与监控的花费是惊人的,供养收买“自家人”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不足以填补这些巨大的开销,这个看起来超级稳定的政治体制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個人比較悲觀,中國沒有啟蒙的歷史,自由的種子從未被播撒,中共很大程度上是五千年封建王朝的繼承者,在現代化的外衣背後,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習本人就是皇帝。
在這種條件下,不具備傳播現代政治的土壤,對政治不滿又有機會的很多人已經離開了,支持憲政民主的永遠是少數,因為他們不斷在流失。支持政府(中共)的佔社會多數。
喊口號洗腦雖然看起來蠢,但是非常有效,學校教育又從未培養過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試想,合格的現代公民從哪裡來?
其一,這屆政府利用18世紀末-19世紀初「國恥」與今對比來維護統治正當性,官媒不斷傳播國際主義話語,自我膨脹的中國有可能走上納粹德國之路,給本國和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
其二,黨國黨國,黨在國之上,維護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與最普通公民的富足和尊嚴比,孰輕孰重?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像朝鮮這般貧困,其統治者生活水平是不受影響的。
2013年王岐山曾會見福山,會議記錄裡一段讓我印象頗深,他講,美國這個國家很會挑時機,國家先發展,過了百年後再把黑人拿進來,近幾十年又把女人拿進來,讀來讓我毛骨悚然,他絲毫不顧及歷史背景,不把人當人,公民個人的 suffering 他絲毫不在乎,追求「國家整體」的強大。
千萬不要心存幻想,把未來寄託於執政黨的「道德水平」之上,never live under kindness of a monster. 況且此處 kindness 要有個大大的問號。
solina
通篇充满了对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任何国家任何体制都有矛盾与缺点 将中共的矛盾放大并夸夸其谈 难以表现其深刻 此外 就男女平等来说 商业集团 基础干部等男女比例情况视而不见 竟然说男女比例相当之差 差于毛时代? 真的令人咋舌 前不见吴仪后不见傅莹?说到女姓名单 更应该讲政治局常委和内阁比才合理吧 有才能者居上位 本来就跟性别无关 占此角度看 不知是何居心 最后再说一点!!腐败想来不是民主能避免的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遏制腐败的发生 中共是专制 但是跟古希腊的所谓民主制度相比 简直不要好太多
寫得太好,看到最後的心情真的太複雜了。
「因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強韌,非政府組織很多,不管是和政治或者和教會有關,不可能被統統取消掉。
無論如何,香港將繼續會是全中國最自由的地方,也會持續影響中國的政治未來。」
默淚。
有个小问题,但编辑或许还是需要检查一下:文中有关“Nomanklatura”的一问里,该词是不是拼写出现了错误,应为“Nom[e]nklatura”?
见:
https://fr.wikipedia.org/wiki/Nomenklatura
感謝指出,已修正!
为什么很多客观分析之后,突然冒出一句“我的结论其实比较乐观,还是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成功。”,感觉很突兀,文中论据无法支撑题目和这样的结论,不知道书中有没有答案。
这篇专访真的太好了。解了很多惑。感谢。
这本新书会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