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於一位專欄作家的憑空消失,「失蹤」,成了這幾天中國的寫字人們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哈光甜是端的評論作者,他來信說,令他覺得可怖的,不只是「失蹤」後未知的危險,而是黑暗之中生命從未存在過的幻覺。它吸光了生的活力,讓一切都無意義。

每次遇到熟悉的人「失蹤」,越是抑鬱,我就越想去幫助別人,關心周圍所有的人。這不是因為我想去關心別人的苦難,不是因為我因為一個人的消失而想去珍惜還在的人。只是因為我脆弱,所以想要盡力在別人的生活裏、在這個世界上多留下一些印記,多讓別人欠我一些人情,多讓別人記住我的存在。
這類事永遠都是雙重的:你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那些權力力求讓你忘記的人,同時又絕望地希望別人也不要忘記你。除了不停底付出,不停底讓別人欠下你的帳,要在這個世界上留下印記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事。這個debt幾乎是個體在龐大的歷史和強權下的全部重量,輕如鴻毛。幫助別人的出發點,乃在於絕望。生命真的是一場苦旅。
忘卻是一種奢侈,記憶是痛苦的負擔。我們生來為了享受奢侈,卻總希望別人可以為我們承擔痛苦。我們不願分享別人的苦,我們選擇忘卻——這不但容易,還能獲得權力的嘉許。
但我們卻竭力不想要別人忘卻:我們把自己的名字告訴所有人,我們把名字印在名片上、寫在書裏、刻在石頭上、埋在土裏。我們希望通過名字可以永垂不朽;我們想讓所有人記住,我們曾經到過這個世界。
而死亡卻不一定是肉體的消失。曾有人講述過被逮捕後的經歷:她坐在警車裏,透過暗色的玻璃看着外面的車水馬龍。一切細節都如此清晰鮮活,一切生活都照舊如常:她的消失對世界毫無影響,因而她的存在對世界而言也就毫無意義。似乎她從來沒有存在過,在未來也不會存在。
隔着一層玻璃,似乎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平行宇宙。她希望聽到警察相互間可以聊一聊家長里短,這不僅會讓她放鬆,更會讓她覺得,玻璃的這邊,仍舊是一個有生命的世界。一邊是流動的時間,另一邊是死亡的沉寂。
死亡不是肉體的消失——死亡是你的名字飄零在風中,是你的聲音卡在喉嚨裏,即便放聲大叫也沒人可以聽到。死亡是連你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生的還是已經死了,是開始自問,是不是自己從未生過。
恐懼的目的,就是不斷生產這種懷疑。它希望永遠把我們囚禁在一個密室中——這個密室不是靜房,它也不狹小。它不黑暗,但也不光明。這個密室中有淡淡的光,牆壁是可以有回音的。恐懼要的不是徹底的安靜,也不是要我們迫於黑暗而產生幻覺。
恐懼要的是你在一個有微光的巨大房間中忍不住開始講話——不是講給任何人聽,甚至不是講給自己聽。它要的是你在這個有回音的密室中試探着通過發出聲音來努力確證自己的存在——它要的結果也不難揣測:你孤獨的聲音在空室中迴蕩,你開始發覺你的聲音很古怪,你開始發現這個聲音似乎不但不能確證你的存在,反倒似乎根本不屬於你。
在一個空蕩蕩有回音的密室中,你發現你不敢發聲、如鯁在喉。你喪失了最後一點可以向自己證明自己還存在的證據。你沒有被禁聲——相反,你的聲音通過回音反而得到了放大。但正是這個放大徹底奪走了你的生命,了結了你的呼吸。你開始害怕自己的聲音,你聲嘶力竭的吶喊反倒成了絕對的死寂。你寧願變成聾啞——你已經聾啞了。死去的人如何可以發聲?
我們的言和承載這個言的聲就像是即將靠岸的船拋出的纜繩。我們總期盼能有岸,岸上能有人——沒有人的岸只是固化了的海洋,而不是陸地;不能靠岸的船也不是船,只是海面上捲起的浪花。只有在岸上有人一把抓過纜繩,我們世界的一切才有意義,我們才能感到生的活力。
這訴求既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困難的:它最基本,因為它只要你抓住纜繩,只要你確證自己可以聽到,它不要求你在這之上做任何其他選擇,它只要你說「我聽到了」;它最困難,因為它要求的,是毫無條件的傾聽,是在絕大多數人聽不到或者寧願不要聽的時候,仍舊毫無條件地傾聽。它不要你做燈塔,不要你照亮整個海灘;它只要你做一個深深扎根在岸上在黑暗中甚至看不見的矮矮的纜桩。只要它拋出纜繩,就能確定你會在那裡。
我們不可能擊敗恐懼,我們也很難找到希望,一切看起來都堅如磐石天長地久。但我們都得記憶,我們只能像瘋子一樣癲狂地愛,記住每一個名字,記住每一件事。記憶是他們最大的敵人,也是我們唯一的武器。直到這個世界土崩瓦解、滄海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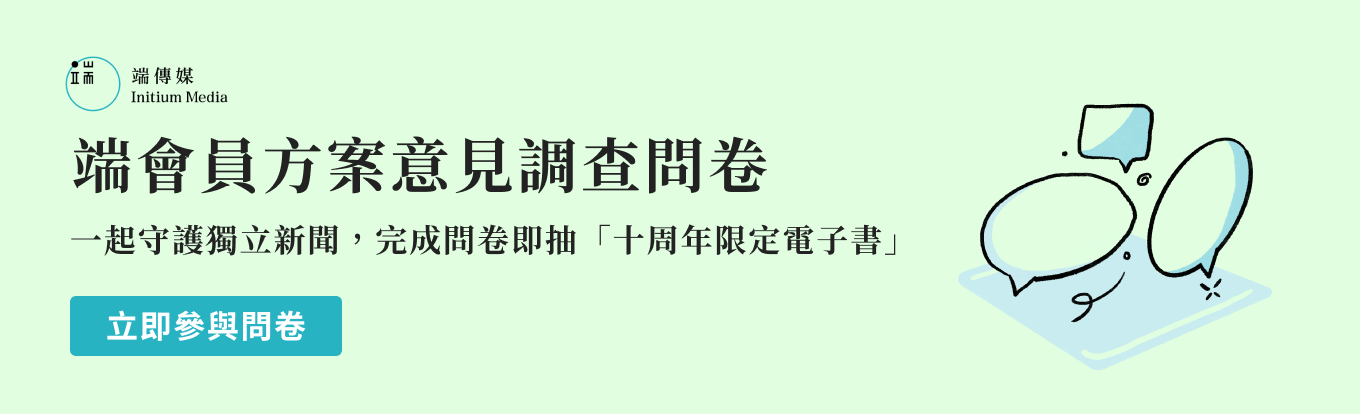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