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頂之上]身在穹頂之下,心在穹頂之上;觀往事、思當下、覓來者。
近半年來,在百忙之中一有空,我就趕緊寫要給兒子看的歷史書。這可能是作為父親的我,能夠給兒子的最好禮物;即便,這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寫這本書,是為了回答十年後或二十年後,我那火象星座的孩子必然會問:「把拔,當初你為什麼要把我從台灣帶到北京來?」
我猜想,作為母親的柴靜,心中也有類似的掛念吧?她的女兒,以及千千萬萬的零零後,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或許會問他們的父母同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霧霾這麼嚴重,為什麼還要把我生下來?」問題很沉重,但身為父母,面對這直問,是無可逃避的。
今年春節過後,以柴靜為主演的《穹頂之下》,被稱為公益紀錄片,以自己女兒出生之時的病變為開端,鋪陳中國霧霾的嚴重程度,然後節節叩問、進逼能源產業的弊病,最後收在號召每個人的自作為上頭;此片開春之際透過網路,而非CCTV,遍撒全中國。
當時網路上的褒貶幾乎都集中在柴靜及其團隊身上。但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形式上跟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2006年主演的奧斯卡得獎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非常相近:一個全國知名的公眾人物,運用ppt與公眾演講的技巧、論述一個大眾關心的環保話題,最後呼籲普通公民群起進行和平改變。
《不願面對的真相》,是近年來歐美諸多上院線的調查記錄片的濫觴。在此片取得全球矚目的前後,麥可摩爾的一系列調查紀錄片如《科倫拜恩的保齡》、《華氏911》、《資本主義:一个愛情故事》等等,揭發各種主流制度與論述的弊病,都受到觀眾與影展的追捧;這是紀錄片這個類型在上個世紀初成立以來,所未曾見到的現象。
而在中國,調查紀錄片向來是冷門類型。一方面,如果是內參影片,那麼就要有著類似中紀委那樣的低調行事作風,才有可能將真相上報;另方面,如果是獨立紀錄片,那麼就要如美式橄欖球四分衛那樣抱著攝影機進行各種閃躲,如徐辛導演的《克拉瑪依》以及王利波導演的《掩埋》與《三峽啊》;否則一不小心,就會有了這村沒了下店。
那麼,這次《穹頂之下》透過非官方的視頻網站進行大張旗鼓的發布,走老美的套路,其實,跟過往諸多調查紀錄片的風格與路徑,是很不相同的。從這裏,我想到《河殤》。
1989年中央電視台的扛鼎紀錄片《河殤》,跟《穹頂之下》有著相近的時代動力。《河殤》意欲改變中國千年來小農經濟的思維,鼓勵群眾擁抱藍色海洋的開放性;借用科學哲學家孔恩的話語,這是關乎思想價值的「典範轉移」;這部紀錄片在80年代末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引發知識界與文化界強烈爭議。二十六年之後,三天內創下兩億次網路點擊率的《穹頂之下》,則是呼籲大眾反思二三十年來「有房有車」的唯經濟思維邏輯,以節制當前過於虛胖而無法迴旋的能源產業。這是從既有發展主義模式脫出、尋找新發展道路的典範轉移。
有意思的是,跟《河殤》不一樣之處在於,《穹頂之下》的發布管道是所謂民營的視頻網站,而非官方的CCTV。顯見,這次典範轉移的力度,如果真有可能,將不僅僅及於影片所要陳述的核心理念而已,更及於影片所傳布的媒介本身。
深知中國人特性的魯迅早就告訴過我們:你無法叫醒一群裝睡的人。
然則,中國最終能有調查紀錄片嗎?這類的調查,最終能夠獨立於權力之外、有其自主意志,從而可以真正揭示真相、改造社會嗎?調查,是否其實是西方的玩意兒,跟它們所謂「普世價值」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抑或,中國有其固有特色的調查?而這調查,在什麼程度上,可以直接跟大眾產生立即關聯而不是只在深宮內苑裏發酵?深知中國人特性的魯迅早就告訴過我們:你無法叫醒一群裝睡的人。
調查也者,是針對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進行蒐證、紀錄、分析與再現,讓這些看不見摸不著變得可感可見,然後呈現在觀者面前,進而跟觀者的身心靈產生具體連結,繼而改變之。那麼,什麼是看不見摸不著?外太空、烏托邦、前世今生、海外仙山、量子物理、上帝佛陀,以及PM2.5。對於身陷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來說,現世此在是唯一可確定的依託,除此之外,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除非影響了當下眼前利益,否則並無探究或調查的價值;故而「祖宗之法不可變」向來是擅長以歷史為師的中國意識形態內核。
然而,調查的終極目的,難道不是為了要改革眼前利益團塊,放眼未來那尚未看得見摸得著的,新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如果這個文化體內在就缺乏對於那看不見摸不著之未來的想像與描繪,那麼,調查的意義與指向又是如何?這是調查在中國的根本悖論。因此,調查這件事在中國,不是掌握了多少統計數據與學者專家的科學問題;這根本就是個文化問題,亦即:有了「穹頂之下」,那麼「穹頂之上」呢?
當千千萬萬中國的父母親,擺開一切既有的、僵化的制式言說套路與懶人包,開始用新的態度,為自己的兒女,上下求索地回答這兩個單純不過的本體論問題時,中國的所謂悠久歷史文化,或許就啟動了另一程典範轉移的長征。
但,我因此就要質疑《穹頂之下》在現世此在的價值嗎?不。至少,柴靜作為一個母親,她奮力嘗試在回答她女兒會問的問題:「我從哪裏來?」;就一如我作為父親,嘗試要回答我兒子會問的問題:「我往何處去?」。當千千萬萬中國的父母親,擺開一切既有的、僵化的制式言說套路與懶人包,開始用新的態度,為自己的兒女,上下求索地回答這兩個單純不過的本體論問題時,中國的所謂悠久歷史文化,或許就啟動了另一程典範轉移的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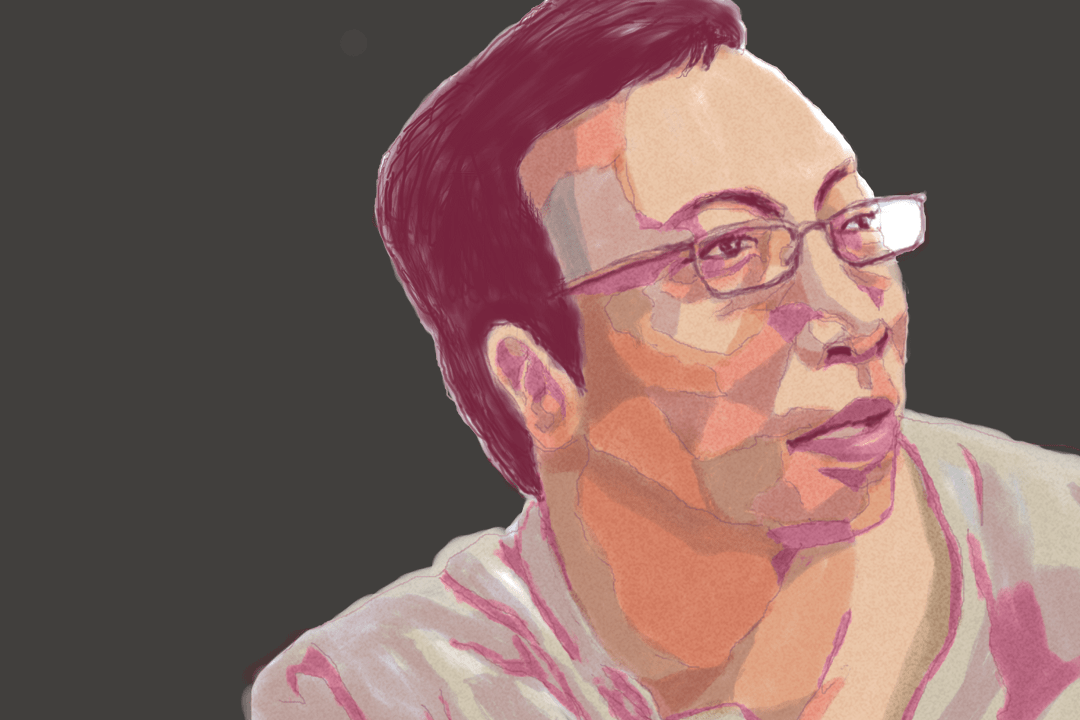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