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剛踏入2017年,教會人們「凝視」(gaze)的英國視覺藝術評論大師 John Berger 在巴黎郊區安息。同時作為英國作家、畫家、藝術評論家的他,留下許多藝術瑰寶給我們,並引導我們可以如何欣賞它們。
在藝術理論以外, John Berger 寫下雋永且富含哲思的文字,《我們在此相遇》以八個城市、八次穿越時間空間的「相遇」。在真實與虛幻之間,John Berger 既描劃城市風貌民情,更與相遇的人在散步中對話,乍看如日常瑣事閒談,細嚼後便知慧黠處處,都是大師的所思所想,並留下線索讓我們繼續反思、批判。
感謝大師 John Berger 寫下他所發現的東西,讓世人注意到、看得到。以下節選自《我們在此相遇》的第一章〈里斯本〉,獲麥田出版授權刊出。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
《我們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
出版時間:2008年3月
出版社:麥田
作者:John Berger
譯者:吳莉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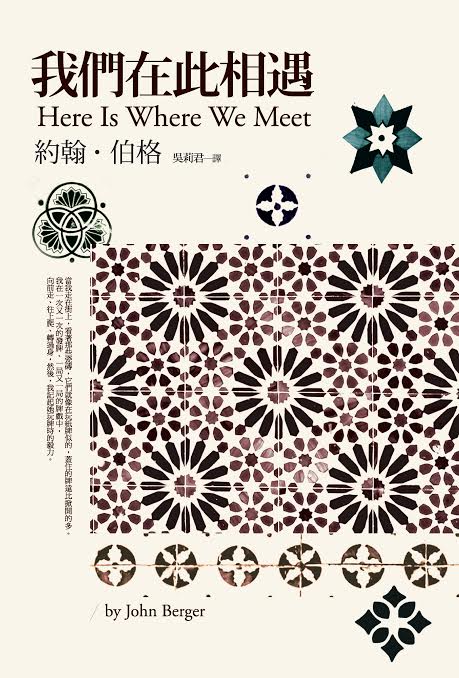
「所以時間不重要,地方才重要?」
「不是任何地方,約翰,是相遇的地方。」
5月的末尾,天氣炎熱,約莫攝氏二十八度。再過一兩個禮拜,就某方面而言始於太加斯河彼岸的非洲,就會出現在肉眼清晰可見的距離。一名老婦人帶着一把傘寂然不動地坐在公園長椅上。是那種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動。以這般姿勢坐在公園長椅上,她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一名男子拎着公事包穿越廣場,帶着每天每日往赴約會的神情。然後,一位面容悲傷的女子抱着一隻面容悲傷的小狗經過,朝自由大道筆直走去。長椅上的老婦人依然維持着她那展示性的寂然不動。那姿勢究竟是擺給誰看呢?
就在我喃喃問着這問題時,突然間,她站了起來,轉過身,拄着雨傘,走向我。
我先是認出她的步伐,過了好一會兒,才看清她的臉龐。那是某人期盼已久的步伐,期盼它走過來坐下的步伐。那是我母親。
[…]
在廣場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像說好似的,我們穿過對街,慢慢往「水之母」(編注︰原名為阿瓜里弗渡槽 Aqueduto das Águas Livres,是里斯本一個歷史性的高架渠,是18世紀葡萄牙最傑出的工程之一。) 的階梯頂端走去。 「約翰,有件事情你不該忘記—你已經忘記太多事情了。這件事你該牢牢記住:死者不會待在他們埋葬的地方。」
她開始說話,但她沒看着我。她緊盯着我們前方幾公尺的地面。她擔心跌跤。
「我說的可不是天堂。天堂很不錯,但我要說的剛巧是件不同的事!」
她停下來,咀嚼着,彷彿其中有個字眼包了一層軟骨,得多嚼幾回才能嚥下。然後她繼續說:
「人死了以後,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想住在這世上的哪個地方,他們最後總是會決定留在人間。」
「妳是說,他們會回到某個生前讓他們覺得愉快的地方?」
這時,我們已站在階梯頂端,她的左手扶着欄杆。
「你以為你知道答案,你總是這樣。你應該多聽你爸的話。」
「他解答了很多事情。我到今天才了解。」 我們往下走了三階。
「你親愛的老爸是個充滿疑惑的人,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得時時跟在他後面。」
「幫他揉背?」
「沒錯,還有別的。」
又往下走了四階。她放開扶欄。
「死者怎麼選擇他們想住在哪裏?」
她沒回答,她攏了攏裙子,坐在下一層階梯上。
「我選了里斯本!」她說,那口氣,像是在重複一件非常明顯的事。
「妳來過這裏嗎—」我猶豫着該用哪個詞,因為我不想太過凸顯其中的差別—「以前?」
她再次忽略我的問題。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以前我沒告訴你的事,」她說,「或是你已經忘記的事,現在可以問我。」
「妳根本什麼也沒告訴我,」我說。
「誰都會說!說這!說那!所以我做別的。」她表演式地望向遠方,望向太加斯河彼岸的非洲。「不,之前我從未來過這裏。我沒跟你說,但我做別的,我讓你『看』。」
「爸也在這?」她搖搖頭。
「他在哪?」
「我不知道,我沒問他。我猜他可能在羅馬。」
「因為教廷?」
她第一次看着我,眼中閃耀着玩笑得逞的小火光。
「才不是,是因為那些桌巾!」
我挽着她的手臂。她輕輕將我的手從手臂上移開,握在她手中,然後緩緩地將我倆的手放到石階上。
「妳在里斯本住多久了?」
「你不記得我告誡過你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嗎?我告訴過你它就會像這樣。超越了年月日,超越了時間。」她再次凝視着非洲。
「所以時間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說這話是為了挑釁她。我年輕的時候很愛挑釁她,她也順着我這麼做,這讓我倆想起了一段逝去的悲傷往事。
[…]
「這裏至少有隻動物可以拯救我們,」她說,眼睛盯着十個階梯下方一隻她以為正在曬太陽的貓。
「那不是貓,」我說。「那是一頂舊毛帽,一頂筒狀的小牛皮翻毛軍帽。」
「就是這樣我才吃素,」她說。
「妳很愛吃魚吧!」我爭辯着。
「魚是冷血的。」
「那有什麼不同?原則就是原則。」
「約翰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畫線問題,你得自己決定你要把線畫在哪裏。你不能幫別人畫那條線。當然啦,你可以試,但不會有用的。遵守別人定下的規矩可不等於尊重生命。如果你想尊重生命,你就得自己畫那條線。」
「所以時間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又問了一次。
「不是任何地方,約翰,是相遇的地方。這世界還留着電車的城市已經不多了,對吧?在這裏,你時時刻刻都能聽到電車的聲音,除了深夜那幾個小時。」
「妳睡不好嗎?」
在里斯本市中心,幾乎沒有一條街上聽不到電車的聲音。
[…]
「我可以跟你說件事嗎?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沒有注意到聖胡斯塔瞭望塔?就是下面那個。那是里斯本電車公司的財產。塔裏面有座升降梯,那座升降梯其實哪裏也沒去。它只是把人載上去,讓他們從平台上瞭望四周,然後再把他們載下來。那是電車公司的。現在啊,約翰,電影也可以做同樣的事。電影也可以把你帶上去,然後再帶回原來的地方。這就是人們為何在電影院裏哭泣的原因之一。」
「我以為—」
「別想了!人們在電影院裏哭泣的理由,就跟買票進去的人數一樣多。」
她抿了抿下嘴唇,每次擦完唇膏,她也會做這動作。在「水之母」階梯上方的一座屋頂上,有個女人正一邊唱着歌,一邊把床單夾在曬衣繩上。她的聲音悲傷逾恆,她的床單雪白閃亮。
「我第一次來里斯本時,」母親說,「就是聖胡斯塔的升降梯把我載下來的。我從來沒在裏面往上升喔,你懂嗎?我是從那裏下來的。我們全都是這樣。這就是它建造的目的。它的襯裏是木頭的,就像鐵路的頭等車廂一樣。我看過一百個死者在裏面。它是為我們建造的。」
「它只能載四十個人,」我說。
「我們又沒重量。你知道,當我踏出升降梯時看到的第一個東西是什麼嗎?一家數位相機店!」
她站起身,開始往回爬。不用說,她爬得有點喘,為了讓自己輕鬆一點,也為了鼓勵自己,她噘起雙唇,像吹口哨似的,發出長長的噓聲。她是第一個教我吹口哨的人。
我們終於爬到頂端。
「我暫時不打算離開里斯本,」她說。「我正在等待。」
她隨即轉過身,朝她剛剛坐着的長椅走去,然後,那座廣場變得宛如展示品般寂然不動,彷彿靜物一樣,直到她終於消失。
接下來幾天,她始終沒現身。我在這座城市裏四處閒晃,觀看、畫畫、閱讀、聊天。我沒到處找她。不過三不五時,我會想起她—通常是因為某種半隱半現的東西。
里斯本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關係,與其他城市很不一樣。它玩着某種遊戲。它用白色和彩色小石塊把廣場與街道鋪上各種圖案,彷彿它們不是道路,而是天花板。這城市的牆面,不論室內室外,放眼所及之處,都覆滿了著名的 Azulejos 瓷磚。(編注︰阿拉伯文原意指精美的石頭,早期因價格高昂、工藝複雜只裝飾在教堂修道院和皇室貴族宅邸,後日漸出現在各類建築上,成為葡萄牙與西班牙的藝術風格之一。)這些瓷磚訴說着這世上各種精采絕倫的可見事物:吹笛子的猿猴、採葡萄的女人、祈禱的聖者、大洋裏的鯨魚、航行中的十字軍、大教堂的平面圖、飛翔的喜鵲、擁抱的戀人、溫馴的獅子、身上有着豹紋斑點的莫里亞魚。這城市裏的百變瓷磚,吸引着我們去注意周遭的有形世界,去留心那些可見的事物。 […]

「之所以會有誕生,是為了要給那些打從一開始就壞了的東西,在死亡之後,有個重新修復的機會。這就是我們為何出生在這世上的原因,約翰。我們是來修理的。」
從中央望去,在兩條導管上方,一條石板步道筆直延伸至視線的盡頭。步道同樣很窄。無法容納兩人並肩交錯。費南多打開他的探照燈,開始往前走。
過了一會兒,當我斜倚在他剛剛打開的大門對面的護牆上時,我想我聽到他在說話。他說着一些簡短的句子,像在做註解似的。但裏面沒人和他一起。
在水道橋的筆直慫恿下,我踏上戶外步道,開始快速往下走。從某方面來說,薇艾拉‧達希瓦的畫作都是關於里斯本,以及里斯本的天空和橫越天空的通道。當我抵達峽谷另一端,我回過頭,數着橋拱的數目,直到第十六座,那裏離費南多打開的大門並不遠。
通道下方,是幾條尚未完成的街路,以及幾棟住了人但還在興建的房子。一個窮郊區而非貧民窟。我看見一輛缺了輪子的轎車,一個餐桌椅大小的陽台,一名小孩用一根綁在樹上的繩索盪啊盪,紅色磁磚塗上了水泥以免被大西洋的強風颳走,一扇沒有窗框的窗子外掛着兩床被褥,一隻被鍊住的小狗在陽光下狂吠。
「看見了嗎?」她突然出聲。「每樣東西都是破的,都有些小缺損,像是給工廠淘汰的瑕疵品,以半價便宜出售。並不真的壞了,就只是不合格。每樣東西—那些山脈,那片麥稈之海,那個在下面盪啊盪的小男孩,那輛車,那座城堡,每樣東西都是瑕疵品,而且打從一開始就是有缺陷的。」
她正坐在通道上一只攜帶式的小凳上,離我只有幾公尺。那是一只三隻腳的摺疊小凳,非常輕便;她習慣隨身攜帶,這樣就可以在公共場合隨時坐下。她戴了一頂鐘形帽。
「每樣東西一開始都是酸的,」她說,「然後慢慢變甜,接着轉為苦澀。」
「老爸喜歡他的劍旗魚嗎?」我問。
「我是在談論人生,而不是瑣事。」
雖然她嘴裏這樣說,但臉上掛着笑,甚至連肩膀也在笑。我記得這笑容,很像1935年左右她穿着游泳衣站在沙灘上的笑容,因為當她穿上游泳衣時,她覺得自己不需要工作。
「打從一開始就出了錯,」她繼續說道。「每樣東西都是從死亡開始。」
「我不懂。」
「有一天,等你來到我這位置之後,你就會懂了。創造始於死亡。」 兩隻白蝴蝶在她帽上轉圈圈。牠們或許是跟着她一塊兒上來的,因為在這個高度的水道橋上,根本沒什麼可吸引蝴蝶的東西。
「起始當然是一種誕生,大家不是都這樣認為嗎?」我問道。
「那是一種常見的錯誤,你果然如我所料,掉進陷阱裏了!」
「所以,妳說,每樣東西都是從死亡開始!」
「完全正確!先死後生。之所以會有誕生,是為了要給那些打從一開始就壞了的東西,在死亡之後,有個重新修復的機會。這就是我們為何出生在這世上的原因,約翰。我們是來修理的。」
「但是,妳不算真的在這世上吧,妳算嗎?」
「你怎麼會這麼笨!我們—我們這些死去的人—我們都在這世上。就跟你和那些活人一樣,都在這世上。你和我們,我們都在這世上,為了修理一些已經破損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為何產生的原因。」
「產生?」
「變成這樣。」
「妳說的好像沒人能選擇任何事一樣!」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你只是無法希望每件事情都如意。」 她依然笑容滿面。
「當然。」希望是一支超級放大鏡—就是因為這樣它才無法看遠。
「妳為什麼一直笑?」
「讓我們只把希望擺在那些有機會實現的東西上!讓幾樣東西修好吧!只要有一兩樣就可以造就一大堆。只要把一樣東西修好,就可以改變其他一千種東西。」
「怎麼說?」
「下面那隻狗的鏈子太短了。改變它,把鍊子加長。這樣,牠就可以走到陰影處,牠就會躺下來,不再狂吠。然後這寂靜無聲的環境,會讓母親想買隻金絲雀養在廚房的籠子裏。在金絲雀的歌聲中,母親把衣服燙得更平整。父親穿着剛熨好的襯衫去上班,他的肩膀就不會那麼痠痛。於是下班回家後,他就會和從前一樣,有時間和青春期的女兒開玩笑。而女兒將因此回心轉意,決定找天晚上把她的情人帶回家。然後另一個晚上,父親將提議和那個年輕男孩一起去釣魚……誰會知道呢?這一切不過就是把鍊子加長而已。 」
那隻狗還在叫。
「有些事情想要修好,除了革命之外別無他法,」我說道。
「那是你的主張,約翰。」
「那不是我的主張的問題,那是環境的問題。」
「我寧可相信那是你的主張。」
「為什麼?」
「那樣比較不像推託之辭。環境!什麼事情都可以躲在這兩個字背後。我相信修復,還有另一樣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東西。」
「那是什麼?」
「無可逃避的欲望。欲望永遠無法阻止。」 說到這裏,她從摺疊小凳上站起身來,斜倚着護牆。
「欲望是阻擋不住的。我們當中有個人曾向我解釋緣由。但在那之前,我就知道答案了。想想無底洞,想想空無一物。完完全全的空無一物。即便在絕對的空無中,仍然有一種籲求存在—你要加入我嗎?『空無一物』籲求着『某事某物』。總是這樣。然而那裏終究仍只有籲求;毫無掩飾嘶啞哭喊的籲求。一種錐心的渴望。於是,我們陷入了一個永恆難解的謎:如何從空無一物中創造出某事某物。」
她朝我走近一步。用她那游泳衣的笑容輕聲低語,咖啡色的雙眸凝定在遠方的某一點上。
「這創造出來的某事某物,沒法支撐其他任何東西,它只是一種欲望。它不擁有任何東西,也沒任何東西能給它什麼,這世上沒有它的位置!但它確實存在!它存在。他是個鞋匠,我想,那個告訴我這一切的人。」
「聽起來像是伯麥。」
「別再掉書袋了!」 她大笑,用她十七歲的傲慢笑聲。「別再掉書袋了!」她又咯咯笑地說了一遍。「從這裏,你可以殺死任何掉書袋的人!」
我們凝視着下面的紅色瓷磚,以及窗戶上的兩床被褥。小狗不吠了。然後,她的笑聲終止,我握住她冰冷的手。
「放手寫吧,把你發現的東西寫下來,」她說。
「我永遠也不知道我發現了什麼。」
「是啊,你永遠不會知道。」
「書寫需要勇氣,」我說。
「勇氣會來的。寫下你發現的東西,讓世人注意到我們,拜託了。」
「妳要走了!」
「所以,拜託了,約翰。」
接着,她邁開腳步,將摺疊小凳遞給我,朝費南多沒上鎖的大門走去。她用力拉開大門,像每天早上做了一輩子的動作一樣,跨上導管頂端,步入那條狹窄的石板步道。
裏頭空氣冷冽,彷彿我們是在地底而非天際。光線也不相同。門外,陽光閃亮而透明,滲入隧道之後,轉變成金黃。每隔五十公尺,拱頂天花板便向外開出一座小塔,有如石造的燈籠天窗,將光線引透進來。而每一座天窗,像接力似的,不斷向遠方退去,灑落的日光宛如一道金色簾幕,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裏頭的聲響也變了。在無邊的寂靜中,我們聽見水流的舔啜聲順着兩條半圓形石渠一路通往「水之母」—就像貓舌舔水一樣,聲聲分明。
我不知道我們站在那裏彼此對望了多久—也許有整整十五年,從她死後。
終於,她轉過頭,咬着下唇,開始走。
她走了,「拜託了,約翰!」她又說了一次,沒有回頭。
她從第一座石造天窗,邁入一重接一重的連續光瀑。在她兩側,水流閃映着宛如漂燭般忽上忽下的耀眼星點。她走進了金黃光束,光束似簾幕般將她藏起,我再也看不見她,直到她重新出現在遠方的光瀑之下。她越走越遠,越遠越小。越走越不費力,越遠越顯輕盈。她消失在下一道金色簾幕的包覆之中,當她再次出現,我幾乎看不清她的身影。
我屈下身,將手放進水中,追曳着隨她而去的涓涓流波。




为什么中西方文学中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写法几乎都有“狭窄的通道”和“光束”两个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