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漢,社會科學研究者)
近些年,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在習近平治下發生的若干轉變,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習時代的政策轉型,究竟是對改革開放模式的背離,還是改革開放過程在某種意義上的歷史產物?改革開放歷史中那些相對隱秘、不為人知的片段,如何在潛移默化中為中國經濟在今天暴露出的問題埋下導火索?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摸着石頭過河」的主流改革開放敘事之外,我們是否能對改革開放歷史形成更具深度的理解?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王穎曜教授在今年五月出版的新書《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官僚如何制定政策並重塑國家》(Markets with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How Economic Bureaucrats Make Policies and Remake the Chinese State),為我們思考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養料。通過追蹤多個經濟官僚群體在政策舞台上的興衰起落,王穎曜梳理出一條驅動改革開放政策演變的重要歷史邏輯。
本書提供的歷史敘事和分析框架,如何刷新了我們對於改革開放歷史的認知?本書的侷限與不足之處,又是否能成為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的起點?
Markets with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How Economic Bureaucrats Make Policies and Remake the Chinese State
作者:Yingyao Wang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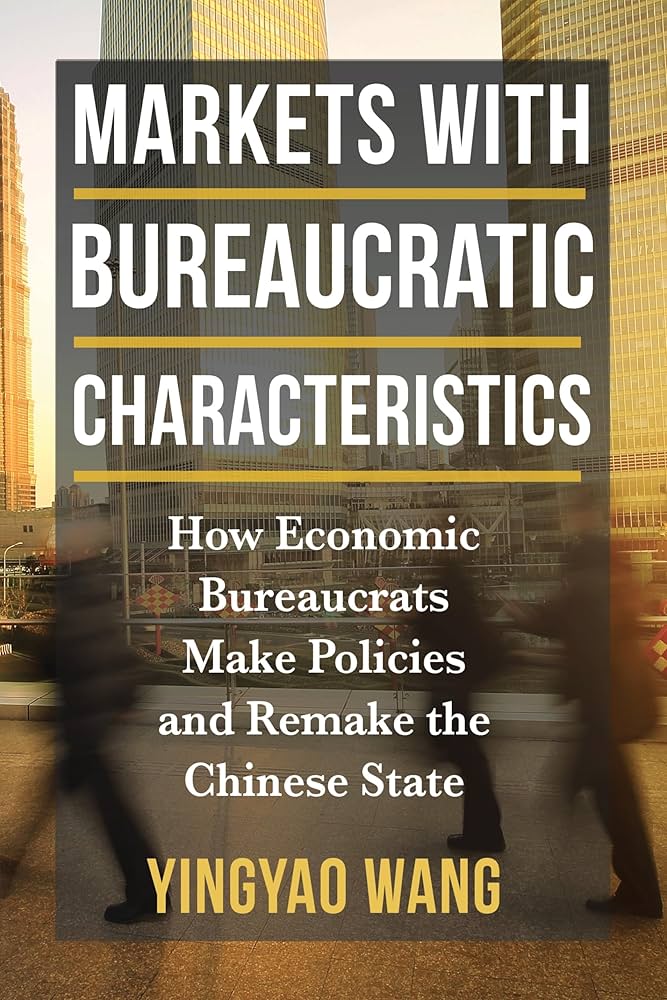
經濟官僚的迭代與政策範式的變遷
雖然「流通官僚」和「地方官僚」共同推動了市場改革的起步,但隨着改革的深入,兩派官僚的分歧也很快暴露出來。
在本書的歷史敘事中,兩群不同的經濟官僚共同推動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市場改革的起步。一群是以陳雲、李先念、姚依林為代表的「流通官僚」(circulators)。這群官僚在毛時代的職業軌跡具有高度相似的特徵:建國初期,他們在穩定經濟秩序、對抗通貨膨脹、建立財政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他們主要供職於中央政府中的財政、銀行、商貿等部門。與重視工業投資、推動資本積累的計劃部門相比,財政、銀行、商貿這些關注經濟流通的部門在毛時代的官僚體系中是被邊緣化的。王穎曜指出,在這些邊緣部門任職的經歷,使得這群官僚傾向於以「流通視角」來看待經濟:計劃部門常常將經濟看作是以大型工業投資項目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資源分配,而「流通官僚」則將經濟看作是一個各環節緊密聯繫的整體,關注物資與貨幣在整個經濟體中的循環、流通與平衡。
在「流通視角」看來,客觀的經濟規律是存在的,一定範圍內的市場流通機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必要補充。在毛時代,每當宏觀經濟出現危機時,往往是「流通官僚」站出來充當救火隊員的角色,穩定經濟秩序、重建宏觀平衡。作為穩定經濟的重要手段,這些官僚傾向於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甚至鼓勵市場流通。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流通官僚」獲得更多經濟政策話語權後,更是旗幟鮮明地鼓勵那些曾經被當作救火手段的市場流通措施,以破除計劃經濟體制的積弊。換言之,「流通官僚」群體對市場改革的支持,源於其在毛時代的特殊職業經歷。
在市場改革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群官僚,則是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為代表的「地方官僚」(local generalists)。本書作者認為,這些官僚在毛時代積累了豐富的地方主政經歷,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們能夠了解民生疾苦,對那些基層群衆自發的、處於政治灰色地帶的經濟實踐——比如集市貿易、家庭副業生產、工農業之間的物物交換——充滿同情。這些「地方官僚」尤其強調通過給基層群衆「鬆綁」來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隨着這些「地方官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來到中央政府擔起要職,他們也自然而然成為了市場改革的熱情推動者。
本書強調,雖然「流通官僚」和「地方官僚」共同推動了市場改革的起步,但隨着改革的深入,兩派官僚的分歧也很快暴露出來。在中央執掌經濟實務的「地方官僚」,重視調動地方政府、企業、基層行動者的積極性,着力推動中央政府對社會基層力量鬆綁放權。一系列放權改革——企業承包制、沿海經濟特區、放鬆價格管制等等——成為「地方官僚」的核心政策主張。而「流通官僚」在「流通視角」的影響下,認為經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維持各種經濟關係的宏觀平衡(比如財政平衡、信貸平衡)是必要的。「流通官僚」進而反對將放權作為經濟改革的核心,認為中央政府的宏觀控制不可拋棄。「流通官僚」與「地方官僚」之間的政策角力,在物價管理、財政赤字等問題上暴露得最為充分;兩派分歧之間的政策搖擺,也成為80年代末通貨膨脹失控和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條導火索。

1989年之後,趙紫陽等「地方官僚」因為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懷柔立場,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邊緣化;而陳雲、李先念等「流通官僚」則因為年齡原因淡出政策舞台。在這種情況下,90年代見證了以江澤民、朱鎔基為代表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群體的崛起。這一群「技術官僚」的最大共同點,就是其教育背景集中在工程學科,與工程技術相關的工作崗位是他們早期職業生涯的起點。這些官僚往往以工科思維看待經濟,作風非常務實,將經濟管理視作一系列需要被解決的工程技術問題。他們既試圖擁抱高速經濟增長,也重視宏觀經濟穩定,因此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引導和控制。在「技術官僚」治下,中國的市場改革狂飆突進、全國層面的市場整合勢如破竹。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權力大大增強,80年代的放權趨勢被徹底扭轉。伴隨着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的「乘風破浪」,90年代見證了政府與市場的雙重擴張。而中國經濟在90年代前半段遭遇的通貨膨脹和90年代後半段的通貨緊縮,也進一步強化了「技術官僚」群體以工科思維調控經濟的政策風格。因此,「宏觀調控」的政策範式成為這一批「技術官僚」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
在「技術官僚」占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企業官僚」、「金融官僚」、「產業官僚」分別在國企改革、財政與金融改革、產業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其各自留下的政策範式亦對中國經濟的後續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技術官僚」時代的大背景下,《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進一步聚焦三個具體而重要的經濟領域,揭示特定官僚群體的興起如何塑造了這些領域的政策範式。在國企改革領域,1993年重新設立的國家經委(後更名為國家經貿委)匯聚了一批職業經歷高度相似的官僚。他們在職業生涯初期大多擔任企業中的領導職務。在毛時代經濟短缺的環境下,他們往往需要絞盡腦汁,推動自身所在的企業與其他企業私下結成合作與貿易關係,才能維持企業運轉。到了80年代,他們紛紛進入地方政府主管企業事務,大力促進本地區的企業之間建立橫向聯繫。這樣的職業經歷,使得這批「企業官僚」在進入國家經委後,將企業與企業之間關係的協調視作國企改革的關鍵抓手。「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在這些官僚的推動下形成了:大型國企之間通過重組、兼併、整合等方式強化相互之間的聯繫,形成跨地區的「巨無霸」企業集團。這批「企業官僚」在90年代所推動的企業重組,催生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中國國企巨頭的雛形。
在財政、金融領域,90年代成為核心政策制定者的「金融官僚」群體由兩批人員組成。一批是198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所培養出的金融工作者,他們也被稱為「五道口學派」(因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坐落於五道口而得名,代表人物為吳曉靈、胡曉煉等);另一批則是以吳敬璉的學生與合作者為主體的、被稱為「整體改革派」的經濟學家們(代表人物為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等)。「五道口學派」與「整體改革派」的共同特點,是認為財政領域與金融領域是不可分割的:發行國債等財政行為是推動金融市場發展的關鍵力量,而金融市場的發展反過來將使得國家能夠撬動更多的財政資金。因此,這些「金融官僚」上任後大力推動財政領域與金融領域的整合:一個相對成熟的國債市場及其次級市場,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成型;而在解決國有銀行壞債問題的過程中,由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注資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也應運而生。這一系列改革舉措,造就了中國今天的債券市場、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國有資產的管理模式,乃至金融化的、以政府債務驅動財政投資的經濟發展路線。

最後,在產業政策領域,2008年工業與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的成立是重要的轉折點。作者指出,在此之前,「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政策制定者中影響很大,政府積極鼓勵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製造業發展——換言之,中國並無嚴格意義上的產業政策。但隨着工信部的成立,一批既具有科學技術方面的教育背景,又有工廠與產業部門的具體工作經驗的官僚被聚攏起來。這批「產業官僚」帶來了一種看待產業發展的新方式:不是將經濟體看作一個一個可被分割開的產業,而是將其視為一系列流動的產業鏈條。「產業官僚」們從而能夠通過這些鏈條,去追溯哪些零部件生產環節可被廣泛用於多個產業、因而最具戰略價值。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將關鍵零部件生產環節的自主創新、技術升級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產業官僚」帶來的認知方式革新,使其在產業政策的制定上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作者在書中細緻地描述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是如何在工信部的推動下出台的。這一批官僚的努力,使得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中國出現了強調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轉向。
在本書作者的筆下,曾經在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經濟政策制定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六類官僚群體依次亮相。王穎曜以娓娓道來的筆觸,描繪了在中國經濟政策的大舞台上,這六批在職業經歷、精神氣質、認知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的經濟官僚群體,如何「你方唱罷我登場」、推動中國經濟政策範式的變遷。「流通官僚」與「地方官僚」在80年代的合作與競爭,既為初步的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動力,又使得中國經濟在追求宏觀平衡與強化基層微觀主體的積極性這兩種政策範式之間左右搖擺、進退失據。而到了90年代,「技術官僚」強勢崛起,以具有強烈工科色彩的實用主義思維,大刀闊斧地推動了「大政府+大市場」的改革。在「技術官僚」占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企業官僚」、「金融官僚」、「產業官僚」分別在國企改革、財政與金融改革、產業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其各自留下的政策範式亦對中國經濟的後續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斷裂」與源流
學者們更應該去回答的問題是:毛時代的種種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特徵,是如何形塑、影響了改革開放的具體進程?
王穎曜的這本著作,從經濟官僚群體的視角出發,重新敘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本書至少在三個層面上豐富了我們對於改革開放過程的理解。第一,本書揭示了毛時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如何塑造了改革開放的起源。在英文學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領域,對「1976/1978斷裂」敘事的反思近來成為一項熱門研究話題。不少歷史學家指出,毛時代和後毛時代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歷史連續性,不宜被看作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歷史時期。然而,歷史時間的流動本就是連續的,指出兩個歷史時期之間存在連續性,並不算是一件在智識上很有意義的工作。學者們更應該去回答的問題是:毛時代的種種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特徵,是如何形塑、影響了改革開放的具體進程?
《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從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富有洞見的解答。作者指出,着力推動改革開放起步的兩批經濟官僚——「流通官僚」和「地方官僚」——其實都是毛時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他們看待和理解經濟政策的獨特方式,得益於他們在毛時代的特定職業經歷與他們在官僚體系中所處的特定結構位置。在毛時代,他們的經濟認知範式多多少少被官僚體系中更主流的聲音(如重點關注大型工業投資項目的計劃部門,以及強調「政治掛帥」、自上而下動員群衆的經濟發展思路)邊緣化了。而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他們走上前台、成為經濟政策制定的主導力量之後,便有條件將他們多年以來形成的經濟認知範式轉化為改革政策。從這個角度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內部邊緣力量對主流力量的質疑和反叛,推動着改革開放初期的市場力量不斷在計劃經濟體制內撕開越來越大的口子。

第二,本書的歷史敘事讓我們看到,在80年代與90年代的經濟改革邏輯之間,倒是恰恰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斷裂。由於「地方官僚」群體的推動,80年代的市場改革常常是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向企業、向社會基層力量放權的形式展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權力擴大,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基層的經濟活動充滿盲目性,造成宏觀經濟的失序。中央政府對經濟的管控能力日益變弱,面對經濟失序常常一籌莫展。而到了90年代,隨着工科背景的「技術官僚」群體上台執政,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大大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保護主義的削弱,也使得全國範圍的市場整合成為可能。重新將權力集中起來的中央政府,開始以狂飆突進的速度推進各項市場化改革,並且也習得了使用新的市場工具管控經濟的能力。隨着「宏觀調控」政策範式的確立,鄧小平在1989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也在真正意義上照進了經濟現實。
中國的經濟官僚群體就像一群群蝴蝶,在官僚體系內奮力扇動着翅膀,為自身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政治資源與晉升前景,最終卻在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天地內掀起了一場場或許他們自己也未曾預料到的風暴。
學者黃亞生曾經指出,8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90年代的經濟改革區別在於:80年代的經濟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強調社會基層主體的能動性;而90年代的經濟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重新開始壓倒一切。王穎曜的著作既呼應了這一論斷,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本書讓我們看到,90年代的經濟改革並不僅僅是「國進民退」那麼簡單:中央政府權力的迅速擴張和市場改革的瘋狂推進,在這一時期同步展開、相輔相成。從本書的觀點出發來看,80年代基層主體積極性的釋放,雖然有助於市場改革的啓動,但其造成的地方保護主義、盲目投資行為、宏觀經濟失序,都不利於市場改革的深化。反而是到了90年代,在中央政府重新獲得「乾綱獨斷」的政治權力之後,構建全國範圍的統一市場秩序——如成立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建立全國性的金融市場等——才具備了客觀條件。
最後,《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還向我們揭示了當下的中國國民經濟中許多重要現象的政策起源。跟隨作者的敘述,我們得以看到:「做大、做強國企」的經濟戰略,源自國家經貿委的「企業官僚」在90年代推動的一大波國企重組、兼併、整合浪潮,這才有了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中佔據支柱地位的那些「巨無霸」國企集團。而困擾中國經濟至今的金融泡沫與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很大程度上是90年代末、21世紀初「金融官僚」打造的「財政撬動金融、金融反哺財政」模式的副產物。近年在國際社會上引起高度關注和不少恐慌的「中國製造2025」產業計劃,一開始也並非是來自於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意志和通盤規劃,而是工信部的「產業官僚」積極策劃、遊說的結果。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官僚群體就像一群群蝴蝶,在官僚體系內奮力扇動着翅膀,為自身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政治資源與晉升前景,最終卻在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天地內掀起了一場場或許他們自己也未曾預料到的風暴。
官僚體系、國家干預與市場經濟
王穎曜筆下的中國官僚體系,是一個充滿個體能動性、人物戲劇性的官僚體系。
基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語境,王穎曜的這本著作進一步促使我們反思對於官僚體系的慣常認識。在人們的傳統理解中,官僚體系是一架龐大、笨重、效率低下、被各種繁複的規章制度所綁架的行政機器。當我們在日常語言中將「官僚」和「官僚主義」作為形容詞使用時,往往指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理性官僚制的經典定義:這樣的組織形式通過層級化的信息傳遞與決策機制、專業化的分工、辦事程序的標準化與規則化,能最大程度上確保自身的穩定與持久。而身處官僚體系中的官僚個體,受制於無孔不入的標準與規則,被規訓成官僚機器中的螺絲釘,而非擁有獨立形象的個體人格。

但本書作者指出,官僚體系歸根到底是由一個個具體、鮮活的人組成的,這些人並不真的僅僅是官僚機器的螺絲釘,而是有着自己的精神氣質、認知方式、喜怒哀樂、職業野心。因此,如果要深入理解官僚體系的運轉,僅僅在組織層面分析官僚體系的運行邏輯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關注身處官僚體系中的那些人究竟是怎樣的人。本書作者對各個官僚群體的背景爬梳,使這些人物形象在讀者眼中變得生動起來。我們看到,不同官僚群體的教育背景、以及其在官僚體系中的職業軌跡,是如何賦予這些官僚群體特定的認知模式、形塑他們對經濟問題的理解。我們同時還看到,在圍繞政策制定而展開的競爭中,不同的官僚群體如何運籌帷幄、尋找機會,努力推動自身的政策主張成為主導範式。換言之,王穎曜筆下的中國官僚體系,是一個充滿個體能動性、人物戲劇性的官僚體系。
據此,本書作者進一步認為: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政策制定並不是一個「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政策制定者並不是在一團未知中試探、摸索什麼樣的政策是可行的。恰恰相反,不同的政策制定群體基於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任職經歷,在進入核心政策圈以前就已經形成了獨特、系統的經濟認知模式。進入核心政策圈以後,這些經濟官僚各顯其能,努力爭取將自身的經濟認知模式轉化為政策路線。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實際上是這些不同的政策路線互動、糾纏的結果。作者在書中寫道,這些不同的官僚群體和他們的政策路線就像一波一波涌動的浪潮,推動中國經濟這艘大船駛向對岸。當然,這些浪潮的涌動方向往往並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馳,這也給中國經濟大船的航行增加了挑戰。
《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同時也提醒讀者:國家干預與市場經濟兩者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大市場」並不必然意味着「小政府」。在當下,隨着新自由主義範式在世界各地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反思,這已經不再是什麼新的洞見。人們已經廣泛認識到,市場經濟體系往往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支持方能形成,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持續運轉也依賴於國家不斷出手干預。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提出的觀點依然發人深省: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主導力量的市場體系,其本身就可以被理解為一項國家計劃。
在這一系列洞見的基礎上,本書更進一步,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國家權力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共生關係是雙向的:國家權力不僅能夠推動市場經濟形成、維持市場經濟運轉,而且市場經濟反過來也能成為國家進一步鞏固權力的工具。本書的歷史敘事,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展示了國家如何動用市場工具來鞏固權力。第一,中央政府通過建立全國性的市場來消除官僚行政的地方化、碎片化,完成全國領土的政治整合。第二,某些經濟官僚群體通過扶持市場的發展,來「製造」出支持自身政策主張的利益群體。第三,政府通過市場手段來完成國家資本的進一步積累和集中,這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和財政、金融配套改革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雙向共生關係,為市場經濟注入了鮮明的「官僚特色」。
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是「去政治化」的嗎?
本書作者之所以認為經濟政策制定是「去政治化」的,恐怕是因為作者在分析時僅僅關注了經濟政策場域,而忽視了經濟政策與其他政策場域之間的聯繫。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為我們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軌跡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洞見,但本書對中國經濟政策制定過程的描繪仍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王穎曜筆下,經濟政策制定是一個高度技術化(technical)的場域:不同的官僚群體依據自身關於經濟問題的認知模式和專業知識,試圖為中國經濟遇到的一系列挑戰提供他們認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在這樣的視角之下,不同的經濟官僚就好像是受過不同專業訓練、擁有不同專科特長的醫生,紛紛為「中國經濟」這個病人做出自己的診斷、開出自己的藥方。經濟政策制定被看作是由專業觀點驅動的,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問題解決過程。作者在書中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改革年代的經濟政策是一個相對去政治化的政策場域。或者說,經濟官僚體系將經濟看作是一個獨特的、去政治化的管理對象……隨着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從意識形態轉為經濟發展,經濟也與政治鼓動脫鉤,階級問題——以及相關的分配問題——從經濟事務的討論中被移除。(第13頁)」
但是,筆者在讀完本書後還是不禁要問: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在中國,經濟管理真的是一個由「專業的人辦專業的事」所驅動的過程嗎?誠然,中共政權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使用了「去政治化」的統治策略,即通過調動人們在市場經濟中致富的熱情來消解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的訴求。但這並不意味着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以及階級問題不再是中共統治者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如何穩定自身的統治基礎與分配聯盟、如何構建與時代大環境相適應的統治策略和公共話語、如何回應社會基層力量中潛滋暗長的政治挑戰——這些問題歷來在中共政權眼中是優先級最高的,經濟政策也是為這些目標服務的(在習近平時代,這一點變得越發明晰起來)。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至少是一個政治考量與技術考量共同驅動的過程。本書作者之所以認為經濟政策制定是「去政治化」的,恐怕是因為作者在分析時僅僅關注了經濟政策場域,而忽視了經濟政策與其他政策場域之間的聯繫。

只見技術、不見政治,只見官僚體系、不見統治機器,這是本書分析框架與歷史敘事的主要不足。
其實,現有的歷史材料已經透露出許多蛛絲馬跡,顯示執政者對於穩定統治基礎、化解政治挑戰的需求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年代的重大經濟政策。例如,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在中國重演的恐懼,貫穿了整個80年代中國政策制定者關於財政赤字、通貨膨脹乃至企業改革問題的討論。而中國的市場改革之所以在90年代進入狂飆突進的階段,恐怕也與中共政權在1989民主運動之後逐漸形成的吸納精英學生群體、鎮壓城市工人階級的「分而治之」策略大有關係。當然,本書並非全然忽視了經濟政策制定的政治背景。例如,作者在分析「技術官僚」群體在90年代初上位的背景時,也強調了八九民運後鄧小平等高層領導人對穩定的極度追求與對大衆政治動員的拒斥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對於經濟政策制定背後的政治驅動力,本書並未在歷史敘事中給予系統的關注,也未將其納入理論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只見技術、不見政治,只見官僚體系、不見統治機器,這是本書分析框架與歷史敘事的主要不足。
作者在書中坦陳,本書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提供了一個內生(endogenous)的解釋。「內生」的具體涵義是,作者通過經濟政策制定者自身的理念主張、精神氣質、職業動機來解釋政策制定的結果。政策制定者自身的思想和行動對解釋政策結果來說固然重要,但經濟政策場域畢竟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它是整個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經濟政策場域必然與國家機器的其他組成部分不停地互動、糾纏,也必然受到國家機器與各種社會基層力量之間相互關係的影響。如果想深入理解經濟政策制定的現實邏輯,我們就需要回答:國家機器所面對的多重政治考慮、各種社會基層力量給國家機器施加的壓力,如何與官僚自身的思想和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雖然在中國研究的具體語境下,尤其是考慮到材料獲取的難度,想要回答這樣的研究問題並不容易,但依然值得研究者今後不斷嘗試。
最後,《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書也幫助我們反思「能動性」(agency)在歷史敘事中的意義。一方面,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個體行動者的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歷史的走向;另一方面,本書的歷史敘事又似乎僅給那些作為精英行動者的經濟官僚群體賦予了能動性。難道只有那些手握政治權力的人們才有歷史能動性嗎?歷史能動性是否只是精英的特權?那些被政治權力格局排除在外的社會基層行動者、歷史中的失語者,是否其實也通過自身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明顯或微妙地塑造了經濟政策的變遷和歷史的走向?如何在非精英群體身上找回歷史能動性,是一個值得我們在審視各種歷史敘事時不斷探索的問題。





请问大陆怎么购买这本书
90年代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全国统一市场与金融体系建立,由此中央-边缘的分化在经济上被强化。这也回应到此前我长久的困惑:在当代经济史的叙事中为何越来越难以看见县镇和农村的身影(而在此前它们更为具象,例如农业合作社和乡镇企业)。
写得好好。
好文!仔细的做了笔记
好文!
同意作者將幹部群體分成不同的官僚類型能有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政治,從不同的經濟官僚切入也能理解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和結果。
但改革開放始於農業,農業改革也始終貫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在中國的政策圈,感覺也有一批「農業經濟官僚」,他們不是在農業談農業,而是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談農業,這部分的經濟官僚或者值得進一步研究。
真是好文!
不错的书评!
真不错,希望端能多做一些这类专业学者的书评或综述
我非常喜欢这篇书评!这本书我之前就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阅读。本文作者能给出如此清晰易懂的梳理,和富有洞见的不足分析,真的很棒。本文和书本身相得益彰,读完收获非常多。
很不錯的文章!我認同種種的經濟官僚在開革開放的影響力,但社會本身已經存在強烈對經濟、生活追求的渴望,充滿活力,即使粗放型的發展帶來更多的環境及社會問題,但的確改善了社會的經濟發展,不能否定改革開放的功續、但不需過於讚揚那些經濟官僚,他們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少,那些中共精英就如農村長大的小孩跟城市長大的小孩的差距,那怕他們都是劍橋牛津畢業。
很多人會比較日本跟中國,都說日本經濟迷失了三十年,假設日本真的凍結了三十年,但比較之下,從發達程度、國民均富程度、社會發展、環境等各方面,中國都被完全比下去,這就農村小孩跟城市小孩的差距。
喜歡本文作者在末段的評論。
好有趣的文章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