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習近平發言說:「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確實『照』出了、『考』出了在應急管理、公共衞生、國家儲備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我深以為然。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公布「人傳人」的論斷之後,中國大陸公共空間出現了罕見的信息爆炸與集體狂歡,但至今,作為一名忙於搶購口罩與無限期自我隔離的普通國民,我仍無法從公開信息中得知所謂的短板是哪一塊,或者另一隻靴子何時落下。
在2013年開始的政治週期中,中國的官僚系統出現了一些顯見的特徵。其中一些是加速展開了過去行政結構變化的線索,有一些是這一週期中的新發展。它們都深刻形塑了此刻中國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的行政應對。
我嘗試在此文中尋找的,首先是一個結構性的答案。我將回顧中國官僚體系的結構性矛盾,說明地方政府如何產生了「超調」反應,對於防疫有何影響;而公民社會又是否是替代性的出路。
此時此刻,整個中國都成為了疫區,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答案。這兩者從來不是矛盾的,答案也從來不是唯一的。
中國官僚體系的三個結構性矛盾
行政權力的集中與地方官員自由裁量權的縮減,也和政治精英的權力結構變化密切相關,但必須與基建能力的提升相結合才能改造行政系統。
首先是行政與政治權力的進一步集中,與強大的基礎建制能力。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從朱鎔基時代的分税制改革、金融大區和行政改革等強硬舉措開始的,也是鄧在九十年代下決心統一領導核心、加強中央領導力的結果。這一運動在胡温時期以一種更低調的方式繼續,比如發改委和國資委的建立;而在最近又因麥克爾·曼所言之「基礎建制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提升而進一步拓展:其中之一就是全國性高鐵網絡的貫通和信息能力的提升。
比如高鐵網絡的連通性和即時性,使得廣大縣城現在可以直接與網絡中的一些超級節點聯繫,而不必依靠過去漫長的、多層級的行政-交通系統。這不啻是一場深刻的國家(再)建設運動,行政的毛細權力現在愈發通達無礙,而中央對於地方資源的攫取無疑增加了。
這種基建網絡的建設促進了政治共同體的深入,也導致現實並不是一個社會/政治資本均衡分布的網絡——「中心」從中得到了最大的好處。歷史上,羅馬帝國依託其高超的工程能力建構了行省政治中心與羅馬的道路系統,大大遏制了地方的離心力;建國初期的美國,在托克維爾筆下是一個地方自治、自願結社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卻通過聯邦政府建構的郵政專車系統形成了政治共同體。

當然,行政權力的集中與地方官員自由裁量權的縮減,也和政治精英的權力結構變化密切相關,但必須與基建能力的提升相結合才能改造行政系統,這裏不再展開。
但反過來看,政令與資源流通的網絡,也完全可以成為加速病毒散播的網絡。比如「一帶一路」計劃近年來通過中歐班列、路橋建設等各種手段,力圖構建一個貿易網絡,其成功與否姑且不論,但在「中國製造」輸出的同時,疫病和恐怖主義也可以通過網絡反向輸入。其得失之間的計算未可易言,但不知視政治正確為第一要務的官僚體系是否對此做好了充分的預案。
新冠肺炎的爆發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如今縣城洞開的中國,與2003年防疫力量集中在大型都市的中國,已不可同日而語。非典時期大部分病例僅僅集中在北京、香港和順德,而現在僅從湖北內部數據來看,武漢之外地區的確診病例大約佔到一半。
官僚系統的第二個問題是官僚體系的整合後遺症,使得各部門之間再難有共識和統籌。
很多公共行政專家以為「部門競爭」是官僚組織的普世難題,而中國的情狀用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所謂的「碎片化權威」也可以概括十之八九了。然而,李侃如所說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整合效力下降、各種意義上的承包制試行的背景下,官僚系統出現的問題。
但概而言之,八十年代官僚體系正從文革的重創中逐漸恢復,政策的利害關係還未顯現,因此進行跨部門協調、總體設計改革方案的政策平台還是可以建立併發揮作用。而到了九十年代,這些平台基本被解散,政策發明的權力被政治精英壟斷(朱鎔基就是典型),而官僚部門在去政治化、技術化的同時也獲得了意料之外的擴張機會。
回過頭來看,中央和地方官僚系統的人員膨脹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即使朱鎔基、温家寶試圖通過一系列減員增效的措施來精簡行政系統,但並不十分成功。「部門利益」就這樣再次誕生了,改革共識再難形成。結果是我們看到,胡温時期開始改革越來越難,既得利益越來越頑固,立法數量越來越少。
習近平政府其實敏鋭地抓住了問題,並出於多種目的,企圖用「大部制改革」加上反腐剪除利益鏈條的方式來作為解藥,但很多時候只是把原來部門之間的鬥爭,帶入了部門之內。2018年最近一次機構改革帶來了很多人事與職能調整,其中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大概尤受內部分裂之苦。 根據應急專家們的說法,這一部門需要整合十幾個官僚機構的資源,而最重要的權力實際上又被公共安全部門拿走了,其無力狀態可想而知,與其職能之間出現了巨大落差。
官僚體系內部整合問題的後遺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消化,並不是更換一批「之江系」技術官僚可以短期解決的。
官僚體系內部整合問題的後遺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消化,並不是更換一批「之江系」技術官僚可以短期解決的。習的另一個解決辦法是90年代「行政化」的反向操作,即「政治化」:換言之就是把官僚系統既有的管轄權劃歸黨,用各種非常規的領導小組等方式替代官僚體系已制度化的功能。而這必然會激起官僚體系明裏暗裏的反抗。在這種情況下,超部門的公共危機應對平台是沒法真正建立起來的。比如現在的防疫需要衞健委領導、應急管理部統籌、住建部和交通部參與物資調配、商務部採購支持和人社部後期跟進,但目前我們在前台只看見一個疾控中心——這只是衞健委的下屬機構。可以想見,其他部門也很難買衞健委的帳,畢竟它在官僚體系中地位不高。而李克強的領導小組,目前看來權力也不大。防疫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

第三個問題是迄今為止行政專家和政治學家很少涉及的,那就是技術專家,或者說廣義的「專業群體」(profession)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對國家機器的制衡。
醫生、律師、科學家這些職業,其專業權威本該來自從業者對於技術、內部組織和工作場所的自主控制,以及對於超越性公共價值的承諾。但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專業群體的自主權面臨國家的進一步侵蝕,比如醫院管理體制的持續官僚化,學院體系內的學者被近乎嚴苛的評價標準與高度競爭的課題制度所束縛,律師職業仍被內部分裂、准入標準始終無法建立所困擾。
這種將專業體系「官僚化」、加強行政控制的策略至少有兩重目的:一是因為專家的權威和裁判權(jurisdictional power)本質上和國家是有競爭關係的;其技術知識越是具有政治的意涵,其價值承諾越是有公共性,和國家的競爭關係越強。因之,中國律師的職業化運動是受挫最甚的。國家如果想控制最終的裁判權,鞏固自身作為政治和道德的唯一權威來源,自然會限制專業群體的自主權。
第二是因為專業群體一旦有能力壟斷市場,就可以像美國的醫療體系一樣提高服務價格,限制專業服務供給,這對於社會主義人口大國而言並不是一個好消息。由此可知,對於醫生群體的行政控制是平價醫療的制度基礎和代價。代價是——頻繁發生的醫暴事件,把國家資源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隱蔽地轉換為醫患矛盾。甚至在這次疫情爆發中心的武漢,還出現了數起針對攻擊醫護人員的行為。此前北大學者李玲等經濟學家有關醫療服務應該私有還有公有的討論,只涉及到問題的一個方面,並沒有回應這一本質問題。
在國家的權威之外,已沒有制衡性的權威。
這種國家-專業群體-社會三方關係的權力安排,有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即專業群體很大程度喪失了獨立的權威,也沒有獨立於國家的合法性,更無法成為公民社會當中的領導者和理論資源提供者。在國家的權威之外,已沒有制衡性的權威。技術專家的信息和判斷,也無法得到真正的尊重。
正如一位前應急管理專家和筆者所說的,中國應急管理專家沒有真正的權力,卻要調動巨量的資源,這就好像「稚子懷金過市」一樣可笑,因而無法真正地專業化。
在早期防疫失利責任層層暴露的過程中,武漢地方政府無法與中央/地方的醫療專家達成任何意義上的政治聯盟來遊說中央,而其後公共空間又有一波波針對疾控中心和武漢病毒所石正麗、王延軼等科學家的攻擊,這都說明在醫療職業之外,科學研究職業的權威和信譽也甚為低落。
雖然鑑別真相並非本文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專業知識是國家權力的道具,專業知識是研究者罔顧公共利益謀取私利的手段,已成為公眾易於接受的話語之一,在某些例子中也是不容辯駁的事實,比如所謂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學者,「一帶一路」學者。2月5日微博和新媒體又繼續爆出防疫專家李蘭娟背後的商業鏈條,以及武漢病毒所搶注「瑞德西韋」抗新冠病毒的用途,讓人不禁懷疑科學家們是否還對那些遙不可及的公共價值負責,還是在被國家收編後只關心自己的利益。
而在疫情展開的過程中,公眾的茫然失措,彷徨無依,在國家遭受信任危機後不知道該聽誰,信誰,也是這一邏輯的必然後果。謠言與其說出於無知,不如說是一種反抗和自我保護。謠言嵌入對技術專家的刻板印象中。

超調機制
這種超調機制並不是武漢或湖北官僚系統的地方特徵。
這幾個官僚體系內外的結構性矛盾,一起在2020年春節前夕爆發了,導致了目前仍無法估量的嚴重公共安全危機。任何一種單向度的對於國家主義的批判都是單薄無力的,因為這種體量的危機,必然是系統性問題的暴露,是多方面因素負向反饋的作用。
試想一架權力高度集中、基礎建制能力強大的行政機器,但卻苦於內部部門之間的鬥爭,且沒有技術專家權威的制衡並提供有效信息,一旦全速開動是什麼光景呢?從武漢的例子開始,我們似乎部分看到了答案,那就是,作為這部機器基礎零件的地方政府處於一種恆長的「超調」狀態(over-performing)。
在危機起始的階段,因為缺乏上級的授權,以及地方發展績效、維持秩序等多重政策目標的考慮,地方官僚必然採用「過度保守」的策略,隱瞞疫情,沒有意願、也找不到公共空間以及官僚體系之外的盟友;而一旦疫情公開後,中央對地方的高度壓力、故意或無意而引發的地區競賽,又轉而導致地方政府從過度保守轉向「過度激進」,以種種大躍進式的政策模式和一刀切的粗暴手法,期望在短期內迅速達到政策目標。而即使在疫情得到實質緩解,或事實證明死亡率並不高時,這部行政機器也不能調轉方向或降低調門。
這種超調機制並不是武漢或湖北官僚系統的地方特徵。早在2017年北京政府進行低端人群清理運動開始,北京市市委書記蔡奇領導的北京基層官僚就展現了「過度激進」的特質,一部分是由於行政任務本身的壓力,另一部分毋寧說是官僚系統的消極反抗:轉譯過來就是,「你不給我自主權,不顧實際情況下壓行政任務,我就用最快的速度、不計後果地完成,把矛盾上推」。
在當年和其後兩年的清潔煤推廣運動中,這一「過度激進」的行政邏輯再次在中國北方上演,並導致了多地無煤可燒,甚至是去年河北清潔煤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對於非洲豬瘟控制不力,某些地區強行撲殺,甚至強拆豬欄,導致養殖戶破產,也是類似的邏輯。這種超調的情況在中央官僚系統有合作性的政策平台,有統一行動、協調部署的情況下,很大程度可能得到緩解,但在部門分立、權力中心調控不利的情況下,只能說是雪上加霜。
相比之下,美國的聯邦官僚系統更受協調困難、自行其是之苦。以八十年代末埃博拉病毒在北美本土局部傳播事例為基礎改變的電視劇《血疫》,就描繪了疾控中心、軍方研究機構和其他官僚部門在疫情之中的無謂鬥爭。而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南方之後,缺乏統一調度、救援混亂無序也是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在此後十年不斷批評的問題。儘管如此,美國地方政府高度的自主性、公民社會強大的行動能力,都使得這個制度缺陷部分得到了緩解。
而在中國,武漢新冠疫情被迫公開之後,從1月20日左右到1月25日成立「新冠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之後數日,中央幾乎沒有出台有力的應對措施,也沒有強大的官僚系統協調平台,中國短暫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而地方政府也陷入了一場應對措施的發明大賽之中。
其中就出現了很多「超調」的典型例子:1月23日武漢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封城,儘管事後證明,感染的病例遠超預期,但那一時刻的封城是否仍有足夠的成效,之後取消公共交通網絡、禁止車輛通行、封閉社區等等舉措是否有足夠的合法性,在沒有提供替代性的、分類執行的交通與後勤支持網絡的情況下如何維持社會運轉並實現有效隔離,似乎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甚至都不是地方官僚考慮的首要問題。
在武漢之外,疫病剛開始的幾天中河南的「硬核」應對舉措在網絡公共空間被廣為傳播:封村封路、強力宣傳、暴力禁止公眾聚集、對武漢乃至湖北人的歧視性隔離,都成為了「河南模式」的典型特徵。與之相對的可以稱為「杭州模式」:宣布不封城,基層排查有序展開,整合醫療資源,分層管理,並接收一部分海外返回的武漢遊客。
但隨着2月之後確診人數的急劇上升和春節返程人員的壓力顯現,我們看到極具「超調」性質的「河南」模式逐漸佔了上峰。先是北京若干社區宣布外地返京的租房人員不得進入,隨後是各地頻現地方官僚機器粗暴封閉隔離人員住處的視頻,最後是杭州也開始半封閉環城高速,並在2月3日一天之內主要城區陸續宣布所有小區封閉管理,房屋出租一律暫停,三墩地區道路封閉。這些舉措的本意當然是儘快切斷傳染鏈條,但間接導致了制度化的社會保護網絡同時急速崩潰。
對於社會網絡的依賴,通常是極具階級性的。那些沒有車的,沒有房的,沒有經濟資源的,沒有各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本的人群,現在被迫艱難地生活在社會孤島之中,甚至喪失了棲身之地;而那些患病的,年邁的,殘疾的,甚至連親屬網絡也暫時無法依靠。杭州的故事也許才剛剛開始,但是我們在武漢看到了腦癱少年的意外死亡,帶着血癌女兒的母親如何在九江大橋試圖突破封鎖線,以及諸多缺乏醫療的疑似病患的絕望求救。而各種擁有社會資源的少數群體,總是有替代性的資源和私人網絡可以隨時調用。
由官僚系統超調而引起的激進主義、封城主義,即將把不分階級的疫病,變成一場階級化的災害。
因之,這種由官僚系統超調而引起的激進主義、封城主義,即將把不分階級的疫病,變成一場階級化的災害。而現代性超級都市的治理,本應是一種「流動中的治理」,目的不是切斷一切網絡和聯繫,而是切斷/削弱網絡中某些層面的聯繫,而加強另一些層面的聯繫。當然,這完全基於政府的信息能力,也基於福柯所說的「分類」的技術與能力。

希望在公民社會嗎?
儘管如此,我們也無法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短短一兩週內急速湧現的公民社會身上。
在這種全國性的地方激進主義氛圍中,公眾作為個體是沒有權利對風險做出獨立的判斷的,一切特殊情況也是必須要被壓制的,而對於湖北之外死亡率其實並不高這一可能性的討論,也是要被遮蔽的,因為「疫情現在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正如中國政治專家 Sebastian Heilmann 在《紅天鵝:非正統的政策制定如何促進中國崛起》一書中所總結的,一個權力集中而激進的體系,必然把合法性、權威和責任也高度集中起來。相應地,它也是成為了各種怨恨、不滿和批評集中的對象。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政治社會學家 Barrington Moore 在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發生的原因時,也早就提到過這一點。在接下來的防疫過程中,我們必然會看到各種矛盾的持續爆發,而問責的主體,會進一步上推。
儘管如此,我們也無法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短短一兩週內急速湧現的公民社會身上。當湖北紅十字會把法團主義社會組織的僵化無能集中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而慈善總會尚未從此前的春蕾女童項目醜聞中完全翻身的當口,各種臨時建構的公民社會網絡以極高的效率和超強的動員,部分緩解了湖北物資緊張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些網絡以校友、同鄉等私人、特殊聯繫為基礎,很少以一般性的信任和共同的政治/社會目標為團結的基礎。其中唯一的例外也許是各種粉絲後援會(比如朱一龍的後援會)。募捐和動員是這類組織的日常工作,各種物資轉運分配、賬目公開自然也是輕車熟路,因此自身也成為了援助武漢力量中的標杆。然而其組織目標決定了它們在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中的局限性。
此外,公民社會本身和政府的官僚體系一樣存在委託-代理問題與誠信危機,這也是不容迴避的。上週曾高調捐贈340萬套防護服的北美留學生,最後被證明無非就是一場互聯網營銷,而這僅僅發生在全網募捐幾天之後。
美國因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和共和黨政策平台的得勢,開始鼓吹一種與國家分離、甚至對抗國家的公民社會理論,而蘇聯、東歐的鉅變實際上加強了這一話語。然而,公民社會的基本邏輯和組織方式與政治社會(國家與政黨)、經濟社會(企業與市場)是不同的,前者是涵育多元性,後者要追求政治效力(efficacy)或經濟效率。這三者之間應該是一個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的關係,而不是零和對抗關係。
公民社會的基本邏輯和組織方式與政治社會(國家與政黨)、經濟社會(企業與市場)是不同的,三者之間應該是一個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的關係,而不是零和對抗關係。
長期來看,以制度化的方式統籌、調動資源並分配,並不是公民社會的長項,但也並不是說公民社會不能參與。試圖用公民社會來拯救疫情是不切實際的;而以此為契機,期待超越私人網絡的公共網絡能夠逐步建立起來,最終改變國家-社會的權力關係,確是可期的。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詩人王煒《不可安魂者》中的一段,來向仍處於圍城之中的武漢人民致敬,並感謝每一個在公共空間中堅持發出噪音、反對「安魂」,不憚譜寫錯誤的人。
「必須生活就是反安魂曲
是的,一個死神來建議你
必須生活,因為死亡仍未被理解
在每次希望渺茫的行動中
重複的交談就是反安魂曲
繼續下去就是反安魂曲
聽,你是否有能力用它譜寫錯誤
把希望譜寫成不可替換的噪聲?
聽,不要看,要去聽
記住我們的面孔不如記住
我們的聲音」
(酈菁,社會學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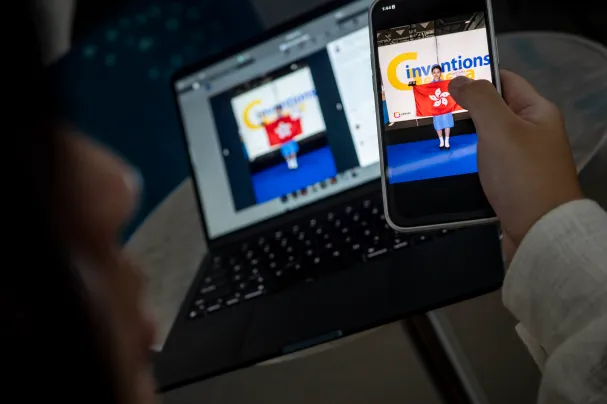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離題一問 端甚麼時候會有highlighter功能? 如果有的話可以記錄好文章裏面的重點 重溫起來方便一些
提到了很多可以继续深化讨论的点 不过希望有些词汇能够给出详细的解释
觉得写得很棒,很多点都很有启发
写得真好,期待该作者更多作品,谢谢!
怎麼加入不了會員啊,一登就卡死。
“必须生活就是反安魂曲/
是的,一个死神来建议你/
必须生活,因为死亡仍未被理解/
在每次希望渺茫的行动中/
重复的交谈就是反安魂曲/
继续下去就是反安魂曲/
听,你是否有能力用它谱写错误/
把希望谱写成不可替换的噪声?”
王炜《不可安魂者》
这篇写得非常好,把理论和对中国现实的观照融合了,此时此刻在大陆读到这个,很无奈。
美国医疗服务昂贵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医师协会垄断,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私人医保无效和政府补贴大企业集体医保造成的。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層的起源》
覺得寫得很好。對我而言,補充很多我不熟悉的面向與訊息,開啟不同層面的思考。謝謝這篇文章。
文末“以此为契机,期待超越私人网络的公共网络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最终改变国家-社会的权力关系,确是可期的。”
如此突然的转折,为何“可期”?
不错,继续加油。
最后那首诗,可否用隔行符标识出原诗的分行?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断句。谢谢
写得真是好 看透中国地方政治 从过度松懈走向过度激进
感谢分享,也认同其中的不少观点。但是某些用词有待斟酌 ... 开头的 “全民狂欢”,何欢可言?
谢谢贡献。
第三点专业人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写的最好。其他部分应适当延伸,用更平实的名词和例子来表达会更好。
如果有references就更好啦~
好文,但是不能同意里面的一个论述:“由此可知,對於醫生群體的行政控制是平價醫療的制度基礎和代價。代價是——頻繁發生的醫暴事件,把國家資源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隱蔽地轉換為醫患矛盾。” 不能同意这里的因果关系。即使国家控制的医疗体系变成社会或市场控制的医疗体系,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就依然会体现为医患矛盾。
文章配搭「高效的『中國模式』」一同閱讀,效果更佳。
另,文章中提及的「中央權力透過道路網絡深入地方」的觀點十分有趣,不知各位有沒有相關文章書藉推介閱讀一下?
【另一部分毋宁说是官僚系统的消极反抗:转译过来就是,“你不给我自主权,不顾实际情况下压行政任务,我就用最快的速度、不计后果地完成,把矛盾上推”。】感觉官僚系统虽然可能有这个心理,实际上是不自知的。它们对所做行为的后果,即使个体能察觉,整体依然无知。
別自說自話吧 !我國哪裏曾存在過公民社會呢 ?公民社會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玩意 ,咱們中國只有 人民,没有公民。
今天看内媒,本文首插圖中的紅衣防毒面罩男,已被視為"歐洲人有排華、仇華心結''的代表符號了,這種先發制人的手段,正是大陸官僚體系的強項,只要有外敵,就可諉過於人,公民社會頂啥用???
這篇是目前為止華文媒體最 up to date 又厚重的分析了。
理論名詞太多,有點生吞活剝。公民社會基本沒談,匆匆收尾。缺乏具體事實和案例的分析。
文章所說的實例是什麼?今天我所屬的中資公司派給我們每人一個「單層」口罩。上級的指令暢通無阻地實現了。中間能阻止禍害的專業科學知識的安全網給壓下去了。這是一種取捨,想要向好的時候𣈱通無阻,就同時要接受向壞的時候也會毫無阻礙地無底線地壞下去。所謂的穏定,究竟是在一個有上下限可預測的範圍內上落,還是短時間內無限上升同時背負無限下跌,哪一個才是口口聲聲的穏定。
@Dray 中央集权集的是权,尾大不掉、内斗严重争的是利。
恰巧今天就在和一位湖北的朋友讨论国内这种单向度的对上负责制给防疫造成的妨害。
私以为当下广泛出现的基层村民自治——封路、排查等等就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形式,但显然流为粗放乃至粗暴,缺乏专业技术官僚的统筹和监督,不但影响防疫效果还会阻碍社会正常运转和流通。
也许在不同层面上,基层自治+法人团体+专业技术官僚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且在各个层级都需要打破固有的有限准入秩序(limitied access order),把只属于本地居民的社区自治变为和外来居民的共治,把依托于同学、宗亲的公益组织拓展为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把仅属于政治精英的决策层引入专业技术官僚的议论和监督,而这些又恰恰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让步,或许这次的疫情会成为变革体制的一次契机也不一定呢。
好文章
「以此為契機,期待超越私人網絡的公共網絡能夠逐步建立起來,最終改變國家-社會的權力關係,確是可期的。」
在看完今天網信辦發出「違規自采」這新聞後,老師抱歉,我還是對於從公民出發推動國家權力改革這個看法持悲觀看法。
《叫魂》
作者认为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各部门尾大不掉、内斗严重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有没有人可以再解读一下?毕竟在人们普遍认知中,中央集权可以减缓各部门合作不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