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史碧瓦克是當代知名的馬克思女性主義者、後殖民論述的重要理論家,發表於1987年的《在其他世界》是她的第一本個人論文集,也是影響後世深遠之作。2021年12月,聯經出版了由李根芳翻譯的《在其他世界》,再度引起學界對史碧瓦克學術理論的討論。學者戴遠雄從去歐洲中心面向著手,談談史碧瓦格的跨文化論述之重要性與啟示性。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今天史碧瓦克廣泛被文學、文化研究、社會學、人類學和哲學研究者閱讀,後人從不同的角度繼續發揮其創見。《在其他世界——史碧瓦克文化政治論文選》(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是史碧瓦克第二本著作,代表著她從博士論文階段的英語文學研究,轉而邁向後殖民研究的重要階段,有助開啟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風潮,影響遍及非洲和亞洲。
我認為史碧瓦克不僅對文學和文化研究有重要貢獻,而且對歐洲哲學有重要啟示,因為她提供了跨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哲學一向宣稱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而其起點是經由翻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吸收當代法國哲學的成果,逼使歐洲哲學正視其排斥的異文化,進而開展批判歐洲中心的跨文化論述。
批判與堅持:要把「面容」還給他人
首先,史碧瓦克在《在其他世界》延續了德希達的解構實踐(deconstructionist practice),但不再局限於解構歐美的哲學和文學作品,而是指出它們如何有助我們重新認識非歐美的文本。
眾所週知,史碧瓦克在1976年出版德希達《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的英譯本,並撰寫長篇譯者導言。德希達的解構不是一個個規條或一套理論,而是主張批判地閱讀一個文本,需要指出文本意圖帶給作者的意義和遺漏的地方,從而突破作者框定讀者理解的範圍,所以解構是一種閱讀策略。[1]雖然德希達解構西方形上學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史碧瓦克卻觀察到他從沒有嘗試解構東方的思想,東方思想是他不認識的異域,因而也無法借由東方來突破西方形上學的框架。[2]
《在其他世界》裡〈國際架構下的法國國女性主義〉一文提到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關於中國女人》,史碧瓦克批評她「沒有引用任何的檔案證據」[3]的第一手資料去理解中國女性,卻論斷中國傳統對女性更少壓抑,毛澤東的革命政權如何解放女性等,只是反映了她身上帶有殖民者的態度。[4] 與之相反,史碧瓦克提倡的「國際架構」(international frame)並不是要用西方哲學或女性主義概念去衡量東方文化,也不是要對西方和東方加以平衡的比較,而是要向第三世界的經驗開放,「學習去跟她們學習,對她們說話」[5]。也就是說,不要想著利用歐美的女性主義去「解放」第三世界的女性,這只是顧著「我是誰」,忘記了問「其他女性是誰」。[6]用德希達的話來說,我們不要把他人的「面容」(visage / face)視而不見,不要化約其為自己可以決定的內容,要把「面容」還給他人。
如何研究底層:讓不可見變成可見
其次,史碧瓦克正是要把這種正視他人的倫理態度實踐到底,落實在後殖民的研究裡。
《在其他世界》的第三部分〈走入第三世界〉翻譯和評論了印度當代作家瑪哈綏塔.戴薇(Mahasweta Devi)的小說作品,代表了「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方向,也可能是全書最引人入勝的章節。史碧瓦克之所以譯介瑪哈綏塔,因為後者並非靠印度之外的歐美女性主義思想來解放女性,而是發掘本有的歷史傳統,再加以衝擊既有的權力位置。
瑪哈綏塔的〈都勞帕蒂〉(Draupadi)中的主角都帕蒂(Dopadi)代表農民起義,雖然飽受印度男性軍官凌辱,卻同時手無寸鐵地挑戰了男性軍官,不僅是一則「女性在革命中的奮鬥寓言」[7],同時也是重寫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因為這部史詩的女主角也叫都勞帕蒂。瑪哈綏塔的另一篇小說〈乳母〉[8]中的主角雅修達藉由豐富的母乳,為其他人哺乳來賺錢,改善家庭的生計,而且因為她成為了眾人的「母親」,所以得到其他人尊崇。雅修達一方面是被壓逼者,被丈夫無窮地索求性滿足,另一方面也是自主的女人,比丈夫更有力地獲得經濟權力和社會地位,因而小說呈現了十分複雜的現實。
史碧瓦克認為這篇小說有力地質疑西方馬克思主義,因為它忽略了女性藉由生育也可以成為主體,同時也批評自由主義只重視來自第三世界的精英女性,因為她們成功進入了和白人精英相同的階級,可以追求性歡愉的自由,不受家庭和丈夫的壓逼,卻漠視了第三世界的底層女性的實際經驗,她們總是被逼在父權壓逼和勞動困苦中,幸運的話才能偶爾獲得自由。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底層研究並不是單純的書寫底層,找出社會被受壓逼的族群,通過書寫讓他們從不可見變成可見,更重要的是,底層研究扮演了超越西方哲學(形上學、馬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所宣稱的單一普遍真理,尋找另一種國際主義,也就是可以包含第三世界獨特的後殖民處境論述。[9]因此,底層研究不是單純地認同或讚揚底層經驗的政治表述,它同時批判第三世界後殖民處境當中的壓逼。史碧瓦克後來在〈底層可以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中,更清楚地主張底層研究要呈現去殖民空間的異質性,從而使之走向建立統識(hegemony)的道路,也就是逐步動搖以歐洲為中心的知識體系。[10]
警惕歐洲中心論的聲音正在出現
《在其他世界》出版十二年後,史碧瓦克出版了《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書中第一章就解構西方現代哲學對第三世界文化的偏見,例如康德對土著的蔑視,黑格爾貶斥印度思想為愚昧,馬克思對「亞細亞生產模式」缺乏歷史認知等。[11] 此舉並不是要藉由批評西方哲學家無知(畢竟沒有人可以對所有文化都通曉),而否定他們整套理論的有效性,而是通過矯正他們對第三世界的錯誤偏見,避免歐洲哲學繼續做殖民帝國的共謀,阻止哲學家有意無意間在文化的角度上證明歐洲文化更為優越,來支撐政治經濟上對第三世界的宰制。
我認為《在其他世界》對歐洲哲學的啟示在於警惕其歐洲中心論,無視歐洲知識體系對異文化的偏見和無知。事實上,近年不論歐洲學界或華文界都有不少學者致力以不同方式來擺脫歐洲中心論,跟史碧瓦克有類似的看法。出生塞內加爾的哲學家Souleymane Bachir Diagne就曾指出「對哲學史作出後殖民的重寫意在指出,例如把歷史看作由「聖經和希臘人」組成的單一軌跡所構成,由耶路撒冷經由雅典,再到羅馬,然後到海德堡、巴黎和倫敦,這是完全是錯誤的。」[12] 這並不是意味著要把歐洲哲學對各種課題的研究都全盤放棄,反而是要擴充歐洲哲學的範圍,讓哲學走出意識到自身的局限而走向其他文化。Diagne認為即使接受後殖民的挑戰,哲學也不應放棄對普遍知識的追求,因為「普遍之知識(the universal)不是就此給予的,而是在不同的抗爭裡被經驗到,也在這些抗爭滙聚和共同發生的過程裡,在團結之中,彼此分享著共同的解放目標,普遍之知識以尚未能被解讀的方式而受到測試。」[13]
2022年2月20日
(戴遠雄,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約聘助理教授)
[1]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8.
[2] spivak’s preface, of grammatology, lxxxii.
[3] 史碧瓦克著,李根芳譯《在其他世界》臺北:聯經,2021,頁295 。
[4] 同上,頁297。
[5] 同上,頁291。
[6] 同上,頁320 。
[7] 同上,384。
[8] 同上,522。
[9] 同上,434。
[1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ed. rosalind morr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80.
[1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著,張君致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國立編譯局,2005,頁9-130 。
[12]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on the universal and universalism,” in ed.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and jean-loup amselle , in search of africa(s): universalism and decolonial thought, trans. andrew brow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23.
[13] 同上,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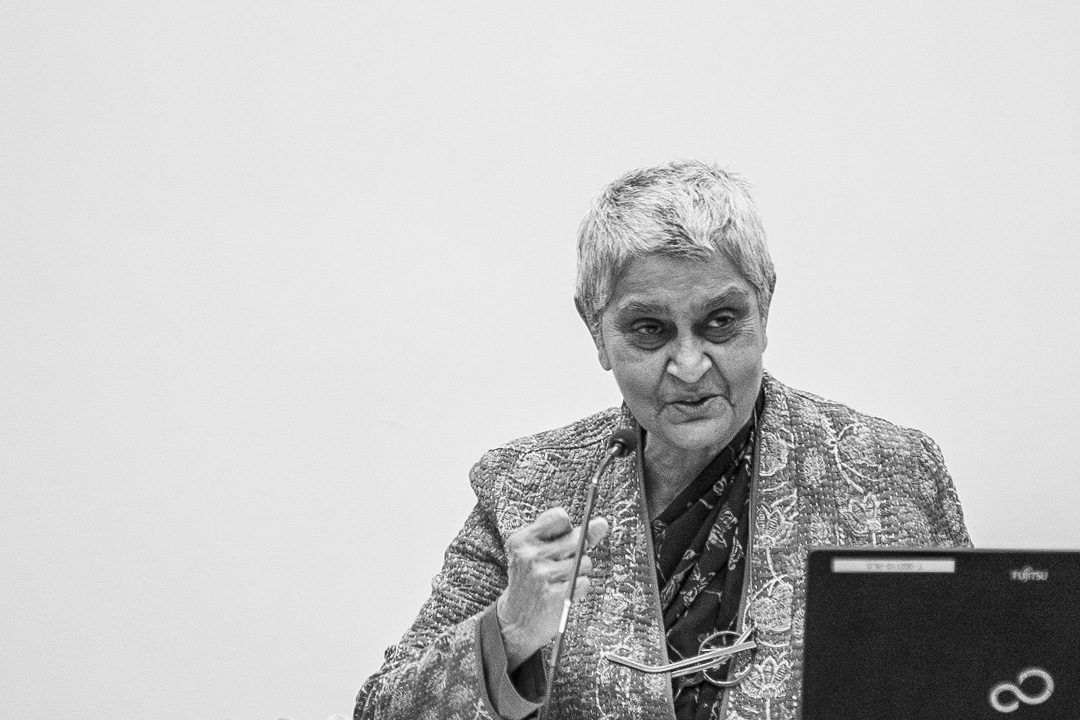




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