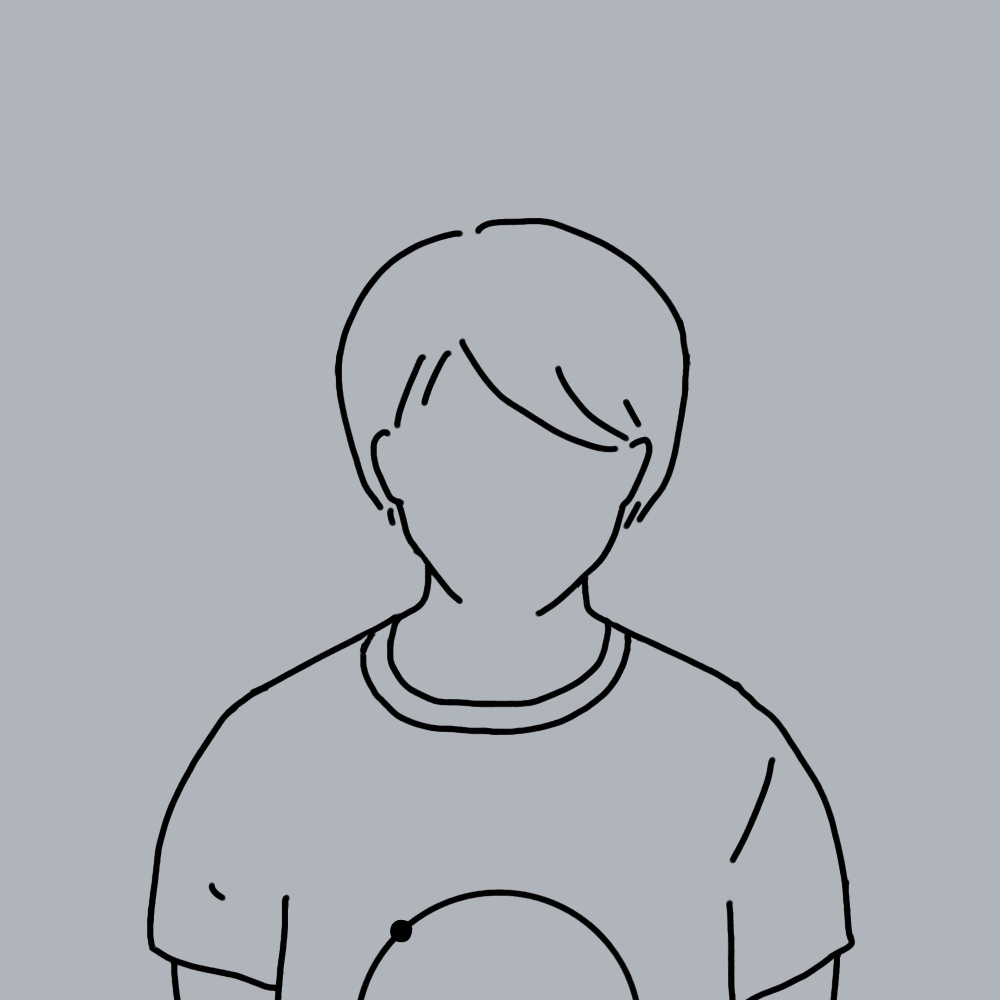關於編輯-許伯崧
大家好我是台灣編輯許伯崧。踏入新聞業十餘年,深深感到「難以全身而退」,即便時常無言以對,依舊得試著回答這個世界。很高興有機會分享我的收藏,這次分享的主題是「十週年」,希望大家會喜歡。
本次活動分享的「新聞地圖」主題-十週年
會選擇分享「十週年」這個主題是因為,這十年世界變化劇烈,而回顧式報導能將重心放在「事件如何影響個人/社會」,並有助於建構「公共記憶」。這是一場記憶的陣地戰。趕緊來揭曉我的私藏新聞地圖吧!

「當我踏進來後就難以再全身而退」是台灣饒舌歌手 Gummy B 在《REGRET》中的一句歌詞。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更好,但我知道自己踏入新聞業後已難以全身而退。在這不長的十餘年新聞職涯中,你問我會不會後悔,也許有時候會,後悔無法迅速回應世界,後悔在回應世界後,換來更多的是無言以對。
即便無言,我們依舊得試著回答這個世界。
這次分享的新聞地圖,主題是「十週年」。這十年,這個世界用「天翻地覆」都難以精確說明局勢的劇烈變化;也難以涵括在翻覆之後,那些現實中的個體與經驗的歧異與頓挫。
時間是公共性的嗎?還是是一種「共時的非共時性」?尤其這十年,社群媒體成為日常,除了替人們省掉社交外,連可有可無的新聞媒體都順道省掉。人們滑著手機、瀏覽著社群媒體上的所謂「新聞」,新聞的定義更像是後現代,但人們卻也將其當作一種當代新聞的實踐。
在這樣的非共時、非共感、非共構的世界基礎上,我們的十週年,是誰的十週年?這像是薛西佛斯的問題,當問題被提出的當刻,問題成了問題自己——成為新聞議題的事件更是如此。
即使帶著這樣的困惑,但面臨將屆的週年議題(特別是十週年),總是令人感受到如臨大敵的壓迫與窒息感。從來沒有行業前輩告訴過我,為什麼是「十週年」,又為何十週年重要?我向來切身感受到的,一個事情重要是不需要理由的,事件會自己說出原因,原因也會描繪出社會中那隱約、模糊的癥結——也許是個細微的衝突,又或許是個始終落空的期許。
週年報導的矛盾與需要
多年前,我還在編輯室規劃某個週年系列報導,找了一些撰稿人討論,令我意外的是,多名撰稿人告訴我,他們其實對「週年」的報導形式略為介意。其中一人對這類形式化的週年報導半開玩笑地說「又不是做對年」(台灣喪葬習俗,亡者逝世一週年祭禮之稱)。也有人提及,他感覺「週年」把事件商業化,就像一個固定週期的盛大展演活動,也把事件神聖化,「一旦事件神聖化,便失去彈性,也難以找回現實感。」
不過,即便有著這些來自寫作人的切身反思,但週年報導對新聞業來說依舊無可迴避。今年9月,我參加一個新聞基金會關於回顧式報導的講座,主辦單位將這類型的報導定義為,「相較於新聞當下,經過時間沈澱,回顧式報導可以重新審視事件起因、過程與後果」,主辦單位認為,該報導可以補足事件當下被忽略或未知的資訊,提供讀者更完整的脈絡分析及觀點。
於我而言,這段話讓我更有共感:「(回顧式報導)也能將重心放在關鍵人物或群體的變化,觀察事件如何影響、重塑個人及社會;不只重述事實,提出對事件的歷史評價或社會啟示,也有助公共記憶。」
這句話的的關鍵,一是「事件如何影響個人/社會」,一個是「公共記憶」。一個事件之所以成為新聞,在於它具體對個體、群體產生影響(甚至衝擊),個人作為社會中最小公共主體,首當其衝的是事件作用在其身上的後果。而當私人的、私密的記憶,上升到公共性的層次,在私人與公共之間,便成為一場記憶的陣地戰,透過詮釋與再詮釋,彼此拉扯奪下歷史的灘頭堡。
這兩年在台灣,我們規劃執行了兩個十週年的專題系列報導:先是2024年的太陽花運動/學運(又名三一八運動),再來是今(2025)年的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件。而這兩場性質截然不同、關注與衝擊層面又迥異的議題事件,甚至在議題的命名分歧、認知嫌隙下——是太陽花/三一八學運或運動?是八仙塵爆又或是粉塵燃燒——我們又該如何重述、或是回溯該事件?
就像有人批評,太陽花不是學運,使用「學運」一詞是為以學生單純、容易遭洗腦的印象加以貶低這場運動;而八仙粉塵事件亦不是「塵爆」(粉塵爆炸),無論是從事發當下的影片、或是瞬間燃燒的現象,這場公安意外並不肇因「爆炸」,它是高密度的粉塵快速燃燒導致大規模死傷的悲劇。
特別提這兩起新聞事件,一則是我新聞職涯的正式起點,一則是十年前首次企劃及執行的大型專案。共同的是,它們強烈形塑了我往後的世界觀,就像涉水在一灘泥濘後,雨鞋上留下的水痕般,你知道自己走過那灘泥地,你知道那攤泥地發生了什麼事,你從此難以從那攤泥濘全身而退。
在這次展示的收藏地圖中,各自收納了來自不同地域、事件的十週年報導。我想先從「台灣八仙粉塵燃燒事件十週年」及「太陽花學運十週年」分別談起。
八仙十年:在遺跡中重生
八仙粉塵燃燒事件發生在2015年6月27日,媒體上幾乎以「八仙塵爆」來指稱此一大規模的燒燙傷災害;實際上,災害現場並未發生有「爆炸」情況,火勢整體燃燒時間「僅有」40秒,但依舊造成了484人受傷、15人死亡的悲劇。這場意外,也是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安事件。
十年前,我在一間傳統媒體任職,後來另外參與報社一個專題報題項目,通過遴選後進一步籌組報導團隊,以召集人的角色展開這前後逾十個月的追蹤報導企劃。
當年,這個企劃分為幾個塊狀主題:其一為「追蹤報導」,從事發同年的11月起,開始展開追蹤,以一週一期的報導頻率,持續追蹤傷者半年。其次,這個專題報導也進行海外報導,聚焦在各國如何進行「大型群聚活動」的安全管理。當時台灣針對大型群聚活動雖有管理法源,但落實上多流於形式的紙本作業,缺乏實質風險審查。在當時也因應新的媒介技術興起,做了空拍與現場重建的模型,不過很可惜的是,時隔多年,這個網站現在也已經不在網路空間。
自然,規模達499人的大型公安事件,太多的個體與經驗,在集體性的災害與傷害底下,都被抹除了。他們被抹平為一種失去面孔、沒有表情、沒有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情緒,在彼時的輿論漩渦中,他們成了一群遊手好閒的「跑趴仔」,一場流行於全球的粉色玉米粉塵派對,在歷歷指控中成為「吸毒趴」與「性愛趴」。
他們既失去了自己的聲音,也失去自己命名這場意外的權力。在一則則浮現的指控中,他們是「愛玩」、是「活該」,談到賠償,輿論更是激憤,漫天襲來的「死要錢」譏諷更是幾乎席捲整個輿論場——他們不僅無法為自己澄清,連話都還沒說出口,就已招致惡意的奚落。皮開肉綻的傷口,早已不限於可見的身軀。
持續關注八仙事件,其實一開始是受到荷蘭公共電視追蹤「福倫丹大火」後續的影響。
2001年,荷蘭觀光小鎮福倫丹一間名為天堂的小酒館發生大火,火勢起因為不起眼的仙女棒點燃了酒館中的耶誕掛飾,火勢沿著耶誕數燃燒,也因為酒館擁擠導致疏散不易,最後導致了14死與241傷的慘劇。其中近兩百名傷者,受到二到三級的嚴重灼傷,且傷亡者多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荷蘭公共電視為此展開追蹤報導。先是事發一年後,他們採訪了燒傷者在治療與復健的歷程。並在事發十年後,回頭重訪這些傷者,也帶領觀眾認識到他們已走出新的人生道路。儘管身上的火痕依舊難以忽視,但每個人都在新的階段,走過舊日悲傷,展開新一段人生。
當時在報社資源的挹注下,完成了第一個八仙週年的採訪專案,今年的第十年,於去年底就在心裡想想一定也要做些什麼。
今年的十週年,端傳媒以〈消失的樂園,新生的人〉作為主題,以「遺跡/遺留」作為概念,並以三篇報導的「物件篇」、「標籤篇」及「親密關係篇」作為方法。在十週年的此刻,希望透過傷者在這十年來重視的物件,回溯自己的火後人生,並以物件,作為自己與家人、自己與社會、自己與他人的回顧。「物件」本身並不只是物件,更多時候是關於一段關係的連結,一個證明且自我賦權的角色,更甚者,是一段對自我的凝視與省思。
我想到一名編輯朋友的分享,他提及日本重要生活風格雜誌《BRUTUS》在電子報中分享了編輯幕後故事,這期的主題「腕錶,訴說著主人的故事」,編輯之二的清水政伸在一張過往雜誌的舊照中看到一只手錶被收納在一個罕見的錶盒裡,他說「該戴哪支錶、又該如何配戴,這些固然重要,但或許就連手錶從腕上取下時的擺放與收納方式,也能展現出主人的風格。」
「即便是錶盒也千差萬別,有著各式各樣的選擇。」清水政伸繼續說,有些人則可能會將手錶與日常配戴的飾品,一同隨意地放在托盤上;有些人可能只是隨意地將東西塞進包包裡,「即使是脫離手腕的錶,也能融入生活風格,訴說著主人的故事。」
從手錶的角度來看,怎麼戴、選擇什麼樣的手錶是一種物件與人的連結,輻射出個人的美學與對自我的理想投射,《BRUTUS》的選題從反向來看,當手錶脫離主人之後,它如何被安放、又放在哪裡,那也是一種生活的風格——看起來說的是手錶,但說的更是「主人」的故事。
八仙的物件篇,雖然不那麼直接談物件身後的主人,但從主人為何選擇該物件,重新回溯傷友的生命/傷後歷程。「那個」物件於主人而言意味著什麼,是傷後一年、兩年、三年,曾經珍視的物件,與十年後所展示的,必定在意義的重量上有不同層次。
在時間線上,傷口隨著時間遷移逐漸結痂、癒合並長出新生皮膚。一個原賴以維繫的物件,如今已成昔日記憶,它並不消失,而是成為現在的自己——有人因為一本日記重新理解燒傷與家庭的關係、有人為了穿上義肢重新站起,傾盡全力地復健;也有人讓自己成為奶酪本身,隨著瓶罐自由延展,不再活在既定的框架中,他更感到自由。有人因為寵物,讓自己重新學會愛人的能力;有人因為寵物的老衰,而意識到原來自己難以放下別人對他的眼光。
講的雖然是物件,但也不只是物件,它是一段關係的起點,也是關乎自我的重新定位,它折射出的鏡面讓自己重新認識了「我」;它也是一個與之拚搏的目標,因為想證明自己,必須有看得見的未來去使勁突破。
我們不選擇直面受傷的個體,我們選擇從一個無機的物件、一個負面的標籤以及一段難以言說的親密關係,從十年長河中重新打撈人們對事件的記憶,以及打撈我們對事件的觀點。我們層層摺疊事件,使其可以如洽收納,在你記起這場災害之際,亦可以翻折展開,這些摺痕是我們設計的觀看方式。
- 「十週年」私藏之一:台灣八仙粉塵燃燒十週年
太陽花十年:記憶與詮釋的戰場
如果說,八仙粉塵燃燒是一系列事件如何影響個體與社會的回顧式報導,太陽花學運十週年,更接近一種對於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或者說,是對於如何詮釋這場全面逆轉台灣走向的社會運動爭奪。
彼時,台灣正屆2024總統大選期間,政黨近身肉搏、氤氳蒸騰情緒熾熱,由於代表民眾黨參選總統大位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被視為乘著2014年太陽花後之民氣選上國民黨的鐵票倉台北市長,加上競選期間柯文哲頻頻喊話「太陽花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貿』」,讓許多太陽花運動者大肆批評。不過,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中,究竟運動目標為何、每位參與者的認知為何,個體經驗分歧,難以透過一個特定的字詞加以涵括。
與此同時,輿論場上亦出現對太陽花運動的「誤讀」與「超譯」。「太陽花學運十週年」與其說是一系列的事件回顧,更是一場「回溯記憶」的行動,其中,更深刻涉及詮釋權的再拉扯。它自然無可避免提問到「太陽花運動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運動後又留下什麼?」,但回答或許也是個人的、私密的,正因這樣的私密性,構築起這場公共行動的記憶——行動是公共性的,但記憶是個體性的。
在這系列報導中,我們提出「位置 x 記憶」這個核心概念。記憶如何私人,涉及到人們所身處的「位置」——這個位置包含了「物理位置」與「時空距離」,深刻形塑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場運動的方式與如何記憶。
也因此,在方法論上,我們從「空間軸」與「距離/世代軸」接近命題,從空間的國會建築一路輻射至場外道路;也從親身參與者,延伸到遠離台北、以及當年僅有十多歲的Z世代。透過不同座標的交織,呈現複數的、立體的運動記憶與再詮釋。
詮釋難以逃避武斷的質疑,但質疑也難以回應詮釋的個體經驗差異。其中的矛盾、衝突與歧異,在十年跨度中生氣蓬勃,這也是我們嘗試捕捉的。
報導結構沿著三條軸線展開:首先聚焦「人的變化」,觀察參與者如何因其所處位置而產生不同記憶;其次補足運動的完整脈絡,透過〈運動記憶與回聲〉與〈太陽花前浪〉兩篇報導,回溯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伏流,說明太陽花並非橫空出世,而是長年累積能量的爆發;最後提出社會啟示,探討一場運動如何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從近景的〈「無論好壞,都構成現在的我」〉五位核心參與者的十年軌跡,到遠景的〈一念十年:台灣20世代的太陽花記憶〉中年輕世代的模糊卻深刻印象,再到林飛帆專訪與「十年後才到場的普通人」的對照分析,我們看見一場大型運動底下,必然存在著歧異、甚至完全相反的個人生命進展。十年的跨度,讓其中的人們走上不同的軌跡與有各自的際遇;我們在共同中,卻又似不在共同中。
- 「十週年」私藏之二:太陽花學運十週年
守住火:讓昨天不結束
在這個收藏頁面中,也收納了「香港十年」與「莫拉克風災十週年」的專題報導,前者描繪香港「運動世代」在雨傘運動十年後,從理想、挫敗、逃離、療癒到再出發的情感脈絡,並細緻呈現當年中學生如何面對身分、信念與時局變遷,學習與過去和解、勇敢前行。
而後,則以一場颱風引發的滅村巨災後,那些被留下的村民,在深重悲痛之中,努力在生死、過去與未來之間尋找意義與連結。十年來,小林村的故事,呈現出一個災後社群在失落、傷痛、抗爭、凝聚和文化復振間的複雜情感脈絡。死者與生者、祖靈與新生、家園與重建,交織出災難記憶與地方認同。
十年,久得足以感受到物換星移與人事已非的感慨,也足以看到一場災害不僅在於當下的瞬間衝擊,亦包括後續演變、反覆協商與未竟之事。十年,也短得讓人留在自我質問、懷疑與懊悔中,短得來不及與自己和解,短得來不及放下過去。
十年,揭示了記憶與遺忘、共鳴與疏離如何在長時間中交織錯雜;十年,新生兒的誕生,形成新的家族、社群的記憶圈。十年扯掉了歷史的巨幕,時間亦改造了人心。
昨天發生的事,不會只在昨天結束,但只會記得片段,記不得全部。「十年」,是我們讓昨天從不結束的方法,也是我們試著記得全部的努力。回到開頭那句「當我踏進來後就難以再全身而退」歌詞,當我們都在時間之河盤旋打轉,其實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即便你不是自願踏入。
但我仍想守住那團火——那是我們記得的方式,也是讓新聞不至於熄滅的微光。
以上是編輯的新聞地圖私藏開箱Show,經過編輯的分享與介紹,相信大家對於「十週年」主題有了更多想像與解讀。
如果你也對編輯分享的文章或是專題產生共鳴,歡迎按下收藏鍵,開始建立專屬你的新聞地圖!
💡還有什麼想問編輯的嗎?
歡迎在本篇評論區留言交流,與編輯一起討論報導背後的脈絡與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