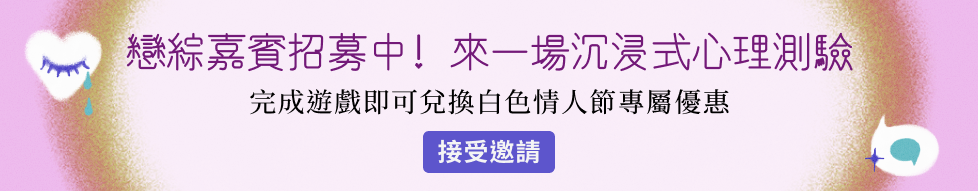速递 Whatsnew
更多
解读
更多

/
仅限会员
解读| 中国掀起“文旅热”:当地方财困,城市开始经营流量
从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到天水麻辣烫,地方争先恐后树立城市文旅IP,塑造流量现象。更有甚者,地方官员亲自下场,开直播,拍视频,博取网友眼球,只求城市获得青睐。
评论
更多
系列
更多
栏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