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北,指中国大陆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个省份。它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在20世纪初期便是东亚最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在1949年之后因拥有煤炭、钢铁、石油等国有企业和军事工业,一度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骄傲。但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东北逐渐衰落。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东北有大量工人被迫离开工厂,失去工作。近年来,东北更因高迁出率、低出生率和严重的老龄化而成为“失落之地”。这片黑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它会成为转折时代的失落者?我们决定与数位从东北走出来的作家、导演和智识分子进行对谈。本篇的对谈对象是来自东北沈阳的80后作家双雪涛。
2018年是作家双雪涛在北京生活的第三年。他的东北口音丝毫不减,直接、简短、有节奏,并极富感染性。就像回避北京的快节奏、重污染、无休无止的饭局和近在眼前的全球化一般,双雪涛回避使用普通话。说东北话、写东北的故事,都是他最自在的频道。
他因书写东北而成名。在已出版《翅鬼》、《天吾手记》、《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等作品里,双雪涛的笔墨着力在衰落东北社会中的边缘人,譬如沉溺幻想的小职工,落魄潦倒的写手,被遗弃的孩子、女人或丈夫……背景无不是废弃的工厂、破败的街道、空荡的广场、深夜的歌舞厅和台球社——从某种角度说,这些故事回答了外界关于“东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疑问,也印证了人们对于当今东北的既有想象。
在被媒体称作“迟来的大师”、“为故事而生的人”之前,双雪涛曾是个一看到领导“嘴就发瓢儿”(东北话,是口才差、不会讲话的意思)的小职员。他是八零后,出生于辽宁沈阳,少年时经历父母从工厂下岗,他在吉林大学念完法律系之后,回到家乡的银行工作,然后娶妻、生子,平静地生活,人生的前半程几乎从未离开过东北。
直到2010年,当时27岁的双雪涛看到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台湾文学比赛通知。为了60万新台币的奖金,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在20天之内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也就是后来出版的《翅鬼》。这是一篇发生在“雪国”的虚构小说,主人公是“带翅的婴孩”,“生而为奴”,却依然拥有飞翔的天赋。他靠这个故事拿到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从此,白天的双雪涛仍然是那个埋头于财务报表的银行职员;但在夜里,他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职业小说家。在台湾的获奖让他看到了一种逃离的可能。两年后,双雪涛完成了12万字的长篇小说《聋哑时代》。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以工业为支撑的城市里,一批在应试体制和竞争逻辑里成长起来的少年们,这些少年中既有顽固体制中的幸存者,又有突破制度、开创小小天地的怪孩子。再之后,双雪涛成为沈阳这家国有银行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提出辞职的员工,这在当时那个人们根深蒂固地崇尚体制、依赖体制的东北社会,无疑是一个令人讶异的决定。
真正在大陆崭露头角是31岁那年,双雪涛在知名文学杂志《收获》发表了短篇小说《跛人》,并在次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北京生活。那是他第一次完全离开东北、离开家,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生活”。
这样的生活经验可能比大部分的“北漂”晚了十几年,像是迟来的青春期。他有更多时间独处,也有更多机会结交新朋友。生活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白天看报表、晚上写小说的分裂了。那样的分裂曾经带来压抑,压抑使他反抗,反抗最终成为他创作的动力。那时候的双雪涛面对的压力是外界的,但现在的他需要面对的压力更多来自于自己。
在他去年最新出版的小说集《飞行家》中,双雪涛笔下的主人公开始和作者一样,从东北移居北京。对他来说,如果东北经验是他的本体,那么北京经验仍是一片扑面而来的迷雾。他对北京经验的处理显然不似处理东北经验那样娴熟,读起来也不似东北故事那样运筹帷幄,可是却更加鲜活,甚至更加可信。如果说对东北的书写让他横空出世,那么对北京经验的处理,才让他真正具有了当代性。

“不要让我再谈论东北了。”他这样表示。当东北的下岗潮、破产潮、移民潮频繁出现在媒体的标题上,好奇心和猎奇心驱使着人们扑向双雪涛,大家热衷讨论他和地理的关系,在他身上贴上“东北”二字的标签,并试图让双雪涛给予有关东北最准确、也最恰当的解答——究竟是东北成就了双雪涛,还是双雪涛重塑了东北?
答案是:相比反反复复地谈论真实的东北经验,双雪涛更愿意虚构它;而相比追问东北对他的影响,双雪涛正在发生中的北京经验中寻找踪迹。
下面是端传媒与双雪涛的对谈。(端传媒简称为“端”,双雪涛简称为“双”)
谈论东北,是媒体和读者做的游戏
“那东西,我是捏给自己的,别人没权利看,所以我把它扔了。你保卫的是主席,我也有要保卫的人,人生很长,审判不是在此时,很久之后你回想,也许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鱼喝水也能长大,不用吃人。”——双雪涛《光明堂》
端:你在北京这几年,东北口音一点都没有改?
双:没有。没有减弱,如果是特别熟人,(我的东北口音)那还更强烈。
端:你过去的小说里面,一些故事有牵扯到北京,但细读,其实都是间接的北京。你现在是完全生活在这儿了,你觉得生活在北京,对你写的东西有影响吗?
双:有影响,有影响。会比较自然地影响我。不是说我住在北京,我得写一些北京的故事,而是北京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了,自然会从我的身体里淌出来。比如说,我要写什么东西,写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在北京见到过。不仅如此,见到的人,或者是见到的事,都会下意识地写进去,因为北京就是我现在生活中的主体。
但也有些作家住在北京或上海,他写自己的童年。我也会写,但是目前,我想琢磨琢磨我现在的工作、职业和生活。
端:你说起在东北的银行里工作的那段时间,是特别压抑的感觉。创造力是被压抑出来的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双:正常来说,在一个写作者的起点,或者是真正和创作结缘的时候,需要比较适宜的压迫性。在那种情况下,从无到有那一下就出来了,有可能你原来从来没有想过。我在那个时间段(指在老家银行工作的期间)从来没有想过写小说,但是那压得我不行了,我四处想办法,想办法疏解,找一个树洞说点什么事,就找到写小说这件事。
当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之后,那种情况可以不用去想了,也不用去奢求了。作为个人来说,现在的时间是我自己可以调配的,生活也没有到吃不上饭的地步,跟那种不自由的、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被操纵的感觉相比,压力弱了一些。现在我感觉到的压力是公共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看一些事不顺眼,或者是希望生存的世界会更好。
按道理说,这种情况应该能写得多一点;按道理说,人不能矫情,不能说“压迫压迫我吧”。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状态下,其实更应该主动。比如说卡佛当年在低层干活的时候,作为蓝领,酗酒,他也写,但是他写的是片断式的诗,也写的很多。但当他到了一个稳定的时期,到他去世之前,也有一定的名声,也从酗酒的状态里走出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这个稳定的时期并没有维持太久,他就去世了。但正常来讲,他这么写,他也许会越写越好,也许会越来越稳定,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工人下岗、国企没了都是小事,但——北方消失了,北方就化为乌有了啊,你知道吗?”——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
端:你发现东北有什么新的创造力吗?
双:没有,暂时没有。
东北出了些写东西的人,我很期待有更多写东西的人从东北出来。因为我觉得东北其实有很多有才华的人。
东北本身的语言,如果你掌握了,把东北的语言书面化,你就有先天优势,因为(东北话)能够传达的信息、感染力,其实蛮不错的。对于来自东北的创作人来说,把自己的东北节奏和腔调变成一个好的表达工具,是有优势的。
而且东北又有很多有意思的人。那里的人有很多戏剧化的地方,有很多可以做、可以写的。东北人是挺会说话的,挺会聊天的,挺会调动气氛的,也挺会把语言的效果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起话来比我有意思多了,咔咔咔,那小嗑唠的,我就听着,跟着乐。幽默,而且节奏好,讲一个事讲的特生动。
端:这是什么原因呢?
双:这个得要文化考古学家去想一想,我想不出来这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出人的地方,就是出创作者的地方,现在出的还不够多,应该更多。但有的时候,东北人的娱乐感比较强,而大家觉得写作是文化人干的事。
我这两年是远离东北的。2015年我32岁才来北京,现在大部分的生活在北京,首先要适应这个生活,花去一份精力,然后还要写东西,然后还要有一些其他的琐事要处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重心在往北京这边转移。
不是我去选择写东北,东北就是我生活过的、现在也经常回去的一个地方,很自然地就要去操作它,因为你在那里看见了很多很多东西。但这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是特别特别客观的,是命运。
端:采访的标题应该叫“不要再让双雪涛谈东北了”。
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游戏。比如说,一个人去讨论东北的写作,甚至有人说东北的没落,其实都是一种游戏,一种媒体和读者做的游戏。这个游戏有多大意义?我觉得不一定。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太关心这个。以前我不理会这个的,我以后也不太倾向于去理会这个,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文学和文坛,区别很大,文学和文学奖,区别也很大。我从没想到得奖,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文坛,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卸载下来好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点,作家不能胆怯,不是说一定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你得敢去尝试、敢变、敢去毁坏,你老是特别把自己当回事,把自己的过去当回事,那太傻了。写小说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事,不是脑子里想好了写,有时候有很多随机的、自由的,这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通过写小说让世界变得更好,是吹牛
“我爸正在用我的电脑下棋,他和我妈都已经退休两年,其实退休之前的二十年已经下岗,做过不少小买卖,在街边流窜,被驱赶着,与城管厮打,争夺一口苞米锅……我妈此时应该正在马路上和一群同龄人暴走,一路走和平区走到铁西区,可是效果并不明显,眼看胖了起来。”——双雪涛《跷跷板》
端:那你认为叙事对于你、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双:一个作家肯定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不太满意的人,特满意的人干不了作家。现在到这个时代了,小说能够改变世界多少,不太可能。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通过小说改变别人的想法,让世界变得更好,这就叫吹牛。
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多器物,这么多人和事,而我想做一个写小说的人,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把我的小说投入到这个世界里,中和一下,可能对大部分人会好一些——汇入到、掺杂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提高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电影里说的。我觉得说的蛮好的,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内容,融入到这个世界里。
端:以前,你在东北写东北;现在,你在北京,北京是另外一个城市。透过对北京的深入,你会不停地反观过去的经验吗?会有变化的感觉吗?
双:当然,人每天都在变。人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会不停地在变化,你的视点和感受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比以前看待同一个东西的心情变得更复杂一些,比以前一些单纯的愿望更复杂一些。过去,我希望这个人这样子,希望这个人这么好,希望这个人念念不忘……少年有少年的纯正,少年有少年的力量。人到中年了,是中年了吧。
端:你为了自己的创作,有特别自私的地方吗?
双:有。
端:能说吗?
双:比如说我有很多保密的(心情),跟谁也不能分享,即使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人,我也不能说。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我会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时间,可能要牺牲一些。还有时候,比如(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形象,我在小说里面写到的时候,会丑化他们,会尖锐一些,对有些人,我有不那么友善的表达。再就是,我有点六亲不认的感觉。
端:所以你跳出来做纯粹的观察者和虚构者,没办法去顾虑原型或本人的感觉?
双: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要把道德感稍微压一压。作家最大的道德,是创作一个好的东西。这个好东西的标准,每个人不太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
例如,你刻画某个人物,这个人物有原型,原型是一个烂人,你写这个人怎样怎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种伤害。但是你这的小说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有某种正义感的,无论是艺术上的正义,还是道理上的正义。因此,你需要牺牲一些道德,来完成自己的作品。所以作家的道德感比较复杂,不能用简单的好坏去评价。
端:有这样的例子吗?比如你小说中某一个原型,对你笔下的自己特别不满意?
双:比如说我写《聋哑时代》,我父母的形象基本上是属于虚构的,很多人就以为这就我父母的样子。但其实,我父亲从来不打我,我父亲也没有那么懦弱,他是有男人身上的那种东西的。但是我必须得戏剧化,虚构给我的暗示,这样写,小说的整体气氛才对。要是家庭特别幸福,那个气氛不对,所以你必须得做一点(虚构),但那个小说的情节又是真真假假的,有半自传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会连累他们。
端:你爸妈看过吗?
双:没问过。不敢问。
端:没交流过这个?
双:没有,从来没有。我从来没问过我妈,看过我的哪部小说。

我的视角是东北的,也是人类的
“厂区的中央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是厂房,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有的已经空空如也,玻璃全都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我扶起一个,发现里面有1996年的报纸。”——双雪涛《跷跷板》
端:你会不会有这种疑问:是不是只能写东北背景的小说,我才写的好?
双:东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限的素材,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台湾拿了我的第一个文学奖,我写的是一个有点玄幻的故事,《翅鬼》。我觉得我身上是有种东北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还有东北语言的节奏,但是不是一定要写东北的事。我觉得这个节奏和看待事情的方法,肯定更重要。
端:你所谓的东北人的独特视角是什么?
双: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有点保守主义。探讨历史、时代和人的关系时,东北人有时候会把问题看得宏大。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男性化的、臭男人的那种东西。
端:大男子主义?
双:挂主义就不好。臭男人的那种东西,有时候我自己的身上也会有。比如说一些男性化的,或者是看待事物的方法。
不能说我个人代表东北男性,我是说我自己受到的影响。因为在那里长了三十年。比如说打架,你上不上?你要是没上,一哥们让人家打了,你在后面躲了八米远。第二天上学,你这一天就不太好过了,别人都会对你有看法。因此你咬牙也得往上冲,这个东西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
我有好几次,高中、大学的时候,打架,是硬着头皮上的。真的不想上,真的想跑,但是一想,这人丢不起。
端:我听说你踢足球。在球场上,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
双:我没有什么样,我就是踢得还可以,踢球的年头比较多,还是前场,攻击的类型,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我踢球是特别爱急的,特别爱跟别人抢。足球队也是一个圈子,我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混,我就是拎包去踢,踢完我就走,我是这种性格的。在大学里我不是校队的主力,我是一个边缘的人。
端:你常说自己特别爱面子,说自己虚荣。
双:我比较好胜,球输了我挺难受,挺憋火。想赢怕输。
端:你觉得自己有输的时候吗,是不会让自己输对吗?
双:我有些领域特别不擅长,我去了一定输,那我就躲一躲。但人生有许多输的时候你自己并不知道。比如在银行工作那几年不是很顺,因为那份工作我确实干不明白,不乐意干,一看到领导,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是个特别不知道怎么跟上级聊天的人。但是有些人不用拍马屁都聊得特别好,既有尊敬,和领导的关系也拉近了,自己还没有跌份儿(东北话,指自降一格)。也有的人是比较生硬地拍马屁,或者是姿态比较低的,那都很正常。但我是哪边也不行,我一看领导嘴就发瓢儿(东北话,指嘴巴笨,口才不好),就不会说话,就特别紧张。尤其是和领导一起上电梯,我就傻了,我说啥,领导说什么我怎么回答,我觉得那几年是过得比较焦虑。
端:本质上那是对权力的厌恶吗?
双:不光是厌恶,我觉得有恐惧,有那种胆小的东西。人家官大,我就发虚。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巴结人家的话,自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老是怕说不好,硬怼(东北话,直接的意思)效果不好,不如沉默,不如不说。在那几年里,焦虑、惶恐,一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中渡过的。那几年真不算是赢家。
端:所以你刚刚说的,所谓东北视角,是一种勇敢吗?
双:我觉得不是吧。我无法概括东北视角,我只能说我的视角。我的视角是东北人的一种视角;但是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一种视角;我也是人类,人类的一种视角。我觉得不能特别强调和区别。
(实习记者郭芷甄、李若一对本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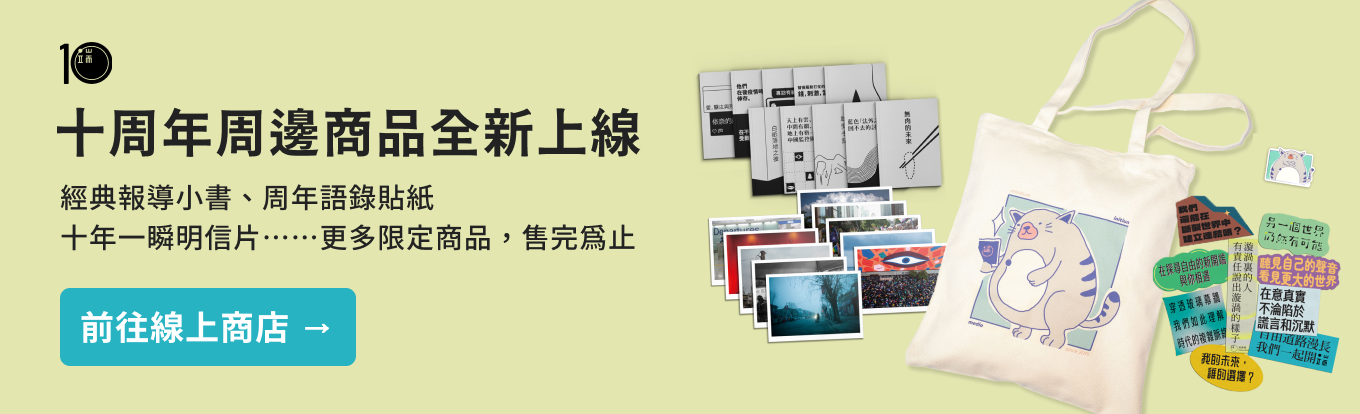
“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访谈有点短
內文有這麼一句:「而大家覺得寫作是文化人乾的事。」,理應是「而大家覺得寫作是文化人幹的事。」之誤,請注意簡繁互譯。
謝謝,已修正!
真正心里有话才能写得出来啊
从去年很多公众号的文章看来,东北好像一个死人。因为东北曾经辉煌过,很多人看似无法承受这种没落。
我三年前的冬天去黑龙江玩,在去漠河的火车上看到很多学生,他们都是父母带去哈尔滨考试的,希望高中能在省城的教学质量好的学校读,光这点,我都觉得有希望。这个部分,西北完全不能比,西北教育资源落后,很多父母还认命,不再为小孩寻找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
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北经济再不济也比西北强。西北现在的数据都是用资源堆出来的,等资源采没了, 我估计西北的未来更凄惨。